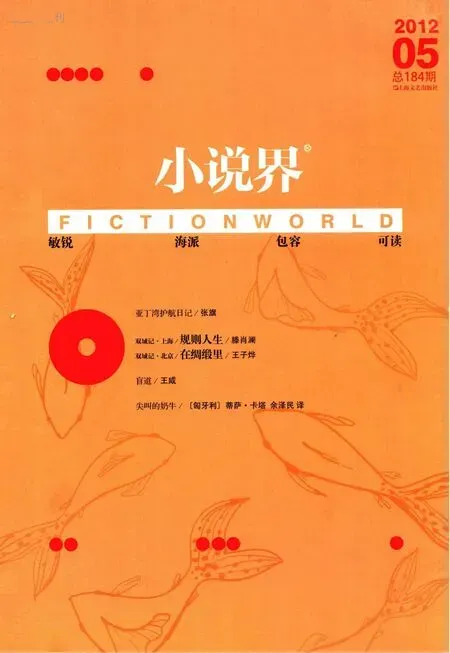无独有偶
李密密
一
“十块五毛。”米米拎起塑料购物袋的提手时说。
老笃没有伸手去接,他望着笑眯眯的米米,脑子在飞快地转动:要十块五毛钱吗?老笃经常在米米这儿买豆腐,一块豆腐要多少钱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但是他不好意思开口问,开口问了,好像他老笃就不是老笃了。老笃原本不是这个名字,只因为豆腐买得多了,自己的真实姓名都被米米隐去,赚来“老笃”这么一个美称。多少年前,老笃第一次上菜市场买菜,不经意之间就认识了米米——米米的吆喝声穿过接踵摩肩的人群,像喊山风的唿哨,掠过树梢撞向山崖,然后乘间抵隙地向老笃回旋而来。
“来啦,来啦,快来买真正的上青游浆豆腐啦!”
老笃侧着身子穿插于人群之间,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米米的摊位跟前:“米米,拿四块金包银。”
“咦,你是哪个地方人?”
“晓得喊你米米,你说我是哪里人。”老笃用久违的闽西北方言对她说。
“哦,你是哪一个旮旯的,我可是真正的上青墟上人。”
老笃不好意思起来,他当年插队落户的山村离上青公社所在地有十里山路之遥,对米米来说,他当初是个乡下人。
“乡下,大坪的。”
“大坪我是有亲戚的哦,村长是我的外甥你认识啵,以后有事可以尽管找他。”
“呵呵,我离开大坪的时候,你外甥应该还没出生呢。”
“哦,你是知识青年。当年你怎么会到大坪当知识青年,可能是听人说‘大坪大坪,又大又平才去的吧?呵呵,上当了吧,我们上青坊才又大又平呢。”
“那个时候我们是革命的知识青年,‘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怎么会挑三拣四。再说,谁到哪个生产队落户都是公社安排好的。”
“不管罗个说,你就是我们的老笃,以后要经常来买我的豆腐哦。”
于是,老笃与米米就相识了。在闽西北上青乡,“老笃”是“好朋友”的意思,“米米”是“伯母”的意思。“老笃”叫起来顺口耐听,对于老笃来说,还能勾起他对青春往事热血沸腾的回忆。老笃后来与当年的知青朋友聚会时,谈起这段偶遇,众人都羡慕得不得了,说我们要找回当年知青的感觉,都要跑回插队的村子里去,你好不好在福州的家旁边就找着了一个当年的小芳姑娘。
“错!她是米米。再说了,把人家农村里的女孩儿都称为‘小芳,那是群落歧视。”
其实米米年龄并不太大,老笃觉得她甚至小于自己,只是已经这样叫开了口,就这么一直叫下去也无妨。
过去老笃到米米这儿买豆腐,一般都是买四块,四块豆腐足够他吃两三天了。今天不同往常,他买了六块,六块豆腐就要十块五毛钱?老笃心里犯嘀咕。
“老笃呀,不好意思哦,豆子涨价好几次了,我这个豆腐,一直到现在,一斤才提了一块钱。”米米看老笃在那儿犹豫不决,赶紧解释。
“豆子怎么会涨价呢,这几年黄豆大量进口,我看降价还差不多。”
“唉,老笃呀,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呐,他们降价是应该的,他们的豆子,我看就是一个转基因,愿意吃的人吃去。我的这个豆腐可是用真正的上青乡田埂豆做的呐,现在乡里种田埂豆的非常少了,豆子供不应求,你说要不要涨价。”
老笃相信米米说的话,上青乡人不打诳语。只不过从米米的口里说出“转基因”这个新名词,倒是让老笃大开眼界。老笃可能是老观念,像转基因什么的,在崔永元、方舟子的口里说说,甚至为了食或不食争个你死我活,老笃都可以理解,但是,一个山乡老妪把它挂在口上,这说明了什么?看来只有一种解释能够让人信服,那就是中国社会在突飞猛进地发展,高科技已经融入寻常百姓家。米米肯定听人说过转基因的优劣之处,不然她不会说,他们降价是应该的。
米米说,上青游浆豆腐售价就应该高,除了原料原因外,制作工艺还比较复杂且全手工,豆壳不能用,磨浆用石磨,浆水(卤水)在豆汁里慢慢地“游”,何时游出豆花来不再游了,全凭师傅的经验。早年,还有一项关键的技术,烧的薪柴必须是杉木,干燥的杉木火旺、没有炭灰,豆浆烧开后,时辰一到,师傅一声令下,在灶口填柴的伙计必须迅速撤火,并把灶灰扒干净,因为师傅游浆是在大铁锅里直接游的,不需舀到大木桶里,火炭不迅速撤掉,豆浆就会烧出煳味。
所以说,上青的游浆豆腐成为一个可以让米米吆喝的品牌,就必须把好几道关。如豆壳问题,一般做豆腐的师傅豆壳是不去除的,黄豆直接浸泡磨浆,但是真正的上青游浆豆腐必须去除豆壳,否则除了有豆青味,磨浆时还会发泡,做出来的豆腐里面气孔万千,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青游浆豆腐了。米米做的上青游浆豆腐凝润如羊脂,白嫩如软玉,横切竖切针眼大的气孔都不见一个。出锅的豆浆压榨一两个时辰之后,米米已经在铁锅里倒入足量的菜籽油,大火熊熊、沸油轻漾,米米把切成大半个巴掌大的四方豆腐依次顺着锅沿滑入油锅,油锅立时沸腾起来,屋里屋外荡漾着菜籽油炸上青游浆豆腐特有的芳香。老笃买的就是这种豆腐,俗称金包银。
“只要是真正的上青游浆豆腐,涨点价没关系。”
“你就一百个放心好了,骗天骗地,我也不敢骗你这个老笃子。哎,你今天做什么多买豆腐了?”
因为今天儿子要从上海回来探亲。不但儿子要回来探望他,还会带他的女朋友回来。前两天儿子在电话里说,我们已经领证了。老笃说,领证了还是女朋友吗?你怎么事先都不打个招呼。儿子在那头语焉不详地说,女朋友干吗就不能领证,我是想先告诉您的,只是时间太紧来不及。
儿子找女朋友、领证结婚,要不要事先告知,老笃倒是无所谓。儿子今年已经三十几岁了,同济大学博士毕业后在上海工作,每次回福州探望老笃,都是孤身一人,老笃问了几次,都被儿子拿话岔开,问得多了,儿子就面露不悦,老笃只能作罢。看来儿子说的话没有错,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现在不是就解决了?
今天老笃不但要买上青游浆豆腐,还要买黄鳅,还要买野猪蹄髈,还要买水鸭母,还要买葛块(魔芋淀粉制品),在市场拐弯头那儿,有一家专卖农家土猪肉的,今天他也要去光顾一下。以上这些食材经传统烹制,最能代表闽西北上青坊乡土菜的特色。老笃插队当知青五年,上青坊的菜肴烧煮习惯(只能称习惯,谈不上技术)学了不少,如红焖回锅肉葛块、茶籽油爆炒水鸭母等等。只不过自己亲手烧煮是五十五岁以后的事,之前都是儿子的妈妈操持。儿子的妈妈与老笃是同一生产队的插队知青,两人在村子里就开始谈恋爱,三十余年时间里,他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所有的饮食起居都是儿子的妈妈打理。儿子咿呀学语的时候,先是会叫“爸爸”,然后叫“妈妈”,当时老笃羞愧难当,在养儿育女方面,母亲付出的辛劳最多,怎么儿子会先叫爸爸?后来他想明白了,婴儿咿呀之声是无意识的,“爸爸”只不过最容易发音而已,从伦理上看,这种现象应该是父系社会的产物,如果我们活在母系社会,妈妈就是“爸爸”了。
老笃出于对儿子妈妈的敬重,就跟着儿子叫她“妈妈”。妈妈烧出的菜特别好吃,无论炒、爆、熘、炸、烧、焖、炖,都带有浓郁的上青坊乡土菜气息,儿子特别爱吃。妈妈撒手人寰,对老笃和儿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特别是老笃,就差一点点缓不过气来随之而去。老笃时常在想,那时候,儿子在读博,有大作为已初见端倪,他们的工资加上额外收入,除了日常生活和供儿子读书,每月都有节余,在他们的生活向富足大踏步迈进的当儿,妈妈怎么就舍得离开他们?是老笃让她生厌,还是她要让老笃换个活法?那一两年,老笃强迫自己相信不是妈妈厌倦了生活,而是生活抛弃了她。因为妈妈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让老笃俯下身子,在他的耳边断断续续地说:“不要为难自己,找一个比我更好的……”
在妈妈逝去的好长一段日子里,每当深更半夜,老笃数着电子时钟发出的滴滴答答孤枕难眠。过去,老笃都是在电子钟的滴答和妈妈轻微的呼噜中安然睡去,电子钟与妈妈的鼾声配合默契、毫厘不差,四声滴答一声呼噜,周而复始如潺潺流水。妈妈以前是不打呼噜的,现在开始打呼噜是她要将过往的辛劳释放出来,还是在帮助老笃将青春年少的记忆重拾?青春永远是美好的,如果你淡忘了青春,那就等同你没有真正活在当下。妈妈的鼾声将老笃带到了插队时那个静谧的小山村,知青点建在村子最外围的溪涧旁,绕村而过的溪涧给生活带来希望与动力,每当夜晚,零零落落顺溪涧而建的水碓房次递传来“咿呀—砰!”的声响,那是木轴磨擦与舂石对糙米的沉闷撞击。舂米的声响从这边延到那边,一声接着一声,井然有序。当秩序被打乱之时,一定是发涧水了,这时只听到村子里的大狗小狗吠成一片,村道的石阶上传来零乱的脚步声,那是社员们急匆匆地奔向各自的水碓房,他们支起水槽、收起糙米,待雨过天晴之后再行捣米之事。
现在没有了妈妈轻微的呼噜声,电子钟的滴答也显得呆板干燥,老笃抱紧肩膀强迫自己入睡,此时,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心跳基本与滴答同步,只不过你愈想认真听,它们就愈不同步,滴答往往落后于心跳,就像美洲豹追逐角马,速度迅猛者取胜,角马被掀翻在地的一瞬间翻起无奈的白眼,它在感叹生命如此渺小且不堪一击。老笃搞不清楚自己是美洲豹还是角马,只不过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凡事知天认命、顺其自然为好。什么叫默契,默契就是知是不知、不知是知。譬如生命,活好当下的每一天即知是不知;譬如儿子的婚事,还有自己与蔡阿姨的关系,即不知是知。老笃猛然想起,这些道理,其实早已在配合默契的妈妈的呼噜与电子钟的滴答中得到诠释。
老笃从菜市场回到家里,已经上午八点多钟了,他放下沉甸甸的菜篮子,热牛奶切面包,匆匆吃了早饭,之后大气不歇地开始拾掇精心挑选的一篮子食材。老笃推算儿子即便天亮就出发,从上海到福州八百多公里的高速路加上出城进城,少说也要十二个小时,天黑能到家就很不错了,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来打理这一堆食材。他对自己的下厨能力还是蛮有信心的,会吃猪肉的人不一定会阉猪,懂得品尝菜肴的人十有八九会烧菜,老笃属于后者,妈妈就相信这一点,她当年常常是在老笃一二三的指点之下完成待客烧菜任务的。
“食(去声)者动手,食食者动口。”这句话念在南方人老笃的口里,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老笃烧菜没问题,在他择菜当儿,脑子里一直打转转的事情是,要不要叫蔡阿姨过来一起吃晚饭。儿子叫蔡阿姨,老笃也跟着一起这样叫。老笃与蔡阿姨认识是经人介绍的。那一年,跟老笃一起晨练的女老张说要给老笃介绍一个对象,说了好几次,老笃不置可否。有一天晨练结束后,女老张约了老笃和蔡阿姨一起喝早茶,终于让他们俩坐在了一起。老笃见着蔡阿姨心里一跳,感觉好似在哪儿见过她。女老张介绍双方的时候,老笃才渐渐想起蔡阿姨是练国标舞的,他们的地盘就在练太极拳的边上,老笃有可能曾经在《探戈》铿锵的乐曲声中注视过蔡阿姨的婀娜多姿。
那天他们交谈甚欢,而后他们单独会面了好几次,老笃请喝茶,蔡阿姨请听音乐会,一来二往两人感觉甚好,直至百无禁忌。自从妈妈走后,老笃都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跟异性接触,原本以为早已死寂的心灵被蔡阿姨的不期造访唤醒,现在无论白天黑夜,用不着电子钟的配合,他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自己的怦怦心跳,在广场,在湖边,在月光树下,最后,在卧室里,他与蔡阿姨一起搏动的怦怦之声将电子钟的滴答淹没。
那年春节期间,儿子从上海回来,除夕之夜的团圆饭有六个人吃,老笃、蔡阿姨、儿子,还有蔡阿姨的女儿女婿与小外孙。这餐饭本来讲好是在蔡阿姨那儿吃的,蔡阿姨家住西湖边上,单位房,六十余平方米,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砖混结构,质量不是太好。房子不好地点金贵,这儿划片钱塘小学,福三中也在区域内,所以说,蔡阿姨住的房子,是家长们垂涎三尺的学区房。
蔡阿姨对老笃说,我们这边有四个人,你们才两个人,少数向多数靠拢,还是你们过来吧。老笃没意见。腊月二十八,儿子从上海回来,听说年夜饭到蔡阿姨那儿吃,他不同意了,儿子说,说是他们有四个人,其实只有蔡阿姨一个人,她女儿女婿还不是要从金山那边过去?老笃想想,儿子说得也没错,蔡阿姨女儿的房子买在仓山区的金山新区,从金山到两边距离都一样。于是老笃回头再与蔡阿姨商量,蔡阿姨体谅老笃,隔天就开始把前些天备好的年货往老笃那儿搬。那年的年夜饭大家吃得很开心,老笃和蔡阿姨苦心经营两三天的年夜饭两个小时结束,因为女儿说小外孙吵着要回去看春晚。在这两个小时里,两家人相敬如宾、和睦融洽。儿子敬蔡阿姨一杯,女儿女婿敬笃老伯一杯,小外孙也来凑热闹,一个晚上抓住饮料罐,挨个儿轮流敬了一遍又一遍。
春节放假七天就要结束时,老笃问儿子,你看蔡阿姨怎么样?儿子说,你看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没有意见。儿子见老笃面色黯然,赶紧又加了一句,我看蛮好的。
就在那年的春节,老笃猛然发现儿子的脾性不像他,也不像他妈妈。儿子回来后,也不与过去的同学联系,也不与老笃谈天,整天趴在电脑前说是有工作做。
“该休息时需休息。”老笃说。
“今天不拼命,明天无休息。”儿子头也不回地说。
孤傲、无节制、吝啬、以自我为中心,是当代高学历人群的基本特征——老笃是这样认为的。老笃转而想想:人活在世上,这样是一种活法,换一样照样是种活法,只要不妨碍别人,自己愿意怎么活就怎么活,活得舒心就好。
二
春节过后,老笃与蔡阿姨商量领取结婚证的事。
“真的就去领结婚证呀?”蔡阿姨脸上飞起一道红晕,略显羞涩地说。
“如果没心理准备,不急着领也可以。”老笃善解人意地说。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还没准备。我是觉得我们这么一大把岁数了,上结婚登记处让人家盯住瞧,很不好意思的呀。”蔡阿姨说。
“呵呵,谁敢说你年纪大了,我左看右看,总觉得你才十八姑娘一朵花呢。”老笃说话的时候,脑海里闪过蔡阿姨身着红色连衣裙的矫健身影,踏着铿锵的舞步,在男伴的引领下,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老笃与蔡阿姨极其低调地领了结婚证后,参加旅游团到新马泰玩了一趟。回来之后,他们各自的生活格局并没有打乱,两边都有房子,你在我这儿住住,我到你那儿住住,好到老笃感觉天天在度蜜月。
时间一晃过去了一年。有一天,老笃没有看到蔡阿姨来晨练,打她的手机,语音回复关机,想要过去看看,上午有一个改稿会,抽不开身,一直挨到中午再打手机,还是关机。老笃心想可能有什么事了,在单位食堂随便吃了一点快餐,就往蔡阿姨家里去。蔡阿姨家的房门紧闭,开门进去也没个人影,老笃此时慌了神,掏出手机再打,还是不通。他灵机一动,查了通讯录,找到蔡阿姨女儿的电话,急匆匆地打了过去,谢天谢地,电话总算打通了,过了好久,对方接了电话。
“你妈妈呢,她在哪儿?”老笃迫不及待地问。
“我妈妈生病了,在我这儿休养呢。”蔡阿姨女儿说。
“生病了怎么也不跟我讲一声,你——你……”老笃忍了又忍,把下面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我妈妈我们可以照顾,谢谢您打电话过来。”蔡阿姨女儿有挂机的意图。
“我过去看看她,你们住在哪栋楼?”老笃赶紧把话说完。
“不用了,等我妈妈病好了,我会告诉您的。”蔡阿姨女儿不由分说地挂机了。
老笃落寞地下楼,在宿舍区院子里的大榕树下,围了好些住户在议论纷纷,老笃走上前去想听听,这些人见他是外人,都用警惕的目光瞅着他,只有一个貌似愣头青的小伙子故意恨恨地大声说:“什么狗屁政策,还不是要把人掐死一个算一个……”
老笃沮丧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默默地在想,此时千万不要碰上满街追着人问“幸福不幸福”的电视台记者,如果碰上了,自己真不知该怎么回答。除却今天自己心情不好的原因,平心而言,关于幸福感,人与人是有差异的。在物质方面,有的人温饱有加就感到万分幸福;有的人贪了十亿八亿还觉得差“先进”一大截,自己十分不幸福。在思想方面,有的人救上一个落水者感到幸福;有的人站在岸上看别人落水并嘲笑,只有这样他才感到幸福。所以说,特定的人有特定的幸福观,所有人能共享一个“幸福”吗?
老笃寝食不安地想着蔡阿姨的病,几近抓狂。想想真是好笑,合法夫妻竟然被小辈逼迫成咫尺天涯,今天的蔡阿姨好像遭劫匪绑架了,而老笃却没地方报警,做人做到这个份儿上,真是悲哀。老笃像热锅上的蚂蚁煎熬了两天之后,想想不能再等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别说蔡阿姨得了什么病,自己的半条老命也要耗尽。老笃想起来了,蔡阿姨女婿的工作单位是省建筑设计院,就在东街口附近,于是他寻上门去,三问两问总算找到了女婿的办公室。女婿请老笃在长沙发上坐定后,转身要去给他泡茶,老笃一把捉住他的手腕,生怕他借故人间蒸发,急匆匆地问:“蔡阿姨生什么病了,要紧不要紧呐?”女婿望了一眼办公室里埋头做事的同事,想要说什么,但欲言又止,只是一个劲地宽慰老笃说:“没什么大病,前两天有一点头晕,现在好多了,我回去给阿珍说说,让她妈妈去找你。”老笃知道蔡阿姨女婿是一个老实人,他既然如此说话,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也不难为他了,说声你忙,我先走了。女婿将他送到办公室门口即止步,说,笃伯伯对不起,手头上在赶一个设计,不送您了,请慢走。
那天晚饭过后不久,蔡阿姨来了。老笃听到门外掏钥匙开房门的声音,心里一阵狂喜,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玄关跟前的时候,蔡阿姨已经进门。她在鞋柜前弯腰换拖鞋的时候,老笃趋身上前双臂合拢,将她的腰身紧紧抱住,此时两人都感觉到对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过了好一会儿,蔡阿姨才转过身来,老笃借着过道里射灯灯光,看见蔡阿姨面容憔悴且目光躲闪,他轻轻吻上蔡阿姨嘴唇的时候,只觉那儿粗糙异常,当他想更进一步的时候,蔡阿姨已经把头扭到一边去了。老笃轻叹一声放开手回身到客厅,蔡阿姨紧随其后,挨着他在长沙发上坐下,把他的一只手握在自己的掌心里轻轻摩挲。此时的老笃心如止水,就像当年他初涉太极拳时,与一个网名为“无极道长”的博友探讨太极终极意义时的心情。
老笃:道长您好,据说太极的“推手”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学会了一辈子受用。这个推手如果称为“以柔克刚”也可以是吧?请您给说说当今世上以柔克刚的范例(不仅仅是肢体操练方面的)。
无极道长:滴水穿石,应该够了吧?
老笃:滴水穿石是自然现象,学生想要请教的是社会现象。
无极道长:本道长以自然万物喻社会万象。水至柔而能穿石,钢至硬遇石卷刃,遇事以暴制暴,如刀砍石头;遇事以柔克刚,如刀砍水流。太极的真谛就在其中。
老笃:刀砍石头,石头受伤,但刀受的伤害也基本同等;刀砍水流,水流虽然表面上很快恢复平静,其实它的伤害已经深深埋藏在心底里了,我认为“抽刀断水水更流”就是水愤怒的表现。埋在心底里的伤害总要找时机迸发,而石头与刀同时都受到伤害,算是不打不相识,倒还更容易尽释前嫌。所以,水滴石穿不能诠释推手的深远意义。
无极道长:也许刚才那个回答你不好理解。我再打一个比方,小人就好比是一个躲在暗处手持利刃、时刻准备出来伤害你的歹徒。那么您是同样手持利刃准备和他对攻,还是将自己变化成浩瀚之水,让小人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