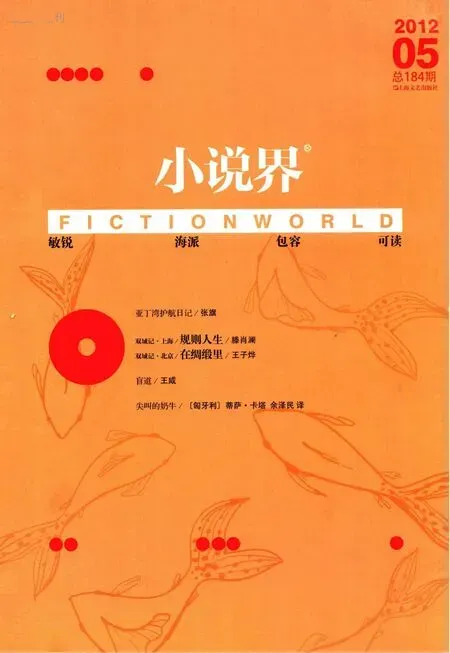白色的世界
文/草白
白色的世界
文/草白
草白
1981年8月生,现居浙江嘉兴。作品散见《北京文学》《山花》《天涯》《江南》等刊,曾获第21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储吉旺文学奖优秀作品奖等。出版短篇小说集《我是格格巫》。
此刻,我搭乘的列车停在一个湿漉的站台上。冷冽的寒腥气,在步出车门的刹那便向我扑来,混合着难闻的尿骚味,陌生人嘴里呼出的隔夜气息,一股脑儿推着我向前。双腿无意识地挪移着,火车上冻了一夜的身体的感觉开始复苏。我感到冷,从脚趾开始,钻心地疼。隆冬的阴森气息让我对身体的亲密关系更产生了渴望,这是过去几个月里,我所朝思暮想的。当天气一天天冷下来,更确定了你的远离,绝望感便像雪地上觅食的群鸟,一览无余。
所有的火车站都如此相似,穿梭其间的男女们,形容疲惫,面无表情。三个月前,我们在此碰面。那是秋的某日。大街小巷,桂花开了。飘忽而强烈的气味。在这个城市西南角某旅店的床上,我们闻了一夜,说了一夜的话。
我在出站口寻了位子坐下。深冬的水泥墩子那么冷,一股冷冽的寒气正由臀尖持续渗入体内,抵达关节各处。寒冷加速了往事向我奔来的速度。那天,你远远地看到我,一路小跑着,一下子抓着我的手。你的手指紧紧地攥着我的,那么有力,让我感到微微的疼。我热烈地回应你的握,生怕你抽身而走。
“让我的手,给你捂捂热吧。”你的声音再次在我耳边响起,一种奇异的欲罢不能的表情在我脸上浮现。
广场上,是粗鄙的景观雕塑,冰冷的水泥椅子,随处可见的垃圾,一个乞丐过来,在我面前停下,几枚硬币躺在破瓷盆里,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他走到我面前,可怜巴巴地望着我,那眼神让我极不舒服。
“你看这里多糟啊,可我们在一起。”那天,就在这个广场上,我们携手走动,说话,大笑,旁若无人。
现在,这里只坐着我。孤零零的我。同样孤零零的手落在水泥墩上,它们的温度在短暂的传导之后已经趋于一致,同样的冰冷,无力。
乞丐被打发走了。对面早餐店的门敞开着,一个戴围裙的女人在门口叫卖茶叶蛋,腾腾热气裹着那张粗糙通红的脸,她始终微笑着,脸在雾气里进进出出,神情动作配合默契,给人一种娴熟之感。
那天,我们就在那家店里吃了米粥、粽子和茶叶蛋。
我几乎吃不下什么,看着你吃。你进食的脸,再次在我脑海里浮现。我此刻的绝望在于永远无法准确拼凑那张充满爱情气息的脸,回忆让它变得模糊,并且永远模糊下去。
水泥墩子的寒气一点点渗入体内,深入骨髓的冷是我此刻唯一真实的感受。刚才,一个脸颊红红的中年女人问我,小姐,住宿吗?跟我来吧。那幽暗语调里所携带的模糊乡音让我一颤,差点跟着走了。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深切的渴望,渴望被带往异地。此刻,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了。
三个月前住过的旅店已经歇业。在网上找到附近的一家,毗邻新落成的广场。我们曾在黄昏的广场上漫步,簇新的水泥地显得一派荒凉。只有我们的快乐是真实的,还有广场上空盘旋的鸽子,咕咕咕地叫个不停。
广场前面有一条河,黑暗里,几乎察觉不到它的流动。
“不知道对面是什么?”你忽然停下脚步,更紧地抓着我的手。
“你说什么呢?”我挣脱你的手,满脸疑惑地望着你。
“哦,河的对面是什么?”你仍然搂着我,一脸若有所思的表情。良久,你不再开口。我们各自迈开步子,继续朝黑暗中的某处走去。我几乎忘了在那样快乐的时刻,你曾有过的茫然。哦,即使在深度的拥抱中,你仍是孤独的。每当想起这些,我就很想把自己裹进一条暗无天日的被子里,迅速老去。
我喝了一点豆浆,那种甜而温暖的液体慢慢汇入我体内,让我获得一点点安全感。离开火车站,我向着旅店的方向走去。我没有选择更加快捷的抵达方式,只想在清晨的寒气中多走一会儿,把一路的感受呈送给你,如果你也能体会到的话。
或许,你正一路陪我同行。你曾经说过,无论我在哪儿,你都会在我身边。
路边鲜花店半敞的木门,有种奇异的质朴感。水润、含苞的红白玫瑰齐整地插在铁皮水桶里。所有花卉中我最喜欢的是玫瑰,它们最接近我理想中花的模样,饱满,羞涩。卖花的是年轻女孩,脸若满月,长发披肩,一袭粉色布裙,身上透着淡淡的幽香。她娴熟地包着一束香水百合,我看到她的手——十指修长、白嫩、洁净——无法想象这样的手有一天会变得粗糙,青筋暴突,长出老人斑来,甚至无法正常屈伸,但这却是它必然的命运归宿。
可你的手依然那么宽厚、绵软,带着身体内部自然发散出的热力,在过去三个月里,一直紧紧抓着我。
我不确定是否要从这双依然姣好的手中接过一束花,随便什么花,酒店房间里可能没有花瓶,一个赶路人手捧花束会不会不合时宜,当这么想着,我仍痴痴地凝视着那双手——每个人都曾有过一双年轻温暖的手。
我还是买下了白玫瑰,全是含苞待放的模样,一个紧密闭合的世界。如今,你的世界也向我关闭。
你好似坐上一趟远行的列车,没有终点,一直开。
一直习惯在火车站观察人群,他们脸上呈现出某种茫然无依的表情,让我感同身受。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渴望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离开熟悉的生活,离开家,坐到亮着灯的车厢里去,让车轮奔跑着将我带向远方。
小时候,门前河对面有一条铁轨。远远近近的火车都要经过那里。黄昏的时候,追着火车跑,风灌进喉咙口,眼睛进了沙粒,闭着眼睛跑,跑到筋疲力尽,在荒草丛中席地而坐。
“这世界那么好。你那么好。”你在我耳边说,呼出的气息依然灼热。
此刻,我想哭,我的眼泪还没有流尽,还有许许多多要流给你。
刚才,来的路上,我看见一个女人在哭。她迎面而来,脸上挂着泪。她毫无顾忌地哭,无声地落泪。她从树的阴影下走过,衣衫被斜生的树枝挂住了。她不再年轻,双眼显得疲惫。她身上有一股沉重的气息,让人怜悯的气息。
当她哭的时候,多么孤独。
现在,我就是那个孤独的人。这个月河客栈的房间如此阴冷,冬的寒气从窗外咝咝渗透进来,白色床单就像覆了寒霜一般,是冷冰冰的惨白,屋子里别的一切似乎也被冷水浸透,我端坐着直打哆嗦,体内积聚的热气不足以抵挡。
我忽然想起你说的,孤独的时候,应当去自然中走走。我的心脏再次剧烈地跳动起来,似乎要跳出胸腔,只为了让你听见。
可我已经没有行走的力气,我只想睡觉。对睡眠的渴望超过了所有。
半小时后,我来到街头,冷意依然强烈,甚至更冷了。云层压得很低,风来了。那些从秋天深处刮来的风,刮到今天,冷意已深入骨髓。我想起一个地方。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地方是为孤独的灵魂准备的。
三个月前,我们去过那里,宛如闯进另一时空。铁路边废弃的园子里,草木葱郁,湖泊安静,却无人影。我们的慌乱很快就被巨大的欢喜淹没。树叶在头顶发出哗啦声,寂静均匀分布在两次火车经过的间隙。树与树之间的草特别绿,一根根,好像可以数清楚,阳光照到的地方呈黄绿色。那一点点附加的黄使得草地呈现油画般的斑驳感。人们绝不会相信秋天里会有这样绿的草。
我们坐着,随意说着话,凝眸对视着,亲吻着,火车来了,又走了,时间在流逝。我们什么也不想。或许,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事,追着火车跑的事。你说过什么,我却忘了。奇异的静默环伺在我们左右。好像我们可以无止尽地坐下去,坐到世界末日,时间的尽头。后来,西边的天忽然暗下来。半边明亮半边暗淡的园子给你不安感。
“我们走吧。”你拉着我的手往外面走。在我们身后,几片阔大的黑褐色叶片快速飘离枝头。
一直一直走,直到看见人群,我们才停下脚步。西边,日正落下,橙红、寂静,轰然有声。回首的刹那,分明有东西再次坠下。
“听见什么了吗?”你的嗓音显得喑哑。
我茫然地摇头。你也不说话,深深地望着我。你用那种眼神看我的时候,我变得迟钝。
那一刻,桂花的香味像极了一个清冽的梦,淡淡的,却又无处不在。我们身披香气,回到旅店里。
而现在,我将沿着那个秋日所走的路,去往废园。我发现自己迷路了。而天更冷,风刮得更猛烈了,好像要把所有事物刮离既定的轨道,要将我刮回你的怀抱。我已经走到一条长街最为荒凉的部分,那里是尚未竣工的楼盘,漫无边际的田地和荒草丛。
风搜集脚下的尘沙,兜头兜脸地向我扑来。
送葬的队伍刚刚过去。一个披麻戴孝的男人沿途抛撒纸钱。一个更年轻的男子抱着牌位走在队伍最前面,后头跟着一具黑漆棺材,上面停着纯白的纸鹤。一身脏污的白衣也无法掩饰年轻男子俊朗的体貌,极度克制的悲戚反而成全了他的优雅。一个小女孩摘下白帽子,拿在手里把玩,很快就被边上一位悲伤的女人制止。风吹起了白幡,把哭声吹走了。他们和锣鼓声一起消失。
理智告诉我不能往他们消失的方向走,必须有另一条道路,一条通向废园的道路,或许也通向你。我必须找到那里,这是眼下我唯一愿意抵达的地方。特别是当送葬的队伍刚刚过去,那个怀抱牌位的年轻男子,他脸上的悲戚宛如你的,是你某部分精神在尘世的延续。
好像是你在指引我,废园之路忽然变得清晰。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那条路。进去的时候,我发现有雪花正在落下。下雪是忽然之间发生的事。起先是一小朵、一小朵零碎地飘落着,试探性地下着,后来,越下越大,我的发上、肩上都覆上了白乎乎的东西。我的眼睛里也落进了雪,有一点点冷。在茫茫雪意中,我走向房屋、树木和湖水。我曾经历过无数个时空,可此刻只有这一个。好似所有的时空更迭只为了切换到这一个。我走向废园,透过树木的枝杈,它的身影逐渐显现。随着我的走近,它在迎向我,逐渐扩大它的面积,它的整体在某一刻豁然开朗。
我继续往前走,进入废园深处。雪飘扬着落下,这世上所有的雪都落到这里来了。落雪是有声响的,轻微的窸窣声,似无却有。我在湖边弃石前站定,听着那声音发愣。良久,身后似有脚步声,正欲回头,湖边巨石后转出一个熟悉的身影来。
我怕不是你,更怕惊扰了你,可我知道那就是你。我默默观望着你,真不敢相信,几月未见,我们的关系已退回相识之初。你眼里含着羞怯和拘谨,而我只默默地打量你,不敢惊动你,只待你的眼神一改变,我就可以顺势投进你的怀里,可这一刻始终没有到来——我们保持着互有好感的陌生人初见时所适宜保持的距离。你微笑着,似乎饱含着深意。我也报之以浅笑,脸上肌肉酸痛得厉害。我们就这样并肩走着,有一会儿,我的肩头触到了你的,你的反应让我马上躲开了。你满足于我们之间所保持的距离。纷扬的雪花正在占领我们身体之间的空隙,占领这个园子。一个白色的世界即将来临。
“你身上带着恋爱的气息。”那次和你见面后,朋友们都这么说。
我微笑着听她们说完,心里非常快乐。是的,我恋爱了,我爱上了你,这种感觉无与伦比,从未有过的澄澈与安宁,阳光一样照耀着我,将我裹藏。
那是秋天,大地之上,到处都是丰收的果园。我在散步的时候经常想,真应该下一场雪,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所有的地方都应该下雪。只有雪,才能把这个世界不同时空里的人串联;只有雪,才能把没有污染的世界重新还给我们。
可我没想到的是,一个下雪的世界会那么冷。雪带来一切的同时,也带来了寒冷,它们拥抱着我,好像要将我吞噬,成为白色世界中的一部分。
我痴痴地望着你,手脚哆嗦着,眼睛在说冷,我试图用眼神与你交谈,可你轻轻地避开了——你表情中的茫然与天真刺痛了我。你竟然什么都不知道。你走在雪地里,就像走在一个稀松平常的地方,你对雪的无谓感刺痛了我。你肯定忘记了在南方,雪是多么珍贵的东西,是我们期盼已久的精灵之物。
这么想的时候,雪下得更大了。一会儿工夫,废园已经在雪的怀抱里了,草木一半的身子掩藏在雪里,还有更多更密集的雪持续不断地抵达。
“你看,下雪了,多么美——”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几乎要倒在你怀里。
你终于笑了,轻声说:“是啊,是啊,下雪了啊,真好呢。”
我期待你再说点什么,可你整个表情就像在梦游,你的身体在雪地里走,就像雪花一样无目的地飘移着,挪动着。你忽然低了头,好像在确定自己此刻的所在。你看见一片模糊的雪花飘落在手背上,雪马上化为一滴水。当你试图擦拭水滴留在皮肤上的寒湿感,它已经提前消失了。
亲爱的,你皱了皱眉头,是感到疼了吗?那一场意外留下的疼痛还在你身体里持久地释放吗?可你马上恢复了安宁,对一切事物安之若素的神情重新占领了你。你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只把所有的不安、疼痛都逼回体内,不给人留下丝毫窥探的可能。
你甚至没有用那种眼神再望我一眼。
这会儿,天地寂静,除了雪轻微的飘落声,我们脚步在雪地上的踩踏声,再没有别的声音。当然,如果我们静心倾听,总还能听见一些别的什么,比如积雪压折草木的声响,树叶上的雪因重力作用忽然坠落的声音,雪飘在湖面上发出轻快的融化声——可这些,我都没有听到。我走得很慢,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部力气。而你,几乎是轻盈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们靠近。你越走越快。你在用行动告诉我,我们终将抵达的地方是一片茫茫的雪野。所有的爱和语言终将成为融化的积雪。
你的衣袖忽然划过我的脸庞,我似乎闻到你身体里的气息,那种阳光的清香,浮世里的欢乐。我抓不住它,它们倏忽而过。一片雪花落进我的眼里,清冷的气息瞬间在身体里蔓延开来。
小路尽头,一片白茫茫的竹林,积雪压弯竹枝,簌簌落下。转眼,毫无预兆地,你消失在竹林里。我想拉住你的衣袖,追问你何时再见。可你只挥了挥手,向着竹林深处缓步走去,不置一词。你微笑着的神情,就像之前每一次的凝眸对视。可这一次,我只眼睁睁地看着,身体宛如陷在沼泽地里,毫无伸手之力。
你离去之后,我独自一人在废园里走。永远也走不完的路,竹林之后是坡地,转眼,另一个湖泊映入眼帘,湖泊周遭一片白。雪越下越大,落在我身体发肤上的雪再也不能瞬时融化,它们在我身上堆积起来,把我包裹。好像全世界所有的雪都下到我身上来了。
我在雪地里走着,草木、山坡全埋在雪里了,肥厚的雪裹住了废园,枯草的脑袋探出在雪地上,树的身上,一半白,一半黑。
铺天盖地的雪……
我醒了。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一张憔悴苍白的脸。在梦里,我变成雪人。在离开废园向着城市走去的路上,我慢慢融化,彻底消失了。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你,我要融化自己,让自己彻底消失。
几天后,我仍想着梦中房间里的白玫瑰。它们或许已经枯萎,通体焦黄。那奇异的萎谢场景在我脑中久久地,萦绕不去。
窗外,街边梧桐树掉光了叶子,青灰色的树身裸露在风中,一辆清洁车从底下开过,那人身上鲜艳突兀的橙黄马甲给我莫名的无常感。过了许久,那种被抓挠着的感觉才渐渐平复下来。
我得去一趟裁缝店,早就该去的,电话已经打来三次。“快要过年了哦。”话筒里女师傅的声音温柔绵软,“如果真来不了,叫人送来也是可以的。”
“不要哦。还是我自己来取吧。”我下了决心,既然它是我与你最后的物质关联,那我必得亲自取它回来。
一件手工精作的呢料上衣,是我给你预留的惊喜。无数次想过你穿上它的样子。现在不必再想了。你在雪地里飞快走着的样子,让我心疼。一个在黑暗里行走过很久、目睹过许多人事的人,才会如此决然。走吧,你走吧。
这个时段不算拥挤,开车的女司机把油门踩得飞快,是在这个拥堵城市里好不容易等到的放纵吧。她不时将头扭向窗外,顺着她的视线,我看到路边花坛里灌木叶片上缀着未消的薄霜,在冬阳的映射下,闪着凛冽的光。
“小鬼头真不让人省心,半夜三更房间里还亮着灯,可乐藏在衣柜里,说过多少次了,垃圾食品不能多吃,要发胖的,根本不听你讲……”终于听明白了,她说的是上小学的儿子,考试成绩不好,放寒假了,天天喝可乐,玩游戏。
真不喜欢这时候有人在耳边嘀嘀咕咕,有明确内容的嘀咕,期待着别人回应的嘀咕,真让人难受。在等红灯的时候,她还在说着什么,当绿灯一亮,便快速踩了油门,车子飞出斑马线外,一百米内,已经换到三挡以上了。
她已经不说儿子了,忽然,嗓音霎时抬高了,“你看见了吗?刚才,有个人躺在地上,露出一只脚。”她大声叫嚷道。
“怎么会呢,还躺在地上……”我扭头望向窗外,什么也没有啊,只有后退的行道树和店铺,以及缩着脖子、三两行走的路人。深冬街头特有的景象,只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肯定死了,电瓶车翻倒在路边,好可怕哟。”她边说边捶打着方向盘。
“是被汽车撞的吗?”肯定是的,除了这个,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
“没有汽车,什么都没有,就孤零零一个人,身上盖着件衣服。”女司机越说越兴奋,“可一个人好好地躺在地上干什么呢,肯定,死了的……”说到死字,她似乎停顿了一下,马上又絮叨上了,带着莫名的无法抑制的亢奋。
“真的没有别人吗?”我想着事情应该不会这样,那个将衣服盖在他身上的人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留下来等着。好像躺在冰冷路面上的人是我。孤零零的我。不,那一刻,我想到的是你。一个月前,你也卧在相似的路上。脊背后面瞬时一片冰凉。
“好像没有,看不清,太快了,一晃过去了。”她茫然地摇头。或许,她并没有摇头,却再次把油门踩得飞快,好像是为了躲避此刻正疯狂追逐她的东西。
我紧紧抓着椅背,速度加剧我的恍惚感,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并非亲见的一幕却清晰映入我的脑海,我甚至看到衣服下露出的脚踝,白色棉袜子,其中一只裸露着。
直到我在裁缝铺门口下车,她都没有再说什么。我将门碰上的刹那,回望了她一眼,两秒钟后,车子绝尘而去。
电话里那个温婉的女人递给我一包衣服,鼓鼓囊囊的一包,用剩余的布料包裹着,“你不打开看一下吗?”她疑惑地望着我,小心翼翼的眼神,忽然又低了头。暖烘烘的各式布料的气息将我包裹。屋子有些昏暗,适度昏暗的地方,让我觉得温暖。布匹躺在架上,蒙昧生尘。女裁缝温良和顺,眼神却欲说还休。可我能说什么呢?
我将衣服抱在怀里,付了钱,推门出去。
冬天的街头,天色过早暗下来,人群在寒冷的空气里簇拥着,如鱼在冰层底下艰难地游弋,他们聚集又分开,回到各自的道上。井然有序。我怀抱衣服,在街上走着。一辆辆车子从我身边经过,却不停靠一下。它们载着客人,奔跑在回家的路上。街上越来越冷。
我走了很久,穿过好几条街,经过许多亮着灯光的店铺门口,看到许多热气腾腾的食物摊,没有停留。如果没有车子载我,我打算就此走回家。那包衣物在我手里变得沉甸。有一刻,我想起那个手捧牌位的年轻男子。他的悲伤和我的叠加在一起,在那个遥远的梦境里汇合。
好似有身影跟着我,一种恍惚感也如影相随。我不回头,一直往前走。手机店门前,一大片亮光叠置在微弱的夜光上,呈现舞台中心的效果。
蓝色出租车停在我身边,刚刚下了客,车窗摇下的刹那,我再次看到那张熟悉的脸。“要车吗?”他的声音充满犹疑,且带着几分惶惑。
我上了车,将衣物放在旁边的空位上,双手交握放在膝上。车子启动,匀速、平稳,又有轻微的晃动,眩晕,如水上航行。
闭上眼睛,任身体在黑暗里飞。
十分钟后,我回到家。我走上楼梯,走进屋里,开灯。站在玄关前,脱鞋,换鞋。刚才,我将那包衣物弃置在座椅上。没来得及望它最后一眼,路边痴愣的刹那,车子启动,冲向绿灯闪烁的十字路口的那一头。他什么也不知道,仍然开着车去找他的生意。直到下一位乘客,坐在它边上,发出疑惑或惊叹声,他才知道有一样东西落在车上了。
我喝茶。站到窗前张望。合上一本看了一半的书。打开电视。我想到一个人,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这么多年,我一刻不停地,做各种各样的事,不让自己去想。
可没有用。那个与你酷似的男人,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与那件衣物之间可能存在的隐秘关系触动了我。我甚至想过回去找他。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打电话到出租车公司,渴望再次坐他的车,都没有结果。
我没有找到他。他代替我成了那件衣物临时或永久的主人。他带着它四处搬家,去和适合或不适合的女人约会,不断地陷入爱情,不停地从疯狂的热劲中缓和过来。与此同时,一种难言的羞愧感不时浮上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