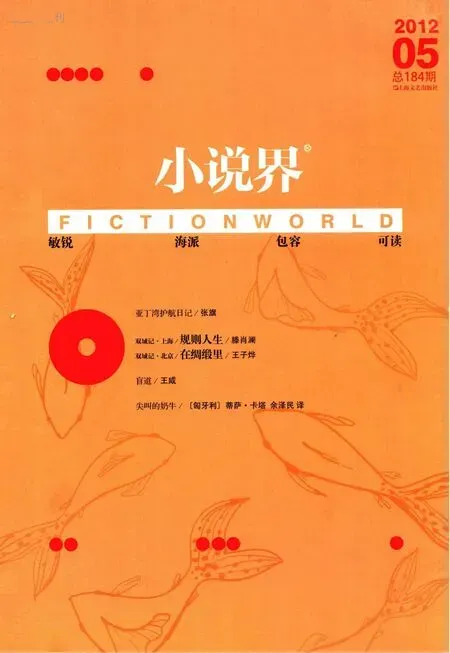降落
文/邱华栋
降落
文/邱华栋
邱华栋
1969年生于新疆,祖籍河南南阳。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曾任《青年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现任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十六岁开始发表小说,迄今出版有长篇小说十部,中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集、评论集数十部。
一
“飞机降落的时候,后轮落地的一刹那,会发出摩擦和撞击地面交织的声响,飞机后轮先着地,会迅速弹动并稳定下来,然后,前轮才与地面接触,整架飞机在轮子的支撑下保持平衡,安全降落到地面上,像扑向对手的雄鸡那样雄赳赳地在跑道上飞奔,然后,就停了下来,在一条斜的匝道上转弯,这样,主跑道就立即让给了那些即将降落或者马上要起飞的飞机。这架飞机开始平稳地驶向有廊桥的停机位,没有廊桥了,就会在引导车的引领下,前往露天停机坪。等到飞机完全停稳下来,地勤人员会迅速固定住飞机轮,然后,发动机停转,客舱里的灯光会全部亮起来,这个时候,空姐会提示大家,航段结束,大家准备好物品,要下飞机了。”
方强在给他的女友薛媛讲自己驾驶飞机的情况。薛媛比他小十岁,因此叫他小哥哥。薛媛是一个独生女,所以多少有些黏人。方强是一位有八年驾龄的飞行员,作为机长,他驾驶飞机超过了6000小时,经验已经很丰富了。
“可老是有性急的旅客,飞机还没有停稳,他们就站起来取行李,很讨厌,”薛媛说,“他们为什么那么性急?这时是不是很不安全啊?”
“是啊,中国人就是这么着急,干啥都着急,上飞机要抢,下飞机也要抢,不知道他们到底急什么。实际上,这是很坏的习惯。因为,飞机在驶向廊桥或停机坪的时候,也是有一定危险的。我上次飞到巴黎戴高乐机场的时候,就听说有两架飞机发生了地面碰撞,结果,没有系紧安全带的旅客,在飞机里都飞了起来,撞到了飞机舱顶上,有人掉了门牙,有人破了相。因为飞机体量大,一旦互相发生碰撞,即使在地面上,都是非常危险的,力道之大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空姐,总是要制止那些飞机没有完全停稳就站起来取行李的人,要他们坐下来,赶紧系上安全带,这都是为他们好。”说到了这里,方强忽然揽住她的腰,说,“我们是不是要考虑结婚了?”
薛媛就愣住了,她对这个问题还真的没有最后的把握。她和方强已经同居五年了,无论身体、声音、气息,彼此都是那么的熟悉。但是,现在,薛媛无法确定的一点是,她是不是应该嫁给方强了。方强体魄健康,飞行员的伙食营养充分,精神状态也总是最抖擞的,只要穿上制服,他就是那么的英俊挺拔。她看着他,觉得他亲切、温柔,可就是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应该嫁给他了。
五年前,薛媛刚刚大学毕业,在一家公司做文员,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方强。那一次,是在一家商场里,薛媛买了一些东西,正要出门,忽然看见有一个橱窗里展示着很多飞机模型,各种各样的飞机模型都有,组成了整整一个大型机队。都是波音公司生产的民用航空飞机的模型,从老的波音707到最新的波音787型飞机都有,此外,还有一些概念型飞机模型,超音速飞机、公务机、双层宽体大飞机、大型货机、透明飞机、流线型空气动力飞机和降落伞型飞机等等。薛媛不经常坐飞机,她对这些模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驻足观瞧。
“美女你好!你对这些飞机模型有兴趣?我们可以送给你一个模型,现在是我们公司的宣传周活动。这些飞机,我都会开——当然,波音787型才交付给我们公司两架,还没有轮上我呢。”一个穿淡蓝色衬衣的小伙子出现在她身边。
“你是飞行员?”薛媛瞪大了眼睛。
“是的,我们航空公司在做推介活动。你有什么疑问,我可以为你解答。”这个小伙子非常热情,他英姿勃发,身上还有一种淡雅的松香型香水味儿,也许是阿玛尼,也许是范思哲。薛媛指了一下那些概念飞机模型:“啊,这些飞机,很奇怪啊,尤其是那个降落伞飞机,现在这些飞机都投入生产了吗?”
“呵呵,这些都是概念型飞机。什么是概念飞机呢?就是还没有投入生产,还在设计研发阶段,是往某个方向发展的未来飞机,有的,还仅仅只是一个设计概念。比如超音速飞机,过去欧洲有过协和飞机,但失败了。可早晚还是会继续研发的。更快、更舒适、更安全,一定是飞机的未来发展方向。像这一架飞机,宽体的,比空客A380型飞机还要大,能够承载1000名旅客。不过,我猜波音公司可能永远也不会生产它了。并不是越大就越好。空客A380在使用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但货机就不一样了,你看,这架货机,这么大,能装进去多少辆坦克,你能猜得出来吗?”
薛媛为这个飞行员那好听的声音所迷惑了,她的身体里本来有一种磁极,现在,她感觉,就在这一刻,这种磁极忽然被眼前这个男人激活了,然后,她被这磁极所扰动,身体有一种震颤感,这种震颤感只有她自己才能感觉到。“那这架能够打开降落伞的飞机,是什么概念啊?”薛媛指着一架分成了两半的飞机模型问他。
“这架飞机模型,是把机舱和底座分开展示,你看,一个巨大的降落伞拖拉着飞机的客舱。这是飞机设计师的一个概念。现在,飞机虽然是地球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可一旦遇到机械故障,出了事就是大事故,可能机毁人亡。于是,飞机设计师就想,如果在空中遇到险情,比如飞机的发动机完全失灵,那么,整个客舱的座舱弹射出去,然后,降落伞打开,坐人的座舱会安全降落地面,旅客就安全了,就像落地之前的宇宙飞船那样。”
薛媛很赞叹,“嗯,这样的设计概念很不错,多了一个飞机乘客存活的安全保障,类似汽车安全带的作用。”她又指着那架透明飞机的模型,“你看,这里写着‘透明飞机’,透明的飞机在空中飞行,没有遮挡,什么都看得见,谁敢坐这样的飞机啊?”
他笑了,摆了一下脑袋:“这是在展示飞机制造材料的先进罢了。虽然飞机材料大部分做到了透明,但飞机本身却是非常安全稳定的。人类的制造能力已经快到这一步了,就是制造出某种全‘玻璃钢’型的飞机。这样,人在飞机中,而飞机是透明的,这就像是你坐在透明的高空缆车中的感受一样。”
“啊,我可不敢坐这样的飞机。我最害怕没有支撑、庇护、依靠和遮挡的那种感觉了。我就是害怕没有安全感。”薛媛说出了大部分女人的心声。
“女孩子啊,就是最关心安全感了,”他笑吟吟地递给了她一张自己的名片,“不过,这些概念飞机很多恐怕是要永远都停留在概念里了。就像你说的,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坐在透明飞机里的。那实在是缺乏安全感。只有我们飞行员能开得很嗨,乘客估计是要崩溃的。你喜欢哪一架模型?我现在就送给你。”
薛媛看着他,笑了。她就这么和方强认识了。然后,他们就开始了约会和恋爱。
二
五年过去了。这五年的时间里,薛媛与方强的感情发展得不错,但是,她发现自己过去能够闻到方强身上那种体香,现在她闻不到了。
男人也有体香?是的,也有。方强身上的体香不是香水味儿,而是他的身体自带的。这也许与他的父母经营檀木、花梨木等红木家具有一定关系。有一次,薛媛去他父母开的那家家具店的后院,看到一个很大的仓库里,储存了不少原木,大大小小的,安静地躺在那里散发着各色香气。这些香气可能已经浸润到方强的身体里了。
薛媛来自四川一座小县城,父母亲是当地的政府公务员。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华侨大学毕业,在公司里做文员,就留了下来。海岸对面就是台湾岛,因此,每天都能感觉到海风的吹拂,她是那么的高兴。在薛媛和方强同居的这五年里,他们互相已经熟悉到似乎有一点少许的厌倦感了,这是一种隐秘的、谁都不愿意面对和说出来的小感觉。
薛媛还记得,她是那么喜欢亲吻他那健美的身体,他那由高强度的体育锻炼和丰富营养供给锻造出来的男人的美妙身体。她会吻他,她喜欢从他的眼睛开始,从睫毛那里开始亲吻。不知道你有没有亲吻过一个男人的睫毛。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让小刷子一样的睫毛在唇边来回地扫动,她会立即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柔软,散发出芬芳。假如他闭着眼睛,亲吻他眼睛的时候,眼球在眼皮后面缓慢地来回滚动的感觉,不知道哪个女人体会过没有?震颤,奇妙,迷人。然后,再顺着额头亲吻他,亲吻他那滑动的喉结,也是多么的有趣和生动啊,这就像是要逮住一只狡猾的老鼠那样,他那滑动的喉结是不容易被她所捕获的。好了,还有他的耳朵。他长着一双鬼耳朵,因为,他的耳朵里有时候会长出几根长毛,弯曲地、柔韧地伸展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每一次她都是用舌头去濡湿,然后咬断,这样他会尖声叫唤,这让她很兴奋。或者,有时候她让他躺在她腿上,她用剪刀给他剪掉。他的耳垂往往是凉的,这是他身体最凉的部分,像一种奇怪的多余物,长在他的身体上。而他的胸膛,隆起的一片三角形高原,是她觉得最乏味的,除了他那粉红色的两颗乳头。她不会在他的胸膛那里停留很久,就会去探索他的肚脐眼。啊,那浑圆而神秘的塌陷,那螺旋和漩涡一样的深入,被掩盖的洞穴,男人的体香诞生之处,她喜欢用舌尖轻挑他的肚脐边缘的旋转皮肤褶皱。就是在那里,他散发着一种体香。这种体香,方强自己也闻不到,只有她能够闻到。每每到了这一刻,薛媛就沉醉在一种肉体的迷狂里了。
至于他的男性雄起物,他的睾丸阴囊,他的大长腿和他那纤细苍白的大脚,就乏善可陈稀松平常了,就不用多说了,她也都是熟悉的。
身体当然是恋人之间互相吸引的一个因素。他们的身体在那么多的日子里,一千多天互相依偎,互相嵌入,彼此搭配。然后,薛媛就和她的“小哥哥”的身体,熟悉到了再熟悉不过的地步。再激情万丈的爱都做过了,再磅礴澎湃的交流也有过了。现在,他们来到了男女关系的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眼前是那么的开阔,可是,越开阔,他们越不知道向哪个方向走了。这就是他们现在的真实感觉。
薛媛想,这些年,方强每一次都能驾驶飞机安全地降落下来,但现在,他们要不要降落在婚姻里呢?这个时候是应该结婚,还是应该分手呢?她不知道。
她知道的,是从最近一年开始,她常常踏上远足的旅途,而且,是她一个人。他也支持她去旅行。她所在的公司工作繁忙,最后,她就辞去了工作。因为方强每年的薪水有一百多万,足够他们开销,她的父母也出钱给他们买了一套房子,希望他们结婚,早点生孩子。在五年的时间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里都采取了避孕措施,有时候没有,可她从来都没有怀过孕,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她也没有准备好要孩子。有人说,没有准备好要孩子,就不要结婚。结婚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繁衍后代。
他们什么都不缺,他开一辆轿车,她有一辆路虎越野车。这使她能够驾驶车子前往她愿意去的任何地方。一开始是城市周边,然后,是长江腹地,最后,是北方的草原和西部高原,乃至边陲地区的那些高山大漠,她都去了。
奇怪的是,在路上,她又找到了与方强继续相爱的感觉。不一定要每天在一起才相爱,她每次出门,都发现自己更爱方强了,因为,每次出远门,一个人驾驶汽车或者坐飞机出行,方强和她总是通过手机短信,现在还有了微信语音,在紧密地联系着。这样即使是在天涯海角,她也能够感觉到方强和她在这个茫茫世界上的关系是最亲密的。也就是说,距离他越远,就距离他越近。这种感觉太奇怪了。
这么多年来,他一次次地给她讲述他驾驶飞机起飞、飞行和降落的过程中那些有趣或者乏味的感觉,大地那金属的儿子——飞机,最终,总是要降落在大地上。而飞机一旦平安降落,方强的短信或者语音就会发过来,不管她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她都能够很快知道,他安全降落了,不光是他自己,而且,他让一个航班安全降落,在飞机上,还有上百乃至几百人都安全地从飞机舱里走出来,前往每个人生活的喜悦和冲突当中去了。
她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找一个美丽的空姐做女朋友,因为他每天都和很多美丽的空姐在一起上班,早出,晚归,飞两天,休息三天,或者飞三天,休息三天,各种空乘组的组合,每天都在发生,在航空公司里,每年都有新的空姐加入,一定有女人喜欢他,甚至愿意把自己交给他。
“因为,我就是爱你,亲爱的媛媛。空姐很好,但我和你现在的关系,已经是那种起飞之后十五分钟在巡航高度正常平飞的状态了,这是飞行的最好状态,也是最安全惬意的时刻。这,就是我和你现在的状态。让我们继续飞行吧,直到我们想降落到婚姻的跑道上去,我们就降落,好不好?告诉你吧,空姐们长期在高空飞翔,会被大量地面照不到的辐射所影响,她们老了以后可能会得老年痴呆症。起码,记忆力减退,衰老加剧,这是没有人会告诉你的秘密,现在,我告诉你了。大部分的空姐都干不长,这在中国是一碗青春饭。空姐在高空服务旅客,是需要细心、耐心和毅力的。每天面对各种乘客,甚至偶尔面对危险,女人再有韧性,也不见得能长期干下去,干几年,最多干十几年,她们往往会转到地勤从事其他工作,甚至离开这个行当。你明白她们的辛苦了吧?”方强这么说。
薛媛就不再嫉妒和想象那些空姐和方强的关系了。五年的同居时间,使他们之间磨合得很好,连吵架都不会有。可是,他们的关系往哪个方向走,却是眼下两个人内心感到迷茫的。结婚,本来是那么容易的事,现在,却变得艰难了。是否降落到婚姻里面,现在他们还拿不定主意。
其实,主要是薛媛拿不定主意,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立即嫁给方强这个“小哥哥”。人在一种惯性中,对已经获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都会忽视和疲倦的,甚至会忘记自己已经是多么的幸福,而一旦真的丢失了,那个时候,后悔都晚了。这是她当时还不明白的事情。
要不要与方强一起降落在婚姻里?她不停地问着自己,还没有答案,于是,她就更为焦虑了,也就更喜欢远足了。
说起来,是有一个因素的。前年,另外一个男人出现在她的生活里。那一次,是她驾车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沿着呼伦湖边缘的道路在行驶。大地展现出无比开阔的一面,草原遇到了旱季,牧草并不茂盛。在前方的视线里,一些车轮压出来的小道,纵横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早晨是寒凉、清新和湿润的,牧草上挂着露珠,而蚂蚱都还没有苏醒。到了中午,草原上热气蒸腾,暑气也随着上升,燥热难耐,汗流浃背,虫蝶飞蹦,太阳也是毒的。到了傍晚,大地被夕阳覆盖,是无比辉煌的,太阳的余晖让一切都金光闪闪,然后,是热血一样的天边,落日将沉,如同战士喷洒了热血,渐渐进入到黯然的死亡,大地逐渐暗淡下去,将血色带入到真正的黑暗中。
就在那个时刻,她的车爆胎了,就在呼伦湖边的小道上。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大草原从中午到晚上都是这样。她也没有办法打救援电话,因为没有手机信号。只能在那里等待,毕竟,这是一条草原上的主车道。一直到落日完全沉入天边,她感觉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打算钻进车子,在寒凉和孤独中度过这个夜晚。
忽然,远处有一辆汽车亮着大灯开了过来。她那黯淡下去的心情立刻好了,她下车挥动手臂,大声地喊着。那辆越野吉普车开到了她的附近,停了下来,走下来一个长发飘飘的大个子男人,胸前挂着一架照相机,带着很长的镜头。他走到了她跟前,“怎么了?”
“爆胎了。请你帮帮我。”
他很沉稳,“有备胎吗?备胎永远都很重要,对于出门的人来说,要有备无患。”他笑了一下。
“当然有备胎,就在车子里。”她觉得他像是一个摄影家。因为,他的相机非常专业,镜头很大,很昂贵,她一看就知道。
他二话不说,就从自己的车上取来了修车的工具箱。然后走到她的车子跟前,打开工具箱,取出了千斤顶、扳手等等。他又取下她车子里的备胎,就开始给她换轮胎。他的动作娴熟之极,根本不需要她帮忙,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常出远门的男人。她感觉这一刻他是那么的性感,这与方强从机场回到家里系上围裙做饭的那种性感是相似的。她身体里的那种磁极忽然就开始了扰动。
就是几分钟。“好了,”他站起来对她说,“我换好了。你要去海拉尔吧?”他问。
“嗯。我晚上要入住那里的宾馆。”
“其实,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和我一起去看星星。我今晚要拍星星。只有草原上才可以看得到无尽的星空。我还有睡袋,你可以睡在草原上。头枕着大地,眼望着星星,那种感觉,你今后不会有的。怎么样?”
她被他说动了,这太诱人了。“好啊,去哪里看星星呢?”她的内心里激荡着一种东西。身体里的磁极被继续激活。
“你的车子跟着我的车子走。”他说完,将工具箱放回自己车子的后备厢里,然后发动了汽车,沿着一条在车灯照耀下能够看见的车辙前进。车灯的辉映下,有不少草原上的蚊虫被惊扰,纷纷飞起来,撞在玻璃上。此时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大地是黑暗的。她的车子跟着他的车子,在草原上开了半个小时,来到了一片相对较高的坡地上,停了下来。
“那边还有一个敖包。”他下来对她说,“白天的时候,我站在这里拍摄远处的那条河,你看,现在,那条河还在闪闪发亮。”
顺着他指的方向,她看见了这片坡地的不远处,有一条河流在淡淡地发亮。今天的月亮是一点月牙,很细小,因此是看星星的好日子。他说:“我叫沈皓然,我是人文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您——”
“我?就是一个驴友,我叫薛媛。”她伸出手,她感谢他的搭救。
他捏住她的手不经意地握了一下,递给她一件东西,“嗯,这是你的睡袋,现在我们搭一个小帐篷,你帮帮我。”很快,一个野外宿营的帐篷就搭建起来了。是一顶红色的小帐篷。看到她有些心神不定,他说,“你是不是觉得睡在车里更安全些?”
她看了看手机,“不是,是这里没有手机信号,就是觉得,应该与家人联系一下。我习惯这样了。”这一刻,她想起了在空中飞行的她的小哥哥方强,他是不是在准备着一场降落?如果他降落之后没有她的消息,他会不会非常的担心?
他看着她,“这里距离陈巴尔虎旗有一百多公里,你愿意的话,还可以赶到县城去。”
她想了一下,说:“不了,我就和你一起在这里看星星吧。”
他感到欣慰,说:“那我们往那边走走,那边有一片大坡,下面就是那条河,可以感觉到草原河流的湿气扑面而来,非常清爽。”
到了坡地上,她感觉到微风吹过来,夏天的草原上,青草从大地的深处散发出一种生长的气息。蚊虫都不见了,也许是她身上喷的一些驱蚊剂起到了作用。他们坐在坡崖边上聊天。
在他的指导下,她看到了整个星空。是的,草原上的星空一览无余地出现了,啊,这完全是一个弯曲的宇宙穹面所衬托出来的星空,无数的星星,那么多,点缀在黑色的幕布上,这是多么璀璨的星星啊,一点遮拦都没有,只有真正的星星,散发着热气的星星,热闹的、不断游走的星星,静止的星星,大大小小的星星,都在天幕中说话。
她仰望着这在城市里绝对看不到的景观,内心里有着一种声音、音乐,或者奇怪的律动。女人和星空、和天象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所有的星星在她的眼前都是活跃的,不是死的或者呆滞的,而是顽皮的、发亮的精灵。尽管她知道,它们都是星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存活,它们发出的光甚至是亿万年前放射出来的,有的甚至可能都已经死去了,只是现在她才看见它的光亮。他坐在那里,给她讲大爆炸、奇点、银河、恒星、白矮星、黑洞、河外星系、星云、红巨星、彗星、卫星、中子星、暗物质、星团,所有这些词在他那里都是那么的熟悉。
他告诉她,只有在这里,远离北京——他所在的那座喧嚣的帝都、大城市,他才得到了一种能够静心思考遥远事物的能力,因为,人太渺小了,在时间中是不堪一击的,是瞬间就不见了的。而在这里,安静如世界草创的时刻,只有他们两个,一男一女,坐在那里看星星,谈宇宙,谈你我他以及茫茫人世中所有的事情。
那天晚上,就这样,他们认识了。他们后来钻进帐篷里,睡在各自的睡袋里,他也没有侵扰她。第二天早晨,他们留下了彼此的电话号码就告别了,驾驶着各自的汽车,前往不同的方向。
三
此后,薛媛就和沈皓然保持着联系。她知道,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拍摄,他所就职的人文地理杂志需要来自人迹罕至地区的高质量图片。他们互相打电话、发短信,她逐渐对他的生活了解了,也产生了兴趣,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他们之间交流最多的,就是摄影,在他的帮助下,她的摄影水平大为提高。但两年多来,她和他一共只见过两次面。最近的一次,还是在这座滨海城市,那是他来参加海峡两岸摄影大赛的颁奖仪式,他的作品获得了金奖,他来领取五十万的奖金。
沈皓然打电话告诉薛媛,他来了。她觉得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他们约在一座绿树掩映的小山上一间禅意浓厚的茶室见面。那小茶室里有很好的素食点心,是她爱吃的。这一次见面,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他们聊了很多。和他在一起聊天,她感觉他一点都不陌生,他还是那个样子,长发飘飘,高个子,大眼睛里都是笑意。他喜欢她,这是肯定的。临别,他忽然拥抱了她,将自己那冰凉的嘴唇盖在了她那火热的嘴唇上,亲吻了她。但旋即他就松开了她。
那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见面为好。似乎两个人都回避这一点。但是,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一次他出远门,都会告诉她他的行踪和安排,仿佛她是他最亲的人,需要知道这些。他说了,一旦他遇到了危险,她会是第一个知道的人,必须立即报告有关单位,只有她才能如此。他信赖她,她就这么逐渐地开始每日牵挂着他。
现在,她明白这就是她无法下决心和方强——她的飞行员小哥哥结婚的原因所在。有了沈皓然这么一个障碍,她迈不过去结婚的这道坎。
最近的一天,执飞任务结束,方强驾驶飞机安全降落,他发了短信给她。从机场回来,他带给她一个新的礼物,是从泰国一家寺院里求来的佛牌。“有个法师对我说,明年,我就应该结婚了。媛媛,我们是不是应该做这件事了?”
薛媛说:“现在,我们不是也很好吗?”
方强的目光就有些迷蒙,“还是不一样。我忽然有些担忧。今年,全球坠毁的飞机有六架之多。像马航370航班,说是飞到印度洋那边了,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马航17航班在乌克兰上空被导弹击毁,机上所有的人都死了。亚航的一架飞机前不久在印尼海域坠海,一百六十多人全部遇难,飞机残骸打捞也不顺利。这是一个不安稳的世界,媛媛,每次我在高空驾驶飞机飞行,我就觉得,我需要降落,需要安全降落,我不仅要降落在跑道上,我也要降落在安全的婚姻里。”
薛媛想起来最近一年中发生的那些飞机失联和坠毁的事了。是的,马航17航班在乌克兰上空被导弹击落,人就像空中落石那样砸到了地面上,落到了房屋顶上、农田和葵花地里,再也不会复生。这一年中还有非洲发生的飞机坠毁事件,机毁人亡。到年底了,忽然,亚洲航空公司一家空客320飞机坠毁于爪哇海的加里曼丹岛附近,一百六十多名乘客葬身大海。她无法想象那些身处海底的尸体是多么的可怜。而马航370航班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为什么不在飞机上安装上一个即时定位和即时传送的视频系统呢?这么简单的技术,竟然就不能实行。那个马来西亚飞行员,很可能是自杀飞行,让所有的人去殉葬。这是内心多么黑暗的家伙啊。薛媛当时一看到电视上那个叫马扎里的飞行员的脸,就觉得这一切就是他干的——他把家庭矛盾、政治立场和厌世情绪纠结在一起,制造了这一起航空史上最令人不齿的杀人事件——他杀了两百多人!他们肯定不会再回来了。她忽然理解了方强的那种愿望。
“让我想想——就一个星期,给我一个星期,我的小哥哥,好不好?让我想想。”
方强点了点头,亲吻了她的额头,把佛牌挂在她的脖颈上,“愿它保佑你。”然后,又递给她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枚两克拉的钻戒。
现在,薛媛需要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答应与方强结婚,或者分手。在她的心里,还存在着一个疙瘩,就是沈皓然。沈皓然当然不是备胎,而是她对理想男人的一个憧憬。和方强在一起的这么多年,生活是那么的稳定、和谐,虽然已经归于平淡,但是安全可靠,幸福和平实得没有波澜。就像方强驾驶飞机的水准很高一样,他总是能够将飞机安稳地降落到跑道上。他也可以当一个很好的丈夫,驾驶他们的生活稳步前进。
可是,沈皓然在两年的时间里带给了她另外的可能性,满足了她对另外一种不羁生活的遐想。沈皓然一直独身,似乎只有这样才适合他的野外工作,他似乎不大需要家庭的羁绊,但他却需要她的牵挂。这一点是她确认的。可如果她真的来到他的身边,走入他的生活,那又会如何?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了,两个人开始一起在外面行走,一起风餐露宿,饥餐渴饮,在辽阔的大地上行走,离开那喧闹的城市和凡俗庸常的生活,去寻找另外一种人生的图景,那样是不是更具吸引力?
这是薛媛心里一个隐秘的、绝对没有人知道的梦想。这是她无法确定是否与方强结婚的潜在原因。因为,对于大部分女人来说,选择男人,就是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于女人来说,男人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每个男人的职业所导致的生存方式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很大的。选择了一个男人的同时,女人就选择了一种生活的方式。
她想,假如她和沈皓然在一起,他们并肩行走在祖国的山山水水之间,大好河山之中,这样的感觉是多么美妙。而且,他指导她的摄影技术,她也可以成为他的好帮手。虽然他们一直没有在一起好好相处,但她感觉她的灵魂与他很近,她和沈皓然是灵魂的朋友。她与方强的身体在一起,但渐渐地,灵魂却是若即若离的。所以,她想来想去,决定要去和沈皓然见一面,只有见面了,她才能最终确定自己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只有见到他,她才可以确定,沈皓然和她是什么关系,有没有爱情,他们最终会怎样。
四
她飞到北京去见沈皓然。出发前,她告诉方强,她是去北京参加一个老同学的聚会,她的大学同学有十多个都在北京,其中一位最好的女友孩子满月,要喝满月酒。这是一个不错的借口。落地之后,薛媛给女同学打了电话,说自己要先去看望一个老朋友,然后再和她碰面。
在机场,沈皓然来接她了,他还是老样子,那在空气中飞扬的长发飘飘洒洒,十分潇洒。他见到她很高兴,就好像他一直期待着她的到来似的。他接过她的拉杆箱,又拿过她的手提行李,大步流星地向停车场走去。在三号航站楼那迷宫一样的停车场,他找到了自己的汽车,那辆越野车,上面的灰尘很厚,风尘仆仆。坐到了车里,他拿出一束鲜花:“给你的,媛媛。”然后,他扳过她的上半身,亲吻了她。
这一刻是她始料未及的。他的舌头绵软、硕大,跟他那身板一样厚重有力。她感觉到身体里激荡着一种旋流,在裹挟她向很深的海沟落去。然后,他松开她,两个人不再说话,他的右手握住了她的左手,然后只用一只手开车,驶往他的住处,“我住在怀柔的一处半山脚下,我在那里买了一个院子,过着半农民的生活。”
半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到了北京郊区怀柔的山林中,那里是他的工作室和住家。这位于半山腰的院子,是农家小院改造的,一共三间房子,院子的院墙高过人的头顶,是石头垒的,爬满了丝瓜和南瓜秧子。院子里有两棵山楂树,“那边还有厕所和一个地窖,地窖除了储存杂物,也是暗室,可以制作各种相片。”
进了屋子,薛媛感到一丝不安,已经是傍晚了,她说:“我来做饭,你想吃点什么?”
沈皓然笑了笑,“你看看厨房里有什么,咱们就吃什么吧。南瓜、葫芦、丝瓜、黄瓜,什么都有。”
薛媛开始在冰箱里找东西。这个农家小院已经被他改造得很适合居住,三间连起来的房子,两边有两个卧室,其中一间还兼做书房,中间的堂屋里是会客和起居室,两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摄影集。这些摄影集个头大大小小,但是都很厚很重,因为都是彩印和精装的。
“在三间屋子的顶上,我还加盖了一间。那里有一道门可以通向后山的小道,小道两边都是柿子树和核桃树,一直通向山顶。山顶上就是长城。”沈皓然说。
“你等着,等着我做点吃的。”薛媛笑着说。她的手脚很麻利,长年与方强同居,她已经很会做饭了。每一次方强执行完航班任务平安降落,回到家里,她都会做好几个精美的菜肴,等待着他。所以,做饭对于她是小菜一碟,她是行家里手。在这里她也想大显身手。而且,她发现他的厨房里东西很齐备,连刀具都有十多种,可大部分都是没怎么用过的。显然,没有女人常来他这里,否则这些餐具和厨房用具不会都是新的。
只花了一个小时,电饭煲里的米饭熟了,四个有荤有素的菜也做好了。都是冰箱里有的东西。端上来的时候是赏心悦目的,也是让人胃口大开的。现在,她饿了,他也饿了,于是,他们就吃饭。
“吃完了饭,我们可到楼顶去看星星。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星星,此外,还可以看到月亮上的环形山,我在上面那间屋子里,装了一台望远镜。”他说。
“好呀。”她说。
“我想让你先到地窖里,看看我拍摄的照片。”在这顿饭结束的时候,他说。他带她去地窖,那是由一个下伸的台阶构成的地窖,过去在北方,地窖都是用来储存冬季蔬菜的,并不潮湿,虽然深入地下好几米。下到地窖里,他打开了灯。这里被他改造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暗室。有冲洗设备,还有除湿和烘干设备。此外还有一张床,有一个小的可以当做摄影棚的空间。这地窖的空间比较大了。
“来,我来给你拍点照片。”沈皓然说,“你坐在那里。我早就想好好给你拍点照片了。”
薛媛忽然感到一丝异样,因为,她看到了沈皓然的眼睛里掠过一丝阴鸷的快意。他是要干什么?我在这地窖里,会不会——她说,“这里这么暗……不拍了,行不行?”
沈皓然忽然抓住了她的手,“不行,你必须要拍摄,因为,你已经来到这里,落到了我手里。”他的面目变得狰狞了,他扭住了她。她发现自己身处困境,她想挣脱,但是根本就无法逃脱。在挣扎的当口,他三下五除二就将她捆绑起来,还挂到了一个吊钩上,用滑轮将她升起来,然后,一件件地剥掉了她的衣服,让她赤身裸体完全暴露在大灯灯光的照耀之下。在靠墙而立的大镜子里,她看见自己像个被蛛网或者蚕茧所包裹的猎物那样悬浮在空中。她又羞又怒,“放我下来!你这个变态!放我下来!”
沈皓然已经变成了恶魔。他嘎嘎地笑着,并不理会她,而是用相机近距离咔咔地拍摄她,将她的窘迫和恼怒都拍摄下来,还将她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拍下来。她被绳索吊到半空的旋转和无奈,表情的愤怒、羞耻、无助和懊恼,全都被拍摄了下来,他一边拍照片,一边下流而兴奋地手淫。她在摇晃、尖叫,但他制止了,猛力地抽她的耳光。她不吭声了,他用滑轮把她放下来,依旧捆着她,他把她抱到了床上,嘴里呢喃着,我的小宝贝小宝贝,然后将一团布塞到了她的嘴里,将她摁到床上,强奸了她。他一下下地冲撞她,他的生殖器火热、尖锐,就像钻头一样钻入她体内,让她感到了干涩的疼痛。但渐渐地,她感到身体在发热,有一点反应,她更加恼怒自己的快感和耻辱并存的感觉。
然后,他满足了,将一床被子甩盖到她身上,就从地窖口出去了。可以听见他用铁锁锁住地窖门的声音。她裸着身体在被子下面哆嗦着、哭泣着,后悔自己怎么能如此轻信,导致陷入到这样一个境地。这完全是自找的,谁都怪不得。最可怕的是,现在想来,竟然没有人知道她来到了这里。这个沈皓然,一定是个性变态的家伙,欺骗人的老手,会将她的手机没收,把电池取出来,谁都无法定位她。我怎么办?她抽搐着、哭泣着,一筹莫展。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挣扎着掉到了地上,嘴里的布团掉了出来,她大声喊叫救命,可是很奇怪,墙壁似乎吸收了她的喊叫声。不久,他又来了,看到她企图逃跑,就用皮带抽打她,将她用滑轮再次提吊到半空,刚好让她悬垂于他的腰部那么高,他抓住她的被捆得很结实的胳膊,站在那里,从后面干她,一下下的,像是重锤在锤击,又像是推杆在前进,他的身体冲撞她,他淫笑着,她在干嚎,她在哭泣……
她醒了,发现自己还在飞机上。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摘下耳机,她听到机长广播,飞机临近北京上空了,进入空中走廊,现在已经开始下降。刚才那可怕的一幕,完全是她做的一个梦。这都怪《南国都市报》,她刚才看了一篇跨页的核心报道,报道的是河南某个农村一处果园里有一个变态男人,将几个女人关进地窖里做性奴并且虐杀她们的事件。由此才引发她做了一个自己被困的噩梦。
空姐走过来,关切地问她需要什么,刚才空姐听见她很不舒服地喊了几声。她感觉到自己出汗了,被吓到了。“没什么,我很好,谢谢你。”她接过来一杯水,对空姐说。
飞机的降落异常平稳。这使她在内心里格外感谢航班机长。她忽然有些想念方强,现在,他正在执飞去欧洲的一个航班。按照时间推算,他正在俄罗斯那广袤的国土上空飞行。也许,到了乌拉尔山的上空了。每次出行,要到很远的地方,方强总是喜欢给她看自己的航路图,告诉她,公司又开辟了哪些航线,还下载了一个三维的航路图的软件,这个软件可以呈现出方强执飞的航班路途的三维景观,无论是航迹图,还是周边景观图,三维图像可以从上、下、左、右,360度旋转的角度,展示一架飞机的即时飞行。这使她更加了解他的工作,他的重心所在。
她出了机场,看到在出口处,那个高个子的男人就是沈皓然,他正笑吟吟地等待着她。就像她在飞机上梦到的一样,他先帮她拉着那个红色的拉杆箱,然后,果然,接过了她的手提行李。她的心口咯噔了一下。一切都是安排好的,那么,好吧,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不会奔向郊区那个可怕的地窖?
在那个偌大的停车场里,跟她梦见的一样,停着他那辆风尘仆仆的越野车。他放好了行李,然后上了车,果然,就像在梦中一样,他扳过她的上半身,亲了她一下。有一点和梦中不一样,他没有用舌头伸入她的嘴里,只是用嘴唇碰了她的嘴唇。她的心开始怦怦乱跳了。车子出了机场,拐到高速公路上,开始加速,一路飞奔。
她有些紧张了,“咱们这是去哪里呢?”
他转脸看了她一眼,“先去吃饭。去蓝色港湾吃饭。我在那里的一家餐厅订了一个座位,有你喜欢吃的菜。”
她也看着他,想了想,问他:“你有没有一个工作室,是在郊区的半山上?”
他诧异地看着她,“没有。我没有工作室啊,我的工作室就是我的住处,在东三环最繁华的中央商务区的边上,大隐隐于市。等会儿你会看到这个城市最璀璨、辉煌和华丽的景象,从我的房间里望出去,这个城市就会展现在你的面前。”
她舒了口气。这就和梦里的不一样了。她感到了一丝疲倦。人对人的信任,在今天建立起来十分困难。好在她还有直觉,知道谁值得信赖。起码,她觉得她没有看错他。
车子到了蓝色港湾,那是一个购物休闲的场所,就在朝阳公园的水池边上,这里非常热闹,彩色的霓虹灯和灯网布置成灯树和灯的长廊,不断闪烁,到处都是年轻人。有音乐喷泉,也有电影院。在一家新开业的牛腩餐厅,他们吃了饭。都是她喜欢的菜,有带血的牛排。他还带来了一瓶红酒,她喝了半瓶,他开车,不能喝酒,说等下到了住处,再喝。
她看着他。他们的晚餐吃得很安静。他似乎知道她来干什么,但是他不提。他们聊天聊的都是最近的见闻,各类见闻,以及这世界上发生的很多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新闻。他们似乎在等待着一个时机,去触及两个人实际上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关系,他们将如何确定或者了结他们的关系。可他们有关系吗?他们是什么关系?
吃完了饭,他带着她来到了他的住处。就在东三环中央商务区的边上,一套平层、有180平方米的公寓。房屋的装修简约到极致,似乎就是沈皓然的风格,从不雕饰。房间里的东西很少,也没有暗房,不知道他在哪里冲洗照片。或者,真的有一个地窖,但是他不说?或者,现在的摄影全部都数字化了,不存在一个暗房了?她的思绪收回来,从客厅的落地大窗户往外面看,可以看到,眼前是中央商务区那些高达几百米的大厦,它们组成了璀璨华丽的钢筋水泥森林,正被五彩的、变幻的灯光所装扮,闪烁着物质胜利的光彩。
“没有想到,你会住在这么喧闹的地方。”她和他端着红酒杯,站在窗户边上一起看着外面的世界。
现在,她感到安全了。那个梦,是她的内心疑虑的折射,也是她碰巧看到关于性变态囚禁性奴的报道的反应。沉默弥漫在两个人之间。后来他们坐下来说话。她可以感觉到他的友善、智慧和美好。他似乎什么都知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看你吗?”她终于问他了。
“知道,你可能要嫁人了。”他说,然后笑着看着她。
“你——怎么——”她有些结巴了。他确实什么都懂。
他走过来,温和地揽住她的腰,看着她。“媛媛,我就是知道。我知道,我了解你,正如我了解我自己。”他身上有一种淡淡的香气,是香水的味道,与他在野外的时候身上散发的雄性动物的体味,不一样。回到了城市,他就变得精致和典雅了。但他依旧是属于大地的,可能根本就不属于她。
“你真的什么都知道——”她有些嗔怪地看着他,“你说,我该怎么办?”
他认真地看着她,目光清澈而生动。“媛媛,我了解你。你现在需要一个决断,这对女人很重要。你在想,要不要和你的飞行员男朋友结婚。”
她把头低下来,觉得这一刻似乎很不公平。因为这是不平衡的,似乎是有人在帮助她做出选择。
“我觉得,你应该和他结婚。首先,我说吧,我知道你喜欢我,这两年多来,虽然我们不常见面——我们一共就见了两次面,但是,彼此很牵挂。实际上,你对我保有一种想象,就是希望和我一起远走天涯,在大地上奔走。的确,我是一个摄影师,我要常常走在荒野上。你也渴望像我这样生活,放飞自己。是的,我是单身,我曾有一个女友,她去日本了,在那里工作,我们的关系早就散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适合你,我了解我自己,我不适合你。有时候,你现在拥有的,就是你最好的东西,比如你的生活,你和你的男朋友所建立的关系。而你所想象的,却并不是你能够把握的。我不知道你明白了吗?”
她抬起头,心情有些搅扰,但并不纷乱。一些东西在清晰。她看到自己在清晰起来,包括她对自己的体认。她是谁,他是谁,以及,他刚才说的那些话。他说的那些话打动了她,他告诉了她一些最真实的生活态度。可能她就是在想象,想象很多本来就不是她能够掌握的东西,包括他,他的生活,以及她和他在一起可能的生活。
“所以,你应该回去就结婚。”他平静地说。
她看着他,很温暖的感觉。“我明白了。”
现在,他拥抱着她,在她的耳边说话,他们在这个大屋子里来回慢慢走动,就像在跳一曲慢舞。他们看窗外的北京夜景,那个璀璨的大都市在夜晚所展现的腐蚀人心的魅惑力。夜深了,她拿起他的手,轻轻触摸了自己丰满的胸部,那里稍微有点起伏,这是心情所致。“你今天把我拿去吧。拿去吧。明天去看看老同学,然后我就回去了,我会降落在——我们再不会——”她忽然变得非常伤感。然后,她主动吻了他。
他抱起她来到了卧室,将她轻轻地放在那张铺着有简洁图案的床单的床上,两个人看着对方,安静地、缓慢地抱在一起,就像他们想象了很多次这接下来的一刻要发生的事那样,他们拥抱在一起。
她的航班降落了,一出机舱,她就闻到了一股海风的味道。有点咸腥,但却湿润和清新。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和老同学的聚会也很高兴,但她很急切地想回到家里,看到方强。她打开手机,立即看到了方强发来的几个短信:“我已经降落了。”“我回到了家里,我在等待你回家。”
他驾驶飞机从欧洲飞回来了。越过了乌克兰上空,越过了乌拉尔山,越过了北京郊区的军都山。她的脑海里出现了他回来的航迹图。她的心情很淡然,也很高兴。她回到了家里,方强系着围裙在做饭,饭菜很快就好了。还有红酒。
在吃饭之前,方强从自己那个黑色的飞行员拉杆箱里,拿出来几个盒子,“媛媛,我一直准备着,要把这些礼物给你,算是我,求婚的礼物吧。”他把那些小盒子一一打开,装的都是他在世界各地买来的礼物。有捷克的水晶,俄罗斯的琥珀,南非的钻石,澳大利亚的澳宝,缅甸的翡翠,阿富汗的白玉,台湾的红珊瑚……
她拥抱住方强,又闻到了他身上那种奇特的体香,她流泪了,“什么都不需要,我们结婚吧。我们降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