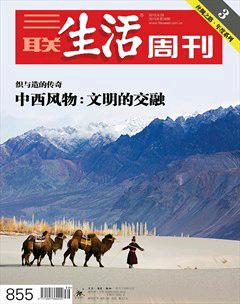陈师傅
张蛮鱼
陈师傅已经快70岁了,稍作打扮,完全是城里的时髦漂亮小老太太模样。你可以从那嘴角眉间的神情,遥想她年轻时的盛气。这盛气被大半辈子的粗粝生活打磨着,造就了她的清高、自怜、认命、不服软和突然的爆脾气——所以这是一个内心戏常常很复杂的老太太。
年轻时的陈师傅从来不觉得自己跟那些乡野村妇是一路人,她可是有资本的——漂亮,聪明,几乎是全生产队公认的,除了那些嫉妒她的粗鄙女人。这些女人在田间地头赤脚走过,从家里端来碗饭往巷子里的青石板上一坐,吃完把碗往地上一搁,拍着大腿亢奋地讲着别人家的笑话和丑事,一言不合便和有宿怨的老对头在巷弄里用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高声对骂——这一切都是陈师傅瞧不上眼的。年纪小小跟一群女孩子做女红,陈师傅早早就显出过人天资。她心气高,人又聪明,知道做裁缝几乎是脱离沉重农活的唯一出路,就下定决心学手艺。上世纪60年代买的那台上海产无敌牌缝纫机,就是家里公公里外几层地揣了八十好几块钱,大冬天去几十公里外的城里生生肩挑回来的,扎扎实实上百斤的国货。那时候的钱值钱啊,在穷乡僻壤80块钱更是个大数目,能抵上乡镇中学老师几个月的工资。等到学好手艺出师了,人家客客气气喊她一声陈师傅——就差要递给她一根烟的时候,就决定了她在农村可以像男人一样受人敬重了。不单是乡里人敬重她,连下放劳动的知识青年们都跟她要好,说她不像是待在农村的,至少看着像工人嘛。
如果看过《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你就会明白,在那时灰头土脸的乡下,这个匠人工种简直是被神一样供奉着。在那个大锅饭年代,陈师傅完全可以靠这个手艺赚着不少于一个壮劳力的工分,而且是体体面面地赚。哪家要做衣服,就得上门来请她,把她的上百斤上海货宝贝缝纫机挑过去,每顿都是雇主家倾尽所能好饭好菜另开小灶。陈师傅的名头响,全家也都跟着沾不少光。就这么风光到80年代,开始了分田到户,陈师傅也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要帮着招呼地里的活儿,裁缝活慢慢就接得少了。家里细伢饿了要吃奶,孩子奶奶常常得抱着伢儿走个十几里路到雇主家里找陈师傅。再后来,镇里城里都开始卖花花绿绿的上海羊毛衫洋布衣裳,白色的确良衬衫畅销乡里,除了白喜事,找裁缝做衣服的也不多了,陈师傅也慢慢被忘记了。只是去城里逛市场,陈师傅还是保留着一个裁缝的嗅觉,去高档的商店仔仔细细翻看那些上海来的呢子大衣外套,收好每一张印着时髦女郎的画报,默记着版型款式,买了布料回去还真就给做出来,有型有款一点都不比“上海牌子”差,洋气得很。陈师傅可以说是最早学会“打版”的那一批了。“哪像你们现在,上网什么衣裳样子都找得到?”
陈师傅说,她其实很早就想去县城盘一家裁缝店,凭她的手艺,养活一家人都没问题,而且可以像城里钢铁厂的“工人婆子”一样,干干净净体体面面过生活。但后来的日子,几乎是可以一眼望到头的庄稼人过活,粗活累活什么活她都干过,最苦的时候,她要在天蒙蒙亮起,肩挑满满一担自家都舍不得吃的新收成的碾好过筛的上好大米,赶去邻近镇上的早集卖掉。有次一个打扮得光光鲜鲜的“工人婆子”看上了她的谷子,压到一个最低价,叫她跟在后面把谷子挑到那六楼还是七楼的工人家里。我有时候就想,当时的陈师傅,担着空空的箩筐走出城里人阔气整洁的家时,心里会想些什么呢?
我没有告诉陈师傅,有个电影里就讲到以前乡下生产队的老裁缝和小裁缝,最后小裁缝走出大山,从县城到深圳,再到香港,当年喜欢小裁缝的两名知青,最后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陈师傅说她不爱看电影。她应该很早就不太会去做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