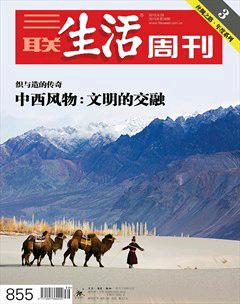人类情绪大全
薛巍
英国学者蒂芙尼·史密斯在《人类情绪大全:从愤怒到旅行癖的百科全书》一书中概述了人类各种情绪是如何被感知、被表现的。

英国学者蒂芙尼·瓦特· 史密斯和她的著作《人类情绪大全:从愤怒到旅行癖的百科全书》
情绪的发明
笛卡儿认为人类有“六种原始的激情”:惊异、爱、恨、欲求、快乐和悲伤。现代的一些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所有人都有六到八种基本的情绪,这个清单通常包括厌恶、恐惧、惊讶、愤怒、快乐和悲伤。但英国学者蒂芙尼·瓦特·史密斯认为,人类的情绪非常多样,她编制了一部情绪百科全书,收集各种情绪,目的是为了“反对把我们美丽、复杂的内心生活缩减为一些基本情绪”。
情绪是难以捉摸的东西,所以不难理解,“在1830年以前,没人真的感受到了情绪”。那时人们感受到的是激情、灵魂的意外或道德情操,而且古代人对这些东西的解释不同于我们对情绪的理解。一些古希腊人认为,恶风会携带着怒火。早期的基督徒认为恶魔会把无聊植入人的灵魂。在5世纪到6世纪,激情不只属于人类,也会影响其他物体,所以棕榈树会相恋,猫会忧郁。
史密斯说:“现代的情绪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期经验科学的诞生。”伦敦解剖学家托马斯·威利斯解剖被吊死的罪犯,他提出喜悦或焦虑是神经系统的作用。100多年之后,生理学家提出,身体在受到惊吓时退缩、高兴时抽动都是纯粹的机械过程,不需要非物质的灵魂。19世纪初,哲学家托马斯·布朗提出,这种新的理解身体的方式需要一个新的名称,他提议称之为“情绪”(emotion)。英语里已经在使用这个源自法语的词,但是不够精确,指的是身体和物体的任何运动,从树的摇摆到脸颊泛红。这个新词表明了理解人类感情生活的新方式,它使用实验和解剖研究,以可观察的现象为核心:紧咬的牙齿,滚动的泪水,发抖、睁开的眼睛等。
史密斯提出,情绪不只是一种生理学或者心理学现象,我们的感受还会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憎恨、愤怒或欲望好像源自我们最不驯服的动物本性。但我们人类特有的因素也会唤起这些情绪,比如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用于理解身体的概念;我们的宗教信念和道德判断;我们生活的时代的时尚,甚至政治和经济。”17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说:“有些人如果没听过别人谈论爱情,他们就会恋爱。”跟谈话一样,观看和阅读也能激发我们的情绪,或者平复我们的情绪。观念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有时它们会决定我们的生理反应。不然11世纪骑士哀伤或渴望爱情时怎么会晕倒?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人类学家对不同语言的情绪词汇产生了兴趣。他们发现,西澳大利亚原住民能够感受到15种恐惧。而对英语使用者来说很基本的情绪,有些语言中却没有,秘鲁的马奇根加人没有表示“担忧”的词。所以,使用不同的语言的人,感受到的情绪也不一样。
这部情绪百科全书一共只有240多页,有的词条非常短,其释义只有一句话,如:“Basorexia:突然想吻一个人的冲动。”“Pronia:一种奇怪的、让人心里发毛的所有人都希望帮助你的感觉。”
情绪的变迁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始于惊异(wonder),但此后惊异这种情绪的地位几经周折:“今天许多人把茫然、惊奇跟幼稚、天真联系起来。但是在12~17世纪,惊异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对充满珍稀、奇迹般的物体的反应。那是一个奇兽的世界,有钱人购买鳄鱼的牙齿,认为那是龙身上的,或者购买牛黄,认为它们能够解毒,还把它们放在多宝阁里加以展示。惊异带有一种困惑、恐惧和茫然的屈服,被敬畏上帝的学者视为一种重要的人类体验,1649年笛卡儿在《论灵魂的激情》一书中列举六种原始的激情时,把惊异列在首位。到17世纪下半叶,惊异消失了。在启蒙运动的文化氛围中,自然哲学家们开始强调秩序高于怪异,他们寻求自然法而不是奇迹,兜售奇珍异品的买卖也随之消失了。到18世纪,人们又努力赋予惊异曾经具有的文化权威。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到20世纪的嬉皮士,都感叹过彩虹的消散。但今天对大部分人来说,好奇遮蔽了惊异,成为一种合宜的情绪。”

英国学者蒂芙尼·瓦特·史密斯认为人类的情绪非常多样
浏览这些词条时会发现,作者对几乎每一种情绪都持正面的观点,无论是愤怒、无聊还是怀旧和幸灾乐祸。表达愤怒有益于健康,这并非一种很现代的观念。一些中世纪的医生就鼓励他们的病人释放怒火。医生、炼金术士罗杰·培根说,怒火的爆发可以放缓衰老的过程,因为它会让身体变暖,抵消老年的冷却效果。愤怒被认为能带来生命的热情和青春的光辉。
那些在无聊倾向量表上得分高的人被认为更有可能死于车祸、暴食、滥用药物。但也许我们不应该过于畏惧这种情绪。但当我们感到不满、不在乎时我们才会受到激励去改变我们的境况,去发明和想象。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说:“人类感觉到无聊的能力,而非社会或自然需求,才是文化进步的根源。”
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认为,幸灾乐祸并不是不道德。我们乐于安全地站在沙滩上,观看一艘船在风浪中翻来覆去,这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摆脱了不幸会令人感到愉快。他人的霉运——离婚、被裁员——会让我们感到释然,因为没有发生在自己头上。幸灾乐祸还能带来别的快感。看到政客的贪腐被戳穿、明星的双重人格生活败露,我们心中都会感到一阵快意。“这不只是因为我们嫉妒他们,或者觊觎他们的权力和成功。我们对自己赋予他们的重要性感到憎恨,我们希望他们受到惩罚,以便恢复我们自己的地位。得知他人糟糕的决定、出轨的配偶、忘恩负义的子女,我们都会觉得欣慰。它让我们意识到,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希望会破灭,别人的也一样。”
怀旧这种跟回忆有关的情绪既让人觉得温暖,又让人觉得忧伤,它通常是苦乐参半的。然而,在不到100年前,怀旧会让人丧命。在17世纪中叶,一种奇怪的新型疾病横扫欧洲,折磨着那些离家很遥远的人,如士兵、学生和旅行者。这种病被称为思乡病。对家乡强烈的记忆激发了这种疾病,其症状包括浑身无力、没有食欲、神志不清、长脓疱、溃疡,甚至瘦削衰弱而死。到19世纪,这种疾病在欧洲成为首要的研究对象。在美国内战期间,有5000名联邦主义士兵被诊断患有思乡病,并被送回了家。
作者说:“到20世纪初,怀旧的意义变成了对过去的事物的渴望,思乡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许是由于现代人信奉旅行和进步。今天,怀旧是充满渴求的、痴狂的时间之旅,一些气味、歌曲和照片能让我们‘回到过去。过于怀旧会让人陷入令人不满的现在和诱人但回不去的过去之间。但经常出乎意料地唤起久违的记忆,能产生一种令人愉悦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连续感。所以有些心理学家强调沉浸于怀旧的沉思之中是有益的,能够提升对生存的意义的感觉以及跟他人相互关联的感觉。美国心理学家克雷·劳特里奇甚至建议人们做怀旧练习,读读以前的书信,列举那些宝贵的记忆,以此来缓解焦虑、孤独感和漂泊感。中国南方的一个研究小组注意到,怀旧之情在较冷的地区更为常见,他们提出怀旧也许是为了实现提高我们的体温这一进化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