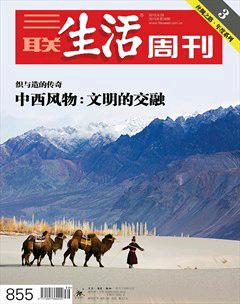物种输入,1500年的历程
陈晓
花园
我的植物启蒙是从四川老家的院子开始的。这是一个看起来并不精致甚至有些杂乱的小院落,在住房外用围墙圈出的一溜狭长土地上,见缝插针种着各种植物。贴围墙根的是蔷薇和玫瑰,荆棘枝干交错缠绕了整面墙体,围墙拐角处是几株夹竹桃。为了遮挡夏季的太阳,住房的每扇窗户下都有一株葡萄,藤蔓顺着竹架弯弯曲曲爬上窗棂,再爬满整面房墙。在葡萄架和蔷薇花墙之间,种着些零碎花果:几树柑橘,一株无花果,一株石榴,还有一丛茉莉。每年初夏,蔷薇开疯了,满墙摇曳,然后翻山越岭垂到墙外,像给墙头搭上了一匹厚重的花毯子。蔷薇开之前是玫瑰,蔷薇开完之后就轮到葡萄。夹竹桃和无花果的花果期最长,从初夏开始,墙角就开出几朵白花,几天后花瓣转黄萎谢,新的花苞又次第绽放,能从6月一直默默开谢到10月。这个时候,秋风送爽,该石榴成熟了。院子谈不上什么园艺布局,植物之间也没什么呼应,只是各自按照自己的花期,寒来暑往次第开放、凋谢。

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
但如果从一个对植物颇有些研究的学者,比如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的眼光来看,这样的院子就不那么简单了,可以说是中国引入外国植物物种史在市井民间的缩影。劳费尔曾经盛赞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杰出的对植物物种的吸纳能力:“中国人是熟思、通达事理、心胸开豁的民族,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富戏剧性的自然景观,其变动范围从世上最高的山峰到最低的地表凹地——吐鲁番盆地,从南方的热带雨林至喜马拉雅高山上的冰河期地貌,这种跨度无他国能及。而且他们的位置处于东南亚丰富的珍稀植物与近东古代农业发源地之间,属于世界上借用模仿的最佳位置。”到今天,即便是一个普通的西南住家院落中,也遗留着这场历时千年的植物传输运动的蛛丝马迹。
比如石榴。原名安石榴,是伊朗至阿富汗一带非常流行的物种。古代波斯人不仅把它当水果食用,还把籽取出来开发出各种用途,以此经营很大的买卖。他们用石榴做酱油,先把它浸在水里,用布过滤,可使酱油有颜色和辣味。还把石榴汁煮滚用来在请客时染饭,为饭食添色增香。石榴传入中国时间很早,在北魏时期的洛阳都城就流传着一句话:白马甜榴,一实值牛。意思是白马寺的石榴,一个就抵得上一头牛的价值,可见其珍奇程度。千年以后,石榴已完全融入中国的农业生产体系,成为非常家常的水果。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水果集市
葡萄被认为是最早引入中国的物种。《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葡萄不喜多雨湿润的环境,因此刚传入中国时,仅在长安一带气候干燥的地区种植。但如今,葡萄已经能在多雨的西南普通院落中茂盛地生长起来。我记得家中院落中的葡萄有四个品种,能结出红、紫、绿、绿白四种不同颜色,不同口味的果实。不仅能吃果实,葡萄叶也有用处。它既柔软,又大小适中,而且没有异味,每到夏季,挑选出成熟度中等的葡萄叶,用清水洗净,刷一遍白酒消毒添香,然后裹上腌过的肉块,扔到焖饭的锅底,就能烤出喷香的肉块,是童年时最乐此不疲的厨事。后来在梅村著的《饮食界之植物志》看到,葡萄叶的用处还不止于此,它可以代替烟草,洗净煮熟后可以吃。还有一种葡萄叶,因为含有糖质,是儿童喜欢的食物。
无花果更是一种完全源自西域的舶来品。它在伊朗高原蔓延之广,不下于安石榴,但最初西域种植的无花果都是早熟品种,也叫新疆早黄,完全成熟后果皮呈黄色,有白色椭圆形果点,果顶不开裂,果肉淡黄色略呈淡红色。后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在他那个时代,中国南方已经普遍种植无花果,种植的方法是将树苗栽在地上。这一点特别引起了劳费尔的注意——“因为它说明中国人一直不知道用早熟法。他们的著作里就没有提过早熟法。”我家院子中那株无花果树,就是用中国南方的培育技术栽种出来的。无花果从初夏开始成熟,果皮由青转红,果体慢慢变软。到临近采摘的几天,日日都要去小心巡视几遍。没有熟透的无花果,中部果粒板结成一团,果汁呈白色,淡而无味。但熟起来非常快,硬邦邦的果实会在一夜间通体柔软,裂出淌着蜜黄色浓稠果汁的大口,采摘稍晚就会被蚂蚁昆虫捷足先登。能成功地摘到一枚全身紫红、光滑圆润、柔软丰盈、咧开大口淌着蜜汁却还没有被蚂蚁抢食的无花果,是童年夏天在院子里得到的最好馈赠。
茉莉是另一种被考证来自西域的植物。它又名悉耶茗花,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上如此记载:“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於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的《南越行纪》中也写道:“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茉莉花期也很长,从5月带花苞,能一直开到晚秋,于是整个夏天和秋天,都能带着茉莉穿成的手串,至今能记得白色小花貌不惊人,却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

葡萄

无花果
幼时记忆中四时更替的园圃之乐,映衬着中国人自汉唐以来在植物物种上兼容并蓄的历史。劳费尔曾写过一本《中国伊朗编》,详细考证了中国对国外植物的采纳和吸收过程,书中认为中国对国外植物的引进是一场历时1500多年的植物传输运动。“在植物经济方面,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他们的经济政策有远大眼光,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如果要回溯这场历时千年的植物拿来运动,就要从张骞出使西域的汉朝说起。
植物的引进
如果身为一个汉朝的农民,应该是相当有自豪感的,因为他代表着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水平。美国学者尤金·N.安德森曾比较过同一时期中国与欧洲的农业生产力:“根据封建时代的标准,汉朝农业产量高于中世纪的欧洲。欧洲每英亩500磅的产量就被视为高产,而且由于种植的谷物品种产出率低,收成中的1/3必须留做种子。中国人留种少得多,得到的回报却多得多。”安德森认为汉朝农业生产力领先的原因在于自秦帝国形成以来,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重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贯彻法家理念,将农业与食物生产置于重要地位,并视为增强国力的关键。在那场著名的大焚书中,明确赦免的类目唯有农业与医学。汉朝后,农业越发精耕细作,官家用各种手段劝课农桑,以养活日益增加的城市居民。帝国政府在田租、公共水利,及对小农阶级维护上的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在中国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绿色革命”。
西汉末期的重要农学著作《汜胜之书》记述了汉朝农耕的详尽过程,表明了当时农业是何等精耕细作。汉朝的农民会将种子浸泡在煮过的骨头、粪肥或者蚕屑制成的人造肥料里,这种肥料还要加入一些植物毒素。种子被反复覆以一层这类糊状物体,必须小心地将裹在薄薄表皮中的种子弄干,使它们不会腐烂——这些手段是西方人在现代科学实验室里才摸索出来的。政府主导修建的水利工程不仅使稻子得到灌溉,稻田得到平整,而且每年还通过变动水道来改变水流,使水温春天暖和,夏天不热。在缺水的北方,土壤会在夏季被反复弄碎,形成一层蓄水的覆盖土。冬天,农民会将雪被压实,以免被风刮走,用这样的方法冻死在冬天幸存的害虫卵。在一些潮湿的区域,每个过大的果实下都会垫以叶秸,使瓜不会因接触湿土而腐烂。任何含氮的作物都被小心存做肥料……
植物在汉朝的生活体系中如此丰富,不仅体现于食物,还有药物,在当时的《神农本草经》中,论述了大约365种药。“偏爱植物的成见在此书中有所显露:67种是动物药品,42种是矿物药品,246种是植物药品。”通过这些史料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轮廓,汉朝已是一个植物物种的盛世:有大量土地用于种植,有足够精细的耕作技术,有重视农业的政策。因此,当出使西域的使者或者远征大宛的将军,将新鲜物种带回国土时,这里已经具备接纳丰富外来物种的能力。
苜蓿被认为是最早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西域物种。它是汉朝帝国军事意图和国家安全的副产品。汉武帝时期一直在寻找善于作战的良马,听说伊朗高原上有纯种骏马,体格比蒙古种的小马魁梧,全身匀称,四足纤细,胸、颈、臀部都很发达,善于征战。于是常派遣使者到伊朗诸国遍寻好马,最多的时候一年中派遣求马使节十几次。最初找到的良马得自乌孙,后来张骞走到了大宛,发现这里的马种更为优良,因为马奔跑后流的汗是红色,因此被称为“汗血马”。汗血马所吃的饲料就是苜蓿。史书称张骞为人重实际,处理经济事务非常有见地。他断定这渴求已久的好马如果要在中国保持健壮,就要把它的主要食粮一并带回。于是他将大宛的苜蓿种子,带回国献给武帝。武帝命人在宫旁广阔地面遍植这新奇的植物。不久,这种饲草从宫中迅速地蔓延到了民间,遍布华北。
张骞是出使西域并生还归汉的第一人,也被认为是开启物种输入的第一人,因此成为引入物种传说的中心人物。大部分带“胡”字植物,都被认为是张骞周游绝域后带回来的物种。比如胡豆。《齐民要术》引《本草经》的说法:“张骞使外国,得胡豆。”还有胡麻,《太平御览》也引用《本草经》,认为是“张骞使外国得胡麻”。还有胡蒜、胡瓜、胡萝卜……一些近代的外国史学家已纷纷否定了这种说法。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专门撰文指出,张骞无法以一人之力完成那么宏大的物种传输运动。因为他出使西域时并不是以搜集物种为己任,而且途中险象环生,还被匈奴囚禁了一年,是乘隙逃走才得以生还,植物种子细小,在逃难过程中并不易保管。但就如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所说,舶来品最真实的活力和乐趣在于它来自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遥远地方,承载着人们对未知之地生动活泼的想象。张骞“凿空西域”的行为,本身就开启了人们对于外域的想象力。众多的驼队贸易商人沿着被打通的丝绸之路来到长安,新的物种因此接踵而至。
移植技术
743年,在西京长安以东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人工湖,实际上是一个海外贸易货物的转运潭。来自各地的贸易船只都聚集在这个转运潭里——来自北方的红毡鞍鞯、来自南方的红橘、来自西域的奇花异果……所有货物要在这里被换装到小斛底船上。大批外国商人也随货物而至,长安城的纳税人口将近200万人,居住在长安城中的外来居民数量也相当庞大。突厥、回鹘、吐火罗和粟特的商人们聚集此地,其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伊朗居民设置了一个叫“萨宝”的官职来监管他们。萨宝的意思是“商队首领”。
张骞之后开启的汉土与西域的相互贸易,在唐朝时达到一个高潮。纷至沓来的外国商队不但带来了很多新奇古怪的奢侈品,也促进了西域庭院植物的栽培。因为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异族人来说,“没有他们深深眷恋的故土植物,简直就无法生活下去。就如同前往美洲的欧洲移民也将他们故土的石竹、樱草、郁金香留在美洲一样”。但要让植物在气候、土壤条件完全不同的汉土存活生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早在304年,古人嵇含就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物种移植的种种难处:北方的大头菜引种到南方后会变成芥菜,因为没有冬季的地方不会生出肥大的块根。而南方的橘引种到北方后会变成低级的枳。柑橘被嫁接到较硬的三叶砧木上以后,在寒冷干旱的天气里,插入的树枝往往会变得虚弱或者死去。

唐代宫廷对药材的需求量很大,许多外来物种都声称具备药用价值
后赵武帝石虎在引种西域植物上取得了一些难得成功的范例。《邺中记》记载,石虎的私苑中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枣,亦三子一尺”,还有可以结出重达两斤巨果的句鼻桃,“子大如盂椀”的安石榴树……”这位羯族君王在历史上留下了残暴嗜杀的恶名,但同时也是一位功劳不小的西域植物推广者。他将许多来自于西域的植物、食物改名,起因虽在于对胡字的忌讳,但在客观上,却减轻了中原居民对这些外域植物的陌生感。
为了引种这些中原本无的植物,石虎花了极高的代价琢磨移植技术。他御使匠人精心围起苑囿,取名华林苑,运来土壤,引水浇灌,以期创造适宜西域果种的生长条件。《邺中记》记载:“华林苑在邺城东二里,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周围数十里,又筑长墙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又凿北城,引漳水于华林苑。虎于苑中种众果。”为了让这些物种能尽早同中原的水土相合,石虎还下令做了一辆大车作为培植这些作物的试验田。大车名为虾蟆车,“箱阔一丈,深一丈四,抟掘根面去一丈,合土载之,植之无不生”。在国君之力的强力推动下,自石赵之后,西域作物移植汉土的技术渐渐成熟,开始在中国北方普及。安石榴在河北地区开始有了优良品种,而在北魏时的洛阳,就有大面积的西王母枣与句鼻桃的种植。
到唐代后,从物种的传输到物种的分类管理和种植上,都形成了一个包含相当多细节的技术体系。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保证植物物种输入的安全运输,最常用的是用蜡将植物的根茎密封起来,再在上面覆盖几层绿色的蔬菜叶,这样就能避免颠簸摇晃,幼苗在几天之内也不会枯萎。植物在细致的保护下运送到长安后,一部分进入“药园师”掌管的药园——唐朝对草药的需求量非常大,药园是由太医署令管辖,专门负责种植、采集草药供太医署使用的庭院。但更多的物种会进入上林苑——这是一个皇家专门管理植物物种的机构,坐落在一座巨大的苗圃和庭院中,世界各地的各种庭院果木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汉土后,都将先汇集在此苑中。上林苑中不乏技艺高超的园丁,他们的职责是研究方法将这些外域植物安置成活,既供给皇室新鲜的珍奇水果,还要为唐朝各地营林植树提供树种来源。740年,唐玄宗曾发起过一场美化唐朝北方大都市的运动,要求在“两京以及城中苑内种果树”。果树的树种,就来自于上林苑。有些植物在苑中移植成功,并长久地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庞大植物谱系的一部分,也有的植物因为技术不成熟,只存在了很短的时期。这是让人遗憾的物种流失,比如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
据说这金桃是将桃树的枝条嫁接在柿子树上长成的,大如鹅卵,其色如金。7世纪时,撒马尔罕的王国曾经两次向唐朝宫廷贡献这种珍异灿黄的桃子作为贡品,专供皇室成员享用。金桃的树种也被长途跋涉穿越西域荒滩戈壁的使臣商队带入唐朝境内,并且移植进了长安的宫廷果园。但或许因为移植技术不成熟,金桃并没有在汉土流传下来,但后世的人们用想象力来弥补了移植技术上的缺憾。美国学者谢弗在写作唐代中国的外来文明时,将撒马尔罕的金桃作为书名:“金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这种水果的滋味到底如何,我们现在已无从推测。种种奇妙的传说,使这种水果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从而也就成了唐朝人民所渴求的所有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
植物的繁荣
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曾说过: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如果从植物传播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唐代皇家林苑中的植物物种,就像最新的审美和消费时尚一样,经年累月后会慢慢传递到民间。晚唐时期,在一些文人墨客的私苑中,已经能看到源自西域的物种。白居易就被传为是白莲的民间推广者。9世纪以前,洛阳还没有白莲,直到白居易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时,才将白莲从苏州移植到了洛阳。白居易在一首诗中描绘了自己在洛阳履道坊私宅中的园池景色,就专门提到了白莲:“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杆……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我所好,尽在吾前。”
在唐代,莲花还保持着外国的风韵,以红色和白色为主,黄莲非常少见,而青色的莲花被认为只有在近于巫术的艺术作品中才能看到。唐代药物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写道:“红莲花,白莲花生西国,胡人将来也。”这说明原本从西域传来时,自然界并没有青莲。但在民间园丁们的奇思妙想下,唐宋时期已经能通过人力配置出青莲。有一部宋初的类书中转引了一个湖州的染户家的故事:湖州有一户染户的池塘里种有莲花。刺史命收莲子归京,种于池沼,发现开出来的是莲花是红色的。这在当时非常罕见,刺史便写信问染工怎么回事。染工说:我家有口世代用于染布的靛瓮,把莲子浸于瓮底,大概一年后,再种植,就能开出红色的莲花。如果在花根部附近的土壤里埋下旧铁钉、金属罐,向花的根部输送铁盐,就能使绣球花变成青色。
物种繁荣与民间智慧相互激发,成就了一些颇受欢迎的著名园丁,郭橐驼就是留名后世的一位。他是一位驼背园丁,家在长安城西边的丰乐乡,以种树为业,擅长移植。经他手种的树都长得高大茂盛,挂果早且数量多。于是长安城中的富豪人家、从事园林游览和做水果买卖的人,都争相聘请他。柳宗元写过一篇《种树郭橐驼传》,里面谈到郭橐驼种植的秘诀讲究“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后来元朝的一本种树书还托名于他。
展示新奇漂亮的植物物种成为长安城中的一种时尚。拥有罕见物种的多少,以及通过技术革新将新植物栽种成活的成果,成为当时长安城中富家豪门“炫富”的方式。史书记载,杨国忠家的年轻人在园林艺术的革新上颇为擅长,他们建造了一种可以移动的木制花园,叫作移春槛——将花园安置在木轮上,园中种植了名花异木。每逢春和景明,就推出这种可以移动的花车上街,车子一边前行,一边还可以缓慢地旋转,使街边路人都可以详细地看到车上的奇花异草。
但真正的物种繁荣还是来自更底层的民间。石虎这些来自异域的君王,对后世植物经济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技术创新和物种引进。他们在统治时引入了中亚土地共有的观念,将其与中国古代均分土地的惯例相调和。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制造出了广大的自耕农小农阶级,他们在小块土地上辛勤地耕作,尽其所能地将最实用的物种栽种进自己的庭院中。陶渊明就是这样一名小自耕农。他弃官归隐后,在魏朝统治的华中务农度过了余生。虽然生活并不宽裕,收支仅能勉强相抵,但他在田地间创造并书写了自己的生活美学。陶渊明的诗歌写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园圃之乐》,也可作为当时魏朝小自耕农田庄的全景图。
陶渊明的田庄分为田地、果园和菜园,种植的作物有粟,可能还有小麦、大豆、桃梅、桑、麻、葵,以及一些别的蔬菜。他还栽培了自己喜爱的松和菊,还有梨、柳、竹子等别的植物。在陶渊明留下的诗作中,我们还不能看到多少西域的物种,但一个拥有小块自己土地的农夫,可以在方寸之地上按自己的意愿种植,是物种流传非常重要的条件。隋唐时代延续了北魏的土地均分政策。在尤金·N.安德森的考证里,当时一位普通的男性户主受露田80亩,一生均可耕种,年满60岁时还给国家。同时还受永业田20.3亩,可以终身拥有并传给后代。在配给的份额中,20亩应种植桑麻,余下的1/3则为宅基和菜田。“虽然面积不大,只是一些小的农庄,但已经比大多数亚洲农民的处境要好。而且中国人植桑非常紧凑,很会利用土地,外观上行修建得像丛林一样,因此几英亩的土地已经可以颇有作为。”尤金·N.安德森曾这样写道。
到唐代时,植物移植技术的成熟,以及多年土地均分造就的小农阶级,促成了植物物种的大繁荣。近东的农作物菠菜、甜菜、莴笋、扁桃、无花果开始广为人知。来自南亚的农作物,海枣、小豆蔻、山扁豆等植物也开始广泛传播。阔叶的甘蓝、类似莴苣的苦菜,以及带香味的胡芹,这些有实用价值的草木,大多被文人墨客忽略,也不太可能出现在达官显贵的私邸花园中,但却在民间自耕农们的土地上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生命和传承。
大众的物种
劳费尔认为中国的物种输入是一个延续1500多年的过程。陆陆续续进入汉土的各类植物,开启了人们对化外之地的好奇,丰富了宫廷和民间的世俗生活,但直到宋朝,才出现了真正能称得上革命性物种的输入。
宋朝是一个艰难的王朝。北方胡族入侵,导致南北国土分裂,战乱不断。坏天气与帝国遭受的磨难相辅相成。在北宋末年与南宋末年之间,气候变得寒冷干燥,偏偏此时中国还迎来一个人口攀升期。人口在北宋期间超过1亿,南宋和金朝的总人口超过1.1亿。在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北方国土丧失的情况下,用农耕充实仓廪成为朝政大事。不管是军粮征集还是平民生计,政府在农桑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一场新的农业革命应运而生,它被一些外国学者描述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新的知识和工具进一步改良创新,农业知识得到进一步的改良;新的材料,粪肥,以及河泥、石灰等肥料的推广,使农民学会了有效地保持地力;水利技术日臻完善,使空前复杂的灌溉网络得以建成。但更重要的是,一些高产、耐旱的早熟粮食品种被引入。这些革命性的物种不再只是满足小农自给自足的园圃之乐,或者达官贵人炫耀的奇花异草,而是对国计民生都影响颇大的粮食物种,其中最出名和意义最大的是来自安南占城的生长季短的稻子。和唐代贸易主要经由西北的沙漠绿洲不同,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在海上。宋朝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水上社会,它的国道是长江,它的国门是中国海。占城稻就是经由海上到达的。
中国是个吃米的民族,因此在寻求国外物种时,稻米是一种天然能引起中国人好奇心的品种。张骞出使西域时,曾细心记录下了在大宛、安息和条支种植大米的情况。在他的亲身经历和听闻传说里,库车、疏勒、和关,和葱岭以北的漕国,还有石国等地都产米甚丰。但这些地方的大米并没有进入中国,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稻米种类非常丰富的国家。据史书记载,光是旱稻就有6种,晚稻有10种,早熟的、晚熟的,耐旱的、耐涝的,有黏性的、偏硬朗的……种类繁多。占城稻能在如此庞大的中国稻米体系里占得一席之地,主要因为它顺应了宋朝天时。占城稻有“百日黄”之称,甚至有的地方可以两个多月就成熟,被称为“六十占”。对当时正遭受干旱侵袭的北方来说,占城稻“高仰处皆宜种植,谓之旱占”。种植上也不因远道而来就需要特殊待遇,“其耕,锄薅、拔,一如前法”,和通常粒小性硬的高产稻相比,占婆稻的口感相对更好,“米粒大而且甘,为旱稻种甚佳”。

清 《 耕织图》之《收割》
宋真宗赵恒是占城稻最大力的推手。佛教作者釋文瑩在《湘山野錄》卷中记录了《真宗求占城稻种》:“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菉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占城稻种到中国后,真宗先是在皇家农苑中尝试种植,然后命令转运司将稻种与种植方式写成榜文,在山地多的地区推广种植。1011年被朝廷分发推广后,到1012年占城稻已经广泛传播。因为它的高产量和易耕种,在“物以稀为贵”的市场上并不如那些低产量的品种那样受到尊重,但却在灾荒年间,为万千穷人提供了得以果腹的食粮。
棉花是宋朝的另一个重要大众物种。实际上早在公元3世纪时,棉花就通过西域和印度两条不同的道路传入中国,中唐时由高昌人种植棉花,然后纺织而成的棉布非常知名,但当时仅是一种新奇之物,就像一只来自西里伯斯的白鹦,一条拂林国的小狗那样,是高官显贵间流传的奢侈品,并不为民间大众所享用。宋朝时对棉花的利用有了革命性创新。擅长拿来主义的中国人,结合中国历史悠久的丝绸衣服缝制技术,将棉花填入衣服中。棉花杰出的吸存热气的功能,对农耕国度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尤其在民生艰难的年间,棉花在缝纫方式上的突破,使在田间劳作的大众得到保暖,使冬季劳动无与伦比地扩大。这些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确立了棉花在中国这个农耕国度重要农作物的地位。
香料与味道
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沿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时,对这个东方帝国富足的物产感到震惊。他看到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杭州有“十个大市场”和“大批其他市场”。十个大市场都每周开市三天,吸引了“四万到五万人”。在这些市场上可以买到小种牡鹿、大赤鹿、黄鹿、野兔、家兔、鹧鸪、鹌鹑,以及多得不可胜数的鸭、鹅等普通家禽,还有“应有尽有的蔬菜和水果”,甘蓝、大葱、大蒜、菠菜、芜菁、胡萝卜、黄瓜和葫芦、茄子、水芹……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形体巨大的水果,最大的梨“每个有10磅重”。当马可·波罗看到这些物质极大丰富的市场时,外国植物物种输入已进行了上千年,绝大部分流传到现代的物种已经进入中国,并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与中国人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餐桌紧密联系在一起。
唐朝行僧义净在求法印度时,很细致地观察了南亚的食物,并将它们与唐朝的饮食进行了比较。他在书中写道:“东夏时人,鱼菜多并生食,此乃西国咸悉不餐。凡是菜茹,皆经烂煮,如阿魏,酥油及诸香合,然后方啖。”通过这段记述,我们大致可以推知,唐朝早期的饮食与现代日本颇为相似,以清淡的食物为主,有不少生食,只是在饮食中添加了少量的佐料或者酱油。另一位考证中国食物史的学者尤金·N.安德森也认为,中国烹饪丰盛香醇的特点,是在宋代才开始确立的。“食物被辅以当地佐料,特别是生姜、肉桂和胡椒、肉豆蔻,也被辅以各种印度与近东的香料果实及种子。糖已用来保存食物,并制作种种甜食与糖果。”这些来自西域的重要佐料,在商人和地方精英的宴席上得到创造性运用,大大丰富了中国世俗生活的味道。
胡椒是最为著名的异域香料。马可·波罗曾记录过元朝时中国人对胡椒的巨大需求量:“只要把一船胡椒运往亚历山大或别的什么地方以供应基督教世界,就有一百船胡椒运抵中国的一个主要港口泉州。”它不仅是深受中国人喜爱的佐料,还是财富的象征。777年,唐朝宰相元载被贬赐而死,在抄家时发现,元载家中有800石胡椒——这既被作为元载骄奢贪赃、聚敛财富的明证,也从一个侧面窥知当时人对胡椒的喜爱。除了胡椒之外,肉豆蔻也是一种被吸纳进中国烹饪体系的香料。这是一种像杏一样球根状的橘黄色果实,收获时用长杆将果实打落枝头,在太阳下晒干后,肉豆蔻皮与仁剥离,颜色由深红变为棕红,炖肉时加入一点,会给食物增加带咸味的辛香。

印度果阿的集市贩卖咖喱等各种香料
甘蔗的输入则为中国人的食谱增加了一种新鲜的甜味。甘蔗大约在公元5世纪时就从东南亚传到了波斯,再经由伊朗进入中国。唐代时,四川中部、湖北北部以及浙江沿海地区都有甘蔗种植。但当时在北方仍然不常见,唐太宗曾经将20根甘蔗赏赐给他的一位大臣,可见这个物种的珍贵。在甘蔗输入之前,中国人已经从蜂蜜和谷物产生的饴糖中得到了甜味,但蔗糖才是所有植物糖中最受欢迎的。它最早被称为“石蜜”,制作方法是在日光下将甘蔗汁晒干制成糖,然后再将糖加工成石蜜。在8世纪时,安国和火寻国都曾经向唐朝贡献过石蜜,康国也出产石蜜。因为西域的石蜜质地优良,唐太宗曾经派遣使臣去摩揭陀国学习当地的制糖秘籍。他们的制作方法不仅是依靠天然的植物,还依靠更多的配料,比如与牛乳、米粉和煎成块。最受后世欢迎的制糖法是将甘蔗汁提纯后,结晶成纯洁雪白的颗粒状,不易变质,适合储藏。这种蔗糖结晶的技术,在唐代时还是秘术,到宋朝时已经被普遍利用于甜食的制作。马可·波罗在杭州的市场上就看到新鲜水果被晒干,用白砂糖腌渍后,做成各式各样的蜜饯出售。
在研究中国食物的学者尤金·N.安德森的眼里,宋朝是一个美食频出的朝代,菜肴种类根本难以胜数。光一次宴会就可能上200多道菜,从许多不同的米制食品到“基于水果和甜食的菜肴”,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每一种汤、馅饼、汤团、面条和小吃,在宋朝几乎都能找到接近于现代的形式。历时1000多年的外国植物物种传输已完成最重要的部分渐进尾声,而中国的农业和食物烹饪体系在此时也基本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