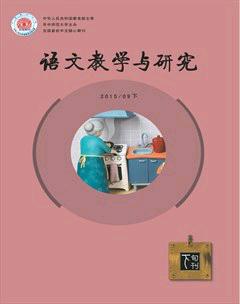咀嚼光阴
刘荒田
牙医助手让我坐在皮椅子上,调到近似躺的角度,正好对着窗外后院——又一次,真巧——退休三年来,回到旧金山居住的日子大体近似,办类似的事情,不能不多次兴起“似曾相识”的感叹。以眼前论,后院的阳光和水洗似的蓝天是跟从前一样的,偎依栅栏的扶桑花一样慵懒,枞树下的马蹄莲一样高傲,老成的日本枫和去年一般高。花圃之间,碎石颗颗洁净如洗,没有落叶,教你忽然想及,“花径不曾缘客扫”的古典意蕴,被按钟点拿薪水的勤快园丁扫进垃圾桶。
牙医诊所的接待室,一年年下来,小圆桌上一样放着《体育》和《人物》。躺下不一会儿,杨牙医进来和我握手,我恭维他“一样英俊”。他担任我家牙医超过15年。打交道的都是熟人,这乃是“老”的部分含义。每年替我们报税的会计师,是25年不变的黄先生。从家门走出,遇见夫妻联袂散步的余先生和余太太(他们的独子26年前因忧郁症从金门桥跳下自杀)。总在来来回回地赶路,十分任重道远似的——那是邻居戈尔曼先生,他每晚要去八十高龄依然开“科韦德”跑车的女朋友家过夜。天天去买报纸的杂货店里,收款员是同乡,她是唯一关注我们老两口行踪的“好事者”……
杨牙医开始洗牙,去年这活计是助手包的,今天师父出马,给老客户以较高的礼遇。这位坚持做“手工活”的大夫,努力清洗齿上的黑垢。电动刮子、手动小钩、小夹子、喷水器,工具不时变换,在口腔里鼓搅。我只负责把嘴巴张成大窟窿。
躺在皮椅上,我信马由缰放牧思想。时间的流速,何以如此缓慢?众多参照物,几乎都一如从前,一如从船上望开去,景物没有推移,因而造成“不动”的错觉。这缓慢,不同于因病痛和失眠之类而生的“度日如年”,也有别于由严冬、梅雨一类倒霉天气所催化的“永昼”,而是命运之神最慈悲的眷顾:让人在最好的风景中停留得长久一些,促使你运用从来没有如此细腻和敏锐过的感官,去感受生活的好意。
牙医在用钩子突破牙龈,清理根部的积垢。对了,日子的慢,若就近取譬,就是细嚼,把进入口腔的食物和饮料,一一品咂,无一遗漏地捕捉其品质,发掘佳处。过去,饱肚是唯一宗旨,狼吞虎咽,多少美食汹涌而下,不留痕迹。那时,有许多“以后”,如今,只剩眼前。
电动工具都关掉了,牙医和助手在更新我的牙齿档案。尽管在老子有关“牙齿和石头谁生存更久”的驳难之中,牙作为“坚硬”的象征,被“柔软”击败,可长久来看,牙齿不但比舌头韧长,而且赢了生命本身。人死之后,即使只齿无存,舌肌尽腐,白森森的牙床不是依然附在头骨上?牙齿所咬嚼的,是食物,更是光阴。从口腔进入,从肛门排出,岂止大跃进年代的野菜,知青时代的番薯,移民年代的牛排,更是甜酸苦辣,悲欢离合,喜剧悲剧,全部人生。
到了晚年,如果你还有能咬嚼的原生牙齿(假牙也凑合,费些功夫就是了),那么,尽可放慢节奏,品尝从前来不及细品的真味。过去的忙迫,是因为欲望的鞭子在催;如今,荷尔蒙的波涛平复了,对金钱和权势的渴望远去了,你终于拿到进入佳境的门票——平静的心情。
“或是在寂静的树林中缓步沉思/想着那些配称为聪明、善良的人和事”,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所道,就是晚年的静观之态。“配称为聪明、善良的人与事”,便是岁月的静水流深。林中盘桓,看日影随着搬家的蚂蚁缓移。和可爱的外孙女,坐在草地上,抚摸落叶的脉络。一碗加上蓝莓的麦片粥,吃掉半个早上。三页纪伯伦的诗集,对付没有蝉声的下午。以咖啡调友情,以铁观音泡亲情。此生终于有这么一段,摒除欲望加诸身上的短视和偏见,力求透彻地体验生命。
“好了!”杨牙医递来一面镜子。镜中的牙齿,白得耀眼,我满意地道谢。走出诊所,依然是蓝天丽日。
(选自《今晚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