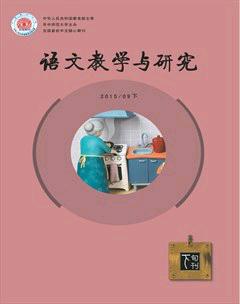老屋里谁人写下光阴的故事
一切老屋里都有光阴的故事。它们的建而复葺,它们的倾而再起,无不属于人事的兴废、生命的往而来复。每一扇窗子都曾照见生命的张望与悸动;每一块饱经风雨的砖瓦都沉积着生命的眼泪与欢颜;树木无言,却记得无量生死;花草谢而复开、枯而返荣,仿佛映射无量的人世喜乐与疼痛。
一切老屋是相同的却又各具个性,相同源于其间生命的哭笑走死,个性依旧源于其间生命的哭笑走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间老屋,只有少数人可以听到老屋等待的呼告,从而打捞起流逝的光阴,用文字固化板结为不朽的故事,从而一如代谢的四季以叶落花放水瘦山青的重复情节暗示天道的永恒,这些故事以老屋的形象变幻一样显影了生命的奥秘。
自然,这少数人就是归有光这样的人。他们有着非凡的特质,他们以此注定被拣选,要去以自身的生命打捞并且传播老屋里深埋的生命的普遍道理。
归有光们是沉静的。他们喜爱光照与美好,他们因此敏感于破败与朽烂、裂痕与创颓。也许出于本能,也许出于久经人世后的顿悟,他们总能深知,破败与朽烂、裂痕与创颓,一如光明与鲜艳,都是天道的印记,不可扭转,但却可以促进迁化,生命的尊严与不可抹杀就在于人可以在破败与朽烂、裂痕与创颓里呼唤引发且护持那光明与美好。于是,老屋的破而得葺并非普通的人世动态,而是生命在不可逆转的命运里努力于向善逐美。因而,“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并非一般的文人士大夫情趣,盖因此地风月不可雅玩,只可感受,人在与世界的交融合一里得以无限扩大,沉静的生命得以雷音滚滚,细节的生命上升为普遍的生命,片刻的美好弥散为永恒,普遍的人类悲哀贯通个体的有限人生。
于是,归有光们总在极乐时兴起悲哀。谁不曾乐极生悲呢?这是人生的注定,但归有光们并非被动地承受而是主动地感受兴发。为什么?盖因他们不同于一般人,他们深知他们活在人群中活在历史里,他们是社会与历史的存在,他人的悲欢、历史的流变总与自己相关,所有人世的流变迁转兴废离合无不最终显形为小小个体生命的悲乐哀喜。因而,“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以及“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这样的记述,并非只是百年老屋的阵发性疼痛与创伤,也不只是百年家族的礼乐毁弃分崩离析,更是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沉痛接受。人总是无由地生,无由地死,人的一生,细数每一哀乐,检点每一细节,无不生死交缠,合离相逐,这是现象,却因其不朽的轮回、普遍的平等,成为生命不易的道理。那么,人能做的还有什么呢?是的,是主动地感受与兴发,而非懵懂无知地被动承受,个体情怀于是在主动中把握了生命的永恒脉动,那些主体介入的乐极生悲便有无量的个体尊严华光灿烂。是的,他们不能把握生,不能拒绝死,不能回避生命里的离合际遇,不能反抗家国盛极而衰的铁律,但他们却可借助生命的哀苦喜乐确证自身并非全然随波逐流,他们在匆匆如寄的生命旅程里至少可以把握他们在给定风景里的眼泪与笑容。他们感受,因而他们存在。
于是,归有光们总是深情的。因为深情,他们拒绝了时间的线性铁律,他们不以时间的流水本性计算生命,而以光阴的触动式记忆突破死亡与毁弃的封锁,在细节的累积搜索中获得无尽的片刻永恒。是以,老妪虽死,老妪的眷恋不死;母亲虽死,母亲的关爱不死;祖母虽死,祖母的期待不死;妻子虽死,妻子的影像不死……老屋如同尘封的胶卷,将所有这些生命的羁痕深埋于岁月的瓦缝风化的砖墙,而深情却如同生命的考古,以温热的情怀融化时间的封印,使他们得以在光照下显现复生。如此深情,自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他们在流变不息的时间里发现了凝固的光阴,他们在湮灭无着的生命里提取了无尽的细节,于是,存在得以永久性地敞开,在文字的间隙流传。
所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这不是物是人非的无奈感叹,分明是个体记忆经由万斛深情的书写突破死亡而昭示生命尊严的枝繁叶茂。
是以,老屋里,谁曾写下光阴的故事,谁就不死。
梁卫星,作家,代表作有《成人之美兮》等。endprint
——归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