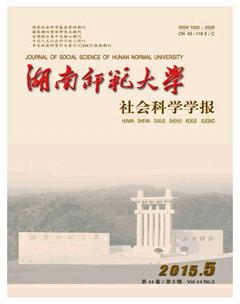论林白水新闻伦理思想及其道德缺失
摘 要:林白水是晚清和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中国白话报的先驱。他在20余年的办报生涯中,发表了许多阐述新闻伦理思想的论文,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他认为,记者办报应有正确的动机;要具备“说人话、不说鬼话”的专业主义品格;要有敢于斗争的硬骨头精神。他的这些观点及其道德实践体现了军阀统治时期新闻记者特有的精神个性。但是,林白水在新闻活动中也有道德缺失的一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收受津贴、公开利用报纸卖文和常常侮辱谩骂他人。他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行为,为我们了解和认识当时记者的生存状态与伦理选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关键词:林白水;新闻伦理思想;道德缺失
作者简介:徐新平,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
林白水(1874~1926)是晚清和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中国白话报的先驱。从1901年到1926年的20余年中,他先后创办了《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公言报》《新社会报》(后改名为《社会日报》)等近10家报纸。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他曾先后担任过福建军政府法制局局长、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督军府秘书长、众议院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务。1916年8月1日辞去议员之职,全力投入他熟悉和热爱的新闻事业,长期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言辞辛辣的政论文章,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多次入狱,也不为权势所屈服。1926年8月5日,因在《社会日报》上刊登了《官僚之运气》,揭露潘复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事实,当晚被捕,次日清晨被杀害于天桥,终年52岁。他是继邵飘萍之后,又一位因敢于同封建军阀斗争而牺牲的著名记者。1986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林白水在长期的新闻活动中,发表了许多阐述新闻伦理思想的论文,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但在新闻道德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将对他的新闻伦理思想和新闻道德实践进行粗略的评析。
一、为百姓办报和为革命宣传的办报动机
林白水的办报活动起始于1901年6月。这一年,杭州名士项藻馨创办《杭州白话报》,邀请林白水主持笔政,林白水欣然答应,并亲自撰写了发刊词和创刊启示。他在《杭州白话报》创刊的启事里说:“这个报纸是属于普通一般老百姓的,因为我是一个平民,所以我说的话,是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不是一般士大夫阶级的咬文嚼字或八股式的文章,……我只是把国内国外发生的大事小事,报告给一般老百姓,同时把我自己对这些事的意见,表达出来……”{1}。他把自己定位为“平民”,把《杭州白话报》定位为“普通老百姓”看的报纸,目的是为了“广开民智”,服务的方式是用白话文办报。他说:“我和朋友们商量想开报馆,又怕那文绉绉的笔墨,人家不大耐烦看。并且孔夫子也说道,动到笔墨的事情,只要明明白白,大家都看得懂就是。”{2}这些朴素的话语,反映了他代民立言、为百姓办报的思想。
1903年12月,林白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白话报》,以“白话道人”的笔名撰写文章,发表了大量排满革命的言论。林白水曾经回忆说,他在晚清时期主持的两份白话报刊是他记者生涯的骄傲。他说:“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语体的报纸来做革命的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3}在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办白话报的当然不是林白水,1897~1898年,维新派报人就创办了《俗话报》、《演义白话报》、《蒙学报》、《无锡白话报》等宣传改良的报刊,但林白水说他是用白话文的报纸来做革命宣传的是第一人,还是比较客观的。
我们选几篇文章看林白水在新闻实践中是如何为普通百姓办报和宣传革命的。
在《中国白话报》中,他分别撰写了《做百姓的身份》、《做百姓的责任》、《做百姓的事业》、《做百姓的思想及精神》。这是他为开民智而撰写的系列文章。他告诉读者:“做人顶要紧的是自己不要看自己太轻,若把自己看太轻了,再到后来便一些儿体面都没有。”{4}做百姓的身份,最重要的一是伶俐,二是在行。所谓在行,就是要知道,“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可是办起事来不能够没有钱,所以纳税完粮是我们百姓应该承担的责任。不过我们出了钱,到底后来那笔钱做什么用账?到底还剩多少,还差多少,用的正经不正经,有人侵吞去没有,我们百姓照理应该去查一查。”{5}
纳税人的义务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时至今日还没有完全解决好。林白水在1903年就启导民众不能只知道纳税完粮的义务,也要知道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其思想的先进自不待言。他提醒民众:“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享得各种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话对读者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在《做百姓的思想及精神》一文中,他教导百姓要树立“国家的思想”、“尚武的精神”和“冒险的精神”,并以此来维护国家民族及个人的尊严。
林白水不仅从正面积极提倡百姓应有的品性,而且从反面告诫民众,要禁止裹脚、迷信、赌博、嫖娼、懒惰、吸食鸦片等恶习。如在《告当兵的兄弟们》、《再告当兵的兄弟们》等文章里,对当时士兵中存在的讹诈、打架、吸食鸦片、吊膀子等现象进行批评,告诫他们要读书识字、要看报,要肩负起保护国家的责任。在《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他自信地说:“倘使这报馆一直开下去,不上三年包管各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6}林白水在办报动机上,抱着开启民智的愿望与目的,从内容到语言都尽量适应普通百姓的需要。为了让老百姓能看得懂或者听得懂,他有意将新闻和评论写得十分的口语化,就连标题也特别讲究通俗有趣。如“养蚕发大财”、“小孩子的教育”、“论开风气的法子”、“好帮侣不怕人欺负”,等等。
林白水主办的《中国白话报》还有一个重要的传播内容就是宣传排满革命。如1903年7月,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提倡用黄帝纪年取代光绪纪年和耶稣纪元。宋教仁也主张以黄帝即位之年为纪元,为汉族开国的一大纪念。资产阶级革命派把黄帝作为汉族的祖先,突出“黄帝”,认同“汉族”的目的是为了“排满”。革命派主张,“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力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7}1904年慈禧太后70寿辰的时候,清廷大肆筹办庆典活动,林白水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有何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这副对联在蔡元培主持的《警钟日报》上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争相转载,令人拍案叫绝。林白水说,他平时发表的意见观点并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民意的代表。他说:“吾国主权在于人民,而代表人民之意见则在舆论。今报纸林立,即京师一隅已达数十家,可谓盛矣。然其中不作响言,不狃私见、能力持正大之主张以号召当世者,殆几绝矣。”{8}正因为许多报纸不能或不敢代表老百姓说话,因此,林白水表示,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报界的这种风气。在林白水看来,报纸和报人本就肩负着反映民意、代表民意的职责,这也是新闻伦理的内在要求。
二、提倡“说人话、说真话”的专业主义品格
辛亥革命之后,林白水在袁世凯政府做过几年议员之类的官,后又加入杨度、刘师培、严复、李燮和等人发起的“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袁世凯死后,他幡然醒悟,毅然脱离官场,于1916年创办《公言报》,开始以“白水”的笔名发表文章。他在《公言报》创刊词中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9}这是他新闻伦理思想中最有影响的话语,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许。
从新闻专业角度说,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就是“说真话”,其他所有道德都在“说真话”的前提下才能成立,才有价值。这如同军人要以“不怕死”、医生要以“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为前提一样。一个“说假话”“说鬼话”的记者,如同一个怕死的军人一样,还有什么资格谈道德呢?林白水提出的“说人话,说真话”的观点,比过去所有人的提法都来得通俗易懂。
林白水认为,说真话首先体现在“奋其笔舌为正义战”上{10},“于政府之过失,每不惮据事直书,窃以为记者天职固应尔尔”{11}。在这方面,林白水表现得最为出色。有人评价说,林白水的文章,最突出的特点是敢于直言,能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
1921年3月,林白水和胡政之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报》。《新社会报》以改造报业风气,革新社会为目标,“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于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12},屡次捅及当权者的痛处。1922年,因披露吴佩孚搬用飞机炸弹和盐余公债的黑幕,被勒令停刊。两个月后,《社会日报》面世,林白水发表论说:“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13}他在报上发表的一篇篇时评如同一根根芒刺扎在军阀的背上。曹锟贿选总统期间,林白水揭穿了他给每个议员每月津贴600元,每张选票5 000元大洋等内幕,结果报馆被封,林白水也被囚禁了3个多月,直至曹锟坐稳了大总统的宝座,才被放出。
林白水在《公言报》上,曾揭露了不少官僚黑幕。他发表的时评《青山漫漫七闽路》,将财政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许世英贪赃舞弊案公之于众,舆论界一片哗然。1923年5月,又有政客在津浦租车案中舞弊,他在时评《罪恶滔天》、《时局无望已极》等文章中,独家揭露,再次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结果,这些政客或被革职入狱,或畏罪辞职。1925年12月24日,他在《社会日报》回忆道:“《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阁员,举发二脏案,一时有刽子手之称,可谓甚矣!”{14}
林白水不是不知道得罪权贵的危险,但为了尽到记者说人话、说真话的职责,他认为,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高官权贵,只要是他们做了坏事,就应该进行揭露、抨击。1926年5月12日,他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斫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15}6月5号,他发表时评《欢迎吴张者注意》,批评炙手可热的军阀,以及嗜利、逐臭的趋炎附势之徒。在林白水看来,“讲真话”就不要怕得罪人,做到“事前事后,无所悔惧”{16}。
其次,说真话要有利于国家利益,在对外事的宣传上,要“慎乃出话,谨尔话言”。1917年2月14日,林白水在《公言报》发表了《同业其注意》的文章。他告诫新闻同行,“国家将有大事,其事为对外之事,吾辈为新闻记者,欲仗此寸管以求力副其国民应尽之职责,则事无他长,惟有‘慎乃出话,谨尔话言八字而已。”{17}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4个年头,中国是中立国。德国以武力相威胁,通牒各中立国,禁止与协约国通商。中国对此提出了抗议,并设法沟通与其他协约国和中立国之间的关系。有些报纸“贸然登载无稽之新闻,曰某督军长电反对矣,某要人亦有不赞成此举之表示矣。”林白水认为这是报纸极不负责的行为,一是消息不一定准确,某领袖某要人也许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二是即使说过,也许是陈述一己之见供上级参考。报纸贸然刊载,会给国家的外交带来麻烦。因此,林白水劝告同业者说:
往常报纸造谣或挑拨或攻击,吾胥无责焉。以其自家人闹自家事,无论至何程度均无妨也。今兹则对外发生重大关系矣,而所对之外不只一国,将无数国焉,成败存亡生死荣辱视于此举。吾望吾同业稍稍留意,及之报馆口头所谓“有闻必录”此四字特限,于此事不能适用也{18}。
林白水的意思是,在对外传播中,“说真话”应有更高的要求。不仅事实要准确,还要考虑国家大局的需要。新闻界流行的所谓“有闻必录”的口头禅是绝对不适合对外宣传的。由此我们也发现,对“有闻必录”这个与新闻真实相背离的新闻观念,林白水已对它提出了怀疑与批评,但这一观念的消极影响在当时新闻界还有一定的市场。
再次,新闻记者不要做谣言的传播者。1924年8月中旬,因为公债陡跌,北京的报纸便刊登了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新闻,什么多少人会破产,金融界会受影响,商业不免凋敝,物价不免暴涨,平民的生机更加逼迫等,给民众带来了不必要的恐慌。林白水认为,造谣的有两部分,一种是外国别有用心的人,想借此激起风潮;一种是中国的投机家,想从中牟利。林白水指出,这些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责任在新闻记者身上。他说:
不幸开报馆的不能辨别真伪,不肯慎重记载,见着新闻就登,拿着通讯社的烂稿就抄。因此,愈传播愈广。要是新闻记者有点责任心,具些眼力,能够指斥他们,不受他们利用。那些谣言哪有什么效用呢?所以谣言的传布不传布,全是新闻记者的责任。我们奉劝同业,要是缺乏材料,宁可拿不相干的旧闻来充塞篇幅,不可因为新闻夺目,能博阅者注意,就随便乱登。在你们以为大家登载,不在乎我们一家。不知大家都抱着慎重的态度、冷静的头脑来选择材料。这些谣言就不容易传布了。谣言不容易传布,社会就少受他的恶劣影响。这就是新闻记者无形的功德啊{19}。
这一段话深刻地阐明了记者应如何对待谣言的问题。谣言如果没有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的传布,其影响是相当有限的。而记者要做到不成为谣言传播的帮凶,就要“抱着慎重的态度、冷静的头脑来选择材料”。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情况下,宁可不登,也不能助纣为虐。如何对待和处理谣言,往往能考验和衡量出记者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和社会责任心的高低。林白水的观点对于记者防止传播谣言、维护新闻真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记者要有敢于斗争的硬骨头精神
1919年3月22日,林白水在《平和日刊》发表的《答客问》中说:“夫报纸为舆论之代表,而非一党一系之机关,此吾所知者也。惟操笔为文者,既须有独立不羁之精神,尤须有鉴空衡平之器识。”同时他向读者承诺:“记者不敏,甚愿执此三寸之笔,不烂之舌,而与彼文武名角相周旋,而无所于慑。”{20}林白水在数十年的记者生涯中,都在实践着他提出的独立不羁、不畏豪强的伦理精神。
1922年2月10日,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报》因抨击反动军阀的丑行,被北京警察厅勒令停刊,林白水也因此入狱。出狱后,他于1922年5月1日将《新社会报》改名为《社会日报》再行出刊。林白水在复刊词中说:“等到我这《社会日报》重行出世的时候,刚刚碰着炮火连天,两边十万人马在大杀特杀的当口。所以我自己闻着,觉得我这张《社会日报》出世伊始就带着一点硝磺气味及血腥。咳,眼见他又是个惹祸招灾、不祥的尤物了。”{21}面对这样的时局,林白水说他绝不会向恶势力低头,该说的还得照样说,该做的还得照样做。他向读者表示:
如今要是投机押宝,干那滑头勾当,希望讨好军阀,那岂不是大大辜负了一般人期许的美意吗?所以,这杀气腾腾有枪阶级鼎盛的时代出报,固然是有不可避免的灾难。但是,为着我自己的人格,以及朋友们、阅报诸君等等期许的好意起见,也只得挺着脖子称硬汉{22}。
独立不羁、无所畏惧、挺着脖子称硬汉,既是林白水的新闻伦理思想,也是他个人刚毅性格的体现。他一生中嫉恶如仇,不惧权威,以新闻舆论为武器,凭着“三寸之笔,不烂之舌,而与彼文武名角相周旋,而无所于慑”,充分表现了新闻记者敢于同恶势力斗争的硬骨头精神。他说他办的《公言报》“无日不受恶势力之摧残,而再仆再起,亦无日不与恶势力相奋斗”{23}。他在清末时期,主张要用报纸来抨击朝政腐败和官员堕落,鼓吹反清排满;民国以后,则专以揭露军阀政客祸国殃民的罪恶为己任。
1923年2月,林白水发表时评《恭喜张内阁快点倒下去》、《缓急倒置》、《请看某部之大拍卖》等文,称“今之北京政府,可谓完全不懂事家伙凑成一堆,自名曰‘政府,自号曰‘中央,犹复不知羞耻,自谥曰‘合法。其实,此等政府,此等中央,此等合法,直不值一顾,不值一喙者也。”{24}他揭露议会、政府钱权交易和明目张胆地卖官鬻爵的丑恶行为。同年6月,《社会日报》大揭内幕,刊出曹锟贿选总统这一爆炸性丑闻,并将受贿者斥为“猪仔”,肆意嘲弄,当权者气急败坏,派人将报馆查封,并将林白水抓入大牢。1923年10月,出狱后的林白水仍撰文披露曹锟贿选总统的丑行,报社再遭封闭,林白水又被拘留三个月。
1925年12月1日,林白水收到威胁信,随即他在《社会日报》登出《白水启事》说:“鄙人办报三十年,从来援助民众,反对官僚军阀,以主持公道之故,牺牲功名利禄,不稍顾惜,下狱数次,终不变其节操。”{25}现在因亲友劝告,不要以言论招祸,于是宣布不再执笔为文。当天,时评专栏作者的署名即由“白水”改为“记者”。 这一启示发表后仅五天时间,就收到两百多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青年学生的来信这样说:“我们每日拿出脑血换来的八枚铜元,买一张《社会日报》,只要读一段半段的时评,因为他有益于我们知识的能力。”{26}这正是林白水所要获得的效果。12月20日,他再刊出《白水启事》:“这半个月之内,所收到的投书,大多数是青年学生,都是劝我放大胆子,撑开喉咙,照旧的说话。我实在是感激得很,惭愧得很。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再干起来罢。”{27}其实,林白水并没有改变撑开喉咙说真话的初衷,只是读者的支持更坚定和鼓舞了他用一支秃笔揭露军阀恶行的决心。
1926年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因“宣传赤化”的罪名被捕遇害,林白水毫不退缩,反而于5月12日在《社会日报》发表《敬告奉直当局》:“依现时情势而观,奉直当局似于政府成立之后,仍专力于讨赤之事业。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斫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28}5月17日,他在《代小百姓告哀》中又直接批判直奉联军讨赤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直奉联各军开到近畿以来,近畿之民,庐舍为墟,田园尽芜,室中鸡犬不留,妇女老弱,流离颠沛。彼身受兵祸之愚民,固不知讨赤有许多好处在后,而但觉目前所遭之惨祸,虽不赤亦何可乐也?”{29}很明显,林白水坚定不移地站在军阀讨赤的对立面,在为邵飘萍鸣不平。
1926年4月,针对奉系和鲁系军阀疯狂镇压爱国运动,屠杀进步人士,新闻界人士人人自危的状况,林白水撰文说:
军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除是死不要脸,愿做走狗,乐为虎伥的报,背着良心,替他宣传外之外,要是稍知廉耻,略具天良的记者,哪有不替百姓说话,转去献媚军人的道理{30}。
血色恐怖下的北京,记者人人自危,唯林白水不畏强权敢于抒发己见,这种勇气令人佩服。1925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官僚之运气》,得罪了潘复,直接招致杀身之祸。林白水与张宗昌、潘复结怨已久,他曾经讥讽张宗昌是“长腿将军”(影射张的部队毫无战斗力,遇到敌军就望风而逃),令张宗昌记恨不已。早在1923年1月2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矿师潘大少爷恭喜山东人发财》,揭露潘复贪污受贿,阻碍了他的官运。《官僚之运气》对潘复的嘲骂更进一步,骂声铿锵有力: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腰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31}。
正是这篇文章,激化了他与反动军阀和政客之间长期积累下的矛盾,招来杀身之祸。张宗昌和潘复恼羞成怒,当晚即逮捕林白水。1926年8月6日,以“通敌有证”的罪名将其杀害于北京天桥。离同样被军阀杀害的著名记者邵飘萍被害之日仅相距一百天。后人感叹地称之为“萍水相逢百日间。”
林白水在他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体现了一贯的硬骨头精神,敌人的恐吓,同行的牺牲,数次入狱经历,并没有使他畏惧,改变节操。相反,他是冒着“因言贾祸”的决心与勇气,提着脑袋在与军阀作斗争,表现了那个时代记者特有的侠肝义胆和铮铮铁骨。
四、林白水新闻活动中道德行为的缺失
林白水的新闻伦理思想及其新闻道德实践有其光彩夺目的一面,但其新闻道德实践也有缺失的一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收受津贴、公开利用报纸卖文和常常侮辱谩骂他人。这是他新闻活动中的道德瑕疵。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落后和报业经营的艰难,许多报纸很难靠自己的收入维持出版,“进退维谷之时,不得不仰给于外界”{32}。于是接受各种津贴就成了当时报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津贴有来自政府部门的,有来自政党的,也有来自政客个人的。据1925年11月19日《晨报》报道,接受津贴的报馆分为四级:(1)超等的6家,每家300元。有参政院支持的《顺天时报》、《益世报》、《京报》;财政支持的《东方时报》;国政支持的《黄报》;国宪支持的《社会日报》(即林白水主办的报纸)。(2)最要者39家,每家200元。主要包括《世界日报》、《北京日报》、《津京时报》、《交通日报》,天津《益世报》、《大公报》、《泰晤士报》,国闻通讯社,新闻编译社等。(3)次要者38家每家100元。主要包括《北京时报》、《群强报》、《中央日报》等。(4)普通者42家,每家50元。包括《民国公报》、《实事白话报》、《正义报》,中俄通讯社等。总计14 500元125家媒体。其中日报47家,晚报17家,通讯社61家{33}。
林白水是名人,他办的《社会日报》是名报,因此,他不仅接受津贴,而且数目比别人还多。在每月享受300元津贴的6家报纸中,就有他的一份。同邵飘萍一样,“林白水也是生活阔绰,他家里的佣人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也有5个。此外,他还酷爱收藏金石和砚台,藏品闻名于世。其卖文、收受津贴和贿赂在报界也并不是秘密。”{34}例如,他创办《公言报》的资金就是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提供的。“林白水还偶尔利用舆论监督搞创收,是个敲竹竿的老手。他秉承的工作理念是:给钱就不骂,绝不恭维。”{35}
人所共知,记者拿津贴的最大危害,是妨碍新闻工作客观公正原则落实,影响新闻职业信誉。“受人豢养,立言必多袒庇,甚至颠倒黑白,淆乱听闻”{36}。当时就有报人这样断定:“今敢下一断语曰:报纸直接或间接接受党派经济上的补助者,决不能有光明磊落之气象。”{37}其实,林白水早在1917年就说过:“若其立一言论机关,专为他人效鹰犬之用,津贴到手,摇笔骂人,忠则忠矣,如吾侪之不理何。”{38}可见,他本人对报馆拿津贴的行为也是否定的。“津贴到手,摇笔骂人” (不管是替出津贴者骂别人,还是反过来骂出津贴的人),都是错误的,那么,收了钱就不骂,但绝不恭维,就正确吗?只要是拿了津贴,骂与不骂,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其本质是一样的。
敢于揭丑是提高新闻战斗力与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报纸的重要职责。但是,揭丑不等于谩骂和攻击。而林白水在新闻实践中恰恰以骂人见长,以伤人为荣。我们翻阅林白水的社论时评,一个明显的印象就是辛辣尖利中带有几分刻薄与辱骂,尤其是以外号和不雅的文辞对批判对象进行人身攻击,背离了新闻让事实说话的基本伦理规范。尽管他自己曾经说他的言论“记载及其主张,咸以公平为主,以偏激为戒”{39},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做到。这里选几则实例看他是如何攻击挖苦别人的。
1923年3月4日《社会日报》时评《我们只得恭维彭允彝》说:“而且这一种似人非人的东西,我们要是劝他说,臭骂他,实际上也很危险。……而在彭允彝这样一身都是屎的人,究竟容易叫人动目。那岂不是反足以巩固他的地位,延长他的寿命么。我们敢相信这种千夫所指的败类,万万不能延续存在于人类社会,政治舞台。”{40}这哪里是正当的揭露和批评,完全是凭一己之意气,肆意骂人了。时评中出现“似人非人的东西”、“一身都是屎的人”、“千夫所指的败类”这样的评价,无论被评的对象如何恶劣,也显示出评论者本身的偏激和人身攻击的恶意。
他骂国务院秘书万兆芝“因招摇撞骗,泄露秘密,为张揆所发觉,遽行免职,逐出国务院。万为遮羞计,暗中嗾令其心腹涂逢福上书总理,藉口于忠良见嫉,公道不彰,声明愿与万某共进退云云。真可谓一摊狗屎,越搅越臭,可以已矣。”{41}他骂当时的国务院“居然变成皇城根一带的大粪圈、大茅坑。每天吹送几阵的恶气味触在鼻观子里,妨害我们的卫生。这是顶难过的啊!”{42}1923年6月18日,在《法在哪里》是这样骂黎元洪及其政府的:“去汝的小姑爷罢(北京土语),黄陂十三以后之命令,为放狗屁;国务院擅窃大权自命为有效之阁议,为放狗屁;若夫两院会合会昨日过半数之表决,乃是放狗屁。盖彼等除放屁外,固不知其他者。”{43}用“狗屎”、“茅坑”、“放屁”之类的语言在报纸上点名道姓的谩骂他人,实在有失文雅。这不仅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报纸和记者自身的形象。
不仅如此,他还喜欢给对手起外号,有意侮辱批判对象。例如:他骂国会议员是猪仔,将国会称为“猪仔国会”。说:“我们问问汝猪:打当选起,扣算到如今,十二年的时间,不可谓不长。汝猪的成绩究竟在哪里?这次北方军阀当祖宗敬奉,不能说是蹂躏议会,威迫议员吧。汝猪除了敲竹竿,以立法干涉行政外,所做何事?”又说:“且以众议院之机关言之,乃国家立法之最高机关。其机关之威信与名誉,本为圣神不可侵犯。今不幸以一群渎职受贿之猪仔,充该机关之分子。”{44}当时的众议院院长叫吴景濂,因为脑袋生得比较大,林白水就给他取个绰号——“吴大头”。又因为他是吴三桂的后代,林白水就骂他是“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他最后写的那篇引来杀身之祸的《官僚之运气》,同样存在这样问题。文中的“肾囊”就是男性的睾丸,指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张宗昌的心腹潘复。潘复看到文章后,恨得咬牙切齿,便找到张宗昌哭诉。张宗昌与潘复密谋,给林白水一个“通敌”的莫须有罪名,连夜逮捕,于凌晨4点杀害。
林白水因文字死于奉系军阀的屠刀之下,一方面说明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没有容人的度量,文章写得再刻薄,也只是名誉损失,不会造成人身伤害。而他们则不经过法律程序,擅自处决林白水,完全是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没有健全法制的社会里,记者想用笔杆子与当权者的枪杆子进行较量,是注定要吃亏的。当然,林白水历来喜欢用人身攻击的方法揭露丑恶,也不可取。他说《公言报》出版之初,“首于政府、国会及舆论界尽其忠告之义”{45},而在实际行为中,恐怕与“忠告”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至少在“忠告”的方式上不能以“猪仔国会”、国务院是个“大茅坑”的谩骂方式来忠告。
在民国时期的新闻记者中,林白水是一个特立独行、毁誉兼备的人。我们很少看到像他这样长期揭丑和敢于骂人的记者。他既有触忌讳、冒艰险、在所不辞的铮铮铁骨,又有接受津贴和贿赂的不良行为;既有令军阀和贪官污吏寒心的新闻“刽子手”的美誉,又有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历史污点;既有透骨见血、义正词严的健笔,又有偏激夸饰、刻薄伤人的文辞;既有清高的气质,又有世俗的习气。这就是真实多元的名记者林白水。从他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那个历史时期新闻记者特有的风采,而且可以从他身上汲取新闻伦理思想的精华和做人的教训。
注 释:
{1}张枬:《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605页。
{2}林白水:《论看报的好处》,《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局,2006年,第4页。
{3}转引自蔡晓滨:《中国报人》,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4}{5}林白水:《做百姓的身份》,《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局,2006年,第35页,第35页。
{6}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9页。
{7}邹容:《革命军》,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667页。
{8}林白水:《本报之三希望》,《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279页。
{9}转引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55页。
{10}林白水:《本报一千号纪念》,《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727页。
{11}林白水:《本报之三希望》,《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279页。
{12}转引自许一鸣:《林白水文集·序》。
{13}傅国涌:《一代报人林白水之死》,《文史精华》2004年第4期。
{14}林白水:《不堪回首集》,《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1037页。
{15}{28}林白水:《敬告奉直当局》,《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1129页,第1129页。
{16}{23}林白水:《办报一千号纪念》,《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727页,第727页。
{17}{18}林白水:《同业其注意》,《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254页,第254页。
{19}林白水:《今日之谣言》,《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764页。
{20}林白水:《答客问》,《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421-422页。
{21}{22}林白水:《本报复业宣言》,《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485页,第486页。
{24}林白水:《缓急倒置》,《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592页。
{25}{27}林白水:《白水启示》,《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1018页,第1033页。
{26}转引自方汉奇、林溪声:《林白水:以身殉报的报界先驱》,《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9期。
{29}林白水:《代小百姓告哀》,《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1132页。
{30}林白水《奉联将领大大觉悟》,《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1124页。
{31}林白水:《官僚之运气》,《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1179页。
{32}{33}{34}{36}{37}转引自王润泽著:《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9页,第265页,第268页,第269页,第268-269页。
{35}陈龙著:《书生报国》,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4页。
{38}{39}林白水:《敬告读本报者》,《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309页,第307页。
{40}林白水:《我们只得恭维彭允彝》,《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594页。
{41}林白水:《丑哉万兆芝》,《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604页。
{42}林白水:《福佑门内一个大茅坑》,《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606页。
{43}林白水:《法在哪里》,《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631页。
{44}林白水:《咄咄……汝猪仔》,《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657页。
{45}林白水:《本报之三希望》,《林白水文集》,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社局,2006年,第279页。
On Journalistic Ethics Thoughts and Moral Failings of Lin Poshui
XU Xin-ping
Abstract:Lin Poshui is a famous journalist,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ist,and the pioneer of Chinese vernacular newspaper of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 Among more than 20 yearsnewspaper career,he published many papers elaborating on his journalistic ethics thought in which some thoughtful ideas were put forward. In his view,reporters should set a newspaper with right motivation;they should“say truth,do not say nonsense”;and should have the courage to fight. His ideas and moral practice reflected distinctive personality of reportersin the period of warlord regime. However,Lin Poshui also has moral failings in news reporting activities,the most prominent performance were accepting allowances, selling articles by newspaper,and insulting others. His theory and practice choice provided an important basis for us to acknowledge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ethical choice of reporters then.
Key words:Lin Poshui;journalistic ethics thought;moral failing
(责任编校:文 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