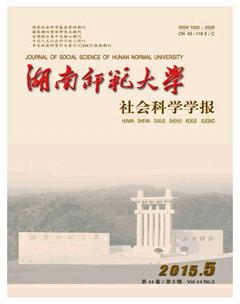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
冯广艺++冯念
摘 要:探讨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问题是创建中华民族和谐共存的语言生态环境的重要任务。新常态下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对于提升语言学科的研究活力,正确处理好语言研究中的各种关系等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社会生态环境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创造了条件,以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提供了借鉴,语言和谐共存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提出了挑战。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做好田野调查工作,了解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趋势,关注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准确把握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位,制订相应的语言生态对策,弄清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尊重他们的语言权利,聚集一批敢于攻坚的学术队伍。
关键词:新常态;少数民族;语言生态
作者简介:冯广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4)
冯 念,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高级动画设计师(海南 海口 571158)
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给我国的经济社会注入了活力,也给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新常态下,思考如何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探讨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现状及其发展演变,构建良好的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系统,创建中华民族和谐共存的语言生态环境,是语言工作者神圣的使命。本文从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意义、机遇和路径等方面论述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相关问题。
一、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意义
我国境内的语言约有129种,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推行正确的语言文字政策,尤其是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呈现出较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需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必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具有提升语言学科研究活力的学术价值。过去我们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注重对语言内部系统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和分析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相应地对社会生态环境对语言生态环境的影响、民族语言生态系统等研究不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基本写法是先简单地介绍某一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如人口分布、地域分布、地理文化等),然后主要描写某一少数民族语言内部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前者虽然涉及语言所依存的社会环境,但语焉不详,所占篇幅很少,后者是主体,描写也非常具体、全面。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问题,就是用语言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系统,探讨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生态的各种变化。语言生态学(也称“生态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实用性强、富有活力的学科,它对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无疑提升了语言学科的整体研究活力。其次,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处理好四个关系即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的关系、单一语言研究与不同语言比较研究的关系、语言本体研究与非本体研究的关系、借鉴与创新的关系,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1}。(1)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的关系。社会生态环境是一个变量,语言生态也是一个变量,它们之间是“共变”关系,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仅用共时描写是不够的,必须将共时描写和历时比较结合起来。如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历史上曾是语言活力很强的语言(如满语),在语言生态系统中,具有很显要的生态位,而到了当今,却演变成为即将消亡的濒危语言了。这类语言的语言生态问题,如果没有把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不可能找出它们从盛到衰、从强到弱甚至濒危消亡的真正原因。(2)单一语言研究与不同语言比较研究的关系。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应该认识到,我国的语言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把一种民族语言放在这个系统中进行语言生态研究,自然会考虑到这种民族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关系了。例如,在我国语言生态系统中,谈到语言接触问题,我们至少会遇到少数民族语言同汉语的接触、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少数民族语言内部各方言的接触等现象,在频繁的语言接触中,语言生态的变化是复杂多样的,有的语言在接触中语言活力变强了,有的语言变弱了,语言替换、语言转用、语言兼用、双语、多语等现象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一句话,语言生态发生了改变,这些仅从单一语言上孤立地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不同语言放在语言生态系统的框架内进行比较研究才能说明问题。(3)语言的本体研究与非本体研究的关系。语言本体研究是指对语言体系内部语音、词汇、语法等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语言学研究领域里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语言的非本体研究是指与语言相关的问题研究,包括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民族、语言与生活、语言与应用、语言与生态等方面的研究,戴庆厦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如除了在少数民族语言本体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之外,他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对语言和民族关系的研究、对双语问题的研究、对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研究、对语言教育的研究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4)借鉴与创新的关系。语言研究贵在创新,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是一个新课题,我们一方面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学习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另一方面在新常态下应有新作为和新担当,要开辟一条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新路子。
二、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机遇
1. 社会生态环境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创造了条件
现阶段,和谐社会的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深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给我们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创造了最佳氛围。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是语言和谐,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和谐、文明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下,由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汉语与民族语言之间、民族语言与民族语言之间、民族语言与外语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语言生态环境也会发生急剧的变化。著名语言学家戴庆厦先生指出:“中国的语言,处在各民族语言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生态环境中,其发展既有语言的分化,又有语言的融合,两者交融一起难以分清。”{2}戴先生所说的各民族语言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生态环境正是现阶段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环境的显著特征,也是我们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新视野。语言接触会带来语言的一系列变化,会对语言的功能和结构等产生重要影响。以黎语为例。黎语是黎族人民的母语,主要分布在我国的海南省。海南省黎语的生态环境在改革开放前后有着显著的不同。改革开放前,由于四面环海的独特地理环境,黎族人民与外界接触较少,黎族社会基本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黎语与岛外其他语言(包括汉语普通话等)的接触相对较少,因而黎语的生态环境是一种受外界影响较少、独自运用、独自发展的面貌,黎族人民运用自己的母语进行族内交际,兼用其他民族语言的人并不多。正如欧阳觉亚、郑贻青两位先生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黎语调查编著而成的《黎语简志》一书所指出的那样:“除琼中东部靠近万宁和琼海两个县的部分地区和白沙县西北部靠近儋县的部分地区有少数黎人使用汉语外,其余各地的黎族居民都用黎语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3}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海南建省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创建以来,海南黎族人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黎语的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改变,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增多了,黎语与其他语言的接触更加密切了,黎族人民使用黎语的情况也发生了改变。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语言》在《黎语》部分(郑贻青执笔)中说:“21世纪以后,随着海南的进一步开放,外来人口不断增加,黎族操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黎族地区正朝着双语制的趋势发展。”{4}郑先生所说到的黎族地区发生的语言接触、语言转用、语言兼用和双语现象等正是黎族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给黎语生态带来的变化。这给我们研究黎语语言生态带来了良机。从理论上讲,语言接触使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在语言态度、语言选择等方面发生了改变,而随之出现了语言替换(语言转用)、语言兼用、语码混用等现象,而从民族语言整体上看,语言濒危、语言衰变等也不可避免。美国语言生态学家萨利科科·萨夫温说:“生态环境是语言演化和形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门语言的演化通过个体使用者以及他们的话语和习语得以推动,同时在各种个体语共存的情况下,由生态作用于变异。”{5}从黎语社会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角度研究黎语生态及其发展是切实可行的。
2. 以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提供了借鉴
以20世纪50年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为代表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其基本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单一的少数民族语言为研究对象,以民族语言本体为核心,描写其语音、词汇和语法体系。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等。现在看来,当时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有几点:一是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把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当做国家大事来抓,当时在国家经济尚不宽裕的情况下,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分成7个调查队,深入民族地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二是一大批专家学者以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为己任,具有吃苦耐劳、勤恳奉献、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如著名语言学家戴庆厦先生当年还是个年轻人,随第3调查队深入哈尼族、景颇族聚居区,与少数民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多年,这种多年如一日的融入式调查研究,使戴先生成为景颇语、哈尼语研究的权威专家,也使得我国对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得到世界同行专家的认可。三是讲究科学方法,强调协作精神。当时为了做好大调查工作,组织了全国性的语言调查培训,特别注重国际音标记音训练,要求语言调查者应掌握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掌握田野调查的方法,搞好民族关系,搞好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搞好调查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协作精神。四是精益求精,旨在推出精品。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大调查是一项重大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是这项工程“打磨”出的学术精品。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除了继承这种语言本体研究的优良传统之外,还要重点研究:第一,少数民族语言的外在生态和内在生态。萨利科科·萨夫温认为研究语言演化生态学,“不光要关注一种语言所涉及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人种环境(其外在生态[external ecology])……还要关注语言系统在变化前及(或)变化中各个语言单位和规则相互共存现象背后的本质(其内在生态[internal ecology])。……外在生态和内在生态在决定一种语言的演化轨迹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6}第二,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主体。人是决定语言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主体即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者,他们的语言态度、语言选择、语言能力等是决定一种少数民族语言能否生存、能否保持语言活力,发挥交际功能的关键。在《语言生态学引论》中,我们强调人在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中的作用,指出:“人是语言的运用者、操作者,人类社会中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语言,语言是民族的标志,也是民族的凝聚物。一个民族的语言如果在语言生态系统中失去了它应有的位置,它可能会消亡,可能会出现濒危,等等。这是语言生态系统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固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但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例如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对官方语言的选择、对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的选定等,都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7}。
3. 语言和谐共存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提出了挑战
我国语言政策的目的是语言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是我国各民族之间的语言和谐共存。国家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允许地方方言的存在和发展;国家把汉语普通话作为全民共同语的同时,也鼓励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这种语言政策为我国的语言和谐共存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也是我国建构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肥田沃土。
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现阶段我们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一个重点。语言与语言之间,不论是强势语言还是弱势语言,不论是使用人数多的语言还是使用人数少的语言,不论是兴盛的语言还是衰变甚至濒危的语言,都应该是平等的,语言平等原则是我处理民族语言关系最重要的原则。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时,我们应该运用这条原则指导具体的语言现象的分析和评价,决不允许歧视弱势语言,歧视使用人数少的语言,歧视衰变语言和濒危语言。
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是现阶段我们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一个难点。我们应该看到,我国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已经濒危,还有的语言处于衰变之中。“赫哲语、满语、普标语、义都语、苏龙语、仙岛语等,使用人数已不足百人。如今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下的(上述六种以外)有15种。这些都是‘濒危语言。”“在我们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语言的消失不会是由于人为的压制;但是一种语言的消失,终归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消失,抢救濒危语言也是当前我们能做和应该做的一项紧迫任务。”{8}
三、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路径
既关注语言本体的研究,也重视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研究语言本体,注重揭示语言结构体系内部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和规律,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就所在。从语言的发展上看,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会给语言带来变化。因此,弄清社会生态环境及其对语言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如周国炎先生的《仡佬族母语生态研究》一书研究已处于濒危状态的仡佬语的生态环境,提出保护仡佬语、维护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主张。熊英的《土家语生态研究》一书同样以濒危语言为研究对象,力图从土家语的语言生态方面探讨该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濒危语言、衰变语言是世界语言发展演变中的一种易发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虽然跟语言的内部结构有联系,然而更多地与语言的生态环境以及这种生态环境带来的语言功能的变化、语言活力的增减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及使用人数等有密切关系。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深入民族地区,做好田野调查工作。
20世纪50年代语言大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做好田野调查工作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成功与否的关键。可以说,没有扎实的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就没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就没有学术精品。关在书斋里闭门造车,不做基本的田野调查工作,是无法取得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成果的。戴庆厦先生指出:“只有通过田野调查,才能真正体会语言是什么。语言在实际生活中发生变化,不到群众中接触语言,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语言的存在和变化。一个有作为的语言学家,对语言要有感性和理性两方面的认识,如果缺少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就没有根基;如果只有感性认识而没有理性认识,认识的层次就得不到升华。田野调查是语言学家获得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取之不尽的源泉。”{9}戴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十年来,他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不少于50次,成果丰硕,即使现在他80岁高龄,还常常奔波在田野调查的第一线,我们应该学习戴先生这种“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精神。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了解民族语言生态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有着不同的语言生态特征,即使是同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内部也可能会有若干种方言,方言与方言之间也会有不同的语言生态特征。如黎语具有鲜明的语言生态特征,黎语内部的五个方言的生态特征也有差异。由于黎语主要分布在海南省,从宏观上看,海南岛四面环海,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新中国成立前黎语受岛外语言的影响较小,这一方面有利于黎语的传承、保护,另一方面也使得黎语相对封闭,与岛外语言的接触相对少一些,由此引起的语言生态变化也相对小一些。从微观上看,黎语内部的五个方言(哈、杞、美孚、本地、加茂)中,使用人数多少不等,与外界接触程度不同,语言内部系统也有差异(加茂方言与其他四种方言差异较大),各方言的语言活力、语言功能等也有所强弱之分。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研究黎语生态就可以根据其生态特征有的放矢,真正弄清黎语及其方言的语言生态面目,以免漫无边际,盲目行事{10}。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重点关注现阶段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发展演变趋势。近年来,很多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本体的同时,把视野投向语言生态研究,他们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和发展演变等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戴庆厦先生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以少数民族语言的“点”为研究对象,在对“点”进行“融入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揭示现阶段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规律,可以看作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佳作。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准确把握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位”,制定相应的语言生态对策。在语言生态系统中,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生态位。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汉语既是汉族使用的语言,也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全民共同语,在语言生态系统中处于高端位置。少数民族语言,不论使用人口多少,都是语言生态系统中的成员,都是构建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和谐的语言生态系统的支撑柱。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有几种情形值得关注:一是处于濒危状态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位即将丧失,二是处于接触性衰变中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力正在减弱,三是不少少数民族语言在语言竞争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语言替换,四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多语现象更加复杂多样等,这些都是影响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位的重要因素,亟须制订相应的语言生态对策。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真正弄清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尊重他们的语言权利。不同语言(或方言)的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既包括对自己的语言(母语)的态度,也包括对其他语言的态度,在语言接触中,不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决定语言的发展走向,也直接影响着语言生态的演变。我们在调查研究海南黎语的过程中,对黎语不同方言区的黎语使用者做过一些问卷调查,发现不同方言区的黎族同胞对待自己的母语的态度有所不同,因而黎语在和汉语或海南话发生语言接触的过程中,有的地区发生了语言替换或语言转用,有的地区黎语语言保持较好,而有的地区则呈现出黎语、汉语双语兼用的情况,这是黎族同胞选择语言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他们的语言权利,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弄清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和语言生态变化的规律。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聚集一批敢于攻坚的学术队伍。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汇集一大批既有献身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精神,又有过硬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本领的学者,才能取得辉煌的成果。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是一项长时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组织多个学术团队,像20世纪50年代的前辈学者那样,分赴少数民族地区,对我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一次彻底的穷尽性的语言生态大调查,真正弄清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实际情况,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发展演变中的一系列问题,为构建我国和谐共存的语言生态环境而努力奋斗。
注 释:
{1}戴庆厦:《正确处理民族语言研究中的四个关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戴庆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导言),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5页。
{3}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1页。
{4}{8}孙宏开、胡益增、黄行:《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338页,第2-3页。
{5}{6}(美)萨利科科·萨夫温:《语言演化生态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页(前言),第171页,第216页。
{7}冯广艺:《语言生态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9}戴庆厦:《戴庆厦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17页。
{10}冯爱琴:《用语言生态学的方法研究黎语的保护与传承——访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冯广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