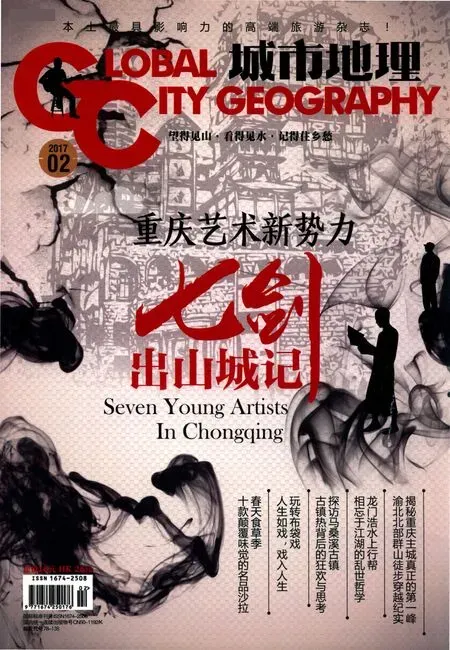他们的火车情缘车厢内外的百态江湖
文+江义高 蒋文豪 李晶 青见
图+李晶 寒溪夜浣 唐安冰 鲁思刚 刘汪洋
他们的火车情缘车厢内外的百态江湖
文+江义高 蒋文豪 李晶 青见
图+李晶 寒溪夜浣 唐安冰 鲁思刚 刘汪洋
每个人都有一段关于火车的记忆,或深或浅。
“呜”的一声,当火车开动的那一刻,记忆便灵动起来。明明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可人们又偏偏被每一声汽笛,每一次“咣当”触动。车头前进的方向,车窗透出的面容,车皮包裹的温度,车轮走过的路,凝结成一个鲜活的百态江湖。
英文导读: Trains as transportations attract many people working for them. Meanwhile, train fans and train drivers have stories to tell us.
播种煤炭的“长蛇”
在重庆,可能很少有人像江义高这样与火车有如此之深的渊源。
幼年时,江义高住在北碚文星场,父亲长年在外打工,自己便与母亲在家耕种土改时分得的几亩坡地。当时文星场正是天府煤矿的所在,小时候,江义高最大的乐趣便是到矿场去看“滚滚车”。当时矿场的运输还很落后,煤矿全靠马拉、人背,劳动效率很低。有个工长,为了多运矿石想出个法子:从山上向坡下平放两排圆木,让中间的距离相同,一根接一根地摆到山下。当装满矿石的斗车顺着两排圆木下滑时,山上的人大声喊叫着:“注意,车下来啦。”山下的人也大声回答道:“车到啦,好!”矿车隆隆的轰鸣让童年的江义高既害怕又好奇。
一次,江义高照例又去看“滚滚车”,却发现这些圆木都拆了,听说是修了铁路,让火车跑,但火车又是什么,没人告诉他。
又是一天,他到垄上割草,突然发现地面开始“打摆子”,抬头一看,只见一条压满煤炭的“长蛇”突然从山坳坳里转出来,“蛇头”冒着灰褐色的浓烟“哐当哐当”地奔过来,他的第一反应是:“吓木老!”他一直呆立着,直到那“长蛇”从眼前呼啸而去。高亢的汽笛声震撼着山村,也征服了江义高的心灵。后来,他知道这“长蛇”就是火车。从此,他就彻底迷上了那些铁家伙,火车将至,他就早早跑上山拗口迎接,每每目送火车从视线里消失后,才悻悻地返回院中。
等他稍微长大了一点,大人们就带他到铁路上去玩,告诉他哪是铁轨,哪是枕木,哪是铺路石,还教他听到远处有火车的叫声就要赶快离开铁轨,不要“呆豁豁地站起”。铁路两边各有一道两尺来宽的人
左页图:人会衰老,铁路,又何尝不会?
右页图:在重钢大量购入火车头前,北川铁路,曾是重庆唯一有火车可看的地方。行道,偶尔可见上面有自行车行驶。这时,大一点的调皮娃儿往往会唱“洋马儿叮叮当,上面坐了个死瘟丧(四川方言:骂人语,指讨厌的人)”。惹来骑车人愤怒地咒骂后,调皮的娃儿才得意洋洋地嬉笑着逃去。
再大一点,江义高发现,火车除了可以看着玩,还能“拿来用”。火车前面的车皮都是装煤的货车厢,最后两节是搭载客人的客车厢。运送的煤分两种,一种是从矿井开采出来的原煤,另一种是经过加工后的焦炭(当时都叫岚炭)。因车皮装得太满及运行中的
左页图:当年天府煤矿的煤,最终都会装在火车上汇聚到这里。
右页图:对蒋老来说,菜园坝火车站就是自己的青春。颠簸,原煤和焦炭免不了会从车上散落下来,这给住在沿路的村民带来了“实惠”,家家户户基本上不用花钱买煤,只需勤快一点,就可以在铁路两边捡到煤炭。由于自己天天“为火车站岗”, 江义高自然是精通此道。捡原煤的办法是“扫”:先把路基上的铺路石一段段地移开,地面上露出指头厚的一层原煤,用扫帚把这些煤扫在一堆,用撮箕“撮”走后,再把移动的铺路石还原。就这样,家里一直靠江老“扫煤”来解决煮饭、煮猪食的燃料。运气好的时候,碰到火车上那堆得高高的焦炭“垮一网”下来,能供一户农家烧十天半月。
后来,随着天府煤矿老矿的开采价值渐失及新矿的开发,铁路分期分批被拆除,而新矿区开发的煤炭则从磨心坡那条路运往黄桷树镇了。
离开家乡后,江义高很少再见过儿时的铁路,但轨道、火车和那一地的煤炭,以及震撼山村的“呜—呜—”汽笛声和“哐当哐当”的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尤其是初见时那种铺天盖地碾压全身的震撼,依旧时时在他的脑海里回响。
“学生们,我给你们跪下了!”
与江义高老人相比,蒋文豪老人的故事显得更具神秘感。
1951年春节,蒋老所在的西南军区铁路警备团(简称:铁警)三营八连在内江—椑木镇之间、成渝公路边的农家大院驻下军训已经3个多月了。立射、跪射、卧射,战士们在砍了甘蔗的旱地里摸爬滚打,尽管一身棉军装被甘蔗桩戳得千疮百孔,却越练越勇,越练越精神。大家都想练好本领迎接3月的打靶比赛。
可是从2月中旬起,连队的气氛就变了。连队里十几位个子矮小、身体单薄的战士被调走,20多位年轻力壮、有文化、能言善说的兵不知从哪儿来到八连,填了空位。武器也变了。原来那些没有刺刀的枪,都配备了刺刀和刀鞘。新来的5位干部不但外挎盒子枪,军衣内还有“短火”,原来的5位干部也换上同样的“新家伙”。
总而言之,干部、战士都被这些新事物、新行动弄得紧张而急促,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接受什么特殊而惊险的任务。
3月2日中午,重庆市公安局的罗政委揭开了谜团。原来,菜园坝竹篷监狱要来大约3000名人犯劳动改造,平整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地基。“内勤”由公安局派干部出任,管理人犯的衣食住行、思想教育等内部事务。因为“内勤”不带武器,所以需要八连作为强有力的“外勤”。蒋文豪至今还记得罗政委的话:“有人说竹篷监狱没有高墙和电网!我说有的——就是我们的‘铁警'八连!”
一个星期后,菜园坝火车站的建设正式拉开了帷幕。白天,罪犯们出工,蒋老和他的同伴就上岗执勤,上岗时着装要整齐,枪上刺刀,还带着120发子弹、4枚手榴弹和1个水壶,而且必须牢牢站在2.5平方米的岗上,手脚不能乱动。一上午起码站4小时,这样的工作强度在有火炉之称的山城显得异常大,所以设了副岗。他们的任务是指引那些到菜园坝办公事或私事的市民、干部及罪犯家属等等。副岗没事时,就站在“门”内,可以走动,可以和人说话。当正岗提出要求时,副岗接过长枪,交出短枪,正岗就可以在执行副岗任务时稍事休息。
当时两路口、菜园坝地区是名副其实的“立体建设”。其上,修筑两路口经鹅岭到大坪、杨家坪的公路;其下,修火车站;中间修筑连接上下弯弯拐拐的4米宽人行道。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是多么宏大的建设场面,因此每天都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
人行道上时常有人不懂,或假装不懂,或罪犯家属混杂其间向“禁区”抛来水果、食品等物。因为这些东西是从战士们头顶或面前扔来的,蒋老称之为“土炸弹”。刚开始的时候,一两天战士们要捡到或追回一大箩各种水果或糖果的“土炸弹”。据说内勤还曾从一个广柑内查到一颗针,所幸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直到“鸽子事件”的出现。
一天,王家坡高台上执勤的战士李清鸿,在上午9点半左右听到鸽哨声,同时看到一群鸽子从树林中飞出,他举起望远镜观察:发现那群鸽的翅膀下有些点状物往下掉,立即拿起电话报告。
警报声响了!八连留在连部的排会同白天执勤的排立刻把菜园坝地区包围起来。近百名保卫工作者在罪犯中开展拉网似的反复检查,查找了三遍,搜集竹筒扁瓶、纸包布包、金属小管鹅毛管等可疑物一箩筐,送市公安局特科侦辨和化验。后来听说查出些可以生热生火的化学药粉,所幸没有被心怀不轨的人利用酿成事故。
紧张执勤3个多月,从九龙坡延伸的钢轨已经进入菜园坝并分了叉——两股道分别进入刚修好的站台两侧。简单的火车运行设施,初步形成而可用。
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30岁生日。这天,蒋文豪所在的三排没有出勤政治学习。连长命令:全副武装练习礼仪——参加火车进站仪式。9点半,菜园坝地区“警报器”长鸣。进入站口,火车发出三声长鸣,三排官兵转身向驶来的火车致肩枪礼(一种上着刺刀的扛枪礼仪)。
驶来的火车头上挂着内嵌毛主席像的镜框,一朵
左页图:这枚通车纪念章,一直被它的主人妥善保管,几十年后,依旧锃亮光鲜。
右页图:图为成渝铁路通车当日的情景,那种席卷全城的热情,如今或许只有奥运会才能与之相比。后表示要进站看火车。正岗把头一偏,让他们找蒋文豪。
蒋文豪见他们人多,就往里退几步,让他们到阴凉的地方说话。听了他们的陈述,他很为难地说了“不同意”的话。他们又说今天是老师安排他们来“写生”画火车,不画回去交不了作业。蒋文豪自然还是不能同意。学生们急了,要求战士向他们讲述一下火车的样儿,让他们过把“看火车”的瘾,也好画画交作业。在这种情况下,蒋文豪开口了:“火车分车头车皮,车头是个大铁筒,铁筒内装水、装煤、烧蒸汽,蒸汽带轮跑……车皮嘛,装东西,装粮食……”
这时一个学生插话说:“我看见过狗皮……车皮是啥子皮?”“我看见过牛皮、羊皮……”“我看过铜皮、蛇皮……”学生们七嘴八舌,吵吵嚷嚷把蒋文豪逼懵了,脱口而出:“哎呀,我也说不清楚,你们自己去看嘛!”“啊!”学生们高兴得跳起来,“看车皮啰!”边唱边往里跑。
蒋文豪这才回过神来:“糟了,说错了——要犯错的!”眼见学生们已经跑了进去,又不可能强行去拖拽。一向不擅言辞的他憋了半晌,突然咚地一声跪倒!大声喊道:“学生们,我错了!我给你们‘跪下',退出来,退出来。我还背起个错误,不能再犯错……”
孩子们哪见过这阵仗,吓得一动不动,这场小小的“危机”才得以解除。“那阵硬是憨大红花戴在上面,两侧红绫直披到煤水箱后。车头后挂七节车皮和一节有两盆鲜花的平板(表示“七一”)。“七一”后面又是一台与前面一样打扮的车头,这个车头的镜框内是朱总司令像。这一前一后两台装饰鲜艳的车头,将车皮送进站台后慢慢停稳,调整位置后并排立在两股道上以展雄姿,供人们观赏。之后,又一齐发出长鸣,成渝铁路正式通车。
从火车进站之日起,市民们都想先睹为快。特别是那些少年。一天,蒋文豪在大营门副岗位上,远远看见十几个穿白衬衣打红领巾的学生走来。他们向正岗敬少先队礼惨老!”半个世纪过去,蒋老再次提起这段往事,依旧把自己乐得前仰后合。
你很好,只可惜不在蒸汽车上……
向炼,据他自己说是个生错了时代的人。他和蒸汽火车两情相悦,但如今却只能隔着玻璃相互欣赏。这倒不是抒情,因为向炼的家就是一个蒸汽火车博物馆——玻璃罩子与模型火车,随处可见。
如果你不是圈儿里人,也许从没听说过“火车迷”这个群体,其实火车的“粉丝”已经成千上万,遍布世界各地。他们的名字也多姿多彩。除了“铁路粉丝”以外,还有“铁路怪客”、“看火车者”等。
但向炼最中意的名字则是“吐白沫者”(foamers),原本用来形容火车迷见到火车后会兴奋得喋喋不休,直至嘴角出现白沫。虽然它有一定的侮辱意味,但许多火车迷还是为这个称号感到骄傲。
火车迷当中也会“细分”。有人只对火车头感兴趣,有人则青睐车厢,还有人专门研究隧道和高架桥等与火车有关的建筑;有人喜欢货车,有人偏爱客车;有人痴迷于火车的历史,还有人对与火车有关的机械问题“发烧”。有些人是因为从小摆弄火车模型才开始对它上瘾,还有人是因为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而对它难舍难分。而向炼,则是古董蒸汽机车这一领域的铁杆,圈内人称为“拜烟囱教”信徒。向炼与同教“信徒”朋友交谈时外人一般听不懂,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火车迷就如摄影迷一样,也有器材党,向炼便是其中之一,一部RadioShacK数字通信频率扫描仪必不可少,借助它们可以听到工程师与列车长之间的无线电通话;迷你DVD摄像机、高清晰数码相机是记录影像的工具;True-train软件则是“教众们”的《圣经》,因为上面不仅有各次火车的抵离时间,还附有车型及铁道线路的介绍和车站调度员面前的车站平面图。
而最让向炼得意的是,他的老婆也是从火车上“捡”的。在一次从重庆开往昆明的火车上,向炼看到一个女孩子坐火车,于是便帮她拿行李。上车后,两人开始攀谈,下车前,据说追女孩很“高杆”的向炼便与这位唐女士留下了联系方式。随后,向炼到昆明上班,两人一直保持联络,2008年他回到重庆,两人确立了关系开始交往——看起来这是一个平凡而温馨的故事,但终于还是长出一截不平凡的尾巴。
2011年5月8号,沙坪坝站前广场上人声鼎沸。这不是春运,而是一场为了告别的纪念,在这最后一趟火车开过之后,沙坪坝火车站将停止运营。十倍于平时的乘客,等待着绿皮火车最后一次驶出沙坪坝车站。5608次火车,7点47分,将用“哐当哐当”的铁轨声,把乘客们送回到过去。32岁的沙坪坝老火车站,在最后的热闹之后,也将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作为火车迷的女朋友,唐女士对陪着自己的男朋友去为老火车站送行早有准备,但她却没有料到,这趟车刚刚从沙坪坝火车站出发,“亲爱的,嫁给我吧……”这句话便如曼妙的音乐一般从耳后响起,他们的恋爱从火车开始,又在火车上完美收官。
唐女士对向炼的精心安排颇为满意,向炼本人却颇觉遗憾:“可惜惨老!那天翻遍沙坪坝火车站,
左右页图:作为一个资深的火车迷,向炼不仅将自己家变成了一个火车博物馆,还把自己的侄子也带进了“火坑”。一辆蒸汽车头的都没得!只有在个内燃机头儿上整老。”
新的一年,我想做个火车司机
左页图:多年来向炼追随着火车的踪迹在国内外行走,拍下了各式火车珍贵的驾驶室照片。
揭开一个巴掌大的红色铁皮盒子,一大堆蓝色的火车票漫了出来。张希是典型的处女座女生,她小心翼翼地取出按顺序整理好的车票,时间划过指尖,2015年2月、1月、2014年、2013年、2012年、2011年、2010年……
火车票的两端,是成都与重庆两座城,是张希和赵毅两个人,是千千万万个往返在成渝线上旅者,是日日夜夜间思念着他乡的异地恋人。
“真正认识了赵毅的那天,我正坐着火车去厦门。”张希这样开始讲述她的故事。2010年夏天,成都和厦门之间并没有直达火车,张希到重庆中转,正好客气地联系了工作中有过两次交道却从未谋面过的重庆崽儿赵毅。爽快,是赵毅给人的第一印象,他马上热情回应:“等你回程过重庆时,哥子请吃饭!记得联系。”就这样,在重庆赵毅招待张希,在成都张希接应赵毅,一来二去的,成渝铁路牵起了二人的缘分。
从2010到2015的5年间,两人如同所有身处异地却彼此相恋的情侣一样,每晚通过电话互道安好,偷空儿就坐上火车前往对方所在的城市。他们形容自己的生活是现代版“双城记”,有句默契的名言叫“我要么在火车上,要么就在去坐火站的路上。”
张希坐在桌前,一张一张地数着缺了小口的火车票。对于这个从20岁开始爱上坐火车的女孩来说,一小盒子车票是她与赵毅恋爱的最佳见证:在每年的生日和纪念日,在元旦节、情人节、劳动节、儿童节、圣诞节,在每一个互相思念的日子里,两人总会找到一张写有特殊日期的火车票。张希用秀气的楷体在票面背后做着记录,有“第一次见赵毅父母”、“第一个周年纪念”、“第一次赶掉火车”、“第一次使用12306和自动取票机”、“第一次前往成都东客站”、“第一次享受软卧车厢”、“第一次到重庆北站北广场”……
作为成渝线上的动车达人,张希对成都站、重庆站以及成渝铁道线上的诸多细节了如指掌。5年的乘车记录,让她可以准确地在39分钟内从自家出门到坐上火车,熟知抢出租车17种技巧,不用查询就清楚哪几号火车在成都站发车,而另外的得从成都东客站上,可以根据计划选择乘坐两小时的车或是两个半小时的车。她了解动车乘务员要求乘客将行李箱放置整齐的规则,也清楚到站前30分钟会有收垃圾的服务员,终点报站10分钟后火车才会真正进站。她偏爱火车中部车厢靠过道的座位,因为那是距离出站口最近的位置,每当听到“嘟嘟”两声开门铃响,张希便会兴致勃勃地冲出车门,抢在人潮之前,奔向出站口。
每一次,她都能在接站人群中一眼就看到赵毅的身影,也曾抢到过那么两三次“第一个出站”的记录!当赵毅接过行李包,给扑面而来的张希一个大大的重庆式熊抱,那滋味堪比荣获奥运会百米短跑金牌。
右页图:张希家里火车票“成山成海”,随手一抓便可以用来打扑克。
时间久了,摆点儿动车上所见所谓的龙门阵也变成异地恋人的感情调味剂。接到女友的赵毅总会笑眯眯地搂着她的肩膀问:“今年车上有没有认识什么有趣的人?”张希细致地描述和生动地表达总是让男友忍不住更喜欢她多一点儿。
记得有一次,张希在车上认识了个缺门牙的五岁男孩,那孩子喜欢坐火车,原因是车上可以吃他最爱的可平时却不能吃的方便面。张希与孩子玩起猜词游戏,她问:“说是豹不是豹?”男孩答:“海豹”。“说是玻璃不是玻璃?”他想了一会儿:“眼镜!”“说是面条不是面条?”“rice-noodle(米线)!”“说是棉花不是棉花?”“云彩!”“说是老鼠不是老鼠?”“鼠标”。看小男孩反应如此迅速,张希终于想出一道难题:“说是梯子不是梯子呢?”男孩最终没能猜出来……张希下车后,曾用同样的题目考过赵毅,最后她给出答案是“铁轨”,赵毅评价:“这还真是一个火车迷才想得出的问答!”
又有一次,张希在火车上遇到过满满一车厢的迷彩军人,清一色二十出头的“小鲜肉”,都是汽车兵。他们开过装甲车、载货车、冰柜车、洗澡车、油罐车,曾驻守在中缅交接地带,整日与傣族、佤族和缅甸人打交道。他们聊起驻边故事,张希听得动了心,例如缅甸和越南的蚂蟥谁更凶猛,又如东南亚国家的外语“过来”、“不许动”、“举起手”、“放下枪”、“蹲下”如何说。张希不禁感叹:“军旅生活那么好玩,干脆我毕业后入伍算啦!”结果一个兵哥哥叫起来:“求求你,不要来祸国殃民了。有你这样好看的女兵进来,军心都动摇完了。”每每遇到这类奇遇,张希下车时总神采飞扬,赵毅却漠不关心:“以后少跟陌生小伙子聊天。”
“哐当哐当……”关于火车的记忆被拉长,无数趣事闪现在张希的脑海里,惟一不变的就是火车与铁轨交汇发出的这一声声响。
火车送来一次次相聚与一次次的分别,无数对异地的恋人们在车站与铁道间留下或喜或悲的记忆。在张希的盒子里,如今已积累了126张火车票,她抬头微笑道:“这里只是一半,赵毅那儿应该还有100多张。”女孩子的心思,被成渝火车牵着,从绿皮车到红皮车到磁悬浮动车,从10小时到4小时到2小时,从陌生人到相恋人到一家人。虽然,一盒车票隔开了两座城市,但也正是这一盒车票讲述着一段双城罗曼史。
当2015刚刚来临的时刻,张希问起赵毅新年的愿望。他说:“如果可能,我很想改行当动车司机,每天都在回家的路上。”
左右页图:数以百计的火车经历,让张希对成渝铁路上的种种细节十分熟悉,从抢出租的方法,乘车的时间估算,动车车次与车站的关系,每班车行驶时长,无不了然于胸。
Their Love to Tra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