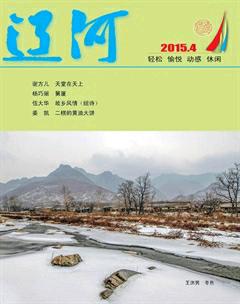白色安魂曲
肖涛
“故人西辞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小说《故人西词》题目可做如此解。其立意,也可从“空/白”中寻绎。
而通篇小说叙事所产生的审美效果及修辞可抵达的境界,亦可谓: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一个余音袅袅的“空白点”,留待读者去不断填充。
的确,小说有几处冷寂而悄怆的白描,既渗透着东方“空白”韵味的生命禅理与精神哲思,又蕴含着洪放的叙事美学与虚构技巧。
西词现在成了一个词语,在屋子里飞来飞去。而西词的肉体正在殡仪馆里那高大的烟囱中,成为飞舞的蝴蝶。西词不在,我们却在谈论他。这种他不在场的场景,让我感到有些冰凉。
事实上,他现在已仅仅是一个供人群吊唁的肉体。我相信:作为灵魂的西词,已经飞走了。他现在或许正在我们的头顶上看着我们,或许他已经远远地逃离了。他留下的肉体,已经与他无关。虽然这肉体还顶着“西词”这个名字,但已经被他自己用最决绝的方式抽干了。
为表达这一“空白”的生命思考,小说在叙事结构上,也采取了近似古典艺术中视通万里、神游八荒的交叉视点:由包含追悼会在内的几次聚会构成不同时段内的闪回追忆,并镶嵌于内核而成辐射性的珠花体,实质也在竭力从外延层面完成对死亡主体内在精神世界的补充,从容将“西词”这一即将进入由无数“空白”织造的死亡词典之能指的所指世界,变得丰盈真切。
由此,小说也成了一阕悲怆幽邃的挽歌,既是一份对上世纪80年代的祭奠仪式,又暗含对当下及未来一种尤为稀缺干净品质的捏合重塑与热望憧憬。
重塑也是追忆,追忆亦是闪回,闪回中隐藏着捏塑的诉求,而捏塑未尝不是依凭语词符号,用记忆之线缝缀成一匹简朴自然的素锦。死亡主人公西词生前的音容状貌、生活习性及其精神危机,在诸多他者、它性的侧面表述中,变得栩栩然起来了。
但丰盈并不意味着繁复,反倒愈加凸显出众人皆醉我独白的素淡美学。在当代社会特有的欲望生产、流通与消费机制中,包含性、政治、艺术在内的诸多追求,莫不沾染了污垢。“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谷欠”为“欲”;当这欲望泛滥而被置入权力的层级结构与进化论式的优胜劣汰次序中,乃至于变成伪善与平庸之恶时,那虚怀若谷、抱朴见素者,惟有一死。
……我打开西词的遗书。一张白纸,我只看见了一张白纸,一个字也没有。白白的,有些碜人。
在这张白纸下面,还有一张纸,南燕在上面写了一行字:他什么都明白,却只用死亡来回击了这一切!
可见,西词之死并非源于懦弱与绝灭,更非鸵鸟战术。与其说西词死于生活与工作场域内因原欲不得志而来的绝望,毋宁说他谋求到了回归传统殉于文化式的死亡。终究西词所从事的地方志也盘踞着权力的交锋,遑论缱绻难舍、几度重燃的文学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