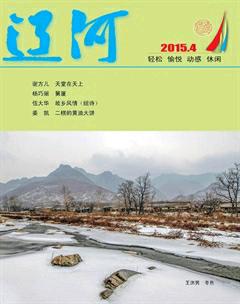故人西词
洪放
队伍缓慢地从西词身边经过,西词是躺在花丛中的。这一辈子,他大概是第一次享受这样高规格的礼遇。花是黄色的,也有红色的,黄色的显得安静,红色的有些让人惊心。不过,好在队伍也是黄花一般的安静。安静的人群都侧着脸,最后再看一眼西词。我发现西词的脸变得很小,相当的小,小得就像一枚稍微大些的纽扣,正扣在花丛之中。而且,不知是谁的安排,他竟戴着一顶黑色的瓜皮小帽,帽子有点大,罩住了他宽大的额头。额头没有头发,据说是在抢救时全部剃光了的。他的身子整个被埋在花丛里,因此很难看清他穿的衣衫。他的眼睛是闭着的,因此也不可能透过他的眼光看到他现在正在想些什么。事实上,他现在已仅仅是一个供人群吊唁的肉体。我相信,作为灵魂的西词,已经飞走了。他现在或许正在看着我们,或许他已经远远地逃离了。他留下的肉体,已经与他无关。虽然这肉体还顶着“西词”这个名字,但已经被他自己用最决绝的方式抽干了。
转过花丛,前面是西词的一长溜亲属。这是礼节,他们站在那儿,向所有来祭奠西词的人致谢。站在第一位的是西词的哥哥,刚刚六十岁的人,头发全白了。刚才在祭奠仪式之前,我曾在外面的场子上遇见他。难得的是他居然还认出了我,满怀悲伤地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支烟,说:“我知道你们都会来,西词走得不痛快啊!”我拿着烟,没有点火,看着他。他上前来要给我点火,我摇摇头。他说:“该点上火的,这是规矩。”我便让他点上了火,烟味有些冲,还有些幽冥之气。我叹了口气,说:“唉,也是。西词怎么就……”他个子矮,仰着脸:“不过想想也是,西词走得好。一个男人……唉,要知道如今这事,还不如当初让他跟着我在农村插田。”我不好回答,而且我觉得他也并不一定要求我回答。我们站了会,他说:“你们同学大部分都来了。还是同学好啊。想当年我到你们学校去找西词,你们就住一个宿舍。那时,西词才十八九岁,可现在……这个傻孩子……要去服侍爹娘,也得是我先去的啊。这傻孩子……”他抹了下眼泪,转身走了。我看见他转过场子,到了屋角那边,一个人蹲着。他的表情我看不见,但我看见青色的烟雾正从他的头顶袅袅地升腾起来。现在,他站在亲属的第一位,表情苍老,甚至有些木讷,他机械地同每一个人握手,眼睛却看着花丛中的西词。在他后面,是南燕。
南燕今天穿着一身黑色,脸色悲戚。她将头发高高挽起,这样,仿佛悲戚又升高加重了一成。她平时挺直的身子,这会儿有些稍稍向前倾,这也是切合她现在的心境的。一个悲伤的人,是没有理由挺直着腰杆的。她的手一直伸着,同每一个走过的人碰一下。也有人说上一两句安慰的话,她只是点头。她的目光似乎也在看着西词,但与西词哥哥的目光相比,显然要有一些距离。如果说西词哥哥的目光是看着西词的眼睛的话,那么,她的目光是看着西词头发上的那一片虚空。即使在悲伤之中,她姣好的容貌,还是透出沉痛的美与冷艳。这也是她最大的魅力。事实上,从大学时代起,她就一直是冷艳的代名词。在中文系这样一个充满浪漫与情爱的地方,她如同一株令箭荷花,高高地冰冷地伫立着。也正因此,当大三西词开始对她发动爱情攻击时,班上所有的人都有些惊诧。很少有人想过要爱上她,追求她。她高高在上,不仅仅是她的容貌、她的情怀,还有她的家庭,学业。她是我们班上很少的几个城市生之一,父亲是我们大学所在市的副市长,母亲是个有些名头的演员。她虽然考到了我们中文系,和我们一个班,但大多数人认为:她只是偶尔走错了道,串错了门。对于我们班,她是个过客。追求一个过客,是靠不住的。但是,西词却勇敢地追求她。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的,谁都不知道。她不说,西词也不说。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大三下学期,她跟随西词到了西词的老家。回来后,她在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句话我们都记得,“那些美好的自然打开了我的心扉。”我们后来戏谑西词,说南燕爱上的并不是西词,而是“那些美好的自然”。西词狡黠地一笑,彼时,他目光清澈,充满激情,因为爱情,他成了中文系最大的新闻。或许那便是西词人生的第一次巅峰吧?
我走到南燕面前,我说:“节哀!”南燕抬了下头,又迅速地低下头。她没说话,只是用手在我的手上稍稍用了点力。我移过身子,后面是她的儿子,也就是西词的儿子。二十来岁的大小伙子,眉目清秀,看不出西词当年的样子。我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说了声:“谢谢!”我说:“照顾好你妈!”他眼神飘忽了下,说:“知道!”
出了大厅,外面的人群已经渐渐地散了。吴卫东过来嘁我,说都安排好了,中午我们大学同学在一块聚聚。我点点头。吴卫东说:这次告别西词,我们当年中文系大二班一共来了十一个人。加上南燕,是十二个。其中从外地赶来的,也就是说像我这样从湖城等地过来的,有三个。大二班一共三十一个人,出国的有九个,跟西词一样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的有四个,至今没办法联系的有五个。余下的,吴卫东都打了电话:有的有事,有的在外地出差;因此真正到了的就这些了。大家不再作声,我回头又看了看整个殡仪馆,竟然都笼罩在阴翳之中。这会儿,有人递过来一杯水,纸杯子,白开水,说:“喝点吧,规矩!”我接过,西词的哥哥眼睛里仍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无助与哀伤。
吴卫东正在招呼其他人,西词的哥哥说:“谢谢你们从大老远过来。西词要是知道,也会感激。”我喉头有些紧,没回答。他又说:“西词是个诚实人,哪知道就这么走了。西词不该上大学啊,更不该……”他望了望四周,人群散得差不多了,哀乐声也正在低沉下去。他轻轻地说:“西词这后十几年过得憋屈啊!憋屈!”我听着,目光却越着他的头顶。我看到南燕正走出告别大厅,她黑色的身影似乎又回头看了眼厅内。然后我看到她同吴卫东说了几句什么。再然后,她又回到了大厅。吴卫东过来,说:“该走了。”我同西词的哥哥握了下手,西词的哥哥说:“我得把他送到山上去。我代表西词谢谢你们了。真的谢谢你们了。”
我眼睛一湿,想哭。这会儿,我真切地想起西词当年在我们班上的那些情景。他不仅跟我同班,还是同寝室。七个人的寝室里,八张床。空余的那张床是我们的公共食物间。西词住在靠窗的上铺,我住在他对面的下铺。因此,晚上睡觉一醒来,我第一眼看见的往往是西词的大脚丫子。那四年,我亲眼目睹他的大脚丫子从一开始进校的泥黑,渐渐变得灰白;放假回去再来,又变成泥黑。当然,这情况并不是他一个人,其它六个人也是。我们都来自农村。那时农村刚刚分田到户,暑假正是双抢时节。大家都是主劳力,刚放假时,大家想的是回家快活。可到了假期后半期,心里就盼着上学了。西词在我们寝室年龄最大,其实也就比我们大一岁。他理所当然地做了室长。这室长一做四年,毕业时,作为对室长的回报,我们六个人每人凑了点钱,给他买了一件白色的衬衫。后来同学十年聚会时,他就穿着那衬衫,站在我们的照片中间。那时他正处在人生的转折点,眉宇间有些忧郁。我们都问过他,他没细说。西词是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特别是关于他自己。我有时甚至觉得他对自己是混沌的,就像农村泥田里那些刚刚被翻耕过来的泥土,隆起着,还没有被润开。
我们离开殡仪馆,出门上车,后面响起了鞭炮声。这是送客的礼数。鞭炮声有些沉闷,也很短促。大家都沉默着上车,阳光却很好了。仅仅隔着一座大门,刚才院子里场予上阴郁而清冷,而这外面,阳光恣意且温暖。我想,西词是享受不到了。西词躺在花丛中,他已经成了我们的故人,成了我们只能想却不能再实实在在看一眼的念头了。
中午吴卫东安排在沙城最大的酒店,包厢的名字有些刺眼:888,但没有人说出来。进了包厢,吴卫东叹了口气,说:“没想到,今天大家从各地赶来,为西词,却见不着西词了。唉!”他挨个发烟,居然都接了,且都点上了火。一时间,十来支烟的烟雾,弥漫着屋子,有些恍惚。徐强已经秃顶了,他拿烟的手有些颤抖,说:“没想到西词这么……上个星期,我还约他出去钓鱼。他没去。说在家整理些资料。我说那破单位有什么资料可整?他说得整整了,否则就来不及了。”徐强停了下,说:“可能那时他就……”西词在沙城志办工作,在我们那一届的中文系同学中,他是为数不多没有进入政坛的人之一。准确点说,他曾经进入政坛。西词—开始分配就到了沙城市委宣传部,当然这得力于他那当时还是准岳父的推荐。南燕也一道分配到了沙城,先在市一中。后来她与西词完全掉了个位置。西词调到冷门的市志办,她从此走上仕途,并成了沙城政协的副主席。说到这里,专门从上海过来的王肖说:“记得十年聚会时,西词已经是科长了。那时他才三十多点,正当年。我们都看好他。后来怎么就突然调到市志办了呢?”吴卫东说:“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到市志办后,一直还当科长,一直。”吴卫东说:“从那时候开始,西词就有些忧郁了。我还是喜欢西词谈恋爱那阵子。还记得烟票的事吧?”
“记得。”大家几乎都点点头。王肖说:“我们怎么会想到南燕的父亲南市长会到我们实习的地方来呢?现在想来,西词当时是得到了南燕的消息的。那次多好!南市长来时,我们都变成了西词的士兵,听他的话,给他面子,长他威风。那时西词多威风啊!真让他那准岳父看傻了眼。特别是我们每个人想办法凑的烟票,硬是让西词给南市长买了条烟。虽然南市长有的是烟抽,但那烟意义不一样啊!是西词的,是未来女婿的。”徐强抢过了话头,说:“还有后来送南市长离开,多排场哪!由西词指挥,我们唱着军歌,列队欢送,把那个军人出身的南市长激动得满脸通红。西词硬把准岳父整成了个将军!”“将军?对,将军!”吴卫东说着,突然停了。
一屋子人也都停了。
西词现在成了一个词语,在屋子里飞来飞去。而西词的肉体正在殡仪馆里那高大的烟囱中,成为飞舞的蝴蝶,西词不在,我们却在谈论他。这种他不在场的场景,让我感到有些冰凉。我借故手机来电,出了包厢。我在走廊上来回走了一圈,想让自己的心平静些。可是脑子里却老是想起西词。大学毕业后,我们一共搞过两次同学聚会,都在沙城。这主要是因为南燕。南燕在沙城如鱼得水,同学聚会风光目.舒适。两次聚会中,西词都出现了。那时候西词是个活脱的人。十年聚会时,他正在宣传部面临着工作上的一次转折。那次他喝了相当多的酒,陪着我们抽烟,说在机关呆十年了,没意思。想出去。我们问他有方向不,他说可能下海,也可能回家作一个专业作家。大家都发表了意见,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大家都觉得他那时候在官场上的势头不错,已经是正科了,我们都天真的以为:那离副处也就快了。中国入骨子里的官本位意识,总是存在的。我们劝他。他笑笑,说:“也难哪!关键是没了激情。”有人就笑话他,问是不是南燕耗费了他全部的青春与激情?他回头看了看正在另一桌上侃侃而谈的南燕,摇摇头。没有谁明白他摇头的意思,也没人追究。大家再说到回家写作。西词在大学时代就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主要是诗。其中有一组爱情诗,或许是写给南燕的,被当作校园里求爱经典。不过大学毕业后,我们再没看过他的诗作。记得那次,我们煞有介事地探讨了回家专职写作的可能性。最后的结果是:不太可能。文学的春天正在结束,文学已不可能达成一个人的尊严了。西词说那也是,那就慢慢来吧!西词说那话时,手里正端着酒。他的手有些颤抖,酒从杯子里一滴滴地洒出来,亮晶晶的,落到桌子上。他放下杯子,用手指将那酒沾起来,放到嘴唇边吸吮着。这使我想起那四年同居岁月中,西词的嚼牙齿声音一直是我们夜晚的伴眠曲。一开始我们六个人也适应不了,总觉得寝室里有异物在活动。胆小的吓得将头蒙在被子里,我倒是起床了,寻声而去,结果就到了西词的床前,然后是他的头上,最后落到了他的嘴里。我们叫醒他,他红着脸说总是梦见肚子饿,找东西吃,就嚼牙齿了。大学毕业后的头半年,我老是失眠。问问其它六位室友,也是。大家细一想,豁然开朗了,原来是没了西词嚼牙齿的声音。我们打电话请西词将那声音录下来寄给我们。这当然是笑话,他没录,只给我们每人寄了两盒沙城特产水晶饼,说半夜里真是饿了,能填肚子,味道好,还实在。
十年聚会后,有一年春天,西词突然到了湖城。那天我正在湖城教育局开校长会,西词打电话来说他到了湖城,就在郊外的八一农场。我有些惊讶,问:“怎么到了那里?”他说:“宣传部同事的老家在这,就来了。过来喝酒吧?”我说:“好!我一定过去。”那天的会议开得也真拖沓,一直到了中午十二点,才勉强结束。局里安排了午餐,我谢绝了,赶着到了八一农场。西词正站在门口张望,我乍一看,觉得他瘦了,黑了。不过精神还不错。西词说:“很长时间没好好喝酒了!”我笑道:“不会吧?你又没有酒瘾,在乎酒?何况宣传部是大机关,有的是酒,能没酒喝?”西词沉了一下,低着头说:“我调到市志办了。”
“真调了?”“真调了。上班半年了。”西词拉着我回到酒桌边,斟了酒,两个人慢慢地喝。西词说:“想来还是市志办好,清净。适合我这性格。你知道我们志办那栋小楼叫什么名字吗?告春及轩,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中的句子。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我点点头,确实是陶渊明的句子,我就想那小楼一定是座古旧的建筑。或许还有座小轩,明月之夜,推窗而望,也许还能生出几分幽情来的。
西词将杯里的酒干了,叹了口气,说:“轩建于1890年,传说那里有狐。不过我没看见。只是阴雨天气,坐在轩里的办公桌前,有些莫名的恻隐。”我说:“或许哪一天真的有狐精来找你了呢?不过,那对南燕……”西词摆摆手,说:“我们不说她,喝酒,好吧?不说她。说说我们同学的事,同学的事!”我说好,于是一一地回想当年大学同学的那些笑话,轶事,说到末了,西词将酒杯重重地放在桌上,说:“记得叶宁吗?““叶宁?当然记得。” “死了。”“死了?”
“车祸。据说黄昏的时候他一个人驾车到省城去会情人,半夜回来时天正下小雨,路滑,车子就不知怎么地撞到了路边的石墩子上。等发现时,人已经没了。”
“你过去了?”
“没有。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他家里人拒绝声张。我还记得当年叶宁在学校大礼堂里朗诵诗歌时的那神情,长头发,大眼睛,真的有些诗人叶赛宁的样子。可惜……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都走了。走了!”我赶紧换了个话题,问到孩子。西词说他现在既是市志办的编辑,更是家里的全职保姆。我说:“这事你适合,你心细。”他叹道:“不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总得有人来干吧!”后来便谈到他从宣传部刚出来那阵子,先是到一家企业去干了一段时间。那老总想起来也算是客气,给他一个副总的头衔,负责办公室。那一阵子,他甚至感到意气奋发,想好好地干下去。但不久的一件事就让他彻底放弃了。那次老总带着他到省城,晚餐后老总陪着省计委的领导去唱歌。歌才唱了两支,省计委的领导就不耐烦了。老总将他拉出来,让他去找小姐,说领导等不及了,唱歌是幌子,目的还不是……他摇摇头,说:“我找不着。”老总马上黑了脸,说:“找不着也得找。不然我要你这副总干什么?”他马上回了句:“那就别要了。老子本来就没劲的。”老总脸更黑了,自个儿去找小姐了。他出了门,换了家宾馆一觉睡到天亮,打车回到了沙城。西词短暂的下海生涯就此结束了。“想来还是市志办好,人少,清净,干净。”西词说着又喝了杯酒,我赶紧拦了,我知道他并不长于喝酒。但他没听,说:“我现在喝酒是乐趣了,不像原来喝酒,是痛苦。痛苦啊!”
那天我们喝了两瓶白酒,西词醉了。临走时,西词说:“那个王为民现在是省政府的副秘书长了。”王为民是我们大二班的班长,当年,他是南燕的主要追求者。论相貌,西词不是王为民的对手;论才华,也不比王为民出色。论家境,王为民的父亲也是老干部,与南燕算是门当户对。但后来的事实是:南燕嫁给了西词,王为民成了失败者。毕业典礼前的那天晚上,我们见证了两个男人的战斗。西词和王为民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每个人喝了一水瓶散装啤酒。都醉了,醉了的王为民丢下了一句话:“西词,你记着,南燕一定会是我的。”不过,这话虽然是丢下了,但毕业后这十多年,倒是没听说王为民在这方面有什么动作。或许都是青春年少的豪情壮语吧?只是十年聚会时,王为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没参加。但他专门安排了别人送来了三十束鲜花。其中最大的一束,是玫瑰。上面系着绸带,绸带上写着南燕的名字。这让十年聚会形成了一个高潮,特别是南燕。不过,在西词面前,南燕却表现得异常的通达。她将玫瑰分成了若干束,分送给了就餐的饭店的员工。
大学毕业二十年时,我们相约再次聚会。但这次来的人更少,只有十来位,还几乎都是沙城的。王为民这次来了,他坐在南燕的左首,面色红润,人也发福了。其时他已官至另一个省辖市的市长,而且外面正有传闻,他即将调任沙城市委书记。因此,这次聚会与其说是聚会,倒不如说是为王为民预接风。聚会的中心不像十年聚会时那样,谈同学谈大学谈轶事谈情感,这次谈的更多的是官场、生死,还有就是那些欲言又止的说不清道不白的隐晦。我是二十年聚会时唯一的一个沙城以外的同学。本来我也是不准备过去的,但是南燕在电话里一再要求,甚至连西词也说了:“同学聚会是聚一次少一次的,来吧!别人不来,我无所谓。你不来,我难受。”那次我们一共喝了两餐酒,第一餐因为王为民,酒喝得不温不吞,在临界点上都卡住了。第二餐,王为民离开了。大家因此就都放开了了喝。西词喝到哭了,南燕倒在吴卫东的怀里,喃喃自语,说:“当女人难,当一个官场上的女人更难。当一个想当个好官的女人难上加难!”那天晚上,我住在宾馆里,半夜醒来,就接到南燕的电话,说想过来喝杯茶。原来她也住在宾馆里,我们喝茶,一直到天亮。南燕说到跟西词的生活,说认识一个人,单是恋爱那些年是不够的,要一生。可是,一个人只有一生,等到真的认识了,一切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说你与西词的爱情,就是现在,也还是我们那所大学的传奇。西词当年能在那么多的追求者中脱颖而出,他是有他的特点与魅力的。其实我想说,在南燕众多的追求者中,像王为民和西词,是勇敢地站出来了的。还有更多,是暗恋,是在心里,是在梦里。唯其是暗恋,因此更深入、持久和存着单纯的美好。但是,我没说。我劝南燕。我说西词越来越沉默了,他的心里是不是……南燕望着我,说西词不是沉默,是沉沦。你知道吗?他有时候甚至去那些下三烂的洗头房。我一惊,西词怎么会?南燕说我亲眼看到了,他与一个叫小贞的洗头女走得很近,甚至……我无话可说。南燕说:“外面很多人看着我风光,其实我比他还苦。你在湖城,我可以跟你说说。在沙城,我被供在台上,这些话都是没法说的。”我极其自然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她顺势倒在我的胸前。我看见她的头发也有几根白色的了,心里涌出一缕疼痛。我抚摸着她,我用手指慢慢地擦去她眼角的泪水。她望着我,然后突然像一片被狂风吹起来的落叶,迅速而毫无征兆地席卷了我……那一刻,我在心里看见的不是南燕,而是西词。
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西词,西词醉酒后哭泣的声音,就如同一段被石头重压着的树根,苍老,皴裂,黑暗且淋漓。
酒菜上桌了,大家却都站着。以往两次大学同学聚会,像安排座次这样的事情,都是西词。现在西词不在了,这些座位就像一把把刀子,不知道怎么让人坐不上去。还是吴卫东说话了。吴卫东说:“坐吧,这中间的位置,留给西词。”大家就围着西词坐下,南燕没来,也留了个位置。
酒满上后,吴卫东提议大家先敬西词一杯。没人说话,酒都干了。西词的酒,被吴卫东洒到了地上。又满一杯,吴卫东说:“我们大二班,现在走了四个了。快八分之一了。时光就是一把刀,现在开始收割我们了。”王肖说:“不说了,太悲伤了。咱们喝酒。”
我望着西词的位置,仿佛看见西词还坐在那儿。二十年聚会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西词。但是电话倒是经常有的。西词喜欢在半夜给我打电话,但却说不上几句,便是沉默。沉默后便挂了。有一年秋天,我在湖城宾馆边上散步,看见宾馆大门边打了个条幅“欢迎参加全省地方志会议的各位代表!”我就想,西词或许也来了。心里甚至有些怪他,到了湖城,居然不跟我联系。我等着他的电话,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仍然没有。我又想:西词也许没来。他要是来了,一定会电话联系我的。我这样想着,心却不甘,跑到宾馆查了下住宿登记。结果还真的查到了西词,只是头天晚上已经退房离开了。我立即打电话问西词,怎么就……西词说:“时间太紧,你也忙。何况见了面,也说不出什么来。”我骂了句:“就是听你嚼嚼牙齿也好啊,西词,你太不够哥们了。”骂着,我有些心虚,倒是西词在电话里说:“要是真能嚼牙齿就好了。可惜嚼不出味儿来了。”我觉得他的话弦外有意,又不好问,便扯了几句寡白,有些索然地结束了。后来有一次,吴卫东到湖城,谈到西词。吴卫东说西词整个变了个样子,除了上班,几乎不出门,也不参加任何活动。外界有传言:西词跟那个洗头女养了个儿子,他每月负担一定的生活费。还有说西词跟南燕提出过离婚,但南燕没同意。据说南燕找人给那个洗头女捎了话,那洗头女便从沙城消失了。但这一切,都没有直接的证据。西词从来没有就此承认过,或者否认过。有一段时间,西词一个人搬到告春及轩里居住,一灯如豆,守着那栋老房子,人便一天天更加地消沉了。我让吴卫东带话给西词,请他到湖城走走。喝酒,爬山,或者去山野打猎。但西词一直没有声息。很多时候,即使是大学时代胼手抵足的同寝室同学,在若干年后,也会慢慢地被时光打磨成了愈加密封的卵石,那些曾经的温度,已很难再感知了。酒喝得有些猛,也有些闷。徐强说:“听说西词留了封遗书?”
没人回答。大家都不曾看到,也就都无法出声了。徐强将早已因谢顶而仅剩下的几根头发理了理,叹道:“不管怎么说,西词这么做都是不负责任的。孩子,还有兄长,还有,我们这些同学……还有南燕。”他停下话头,张了张口,说:“王为民没来。王为民要是来了,西词一定会揍他的。”
“别扯远了。”吴卫东按住有些激动的徐强,说:“喝酒,人都走了,再说这些有意义吗?”“是没意义。可是,我得说。不就是个书记吗?凭什么?要是当年你胜了西词,我们无话可说。可现在,你跑到沙城来,有意义吗?有意义吗?你们说有意义吗?”徐强一仰脖子,喝了杯酒。吴卫东又按住他,说:“那也是传闻。我相信王为民跟南燕没什么。为这事我真的问过南燕,她说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她说得多好,非得西词捉了他们不成?”徐强突然笑道:“现在好了,再说也没意义了。西词,你这个孬种,你走了,倒是清净。可是,大家……大家……来,喝吧,为着西词,咱们喝!”我也将酒喝了。酒辣,苦,火一般,往心里烧。
我望着西词的位置,西词正在一个劲地嚼着牙齿,他眼睛发白,正对着我。西词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但却被他关在牙齿里,被一点点地嚼碎了,然后自个儿吞到了肚子里。西词似乎站了起来,端着酒,要敬我,他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只听懂一个词:南燕。我问:南燕怎么了?西词不回答,只端着酒杯。那酒杯幻化成了一缕烟雾,连同西词,慢慢地升腾起来,渐渐地消失了。徐强还在纠缠着王为民,吴卫东在劝他:“他当他的书记,跟我们何干?原来还因为西词,现在西词走了,就更……”王肖说:“外面有传言,纪委正在调查王为民。把他送到党校学习,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查他。”
我想起我们大学同学十年聚会时,王为民也在党校学习。事实上,就在西词出事之前,南燕有一次到湖城,曾告诉我组织上正在调查王为民。我没兴趣。南燕说王为民跟她之间,就像两张纸。他们从没有合二为一过。在对待王为民的问题上,南燕说她永远记得王为民当年跟西词说过的话,她不会让王为民成功的,她得给西词最后的男人的尊严。我用更加猛烈的动作回应了她的话,以至于她问我到底听没听懂时,我只能啊啊地发出嚼牙齿般的声音。我忌讳南燕说出西词,但是,又迫不及待地希望她说出西词。西词横亘在我们之间,让我们更有了难以名状的爆发力与强大的愧疚感。我们小心翼翼地把西词放在身后,却又无可遏制地冲决、突破,以至于毁灭……酒在继续,西词的位置一直空着。
酒杯在空中飞舞,所有人都醉了。而西词,回到了那方漆黑的小盒子里,然后回到泥土,回到忘却与遥远之中了。当天,我没有离开沙城。我在沙城近郊的一家宾馆住了下来。我觉得我有必要见南燕一面。我打电话给她,她说晚上过来。她语气低沉,声调平稳。我说你到了就打电话来,我去接你。她说不必了,她会找到的。
晚上八点,南燕来了。她依然穿着一袭黑衣,头发盘成了高髻。她面容有些憔悴,坐在沙发上,望着我,说:“西词真的走了。”“走了。”我说。 “我……我不敢想他。”“那就不想吧。何况他自己选择了,走了也好!”
“其实我该早一点发现他的问题的。或许还能……”“不说了。西词是个有主见的人,他这样做,也是为你好。”
“为我好?你是说西词是为我好?”南燕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张纸,说:“这是西词的遗书。我只想给你看看。看完了,便烧了。”我接过来,正要看,南燕说:“等我走了再看吧!我走了。”
我没有挽留,我知道有些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是某一种结果。我看着南燕的背影在走廊尽头消失,回到房间关上门。我打开西词的遗书。一张白纸,我只看见了一张白纸,一个字也没有。白白的,有些碜人。
在这张白纸下面,还有一张纸,南燕在上面写了一行字:他什么都明白,却只用死亡来回击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