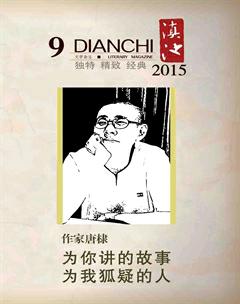四奶奶的遗愿
赵海萍
“苦蛋儿,你这小子发大财了!快过来。一定是你早死的娘保佑你咧!”说话的是上庄村里八大怪之首刘复生老爷子,他边说话边挥舞着一叠纸币。
“是啥?鬼票儿吗?”苦蛋儿哭丧着脸从当街的大碾盘上跳下来,他用一双脏兮兮的小手使劲拍打腿脚下摆裸露着棉絮的棉裤。于是,尘土像细细的烟雾向周围扩散。
“傻,你看不出来吗?你还分辨不出鬼票的颜色和形状吗?这是钱!四奶奶留给你的!八百九十二元四角,一笔不小的数目呢!”刘复生老爷子在距离碾盘十来步远的地方站定,破云而出的太阳将挟裹着寒雾的光芒洒在他的脸上。
“啥,八百九十二元四角?给我的!四奶奶给我的吗?她不是刚死掉吗?死人咋给钱?”
就在半小时前,四奶奶的桐棺被十几个壮汉抬到黑峪口的刘家坟地下葬了。那口棺材的板子只有三寸厚,红漆刷得也很潦草,棺材前面的“高登云路”图像是无师自通的哑巴张画的,关于哑巴张怎样无师自通地会画“高登云路”图像,上庄村最年老的刘复生老爷子也不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由此成为未解之谜。
哑巴张是画“高登云路”图像的高手儿,他只给本村故去的人儿画,外村人即使出重金也请不动他。“高登云路”图像为这幅下等桐棺增添了分量;黑峪口的刘家坟地背山临水,硕大的苍松长年累月守护着这块供死人永久安眠的土地;黄鹂和松鼠是枝头上的常客,它们将愉悦的歌声和灵敏的跳跃奉献给这些孤独的灵魂。
“傻,她临死前交代的。苦蛋儿,你到底要不要,你要是不要,我就拿去买旱烟抽了。”刘老爷子做出转身模样。
“我和她不沾亲不带故,我不要!再说四奶奶还有活着的儿子呢,刘长富不是他儿子吗?我见他披麻戴孝来着。”
苦蛋儿突然想起十年前,那时候他四岁,他也像刘长富一样被女人们用白布五花大绑着为一口未上漆的棺材送行。他看见身体僵硬的母亲被塞进棺材,棺材底部是黑底红牡丹花的崭新褥子,母亲的脸被白麻纸盖着,据说很恐怖。
母亲是上吊死的,早前,苦蛋儿曾看到母亲往门框上栓绳子,母亲冲他温柔地笑了笑,那个笑容是母亲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副表情。
“你去和小黑狗玩吧,他在屋后的沙窝里晒太阳呢。”母亲就这样从容地支开了他,他回头看的时候,母亲正在为绳子打结,脸上绽放着慈爱的笑容,她朝他挥挥手,那意思是“去吧,快去吧,断尾巴的小黑狗在等你呢!”
那是一只生机勃勃的小黑狗,尾巴被狠心的父亲用火钳弄断了,它偷吃了半个馒头,狠心的父亲不能宽宥它的过失。小黑狗没有因为被剪断尾巴而忌恨这一家人,一如既往地看家护院,即使忍受饥饿和责打,也丝毫没有将作为奴才对主人的忠诚亵渎半分。小黑狗看到苦蛋儿从斜坡上爬上来,它兴奋地摇着屁股起身迎接他,并欢快地舔他的脸蛋和小手儿。潜藏、进攻、厮打,他们玩了好久好久。当苦蛋儿感觉饥肠辘辘的时候才想起母亲,但那时那个患上忧郁症且小心眼的女人已经在自家大门上吊身亡。
他看到母亲直挺挺躺在卸掉的门板上,脸上盖着白麻纸。他刚想揭掉这讨厌的白麻纸,就被一个手脚利索的女人拦腰抱住了。他迷瞪瞪地看着姐姐跪在门板边的黄泥地上哭,不知道她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父亲坐在屋子里唯一的杨木椅子上抽烟,他铁青着狭长的黑脸,旱烟使他止不住咳嗽,粘痰像初春的花瓣覆在黄泥地上一大片。
“喂,小苦蛋儿,想什么呢?四奶奶留给你的钱到底要不要?”刘老爷子转身欲走。
“四奶奶说啥了没有?”苦蛋儿超前迈了一步,从他怯怯的脚步判断,他对这从天而降的喜讯不太信任。
“说了,她说你是个善良孩子,要用最后的八百九十二元四角奖励你。”
“呜呜呜……”苦蛋儿突然哭了,哭得很伤心,像十年前跪在门板边黄泥地上的姐姐那样。
“哭啥哩!没出息。”刘老爷子回过身把苦蛋儿扯进自己怀里,用粗拙的大手使劲抹掉苦蛋儿脸上的泪花。
“呜呜呜……爷,我不配得到这些钱。您把这些钱转交给刘长富吧,毕竟他是四奶奶亲生的儿子。我对不起四奶奶。”苦蛋儿哭得更伤心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死人的遗愿。四奶奶认定你是善良的人,一个将死之人是不会看错人的!蛋儿,你怎么也比刘长富强吧。那个龟孙子,要不是怕四奶奶的丧事过于冷清,再加上村支书从中周旋,他能披这麻,戴这孝?龟孙子!丧良心的龟孙子,他连一口吃食都没给他娘送过,他甚至谩骂给他娘送饭的街坊,四奶奶是活活儿被饿死的,她做了饿死鬼!”说这话的时候,刘老爷子按捺不住涌起的怒火,苦蛋儿能感觉到他的心跳明显加快了。
苦蛋儿给四奶奶做过伴,在她摔坏腿的两个月,他几乎天天从那扇临着小巷的窗户爬进去。那扇窗户距离地面一米多呢,但因为石砌的房子有突起,他踩着那些突起很容易上去。四奶奶家的窗户是没有木格子的两扇小门儿,她每晚敞开着小门儿等苦蛋儿进去。
苦蛋儿不敢从正门堂堂正正地走进去,害怕刘长富的拳头和凶巴巴的目光。有一次,他拧着苦蛋儿的耳朵,把他拎到那棵碗口粗的小榆树下,用尼龙绳将他和那棵树缠在一起。他爹找来的时候,苦蛋儿连哭的力气都没了,他爹气急败坏地用镰刀割断绳子,和刘长富扭打在一起。他不能眼见自己的爹吃亏呀,抓起一块冒尖的石头,朝着刘长富的屁股狠狠砸去。一石头下去,刘长富就老实地放开了他爹。
苦蛋儿挣脱刘老爷子的怀抱,重新坐回到碾盘上。
刘老爷子紧挨着苦蛋儿。碾盘左侧是一户人家的猪舍,猪舍很矮,用不规则的条石垒成。一头背毛全白、鼻筒长直、耳大前倾的长白山猪静静地躺在猪舍里侧的麦秸堆上。由覆盖在猪舍上方的破油毡可以断定养猪人是个利索、善良的女人。碾盘正对面是公路,四奶奶的灵棚就搭在公路最宽阔的地方。现在,几个壮年男人正在拆卸灵棚上的白帆布。随后,他们将木桩子拔出平放在地上。
“蛋儿,听说你从家里偷米给四奶奶熬粥喝,有这事没?”刘老爷子攥着那一叠破旧的纸币,他想尽快完成一个孤老婆子的遗愿。
“四奶奶家里除了土炕和灶台什么都没有,哦,不对,有一张观音菩萨像,很破,观音菩萨的裙子都没了。我就知道菩萨不管用,她能保佑什么呢,何况她的眼珠子都被刘长富抠下来扔进灶膛了。最开始的时候,四奶奶给我纸币,叫我跟她作伴,那时候她还能勉强把身子挪到大门外。我路过的时候,她经常叫住我说:‘来跟我作伴吧,我给你钱。我不是为钱,是真想陪她。我愿意听四奶奶讲故事,我在家也是一个人,我爹是个酗酒赌博的疯子,整夜整夜在村西头的张寡妇家鬼混,我也害怕呀,夜又这么长。和四奶奶做伴是最快乐的时光,但她也骗我。”苦蛋儿揉了揉鼻子。他的小脸被懂得通红,清澈的目光出奇地明亮。
“四奶奶咋骗你了?”
“四奶奶说每天给我一块钱,她红口白牙说的。但第一天早起,我向她讨要一块钱的时候,她让我等到第二天。第二天又说等第三天。到第七天的太阳升起,照到铺盖卷儿上的时候,她说,‘小苦蛋儿,你过来,我给你钱。那时候我多么兴奋呀,我把身子伏在她头部上方,她仰着脸看我,很虚弱,眼窝深陷,皱纹胡乱折叠在一张黑黄的脸上。‘七块钱,四奶奶。为了怕她多给我,我提醒了一下。她说:“你靠近一些,把手伸过来。我照样做了。”
他看到她脸颊轻微蠕动,但不知道她是在攒唾沫呀!
四奶奶朝苦蛋儿的手心吐了一泡口水。
“哈哈,小苦蛋儿。被四奶奶坑了吧?”刘老爷子捋着胡子笑了。
“嗯!我怎么也想不到四奶奶把攒下的一大口唾沫吐在我的手心里!爷,你说气人不?四奶奶怎么能这样呢?”苦蛋儿皱着眉头,仿佛手里又攥着四奶奶的唾沫。
“后来呢?”
“后来我生气了,掀掉四奶奶身上的破被子,想拿棍子打她,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四奶奶整个两条腿烂掉了,肉变成黑色,恶臭恶臭。我把被子盖上,唉,自认倒霉算了。大不了以后不和她做伴,让鬼怪吓死她得了。”
刘老爷子长叹一声,他告诉苦蛋儿,四奶奶三十年前被人抓去开会,当场打断腿,就那样残废了。
从此,苦蛋儿经常从窗户翻进去,把家里偷来的一小把米放进锅里,熬粥给四奶奶喝。她勉强能喝点粥,苦蛋儿想,只要能喝点粥,她就不会很快死去。
那晚四奶奶讲了一段捉蝎子的故事,是她自己的。
她说,有一次去魔石沟捉蝎子,一条虎斑游蛇受到惊吓,钻进了她的裤腿。她吓蒙了,凉飕飕的蛇身钻过束腰带,一直向上爬。她甩掉上衣,那条蛇竟然没被甩走,爬到她的后背。蛇尾巴像花布条一般,搭在她的前胸。她顾不得那么多,把浑身力气用在右手,右手像钳子一样抓住蛇尾,狠狠甩出去。哐啷,蛇不见了,地上掉下来一堆钱,一地的银元,老辈人用过的银圆宝啊!可惜啦,可惜啦,那钱现在已经不能用,要不然,四奶奶的日子就会更好过。
四奶奶讲得真好,她脑子里有很多好故事。
四奶奶也有点钱,她的钱不多,几百块是有的。
就在那天早晨,苦蛋儿在枕头底下发现十元钱,他本想还给四奶奶,但她紧闭着眼睛睡觉,就不敢打扰。后来,他把十元钱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他感觉自己像个贼,但想到四奶奶吐在自己手心里的唾沫,也就觉得这钱该得到。再后来,他在被窝里、炕席下、灶台旁,发现过几次十元纸币,都把它们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当然,他没白花那些钱,他给四奶奶做过几次炖肉,虽然炖得不好,但四奶奶吃得很香。
每天喝罢粥,他就用温水给四奶奶擦洗身子,这项工作是从第九天开始的,苦蛋儿想,拿了人家的钱,总应该做点实事。四奶奶瘦得不像样子,肋条一根一根地暴露着,前胸上两块软塌塌的肉,像小布袋一样垂下来,每块肉上都有一颗小黑枣。她的背上整齐地排列着三大颗肉瘊儿,每次擦过那些肉瘊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些异样。”
“小苦蛋儿,这钱你收好,八百九十二元四角,吃饭不够吃多久,但能给你胆量,让你做好多梦了。”刘老爷子硬把钱塞到苦蛋儿手里。
苦蛋儿用手抠着磨盘上残留的玉米皮,迷茫地望着搭建在公路边的四奶奶灵棚。此时,白帆布和木桩已被清理干净,只有剩余的烧纸被风吹得七零八散。
一阵疾风吹来,猛地把苦蛋儿惊醒。
眼前的公路和四奶奶灵棚全部不见,身边的刘老爷子也不见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