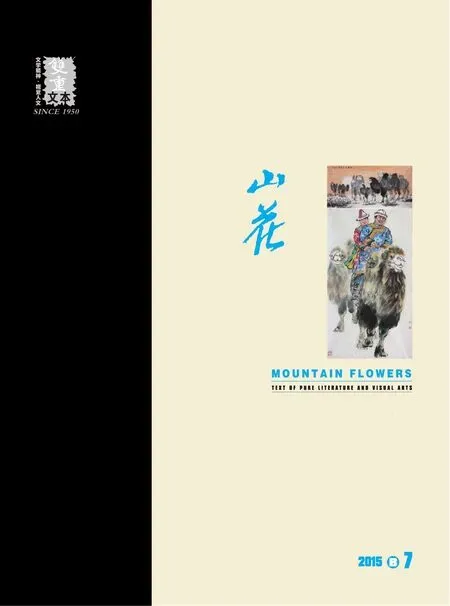中国文学研究中“史诗情结”问题:表现与原因
史诗是指以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古代长篇叙事诗,属于叙事诗的范畴,是不可重复的一种民间文学形式,它是“诗性的历史”。一部史诗是一座民间文学的宝库,是认识各民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能否拥有一部伟大的史诗往往成为衡量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准。
“史诗”同“神话”一样,是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进入中国学术视野的。史诗这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是西方文明的骄傲。黑格尔曾断言“中国无史诗”,面对这种情况,中国一些学者产生了强烈的反应。王国维、鲁迅、胡适、茅盾、陆侃如、冯沅君、郑振铎、钟敬文、饶宗颐、张松如等学者对中国史诗问题进行过专论探讨。这些学者对中国汉民族文学中是否有史诗,以及史诗在汉民族文学中为什么不发达的原因等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很长一段时间,学者们对中国史诗的研究围绕汉民族文学有无史诗的问题展开,从而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焦虑和一个解不开的结。就像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国家和民族会有一种“诺贝尔奖焦虑症”一样,尚未发现中国汉民族史诗的研究者们,也难免有一种“史诗焦虑症”。到现在为止,一些研究者还没有停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他们都把很多精力放在对史诗问题的纠缠上,无法释怀,这也使中国上古文学的研究长期为史诗问题所困扰。这种“史诗情结”不仅对中国史诗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研究。
“史诗情结”的表现
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叙事诗、史诗的发展“尚在幼稚的时代”,中国的叙事传、史诗及戏曲等叙事文体,都是和西欧无法比拟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然自古以来,终不闻有荟萃融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者,第用为诗文藻饰,而于小说中常见其迹象而已。”可见鲁迅也是感叹中国不具有希腊那样宏大的史诗,只是觉得在中国小说中可以窥见一点史诗的迹象;胡适曾认为《孔雀东南飞》是“史诗”;茅盾认为,中国古代有史诗,只是逸亡了,他认为《蚩尤》二卷或许是一部“史诗”,题材是‘涿鹿之战,也有英雄人物,如黄帝、蚩尤等,只是这本书没有流传下来;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认为将《诗经·大雅》里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及《大明》五篇组合起来,可成一部“周的史诗”;现代著名的文学史家,例如闻一多、刘大杰、朱东润、李长之等也都认为中国上古有史诗。郑振铎1923年在《诗歌的分类》中认为史诗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长恨歌》也可算史诗,1953年,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歌传统》中又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史诗,是因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像荷马那样的诗人,中国的远古神话片段未能熔炼成史诗;钟敬文认为,中国远古神话是很丰富的,但并不零碎,而是“散亡”了;八九十年代之后,学者们认为中国汉民族文学中没有史诗,饶宗颐曾提出一些理由解释汉族未见有史诗传世的原因,张松如也认为古代中国没有史诗。
20世纪之后,仍然有一些研究者在努力探讨中国有无史诗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史诗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主要是因为我们受西方学者的观点影响,用西方的史诗概念来衡量东方农业民族的史诗。如嘉应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应斌就认为《诗经》中很多都是史诗。不仅包括《诗经·大雅》中的五篇作品,而且认为《小雅》中的部分颂神诗也是周人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学者为了弥补“中国无史诗”的缺陷,借用人类学方法,发掘和重构中国上古史诗,如叶舒宪的《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
“史诗情结”产生的原因
史诗问题是20世纪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用西方文学起源和发展模式来解释中国文学产生的。所以要探讨这个问题形成的原因,就必须把这个问题拿到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流与冲突的大背景中来考察。
1.中西文化碰撞中产生的文化焦虑
19世纪末,中国文化开始与世界文化汇合,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中各种因素导致了“中国意识危机”。西方文化的侵入使中国固有的文化系统以及中国人的心理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在强大而陌生的西方文化面前,很多人一下就变得不知所措,似乎失去了方向,继而开始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产生焦虑甚至是怀疑。他们担心在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学会丧失自己崇高的地位,失去自己原有的优势。众多中国学者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中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焦虑感:一方面害怕西方文化的强势压倒本国文化,另一方面又担心本国的文化乃至文学不能与西方相抗衡。他们既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又有相当深刻的文化生存危机感。中国学者们一直都有强烈的自豪感,但同时也有强烈的焦虑感。一方面他们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与文明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另一方面当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冲击时,他们又感到非常焦虑,身上的自豪感和骄傲感也随之动摇。在强大的西方文化面前,他们突然感觉到一种无所适从的担忧,甚至是茫然和畏惧。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不知如何开口说话方为得体。实际上这种心理的形成也是某些学者缺乏自信的表现。
中国一些学者的这种心理焦虑在文学研究中就有很深的体现。西方文学的源头是神话、史诗,尤其是史诗,规模宏大,长篇叙述,运用艺术虚构手法,描述了本民族的英雄人物和伟大事迹,结构宏大,充满着幻想和神奇的色彩,史诗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是人类在特定时代创造的高不可及的艺术范本,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西方文明的骄傲,它直接孕育了西方文学,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文学模式,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是这一符合西方文学现象的模式被借鉴到中国,就出现了问题,中国的典籍中并无史诗这样的诗歌体裁,就连神话也是少有记载。这些相对于西方强大的史诗传统来说是非常欠缺的。在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中,中国的一些学者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焦虑,为中国不具备西方那样伟大的史诗作品而焦虑。焦急之中他们就立即到史料中去寻找中国的史诗,他们固执地认为中国文学中肯定有这样的伟大作品,只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而已。既然神话和史诗是西方文学的源头和范本,那么中国也不例外,也应该有这个源头和范本,中国文学也应该像西方文学一样是通过神话、史诗这个源头发展而来的。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地想找出代表中国文学源头和范本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来向世界证明“别人有的东西我们也有”,无形中他们在心理上就形成了一个结,一种渴望史诗的“史诗情结”。
2.对西方文学权威的无条件认同和跟从
20世纪初西学东渐,西方文学带着新颖、科学、进步的优势传入中国,在这个西学滔滔的大潮中,中国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家普遍认为一定要与时俱进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潮流和步伐,才能发展和进步。 “史诗情结”就是在这个学术大背景下产生的,就是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产生的。
神话、史诗是希腊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起源,在西方文学中已经成了不易的定式,成了一个普世性的原则,成了衡量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权威。中国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文学起源的普遍模式应该适合中国。他们迫不及待地用这个文学权威来衡量中国的文学,当他们用神话、史诗是文学的源头来解释中国的文学起源时,就出现了问题。如果按照这个西方文学的起源模式来解释中国文学的起源的话就会遇到很大的困扰,因为中国汉民族文学中没有史诗,若用此模式来解释的话中国文学起源将会只是苍白的一页。学者们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的,于是他们就用各种解释和说法来自圆其说。神话、史诗是西方文学的源头,而中国汉民族却没有史诗,怎么办?为了证明我们的文学也像西方一样从神话、史诗发展而来,学者们就想尽办法来证明中国汉民族文学有史诗。他们对《诗经》、弹词、通俗小说、汉民族活态史诗的史诗因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以此找出汉民族史诗。
的确,神话、史诗是西方文学的源头。但西方文学不代表世界文学,个别权威不能代替普遍性准则,在寻找中国文学源头时,我们搬用了西方文学观念模式,我们自己将本属“特殊性”的西方想象成了“普遍性”的西方。于是就把自己主动排除在了世界之外,把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也排除在了真理、权威之外,从而导致一些学者产生了比附西洋学术、比附西方的文学观念的做法,自然而然地就把西方文学当成了真理和权威。而自己的优势就完全丧失,成了西方权威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中的这种“低势态”与西方文化“高势态”的悬殊差异就使得一些人更加盲目地追随西方,而不能清醒地看到实际问题。正是由于这样才产生了绵延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史诗问题,也正是这样才使一些学者陷入这个问题中无法走出来。如果没有普遍主义的、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文学标准,问题的提法可能就不同了。比如,为什么古希腊没有产生《离骚》这样的长篇抒情诗?为什么古希腊没有产生《战国策》这样的历史散文?等等。只有在隐设和接受了以西方文学为一切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标准这一理论前提,才会有中国汉民族文学何以缺少史诗这样一种提问方式。除了中西文化碰撞中所产生的文化焦虑的原因,“史诗情结”也是由于在西方“学艺权威”笼罩下,用西方的文学起源的观念和普遍标准来解释中国文学的源头所造成的。
少数民族史诗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并不缺少史诗,换言之,即使中国没有史诗,也不重要。史诗是西方文学的起源模式,代表西方文学的较高成就。我们虽然没有出现像荷马史诗那样伟大的叙事作品,但出现了《诗经》《易经》《春秋》《论语》《庄子》《孟子》《离骚》等带有原创意义的文化经典,它们对我国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即使我们汉民族文学中没有史诗,我们也有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文学样式和文学遗产。就连认为“中国没有史诗”的黑格尔在他的《美学》著作中也承认:“中国的一些小说和传奇故事很丰富,很发达。……这些本身完美自足的作品所表现的整个艺术使我们今天读起来仍不得不惊叹。”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曾经说过:“只了解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也不了解。”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只用一种文化、文学为标准,其实我们什么文化、文学都不能真正了解。因此我们要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从民族文学特点来认识和分析中国文学,发掘其独特价值。不必因中国叙事诗歌的短小精悍而丧气,也不必因为没有出现荷马史诗那样的宏大作品而感到遗憾。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一个国家的文学也有它本身的特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典范,各自的文学发展道路也不一样。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不同民族之间文学的差异,尤其要注意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学以及本民族的文学特色。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由文化自觉而获得文化自尊,进而发展和复兴包括文学在内的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王国维.文学小言[A].王国维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235.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A].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
[3]茅盾.茅盾全集(第30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37.
[4]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下)[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845.
[5]杨兴华.史诗阙如与文化垄断[J].西北师大学报,2005(3):30-33.
[6]黑格尔著.美学(第三卷下)[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陈友康.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J].宁夏大学学报,1997(1).
[8]林岗.二十世纪汉语“史诗问题”探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9]刘方.中国美学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型[M].四川:四川出版集团,2005.
[10]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1]苏丁.中西文化文学比较研究论集[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
高连凤(1980— ),女,湖南常德人,硕士,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化、民俗学(含民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