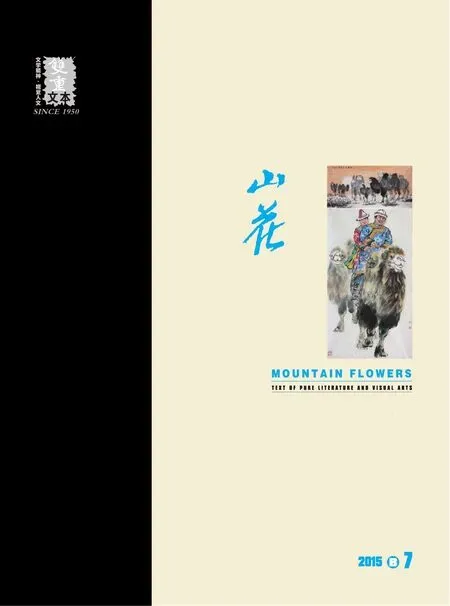在海边
王月鹏
他在自家院落栽下那棵幼槐,已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在这座工业新城边缘,黄沙漫漫,海风寂寥,没有人留意一棵树在某个院落的成长。几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林立,人气越来越旺,特别是夏日夜晚,海边栈桥成为这个城市的休闲之地。他把那棵幼槐从自家院落移至海边,栽在距离栈桥不远的地方。移栽当天,他举办了郑重的仪式,我是后来从录像资料中看到当时的情景的,隔着时间和屏幕,依然能强烈感受到他的虔敬。这是一个心有敬畏的人,他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对于这片土地的深爱。在蓝天与大地之间,在海边,这是一个人的仪式。那天一只喜鹊停留在树梢上久久不肯离去,像是被眼前这个简朴的仪式所感动。幼槐的周围,是护墙。他没有把一棵树直接推向海边,选择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在对风浪有所遮挡的地方,让一棵树安心地扎根成长。成长是一件具体的事情,需要经风历雨也需要关爱呵护,他默默关注这棵树,每天早晨都要去看一看它,绕着树走几圈,在同一个位置亲手给它拍一张照片,不管如何忙碌,这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他不仅仅种下了一棵树,而且每天都牵挂和惦念着这棵树的成长,每天都去看一看它,记录这棵树每一天的成长与变化。我时常在想,在繁忙的现实冗务中,他对一棵树的惦念一定赋予了信仰意味,他的心里一定有某种东西在伴随那棵树一起成长,每天迎着朝阳走向海边,去看望一棵树,他在行走的过程中,精神越发明亮起来。他远远地打量那棵树,有时候走近了抚摸树的枝叶,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海浪声中,他甚至能听到树在拔节的声音,像是与他的心灵对话。他听懂了。一棵树,与大海朝夕相伴,他听到树的身体内部的潮汐,那是生命生生不息的召唤。大海的浪花与树的绿叶遥相呼应,一如他与大海彼岸遥遥相望,这种最沉默的语言,可以诠释世间最浪漫的事。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曾经说过,因为自然的某种状态而唤起的感动,是他创作诗歌最重要的内核,每天早晨他都会到院子里散步,曾经有一整年他在早晨同样时间、同样的位置,以院子中央的一棵枫树为中心,拍摄院子里的风景,300多张照片做成一个相册,记录下院子里的每一个清晨。作为诗人的谷川俊太郎,在他的取景框里以一棵枫树为参照,对周边风景做出取舍和判断。这也让我想到身在海边的他,对一棵槐树的移栽和关注,他不仅仅是在培植风景,他在关注生命本身,以生命关注生命,在一个人与一棵树之间,存有某种隐秘的精神关联。那棵槐树一天天拔高,渐渐超越围挡,露出葱郁的树冠。它看到了大海,看到永不疲倦的潮汐声的来处。作为一棵树,它的根已经足够扎实,可以独自应对来自大海的所有风暴,它将见证大海所见证的,细密的年轮将会刻满这个区域成长演变的密码。一棵树,以年轮的方式,留存成长的记忆,刻下关于风雨和梦想的印痕。他在这棵树的身上寄予了一种期望,让这种期望在缓慢的成长过程中渐渐实现,这样的寄托方式显然不符合当下急功近利的风气,大家早已习惯了速成,习惯了拔苗助长,恨不得一下子省却所有的过程。他拒绝这样,在一棵树的缓慢成长中渐渐走近心中的梦想。缓慢让他心安,一个懂得速度的人,也深切体味到慢下来的真谛。他注视一棵树,注视它的缓慢成长,这是一种价值观,一种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独特理解。他并不期望所谓的理解。他只是在做着,按照自己的方式,他相信当这棵树葳蕤蓬勃的那一天,将是他最感欣慰的日子。立村必先植槐,他在这里扎根,把大海当作故乡。他忘不掉故乡村头的大槐树,那是整个童年的记忆,在大槐树的护佑下,他一天天长大。如今村庄的树木越来越少,到处都在上演大树进城的当代寓言,他栽下一棵幼槐,在自家院落,在海边,在异乡,体味整个成长的过程。他把这片居住地当作自己的故乡,亲手栽植一棵槐树,向遥远的故土致意,在日新月异的生活里,这份记挂传统的朴素情怀有着最动人的力量。他是一个沉潜的人,一个对生活对生命有敬畏心的人。这世上,很多的人在忙碌着,很多的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和抱负,但是心怀敬畏的人委实不多。关于一棵槐树的林林总总,我是在偶然的交谈中获知的,一个人如此郑重地对待一棵树,这让我感动。每次散步路经栈桥,我都会特意走过去看望那棵槐树,在它的身边默默站一会。它天天依旧。在天天依旧的状态里,突然有一天,我发觉它长高长粗了。成长是一个缓慢的不可逾越的过程,明白这个过程,并且懂得体味这个过程,才算是彻悟了人生。
我并不懂得人生。我只是一个对生活有追求也有抗拒的人。
我们去参观的规划展览馆被誉为那个江南城市的会客厅。以客人的身份进入会客厅,我被不安感深深攫住,高科技堆积出的幻觉,还有大地上发生的那些事情,完全被虚拟化了。我的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隔着一层说不清的什么,小心翼翼地走在展厅,生怕脚底下一脚踩空。向前三十年,向后三十年,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浓缩并展览在这个空间,我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念头。那些冰冷的数字化表达方式,它们切割你,将你分成若干份,每一份都有你的影子,每一份都已经看不出一个原本的你。我想回避它们。它们拒绝回避。
从展览馆出来,感觉自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恍若隔世,现实的世界不再清晰。南方的冬日并不寒冷,阳光淡淡地照在身上,有些冷意。我在展览馆门前的空旷地带踱步,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很快就留意到两棵被包围在脚手架里的老树。是两棵香樟树,在这个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树种,只是这两棵树看上去更苍老。许是“主人”对树的造型不太满意,他们围着树冠搭起了脚手架,树的枝杈被捆绑被固定在冰冷的钢管框架里,就像颓然的囚徒。那些钢管在树身周围密密地交织着,像是对一棵老树的不放心,又像在别出心裁地托举和矫正着某些枝干的形态。我恍然明白,这是两棵被绑架的树,他们希望这两棵树按照他们的设计和要求去成长,最终符合更多人的观赏眼光。远远打量这两棵被囚禁的树,冰冷的脚手架让人恍然觉得进入了一个建筑工地,这类建筑工地正在遍地开花。两棵香樟树,被移植到了这个广场的展览馆门前,就像平地拔起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是冰冷的,没有丝毫温情。
两棵被展览的树。
两棵被绑架的树。
脚手架的存在,是为了让树木按照他们的预设来成长,这让我感到无限悲凉。这样对待一棵树,即使再光鲜再标致又有何用?倘若缺少对生命的起码尊重,所有言行都是经不住追问的。我回过头来,重新打量矗立在眼前的展览馆,它是静默的,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
当地的朋友问我:“你喜欢这两棵香樟树?”
我摇头,不语。我不喜欢被展览被绑架的树。我所关心的,是一棵树的命运。这些命运被谁决定,凭什么就这样被决定?一棵树也是有生命有尊严的。从一棵树上,我看到了人类的影子。一棵经风历雨的树,自然懂得季节的意义,懂得顺其自然的意味,在常人目力不及之处,它看到了人的未来样子。
后来,我在安徒生童话中,读到了关于树精的描写。安徒生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言了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树精》中写道:“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童话的时代。”
这样一个童话时代,总在上演一些真实的故事。
一个依附于栗树的树精,梦想着到豪华富贵的环境中去,每天黄昏,她都朝着巴黎的方向望去。这棵梦想去巴黎的树,终于有一天告别自己脚下的土地,向着日思夜想的城市而去。一个声音,像末日的号角一样响起:“你将到那个迷人的城市里去,你将在那儿生根,你将会接触到那儿潺潺的流水、空气和阳光。但是你的生命将会缩短。你在这儿旷野中所能享受到的一连串的岁月,将会缩短为短短的几个季节。可怜的树精啊,这将会是你的灭亡。你的向往将会不断地增大,你的渴望将会一天一天地变得强烈。这棵树将会成为你的一个监牢。你将会离开你的住处,你将会改变你的性格,你将会飞走,跟人类混在一起。那时你的寿命将会缩短,缩短得只有蜉蝣的半生那么长——只能活一夜。你的生命的火焰将会熄灭,这树的叶子将会凋零和被风吹走,永远再也不回来。”
这是对树精的忠告。这个声音在空中回响,丝毫没能改变树精对城市的渴望。作为一棵有根的树,她希望自己像飘浮的云块一样,可以远行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许多人带着铁锹来了。这棵树被连根挖起,装到马车上,向巴黎运去。这是快乐的旅程。这是期盼已久的旅程。这棵树的枝叶忍不住颤抖起来。她并不知道,自己爱上了一个虚无。
她被栽到了城市广场上。这里曾经站立过一棵树,一棵被煤烟、炊烟和城里一切足以致命的气味所杀死了的老树,当树精被运抵广场的时候,那棵老树刚被装在马车上拖走了。树精并没有意识到,她所目睹的这一幕,正是自己接下来的命运。
泉水,微风,甚至清新的空气,都离她远去。工业文明像一个蓄谋已久的伤害,等待一棵远道而来的树。钢筋混凝土的世界,以冷漠的方式接纳了这棵树。
“一切跟我所盼望的是一样,但也不完全跟我所盼望的一样!”树精陷入了矛盾,一种不曾有过的想法开始折磨她。在她的梦想中,既有对人的生活的向往,又有对云块的羡慕。云块是自由的,也是虚无的。树精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被改造的真实世界。回归的不可能,以及生命的枯萎,成为一件注定的事情。“上帝给你一块土地生下根,但你的要求和渴望却使你拔去了你的根。可怜的树精啊,这促使你灭亡。”风琴的调子在空中盘旋着,用歌声说出了这样的话。
十年前,我曾为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命名《远行之树》。我想象一棵树,既得扎根,又要远行,这是它只能直面的命运,也是它无法解脱的生存悖论。这里面有着一个人的犹疑和抗争。我把这些难以言说的情怀,托付给了一棵远行之树。那时我不曾想到,在若干年后的城市化浪潮中,树的远行会成为一个普遍现实。一双看不见的手,把大树从深山移植到了城市,在钢筋混凝土之间,一座座没有年轮的城市正在迅速成长。大树进城,大树的枝叶上蓬勃生长着的,是人的急功近利。被移植到城里的大树,在城市天空下支撑起另一片天空,这是正在被创造的所谓奇迹,是“拔苗助长”的当代版本。
树的渴望与人的欲望,在漫长的时光中交汇成为一个点。这个点逐渐地扩大,逐渐地有了光环,逐渐地被更多的目光关注,被更多的人提起,成为这个时代的热闹景象。
云块是在高处的一个虚渺存在。树精对云块的向往,让她最终成为地上的一朵残花,被人类的脚踩成尘土。我的那份曾经寄望于远行之树的遥远情怀,已成为某些人急功近利的一个注释。那些风尘仆仆的赶路,究竟是要去往哪里?
有生命的事物,是不该仅仅成为装饰品的。一棵经风历雨的树,被移植在钢筋混凝土之间,成为当代城市的一种点缀。这棵树的枯萎枝叶,把城市天空的倒影分割成了若干碎片。
如今,城市建设者纷纷把目光投向大树,依靠大树进城,快速营造城市的历史感。这是对自然规律的强行改变,是人的急功近利的最真实的表现。一个没有年轮的城市,一个无根的城市,所谓繁茂的枝叶,都不过是短暂假象。季节交替,当风霜雨雪走过,这个城市显露本来的荒凉面目,将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那年冬天,我时常去郊区看望那棵古槐。她的树干已经枯朽,谁也不知道她在村头究竟站了多少年。村庄正在拆除,她依然站在那里,像是一个对世界放心不下,心中怀有牵挂的老人。她站在那里,看着村里的人走出去,看着村外的人走进来,她已经没有可以迎风摇曳的树叶,失去了最真切的语言。她无声地看着眼前的这个村子,这个小小的村子,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她的整个世界就要消逝了……
我看到一个老人,站在古槐下,形单影只,像是从古槐身上折下来的一截枯枝。
这棵古槐,对这个村子是有恩泽的。我轻抚她的枯朽的树身,就像握住时光的苍凉的手。那一瞬,我是一个被时光遗弃的人,我比古槐更苍老。
总有一些故事,曾与这棵树发生关联。树是见证者,见证了一些在时光中流逝的事物。
一如此刻的我,是此刻的唯一见证者。
站在山顶俯瞰这个城市,我的心中涌起阵阵疼痛。那些苍茫的岁月,变得如此切近和清晰,我说不出这座城市之于我,以及我之于这座城市,究竟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我的牵挂,我的悲悯,我的无言的爱,消失在冰冷的钢筋混凝土之间。
做一个有着正常体温的人,如此艰难。
曾经读到某位作家写他如何在树叶上写诗的文章。在树叶上写诗,然后收集飘落的树叶,这究竟是浪漫还是矫情?即使作为对生活的一种理解方式,我也不相信它在现实中的可能性。我更愿意相信的是,一棵站在风雨中的树,它将风雨的洗礼,以及对风雨的理解,内化为生命的年轮,沉积到了根部。这种内在的力量,是一棵树坦然面对成长的资本。那对民工兄弟唱的《春天里》,我在网上一遍又一遍地听,忍不住热泪盈眶。所谓艺术,在此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与热爱,是他们以歌唱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一颗心。他们勾起了我对青春岁月的记忆,对当下被遗忘被忽略的现实的关注。我也曾经告别故乡,一个人在城市流浪,心怀梦想,对这个世界付出真诚与热爱。如今麻木多了,看起来我已把生活打理妥当,已经不必再有什么忧虑与牵挂,沉浸在一己情感里,不再拥有更为宽广的情怀。日常生活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我与若干个我作战,难分胜负,似乎战争才是唯一的选择,缺少一种更大的力,超越和掌控这样一个已经沦为日常的战场。
当我看到大海与广场连为一体,心底涌起一种悲怆感。空间如此辽阔,却不知该把一颗心放在何处?大海不合适,广场也不合适,我是一个海边的流浪者,大海和广场都不能让我停步。我走着,却不知将要走向何处,大海和广场也不知道。抗拒被裹挟,需要多倍的定力。我的方向在脚下,就像扎根,朝着大地的深处挺进;而枝叶,是朝着天空舒展的。
在天空与大地之间,一棵树正在远行。
我所要抵达的,其实仅仅是我自己。
如果一种刻痕,不能给我彻骨的疼痛记忆,当岁月的风沙袭来,我会茫然不知所措。直到有一天,我似乎理解了,他从自家院落移植到海边的一棵槐树,是他在苍茫岁月里的刻舟求剑,他在关注成长本身,遵循自然的规律,摒弃那些所谓的效率和效益,留下生命最真实的刻度。在城市化浪潮中,这个人在用心做着最纯粹的一件事情,一棵树承载他的梦想,迎着风与浪,一天天成长。当有一天,太阳从大槐树繁茂的枝叶背后升起,那样的一个瞬间,作为见证者的大海也将被打动。
我走向你,在一个白雾迷蒙的早晨。我沿着海边一步步走去,看不到栈桥,看不到那些熟悉的建筑群,眼前唯有一片白雾。我走向你,已经不再奢望白雾散尽,我所能做的,就是在太阳升起之前,一个人穿越迷雾,走到栈桥的跟前。在栈桥旁边,有一棵被惦念的成长中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