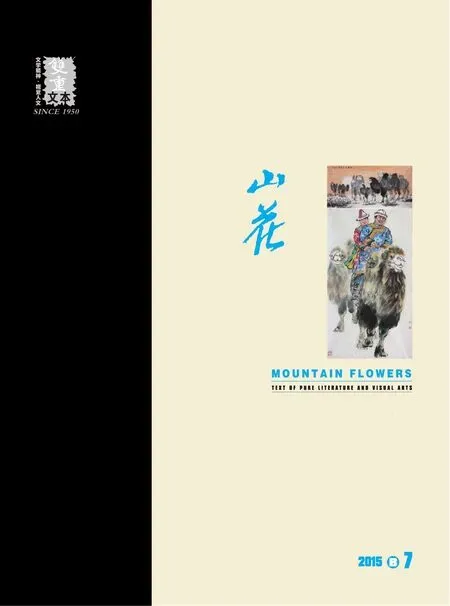乌江,那些远去的纤夫与船号
安元奎
虚拟的船号
如果十多年前来乌江,你还可以在江畔听到那些野性粗犷的船号。那神秘的歌吟,宛如乌江天籁,蕴含着一种亘古的悲壮与苍凉,总让你悲从中来,欲罢不能。而今,纤道和船帆已定格为永远的历史,那些船号一如历史的余音,正在幽幽远逝。
夏日的早晨,我们十余人按事先计划,去思南县城下游十多公里的大溪口搜集船号。会唱船号的老人,如今已是所剩无几了。
说是采风,结果却招来了雨。想起两千年前,为了编撰《诗经》,那些搜集各国国风的周朝采诗官,大约也免不了雨雪之阻——便冒雨从码头出发。江面一派迷蒙,机动木船像一只梭子,在茫茫雨帘中穿梭而行。
没多久就在大溪口靠岸。大溪口位于乌江东岸,不通公路。与之相对的西岸,上有飞珠溅玉的黄龙泉,下有曾发现神秘洞棺的彭家洞和崖下的桶井古渡。因为有一条溪水在此汇入乌江,大溪口由此得名。人家住得较为分散,不是江边那种大寨子。河岸的缓坡上,村长吕仕宣一家正在修建砖楼。
主人的热情都盛在中饭的杯盘碗盏里。菜谱有腊肉、农家菜,乃至价格不菲的乌骨鸡,就是没有乌江鱼,尽管乌江近在咫尺。究其原因一是处于乌江禁渔期,二是乌江里的鱼恐怕也寥若晨星了。几千年靠水吃水的乌江人,从饮食里也可感受到生存的变迁。
吃过饭,邀请的船工陆续到齐,但唱的地点却犯难了。想到江边或船上唱,天却一直下着雨;欲找一家宽敞点的堂屋,但吕仕宣说,在堂屋里闹,于乡风民俗有点犯忌,于是找了一个货店。唱船号的一共六人,他们是张羽生、袁海桥、吕仕宣、杨秀波、杨胜发、苏畅扬。
人未来齐以前,我们与66岁的老驾长张羽生有过简短攀谈。他14岁开始走船,在乌江上漂泊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思南禁止人工木船航运,才改业上岸。他的外貌颇有特点,鼻梁挺拔,鼻头微钩,有点像篙杆中的那种钩杆,脸上是浅浅的麻点。额头皱纹隆起,像凝固的浊浪。身子精瘦,背微微有点驼了,手脚粗大到近于不合比例。身着老式的青色布扣对襟,腰上拴一条白带蓝布的围腰,打着赤脚。胡须黑白参半,状如乱草。说话时嗓音粗大,中气十足。面容虽老,神情一看就是个老顽童。
我们问乌江上的船号到底有多少,他感到无法回答:“那就无穷尽呢,多得很。”又补充道:“从龚滩上来十二天,上大乌江六天。每天巴起来(方言,即起床)就闹起,一直闹到黑,你说要多少号子。”他习惯于把船号称为“闹”。我们请他先哼几句,他随口就“嗨也唑——,安含”地哼起来,很有乌江纤夫的那种专业味道,简直未成曲调先有情了。
另一位老驾长袁海桥有78岁了。他从民国时期就开始走船,在乌江上的年头比张羽生更早。来时戴着斗笠,也是打着赤脚,可能刚刚犁田回来。他身上也是老式蓝色布扣对襟,裤子或许也是白裤腰那种。天庭开阔,面部扁长,甚至有点凹陷。脸上也有些暗淡的麻点,这是天花的遗痕,据说患天花幸存下来的人大都长寿。性格平和内敛,落寞寡言,与张羽生形成有趣的反衬。
袁张二人是这些船工中的元老,其余算是少壮派。六人中有五人均曾长年走船,足迹上至余庆回龙场,下至酉阳龚滩。只有年轻的马店主人苏畅扬算是客串。
张羽生显然是那种性急的老船长,我们录音机尚未备好,他便急切要求“吼起来”。他没把船号说成文绉绉的“唱”,先说是“闹”,后说是“吼”,都有点生猛。而话语不多的袁海桥见采风的听众中有三位女性就特别声明说:“今天娘娘(方言读第一声,对姑娘的尊称)也在,号子就是乱吼呢。”他说的“乱吼”,意思是说有些船号的内容荤素都有,不大雅观。大家笑着说:不要紧,这些娘娘都是艺术家娘娘,船号一定要原汁原味。
静默片刻,一种穿云裂石的声浪骤然炸响。它从这些昔日的走船人口中奔涌而出,聚合为一种雄性的力量,让人荡气回肠。它分明就在眼前,却似乎来自遥远的蛮荒之邦,像受困的雄狮或狼群在旷野的哀号,像霹雳在峡谷或江面炸响。由远而近,由缓而急,由低而高,气势磅礴,苍凉悲壮。它撞击着我们被电子音响污染而钝化的耳膜,所有人都震慑于这种神秘的力量。低矮的屋瓦,竟然嚓嚓作响。
刹那间,我心中潮涌,有泪盈眶。我久违的乌江船号啊。
眼前这群人,当年他们赤裸着雄性的身躯,在乌江的陡滩、乱石、绝壁纤道间攀爬,从胸膛里进出的,就是这种摄人心魄的原始交响。这群乌江的民间歌手,古老纤道上的行吟诗人,他们的船号曾经在千里乌江激荡。
那领唱走在纤夫的最前列,独步荒野,迎着凛冽的寒风,顶着火辣辣的毒日,或不期而至的霏霏雨雪,或前瞻,或后顾,或照应,或呼喊。那悠扬的号子,更像一个孤独的灵魂在江畔且行且歌,吟唱着悲怆的宿命。
而驾长的帮腔,音色高亢、糙砺,如同京剧花腔里的二黄,呈现出一种旷世的苍凉。他并不步随纤夫们的节奏,而是像一个手舞足蹈的精灵,搅和其中,游离其间,来去自由。他有时唱的是优美抒情的地方小曲,有时又直接呐喊、吼叫,甚至谩骂,完全是随兴而起,没有固定程式。他似乎是对领唱的一种呼应,却又若即若离,若断若续。有时似在铺垫、帮衬、托举;有时却又猛然跳开,另辟蹊径。更像在插科打诨,夺二闲,唱对台戏。那音腔自由若流水,奔放如滩涛,飘忽不定,卓尔不群,仿佛一个行踪不定的乌江浪子,游离在故乡的边缘;又像一个桀骜不驯的灵魂,张扬着野性的情感。
而纤夫们的和声沉郁、厚重,顿挫有力。
“喂也——,安含!”
“喂也——,安含!”
他们反复着这样的咏叹,反复着这种有韵无字的原始乐章。咏叹突破了汉语的规范,只有衬字,只有叹词,却胜过狭义的万语千言。像看不见的深塘,翻滚的巨漩;像汹涌的暗流,吞噬一切的回水;像礁石中流击水,发出愤怒的轰鸣。忽而痛苦忧伤,忽而无奈彷徨,忽而又慨然雄起,气冲云霄。
所有的歌吟全部混合在一起,组合为一个雄浑的整体,浑然天成的乐章。你分明可以听到那桀骜不驯的主流裹挟着万千浪涛和旋涡向前奔涌,另一股回水却偏偏执拗地逆向而行,而最终又汇聚到一起,撞击峡谷,澎湃而去。它错综复杂,神秘莫测,像失败英雄的情怀。在船号的歌吟中,你眼前反复变幻着的景象也许是巉岩、绝壁、巨石、暗礁、滔天白浪、险恶的暗漩、断航滩、打烂的船板,是乌江那吞噬一切的神秘伟力。
乌江船号,这雄性的律动,原始的交响;乌江船号,这贯通天地的大音,天人合一的绝唱。
如果用现代音乐理论来解析,船号至少是由四个以上声部交汇在一起的,是一种自然天成的多声部乐章。唱的时候,六人进行了简单的分工。当然,他们的分工也是根据船上的职能。第一轮由杨秀波喊,也就是担任拉纤人中的领唱;张羽生撑,即帮腔;其余四人跟,即应和与合唱。后来进行了轮唱,第二轮由袁海桥喊,第三轮由张羽生喊,后来吕仕宣也喊了一回。从上滩号唱到紧水号、熬滩号,再到平水号、龙船调。这轮唱像西洋技法里的“卡农”,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每个人的音色不同,混合的船号也就有着不同的韵味。
每唱完一轮,就休息片刻。同行的老田、老吕赶紧从我们带来的大塑料壶里,倒出数量不等的散酒递过去给他们润嗓。他们先老后少地做些推让,然后都很受用地喝了,如是唱了三五轮。他们开初有些拘谨,在酒的作用下才渐渐放开,后来甚至是眯着眼睛唱。也许在这片刻里,他们暂时回到了逝去的岁月,回到了离他们生活航道越来越遥远的乌江。也许只有酒精才能引领人穿越生活的繁重与委琐,抵达性灵的本真与诗情。
张羽生本来就是最为投入,几杯散酒之后,更是完全进入了状态,富于激情,连我们都受到深深的感染。虽是坐在一条板凳上,摆出的却完全是老驾长的职业姿势,仿佛他在驾驭的是滚滚惊涛中生死悬于一线的一条船。整个身子重心前倾,头向下拽,略驼的背便高耸起来。随着节奏,身子极有弹性地一俯一仰,整个人都陶醉其中。他嗓音高亢,有喊有唱,中气足得如同正当壮年,韵味十分特别。袁海桥年纪大一些,中气就稍逊一筹。但声音醇和,韵味悠远,像陈年的米酒,度数不高,却也醉人。
其实,不同环境所唱的船号,有着不同的美感。当纤夫们拽着歪屁股船在长长的险滩上逆水而行,陷入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的困境,生死悬于一线之际,那熬滩号子是无比悲壮凄怆的。
遭孽莫过弄船人,
风霜雨雪路上行。
嗨也唑,安含!
嗨也唑,安含!
而一旦闯过激流险滩的死亡边缘进入平水,他们对生活的苦难又开始黑色地调侃:
大雨落来我不愁,
蓑衣斗篷在后头。
蓑衣还在棕树上,
斗篷还在竹林头。
乌江古航道上还有一种“另类”的船号,也就是那种内容有点“荤”的号子。我们要求唱一段这种原汁原味的号子,他们最初都不肯。那一直唱得风风火火的张羽生老人也显出几分忸怩,声调竟然柔婉起来,还偏偏地低下头,粗糙的手指极不自然地来回卷弄着围腰角,宛如一个初恋的农家后生,但有几颗麻点的脸上却挂着邪邪的坏笑。最后还是悠悠地唱起来:
远望小妹洗衣裳,
心中却在想情郎。
手里拿着捶衣棒,
心头不知想哪样。
天一棒来地一棒,
一棒打在指拇上。
其实这应当算是一首优美的民间情歌,对女子心态的描摹很传神,并无不雅之处。但后来吕仕宣唱的一首,的确就有点荤了:
大河涨水冲小河,
钥匙落在回水沱。
哪个捡到交还我,
脱了衣裳等他摸。
据说这些老一辈驾长、纤夫,在乌江航道上都有一两个关系暧昧的女性“干亲家”。于是在休息的间隙里,我们就试问一些玩笑性的话题。比如,你们曾经送盐巴给干亲家没有?因为在那时候,盐巴算得上贵重的礼物。他们都不好意思地笑着摇头否定,但那表情却暧昧而有趣。我们于是得寸进尺:半斤盐巴不够?张羽生趁着酒勇,抬起头来以问代答:“半斤盐巴你就想上坎喽?”那表情异常生动,目光炯炯逼人,惹得哄堂大笑,他自己也快活地笑起来。
但这群最后的纤夫今天的日子也许并不轻松。人工木船的禁航,把这些乌江纤夫逼向生活的边缘,属于他们的时代永远终结了。
乌江作证,当年那些悲凉的祈诉或呐喊,而今却在远离河床与纤道的地方,以一种虚拟的游戏形式重现,就足以让人惊讶于时空的错位与历史的落差。
唱到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杨秀波看了几次表,显然心里惦记着坡上的农活,有些心不在焉了。袁海桥的兴致也不是很高,他的儿子媳妇已全部“杀广”了,78岁高龄的他还要耕种全家田地并照看孙子,此时他的一头牛还拴在坡上。张羽生的儿子媳妇也都外出务工,家里的情况与袁海桥相似,但已有几分酒意的他一直兴趣很浓,还几次感谢我们今天让他这样快活,我却从他的话里咀嚼出沉重和辛酸。
几人当中,只有吕仕宣完成了纤夫的角色转换,在现实生活的航道上,只有他的纤拉得最远。他现在是村长兼护林员,唱船号时穿一身林业公安制服,臂上有“护林”字样,显出一种半官方色彩。他护林的功劳是有目共睹的。放眼乌江对岸,幼树已经成林,草地上几十只白鹭在那里闲庭信步,显然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自己正临江起楼,江岸还系着一条价值数万的机动船。
我们走的时候,这些昔日的纤夫用粗糙的手和不太习惯的姿势与我们握手告别,一直目送我们上了机动船。细雨之中,张羽生老人站在泥泞的坡地上一直挥着手,眼神里溢出一种失落与惆怅。
酒醒之后,他还会吟唱得那么潇洒和奔放吗?
明天,还有谁来听他的船号?
走船人的龙门阵
脚趾头踢落了都不晓得,个子瘦小的屈正林开了个话头。一年四季水草鞋,冬天大明霜、大下雪,放出去的纤藤结成冰坨坨收不回来了,都要下水。话语间,这个身体硬实的筋骨人,眉眼和颧骨的皱纹全都向鼻根那里聚拢,似乎记忆里尘封的痛苦依旧没法稀释。再找不到比走船更苦的活路了。他摇摇头,似乎要努力摆脱那些记忆。
纤夫们的话匣子,打开了古龙川30多年前的时光。
吓死个人了,两江口那回。80岁的敖廷举,走船生涯里不知多少次历险,但提起几十年前的往事,眼神依然拂过一丝余悸。他不时比画着当时环境的险恶:那旋涡几十丈宽,浪子比房子还高。从小河杀进大河的时候,船舵偏了一点没投到哨水(主流),就被扯进大旋涡。木船在大旋涡里头推磨,起码是几十转,就是转不出来。一点都不敢打闪火,拼老命划。他说,个个汗水都来齐了,慢一点就要遭吞,好不容易才摆脱。言谈间九死一生的庆幸。
那回又不吓人?屈正林抢过话头,提高了声调。从思南码头拉一个早上到镇江阁,那天涨水,发泡水像开锅,七柱六的房子大。钩竿钩不住,浪子把船又打回思南城,在一个回水沱才靠岸,白累了半天。
这是古龙川河畔一个名叫山羊岩的寨子,水绕山环,几十户人家临水而居。与水结缘,也就有了一代又一代走船人。
他们口中的大河与小河,就是乌江与古龙川。这两条河,也许就是他们生命的全部航道。在他们看来,只说大小即可,其他名字则是多余的。
30多年没跑了。在短暂的停顿间隙,一个平和的声音慢悠悠响起。屈正龙一直在吸烟,像一个胸有成竹的主角,选在一个恰当的时刻才不慌不忙登场。与众人的七嘴八舌不同,他身上有种处乱不惊的沉着。特意穿的青色新衣新裤,以及头上的新帽子,都在凸显他对这次交谈的重视。我那时是船长。他的自我介绍语速慢,但力道足。
我们原籍是重庆黔江双河口,听说我的公是摆摆箩挑来的,离现在也就百多年。
走了几十年船,没出过事。小河船一般要两人放前头(掌舵),我是一个人放,有那个把握。平平淡淡几句话,让人听出了几分自信。后来的叙述,也基本以他为主。
他的眼神穿过面前的袅袅烟雾,投向时间深处。
那时走的是木船。打船的料子主要是椿木和柏木。船头的拨桡有二丈四,尾桡二丈二。船后侧的侧桡一丈五,篙竿一丈五六,分篙子和钩竿。大船一般装2万4(千斤)。船上七个人,正副驾长,5个拉纤的。驾长的位置,以上下水而定。下水(顺流而下)正驾长在船头,副驾长在船尾;上水(逆流而上)副驾长在前,要是遇到搁浅,副驾长得下水去背。
过去有句土话:河边卵,无人管。为哪样走船人不穿裤子?走船人一下要下水,一下要上船,一会湿一会干的,穿裤子烧裆,还费布。
小河走船,上至石阡中坝,下到思南。思南靠船的地点有盐仓码头、月亮台、卢家码头等。上水拉盐巴和酒,下水拉粮食、生猪、窑罐。河头走船有时候只望得见天上,两边是个夹沟沟。小河有几个险滩,木根洞、鱼梁滩、野猪洞。野猪洞不远处的岩腔里有个天钩石,必须钩住,不然就翻船。从前有个姓张的红喜老爷打烂主意,想在雪坨开号口搞成屯户,就是转运站,让上下的船在他那点卸载。就炸岩腔,想堵塞河道。但天家不容,三炮只响了一炮,没搞成。
走船危险,规矩有点多。逢年过节,都要在船头的苏佬上烧香烧纸。敬的神有水府三官、镇江王爷、野猪洞王爷菩萨。禁忌也多,比如忌讳月母子搭船。说话方面,比如“翻、倒、沉”等字都说不得。在船上,起床要说成“遛动”,翻转要说成“会转”;倒水的倒,要说成“倾”;囥(kang三声)锅,就是盖住铁锅,但囥字有翻船的意思也说不得,要说成“罩锅”。
俗话说:“死人口,匠人言。说福不灵,说祸就灵。”打船仪式上,师傅的“封赠”更要紧。有回在钉木船封头的时候,主人家捉来两只鸡,要师傅选一只,说是重量差不多,“耪(pang三声)上耪下的”。耪就是撞呀,师父的脸就丧起了,主人家无意中犯了忌。师傅只得黑着脸在船头的苏佬上劈一开山(斧头):“上下都不耪!”听说后来还好,没出什么事。
另一回,船下水之前,打船师傅请个秀才来“赐封”几句吉言。那秀才讲礼,双手前拱朝师傅作个揖:“多承,多承。”“承”就是“沉”呀,师傅脑壳搭铁,也没把话圆一下,听说那船下水第一趟就沉了。
我五几年开始走,手上走烂3只船。70年代塘头四合坝修电站,闸阀坏了,就没走了。屈正龙最后做了个小结。并强调一句,没出过事。
接着是其他人的自由发言。68岁的敖顺富对于自己在船上的角色有点不好意思:我是推马门架的。屈正林笑着看他一眼,补充说,最得力的是前头3张桨,马门架是最后一张,作用不大。我18岁走船,是副驾长。
木船日晒水浸,寿命也就几年时间。敖廷举仰着头计算他走过的船,仿佛他的船在天上:麻阳船,石阡船,大船,小船。生产队4只,粮站仓库的2只。
他们回忆的细节,偶尔也有一些分歧。
敖顺富说,走船的都是大强盗,装哪样偷哪样。盐巴紧张时就偷盐巴,企鹅烟、糖果……
屈正林高声调打断了他的话:那我们怎么没差秤杆杆呢?
敖顺富说,把米汤倒在盐巴上,斤两倒是不差。
屈正林说,仓库里的糖果是保管员喊吃的。饼干遭老鼠吃过了缺角,叫我们放开吃。说完扭过头,不再看敖顺富。
屈正虎那时是队长,只有一次走船经历,插话不多。唯一的一次插话是:那回跟你们下思南。差点连老命都丢了。
屈正林诡笑道,那回你是去监视,以为我们享清闲,走船的都觉得气愤。后来你落水,我们还是把你捞起来了噻。
屈正虎倒显得大度。晓得你们是故意整我,但走船确实苦,回来还给你们加工分了嘛。
屈正龙又想起一些往事,做了补充。说是付家岩的船在石阡装米,装了一万八,撞到牯牛石,船底压空了,米散落河底,岩石缝缝都是米,河底白花花的。翻船后就私自撬了几包在河头,过后才去打捞。
又一回,粮站的人坐付家岩装粮食的船下思南。在镇江阁,浪子打来,船后头灌了半船水,那粮站的吓惨了,死命往船篷上爬。
我们走的是副业船,在队里拿工分。一天交队里一块钱,驾长走一回多得两块。那时米粉1角2一碗。中坝有个粮站,没通公路,河道里有槽口。船小,只能装6000斤,派烟票、粮票,样样供应。中坝人好,思南人不行。航管站站长诨名叫龚啰嗦,开会时一个人要讲几小时,翻来覆去,大家都烦他。走船人享受国家补助,粮票每天7两5,按月发。但到了思南,穿起草鞋上街,衣服臭哄哄的,拿起票和市民排队,遭人看不起。走船的安明化排队砍肉,排到了也不拿给他。他按住不动,好不容易才得到一块肉。
现在吃肉还不容易?我一天杀过六头猪,像切瓜瓜崽。还要剔肉,三四百斤的,一家三四箩。今年79了,挑100把斤有点吃力,不行了。
屈正林又想起一件自豪的事。70年代区里搞拔河比赛,我们个子小,开始没人重视,比赛才知道我们厉害,得了第一名。后来拔河都找走过船的人。说完得意地笑起来。
灯光下,火炉边,都是些沧桑的面孔。他们说,除了过年时节,如今寨子里平常见不到几个年轻人,都“杀广”了。敖廷举80岁,屈正龙79岁,屈正虎76岁,屈正林69岁,安元福、安世龙、敖顺文也都60多岁了。他们曾是古龙川的走船人,穿峡破浪如履平地,而今年老,成为寨上的留守者。
最后,他们唱起了船号。
不过,屈正林说,要竿竿拿起,索索套起,势子架起,号子才喊得起来。对于模拟喊唱,有些不以为然。当其他人准备差不多时,他还在说,摸到篙竿号子就出来了,或者用棕丝吊索扯起就展劲了,坐起不行。
但号子最终响了起来,轮流领唱的是屈正龙、敖廷举和屈正林。
一
情姐下河洗衣裳,双脚蹬在石梁梁。
右手拿起衣棒打,双眼盯住少年郎。
一棒打在指拇上,只怪衣棒不怪郎。
崴呴,崴呴,崴呴,嘿呴呴——
二
新打船儿铁箍头,上装芝麻下装油。
芝麻卖给打油匠,油拿卖给姐梳头。
大姐梳个盘龙髻,二姐梳个插花楼。
只有三姐梳得巧,梳个狮子滚绣球。
崴呴,崴呴,崴呴,嘿呴呴——
三
上得坡来坡又长,上到半坡土地塘。
土地面前三条路,不知哪条进花房。
崴呴,崴呴,崴呴,嘿呴呴——
四
上得坡来坡又长,半坡撞着娇的娘。
娇在旁边打抿笑,谅你不敢喊亲娘。
崴呴,崴呴,崴呴,嘿呴呴——
五
过了一湾又一湾,湾湾都是火烧山。
火烧巴芦心不死,路边丢郎心不甘。
崴呴,崴呴,崴呴,嘿呴呴——
六
清早起来把门开,一股凉风吹进来。
这个凉风是个怪,吹得大嫂几歪歪。
崴呴,崴呴,崴呴,嘿呴呴——
七
扯船之人没得祥,麻布巾巾勒颈项。
八匹篾条一样长,扯坏几多少年郎。
崴呴,崴呴,崴呴,嘿呴呴——
八
金竹篙竿铁打钩,钩了这钩钩那钩。
金竹篙竿一样长,钩坏几多少年郎。
崴呴,崴呴,崴呴,嘿呴呴——
这些号子的修辞和韵味令人惊异,但屈正林并不满意。他说,最好是撑起篙杆,身子在船上仰起担平,脚蹬得咚一咚的,那才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