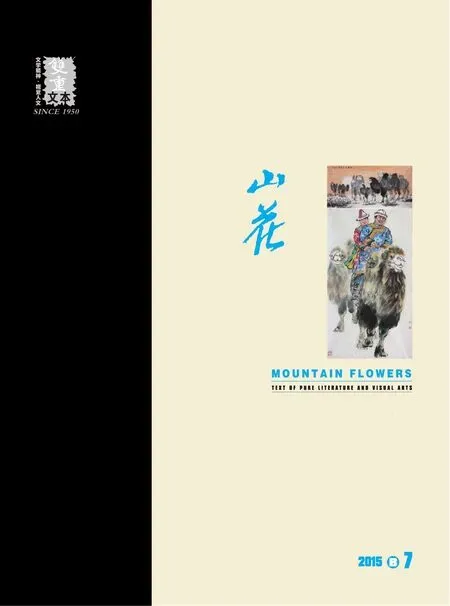理想破灭与理想重建
——论《一个迷途的女人》中尼尔的矛盾与蜕变
杨韩钰
理想破灭与理想重建
——论《一个迷途的女人》中尼尔的矛盾与蜕变
杨韩钰
薇拉·凯瑟是20世纪初美国著名女作家。凯瑟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擅长描写美国中西部边疆拓荒生活而著称。《一个迷途的女人》是凯瑟的代表作之一。从主题意义而言,女主人公玛丽恩·福瑞斯特和小说的讲述者尼尔是处于同一时代的两个人物;在他们身上读者可以看到时代的痕迹。玛丽恩·福瑞斯特这个在小说一开始就引入的已知人物,必须在变革中保护价值观。小说的讲述者尼尔在小说的开头还是个少年,此时他的性格尚未形成,他必须在变革中定义价值观。在小说的开头,还是小孩子的尼尔被安排在一个寓意美好的背景——沼泽地中出场。起初,尼尔和其他男孩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无拘无束地玩耍。在啄木鸟痛苦的反应中,尼尔成了中心人物。当艾维挖下了啄木鸟的双眼时,所有男孩都感到愤怒和不安;却只有尼尔采取行动,说道“要么杀了它,要么放了它”。在形成整个个人力量中,这种反应是一种同情的审美情感——在福瑞斯特上尉的性格中有着极其相似的一面。沼泽地这一幕和与福瑞斯特太太交往的一幕相互作用界定了尼尔性格中必要的组成部分。在沼泽地里——一个寓意美好的背景下,尼尔展现出恻隐之心。在福瑞斯特家里——一个寓意人性的背景下,尼尔表达出美的感受。尼尔在小说余下部分所做的努力就是为调和以上两种因素服务的。
一
尼尔孤傲的个性引起他后来面对“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在甜水镇经历变革之后,尼尔过着清淡寡欲的生活,典型的特点是保守,不再是尴尬和虚荣,而是善于批判性的思考,因此他看上去比同龄人年长些也冷静些。尼尔傲慢个性的结果是他的人际关系出现了问题:尼尔小时候就被人们说成“顽固”,后来长大了,福瑞斯特太太提醒他,“既然你介意别人怎么说,难道你不怕别人说你是势利小人……?你不能这么顽固,如此高高在上!像你这个年龄不应该这样”。而且他的外表也是一股盛气凌人的气势。在尼尔离开甜水镇一段时间后再次归来时,他的着装很引人注目。尼尔早年对福瑞斯特太太的态度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贯穿在小说的始终。对尼尔来说,她代表着自由美好的情感,但同时他对她的反应带有一种潜在的限制和隔离。
这两种情感发生冲突的结果是产生了小说中关键的部分:尼尔从天真无邪的童年到颇有见地的成年的成长历程。最初,尼尔的思想框架是抽象的理想,完全通过他认知的宗教意象来传达。当他穿过沼泽地来到福瑞斯特家的宅子时,他非常敏感,“早上的空气像宗教般圣洁,温柔的蓝天,绿草以及早露点缀的鲜花……”只要尼尔接受人类具有局限性或是将自己从抽象的理想中抽身出来,和谐的一幕就不难实现。当他决定送一束“火红的、花蕾即将绽放的野玫瑰”给福瑞斯特太太时,紧张的气氛就产生了。花的本质是其短暂的辉煌:“它那燃烧般的,玫瑰色的花瓣总是在中午褪去了颜色,这种颜色是由阳光、早晨和水做成的,它如此强烈以至于不能持久,必将像梦幻般消失”。这一幕和早期的沼泽地的场景有着微妙的回应,在那一幕,当艾维·彼得斯掏出一把刀,弄瞎了啄木鸟的双眼,“尼尔拿出刀,用力砍向布满红色﹑带刺的坚硬树干”。凯瑟用拟人的手法表现尼尔此行为之下的复杂心理活动。尼尔的花束“聚集了清晨的面庞……这些花儿只开了一半,为最美时刻的到来做最后的防御”。因此这种说尼尔仅仅拥有“抽象美的嗅觉”的解读是不够的。尼尔确实对沼泽地的美做出了回应,他同时也是沼泽地的破坏者,他懂得美,却也无法与之和谐相处。
在这一幕,宗教的意象继续加强。尼尔俯下身“将花儿放在窗台上”,这时“他听到一个女人轻柔的笑声,这笑声带着不耐烦、放纵、戏弄和渴望。接下的笑声完全不同,来自一个男人,这笑声像是在慵懒的打哈欠声中结束了”。尼尔起身:“从窗台俯下、起身的瞬间,他失去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东西”。从成人的视角,含蓄是这个动作的必然性。就像早晨清新的花儿必定逝去,所以孩子要从儿时的梦想世界走向成人的现实。斗争的过程是将儿时最美好的理想和梦想转化成现实的历程。
尼尔最初的反应是理想的幻灭。“百合花败落了,”他喃喃自语,“百合花败落了,气味比青草差远了”。凯瑟写道:“让她为之愤怒的不是道德上的不安,而是一种美好理想的正在渐行渐远”。为了区分两者,凯瑟描写了尼尔的理想具有双重性——积极的美好情结和消极的回避现实。尼尔认为人们可以依据美好的理想去生活,这种想法是消极的,他无法让这种理想和现实生活和谐统一。
二
伴随着觉悟,尼尔的成长进入第二或者可以说是中期的阶段。他意识到人性的复杂性:梦想和现实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他坚持用最完美的、抽象的、唯美的角度去评价福瑞斯特太太,认为她“看上去浑然天成,真正的巧夺天工!”。当他坚持儿时的理想,一步步误解福瑞斯特太太的同时,尼尔的成年人的意识逐渐增强,他发现福瑞斯特太太正一步步摧毁他的理想。
在这个时期,尼尔的刻意疏离和玛丽恩·福瑞斯特对人性关怀的需要形成鲜明的对照。她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经济和物质变化带来的影响。在尼尔离开一段时间后重回甜水镇,再次看到他时,她说她多么希望他多过来造访,说到“几周以来每天晚上……尼尔就要回家了,有盼头了”,之后就“带着她罕见的笑容望着他,这笑容不带半点虚假,没有欢乐,而是富于感情和渴望的悲哀。同样的情况仿佛发生在她的嗓音里,深深的情感让她突然变得寂静无声”。 但是尼尔继续将她视为美好的理想。他把她想象成“深陷网中的小鸟”,并且希望“如果能拯救她就好了!带她离开这充满悲伤的世界、离开这个时代、离开疲倦和逆境!”纵有这富于诗意的希望,尼尔在这段时期几乎没提供实际的帮助。在艾维·彼得斯经常出入这所宅子后,他所有的只是厌烦和气愤,不再像以往那样经常拜访福瑞斯特家。
尼尔对福瑞斯特临终前的悉心守护不仅仅意味着对上尉个人的守护,还代表着对那个时代的坚守。福瑞斯特上尉去世后,尼尔打算离开甜水镇,他把他的离开视为与过去的决裂:“他认为他将永远地离开,与他年少时所钟爱的一切挥别”。他的离开发生在时代交替的背景下:“那个开天辟地的西部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些利用铁器开辟平原和高山的人已经老了,他们中有些人变得穷困潦倒,即使一些人成功了,也不过追寻着宁静和苟延残喘。那个时代已经走远,没有什么可以把他带回来”。在这个时代交替的环境下,尼尔继续把福瑞斯特太太当作美好的理想:“尼尔最不愿意接受福瑞斯特太太这点:她不愿牺牲自己,随着这个属于她的拓荒时代一同逝去;她宁愿在任何条件下活下去。”这段痛苦的挣扎在尼尔看到福瑞斯特太太和艾维在一起时达到高潮,在那之后他的痛苦变为“疲惫的蔑视”。
福瑞斯特上尉死后,尼尔和福瑞斯特太太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一方面她拒绝把自己束缚在过去之中,另一方面尼尔“最终与他年少时所珍视的一切决裂”。失去丈夫的福瑞斯特太太“仿佛一艘没有压舱物的船,被风刮得四处流窜……她似乎已经失去了辨识的能力,她曾亲切地,毫不费力地让每个人各得其所”。自从得知她和艾维·彼得斯的亲密关系后,这是尼尔“在黄昏的光线下最后一次穿过桥,不仅如此,他也再没走过那条杨树接壤的路”。尼尔似乎和福瑞斯特太太彻底决裂了。
三
然而,凯瑟没有将此书就此结束。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尼尔进入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成熟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丹尼尔·福瑞斯特的太太重新回到他的记忆中”。他开始珍视他们之间的友谊,“很高兴曾经认识她,她在打乱他的生活方面很有一套”。尼尔的思维方式已经开始转移。他不再用完美的抽象的审美观点去衡量福瑞斯特太太,相反他此时懂得用“生活”来评判她:“当她的眼睛笑对着你的眼睛时,仿佛给他生活中从未有过的狂喜。这双眼睛仿佛在说‘我知道该去向何方,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尼尔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他想揭开福瑞斯特太太的面纱,盘问她,探究她对生活永远充满热情的奥秘;询问她是否真的发现了永远盛开,永远燃烧,永不凋零的快乐,抑或是这一切都是绝好的演出。”此后尼尔试探地回答:“或许她找到的无非是另外一种生活,但是她总是能够暗示:周遭的事物甚至比她自己更可爱,正如一朵花的芳香可以唤醒整个春天的甜蜜。”
小说最后为故事提供了结局:“尼尔注定要再次得到这位久违的女士的消息”。当然,信使就是埃德·埃利奥特。在前文中,尼尔曾傲慢地认为自己和埃德不是一路人,说道:“我得意于我不会完全像(他)”。在听到有关福瑞斯特太太最后的消息时,尼尔放下他骄傲的距离,和埃德·埃利奥特共同分享有关玛丽恩·福瑞斯特的回忆并赞叹福瑞斯特太太对人们永恒不变的影响力。埃德·埃利奥特说:“我通过她的笑声认出了她——这笑声一点没变”,然后说,“她并没有你想象的变化那么大”。
这最后的一幕证明了福瑞斯特太太的勇气是变革的动力。福瑞斯特太太的新丈夫被描述为“富有古怪的英国老头儿”,他“动辄争吵且吝啬”。相对于福瑞斯特太太对他的影响,这些只是细枝末节:“但是,她似乎拥有了一切”。柯林斯先生对待妻子慷慨大方扩大到对别人也热情好客:“当她的丈夫来接她的时候,她邀请我去她家拜访他们,她的丈夫也是”。尼尔终于得到了她的消息,这消息仿佛回应了尼尔此前对福瑞斯特太太的愿望:“尼尔想揭开福瑞斯特太太对生活永远充满了希望的秘密……”在这最后一幕,尼尔终于了解了福瑞斯特太太的秘密,为读者提供了这种具有蜕变力量的梦的最终证词:“告诉他我一切都好,柯林斯先生是最好的丈夫”。
凯瑟以此结局暗示未来的希望并不在于追忆那片寓意拓荒时代精神的土地——这种精神已不再适应新的时代。凯瑟认为,这种无能为力着实令人遗憾,因为拓荒时代无疑是个高尚的时代。然而真正的悲剧是那些老一代拓荒者无辜成为那个时代的祭祀品,把未来交给艾维·彼得斯之流。相反,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那些把这种精神转化为生活动力的人们身上。最后,我们意识到“迷途的女人”这个标题告诉我们两个人物在一个充满变化的环境下共同的蜕变:为生活不再无趣乏味而不懈追求的福瑞斯特太太和丧失了寄托生活和价值的理想的尼尔。通过再次寻找“他失散已久的夫人”, 尼尔感到以玛丽恩·福瑞斯特为代表的人性美和以福瑞斯特上尉为代表的精神美的和谐统一。
通过这部小说,我们仿佛被凯瑟带回到那个时代。凯瑟强调个人生活追求的方向本身是一种具有改变性的动力,平庸的现实恰恰反映了普遍的真理。在《拓荒者》和《我的安东尼娅》中,凯瑟试图表达这种动力是恒久的。在《一个迷途的女人》中,凯瑟将这个主题添加了时间的维度。玛丽恩·福瑞斯特和尼尔·赫伯特代表了逐渐与拓荒者断绝关系的一代,他们在经济文化经历混乱和变化的时代追求道德美的永恒智慧。在表达这种探求时,凯瑟并没有将自己束缚在对已逝的中西部拓荒精神的哀叹中,而是再现了如何摆脱这种对价值观的狭隘定义的过程。通过这部小说,凯瑟坚信人们有潜力将过去的精华转化为道德美的动力,这些人当中包含尼尔,他们会在未来的路上勇往直前。
[1]Harold Bloom.Modern Critical Views:Willa Cather[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1985.
[2]James Woodress.Willa Cather: A Literary Life [M].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1987.
[3]Mildred R. Nennet. Willa Cather’s Collected Short Fiction 1892-1912[M].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0.
[4]Phyllis Rose. Modernism: The Case of Willa Cather in American Fiction.1914-1945 [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 1987.
[5]Willa Cather. A Lost Lady [M]. The USA: Vintage Books,1990.
[6]金莉.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叶红.走出女性的樊笼[J].当代外国文学,2003(2).
[8]朱炯强.薇拉·凯瑟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杨韩钰(1981— ),女,黑龙江人,硕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讲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