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坪往事
张品成
陵园是烈士们的家
他们很快有了新任务,是首长下达的。
首长那天说:“走,我们看看去。”娃儿们就跟了首长往坡上走,走走就走到大城寨了。
从那儿往下看,王坪一览无余。他们往那边看,石匠们正用滚木运送碑石。碑石太大,人抬不动,骡马也无法运,但是,石匠们有办法。这是古老的办法:用滚木—— 一些大木头横在大石头底下,从高处一点一点挪移。秋天里已经挤满了凉意,但那些男人还光着脊背。他们唱着歌,喊着号子:“高高的大巴山,离天只有三尺三,要想翻越巴山顶,只有背二哥的铁脚杆!”
万小坎说:“他们在唱背二哥的歌子哩。”
首长说:“你们要帮助石匠们完成那件事情。”他没说那是事业,只说是事情。
娃儿们说:“什么事情呀?首长要我们帮他们运石头?”
徐敬乾说:“运石头,你们插不上手。”
“那是什么事情?”
首长说:“我说过,要给死去的红军英烈立块碑。”
万小坎几个说:“我们又不是石匠,打石头、刻碑的事儿,我们插不上手的呀……”
首长笑笑,突然问:“我们刻碑为的什么?”
万小坎几个就被问住了,心想,首长你说过是为纪念死去的烈士,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问?你都说过好多遍了,你还问?所以,没人接话。
首长说:“我们要建个陵园,红军烈士陵园,碑要立在陵园里的。”

“陵园?”娃儿们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徐敬乾说:“就是墓地,埋死人的地方……”
张乐生说:“坟地就坟地哟……说‘坟地’就是了,叫什么‘陵园’?”
“过去管帝王诸侯、达官贵人的墓地叫‘陵园’。”首长说,“王坪埋着的红军战士,他们为工农革命而死,比古代的帝王诸侯、达官贵人有价值,我们要把他们安息的地方叫‘陵园’,叫‘烈士陵园’。”
娃儿们说:“那是那是,那就叫‘陵园’。”
“陵园是烈士们的家,你想想,你们要是有家,家里会是个什么样子?”
娃儿们说:“可我们都没家呀。”
首长说:“革命成功了,你们就有家了,不仅有家,还有天下……那时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消灭了剥削,人民当家作主,人人都是大户……”

徐敬乾说:“首长让你们想想,你们将来有了家,会是什么样子?”
娃儿们真就闭了眼睛那么想了会儿。然后有人说话了,说话的是蓝都米。“我要筑个小院,院子里种很多树……”蓝都米说。
“我要砌个大屋子,雕梁画栋,柱子有铜盆那么粗……”张乐生边说,还边往万小坎那儿望了一眼,“小坎,你呢?你说说。”
万小坎说:“不说了,还说个什么,谁都想自己家里跟皇宫一样哟……谁不想,谁不想哟……”
徐敬乾说:“说得对,谁都想的。”
首长说:“所以,烈士们的家也应该非同寻常,不仅要庄重肃穆,也要清新美丽。你们看看,现在那片坟场是个什么样子?”
大家往那片坟地望去。
“现在这坟场,草生木长,一片狼藉,蛇虫藏身,鼠兔出没……碑竖了也白竖,不好看嘛,不像个样嘛……”
“是哟,不好看……不像个样。”娃儿们说。
首长说:“我就想你们也出出力,我就想你们帮帮我,把这里弄成个像样的地方。”
万小坎说:“首长,看你说的,你下命令就是!”
建碑的石材有点讲究,那些日子,彭石匠领了那几个师傅往山里四处找寻石料。对墓碑选用的材质,首长要求很高。千年万年的事,能要求不高吗?质地不仅要细密,而且要坚硬。只有那种上好的青绵石才符合要求。
选好了石料,石匠们开始工作了,都是抡锤的行当。
王坪那些天响起了凿石头的声音。
按说凿石头的声音不会很好听,铁钎碰石头,铁锤击铁钎,都是硬碰硬。但事实不是那样,他们抡锤,却也能和苟千全师徒一样,把铁锤抡击的声音弄得悦耳动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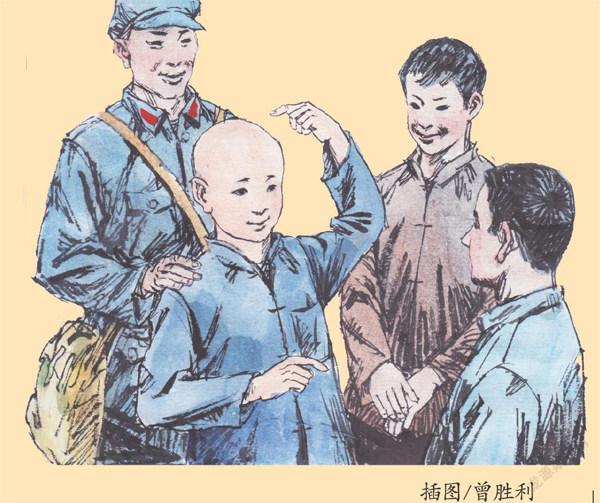
錾字队的那些男人不刻标语了,他们刻碑,这是他们的老本行。当地墓葬很讲究,坟堆前有一面墓墙,其实都是石头堆砌而成的,当然,石头很有讲究,刻有字和图案,还弄得像座屋宇,尖顶石基……石匠们一直做着跟石头相关的活计,没想到有一天会请了他们去刻字。凡有石头的地方、有人来往的地方,都得刻上字。红军说,那叫“标语”,既有拳头大小的字,也有屋宇那么大一个的字。他们开始不明白为什么红军每到一处都要留下一堆的文字,那些石崖、石壁、石墙、石阶、石柱、石桥……凡能刻字的地方,恨不得都刻上标语。后来,刻下的那些字受到首长的赞扬,也受到各方的注目,他们就觉得做这活儿还真不同寻常。
现在,石匠们来到了王坪。其实,他们在红云崖刻字时,就和王坪遥遥相望。尤其是他们悬在崖壁高处,视野开阔,无遮无掩,虽然隔有几十里地,但看得见这边的屋宇田垅,看得清这边的树木和树木掩映中的棚寮……王坪看红云崖,能看清那四个字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但红云崖看王坪,一直就那么个样,没有变化。石匠们当然看不到那些惊心动魄的场景,那些抢救,那些忙碌……那些生离死别,那些与死神的抗争,那些笑声和哭声……
来到这里,石匠们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知道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地方。王坪是红军总医院,因为牺牲的重伤员多,也是红军最大的墓场。那些死去的人中,有些是他们的乡亲,有些是他们的老客户。这一带,哪家没有被石匠光顾过?建屋、修坟、打器具……石匠也和别的乡间匠人一样,哪家请工,就吃住在哪户人家里。大户人家有住一月两月,甚至半年一年的,工程大呀。小户人家多则住三五天,少则一两天。但不管住的时间长短,大家都和睦相处,像兄弟一样。他们一起喝过茶,摆过龙门阵,赶过场,下过棋,观过戏……
首长要他们做一件事,那的确是件重要的事。首长说:“工农革命,牺牲了很多同志,我们要做一件事,让后人记住他们。虽然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死者逝去,生者缅怀,但他们的忠魂永在,彪炳千古,也要千年万年。”
万小坎他们手头的工作都放下了,其实也不叫放下,是他们这阵子都没什么活儿干了。没有战事,就没有伤兵。医院里有的只是普通病人,也就感冒发热,这都不是个事儿,什么时候没个头痛脑热的?也不需要绷带,鲜有死亡。
所以,男娃儿们、妹娃儿们都闲了。棺材没人睡了,苏瓜儿的斧锯就放下了,张乐生也不必打棺材钉。凌照照她们织布队和洗衣队,活儿都锐减,不必每天织绷带,更不必每天洗那些血糊糊的东西了。
首长那天找到他们,带这些少年去了大城寨。
首长说要建红军烈士陵园,当然要是个像样的地方,碑要千年万年,陵园也要千年万年。用首长的话说:忠魂永在,彪炳千古。那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呀?首长说,碑和陵园,不仅我们要瞻仰,后人也要瞻仰。那就不是一般的坟场了,那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地方。
男娃儿、妹娃儿那些天不排练了,他们有新的重要任务,他们在那片坟场上忙碌。把坟场改为陵园,不只是竖一块石碑的事儿,要做的事儿很多:修整墓场,清除杂草,栽种树木,垒坡筑埂……大城寨那片墓地,坟堆都是沿了山坡一圈圈整齐地排过去,还算是排列齐整。但草木长起来就不会有讲究了,杂草灌木肆意疯长,长得高高低低,不成样子。
“山就跟人脑壳一样。”徐敬乾说。
“草木就是长在大山脑壳上的头发。头发要经常剃,半年不剪不剃,你试试?”他说。
“影响容貌嘛,男人半年不剃头,出门人人见了都说妖形鬼样。”他这么说。
徐敬乾的比喻很形象,万小坎兴奋了。
“皇上也离不了剃头匠,就算是皇上,半年不剃头试试?”万小坎说。
有人说:“皇上也离不开裁缝呀,难道皇上不穿衣服?皇上也离不开木匠篾匠什么的吧?难道皇上不睡床,不用器物?”
万小坎说:“皇上当然要穿衣服、用器物,但木匠、篾匠、织匠、裁缝什么的,能见着皇上,能摸皇上的头不?”
人家就哑了声。这事儿的确也是。你看剃头铺那些对联,就是一间茅庐,也敢出语狂放,话大得能遮地盖天。什么“提起刀人人没发,拉下水个个低头”,什么“创人间头等事业,理世上不平东西”,什么“请我挥刀须贴耳,拉你洒水应低头”,还有“握一双拳打尽天下英雄谁敢还手?持三寸铁削平大清世界无不低头”。牛气冲天哟,狂妄得没了边哟,但你能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哪一句没在理,哪一句说错了?人家能摸皇上的脑壳,人家能让皇上俯身低头……你能吗?
谁都知道男人的头发半年不剃的样子,那成了鸡窝了,那成了乱草滩儿了。可剃刀一过,男人就精神了,就换了个人样儿。真可谓:进门乌头宰相,出门白面书生。那么,山的“脑壳”呢?你把山的“头发”剪了,把“胡须”剃了,山也变样儿了哟。山也能“进门来发长须乱相貌老,出店去眉清目秀年纪轻”吗?
医院里能腾出手的男女都来给山“剃头修脸”。少年们成了主力军,力气大的跟大人们搬石头、挖土,力气小的除草、砍树。厨子唐发儿推开厨房门往坡上看,大城寨那片地方热火朝天。他看了一会儿,把手里的菜叶撒在院里,鸡们飞跳了来啄食。要入冬了,秋虫日渐少了,田里的残谷余粒也早被鸡鸭鼠鸟什么的拾食了个干净。唐发儿撒出的烂菜叶子,就是鸡们的美食佳肴。
“不给你食,你能唱那么好、干那么欢?”唐发儿说。
谢模理说:“唐叔,你说谁呢?”
谢模理和洪中生没去建陵园,他们和几个手脚不方便的人在厨房帮厨,其实就是做后勤,给那些在坡上忙碌的人们烧水做饭。谢模理倒没什么怨言,他觉得这很好。他经过吹笛和学步,足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价值。别说自己和正常人比确实有缺陷,那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好腿好脚的人,各自能力也不一样。他觉得,自己不是学会了吹笛、走步就真能和正常人平起平坐了,而是有了那些经历,他已经走进了人群。在别人眼里,自己也和他们一样,这就够了。
首长以前跟谢模理说过一句话,首长说:“模理哟,重要的是你自己站起来。”一开始,谢模理粗浅的理解是“不要人扶,自己站起来”;后来,他慢慢觉得首长说的那话其实意味深长;再后来,他才彻底理解。首长话里的意思是,像自己这样的娃儿,需要“自己站起来”——自己的心能站起来。
所以,谢模理能安静地在厨房做事。倒是唐发儿骚动不安起来,在厨房里不能安分了。坡上那些歌声和响动诱惑了他,他老是出门往坡上张望。
谢模理问他,唐发儿就说:“我是在说鸡哩。”
谢模理说:“我听到你说的话了,我听到你说‘不给你食,你能唱那么好、干那么欢’,那是说鸡吗?”
唐发儿说:“那怎么不是说鸡?”
“说鸡你能说‘唱那么好、干那么欢’?”
唐发儿说:“那只锦毛公鸡不是站在篱笆上叫吗?那些大鸡小鸡不是抢食抢得欢吗?我说错了?”
谢模理笑笑,他当然知道唐发儿是妒忌坡上的热闹,也知道唐发儿内心的反差——厨房里几个好帮手都被抽去修陵园了,却把几个缺胳膊少腿的人派给了他。且这些缺胳膊少腿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就拿洪中生来说,守着贩卖部,有时就看人脸色出售东西,紧俏的东西当然会留一手,谁都要跟他笑脸来笑脸去,好像他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可离开贩卖部,他就是个瘸子,牛个什么?谢模理也是,唐发儿也爱穿这娃儿做的衣服和补的衣服——不仅唐发儿,王坪所有的人都对谢模理的手艺竖大拇指。可是,到了厨房,谢模理也就择个菜烧个火什么的,就这杂活儿也做得不是很地道。唐发儿嘴上当然不好说,但肚里的牢骚肯定鼓胀了不少,指桑骂槐也正常。
谢模理没戳穿唐发儿,他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他在漆家裁缝铺也常做这些灶下的活儿,所以,做起来比洪中生他们熟悉、灵活。
唐发儿又在“中生中生”那么喊了,但没动静。
“中生哟,把那米拈一下,鬼哟,沙石多,他们吃了要骂人。”还是没动静。
谢模理看了一眼洪中生,这男人坐在那儿抽烟,对唐发儿的话充耳不闻。他明显不是不会做,而是不愿意做。唐发儿叹息了一声,自己去弄那盘米。坡上的响动还是不断传来,诱惑了他们的耳朵。谢模理倒很安分,他往灶眼里塞着柴。秋天里的柴干爽,烧起来火花欢跳。那火把谢模理的一张脸映得红红的。唐发儿在炒菜,说:“模理,你还真能烧火。”洪中生把一锅烟抽了,又坐在那儿喝茶。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他说:“烧火还有个讲究?”唐发儿说:“烧火当然有个讲究……你别在那儿喝茶了,去帮我摘几片紫苏叶来。小坎他们大早摸来的鱼,熬鱼汤没那叶子不行,紫苏去腥。”
洪中生拄了拐杖出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