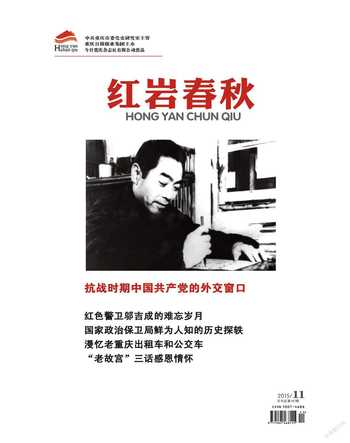历史是记忆组成的
章开沅
我对四川、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从1937年冬至1946年夏,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在重庆江津国立9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我还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的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镇国立9中旧址,附近居民闻讯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期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了当时的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与无形、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的著名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转眼岁月匆匆,但记忆却是那样的刻骨铭心,恒久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