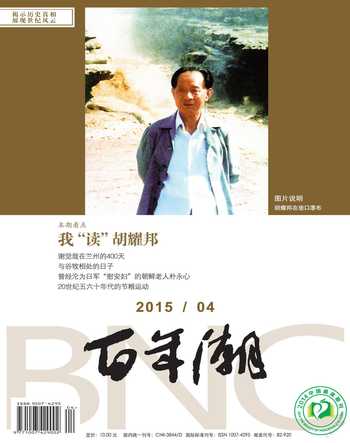与谷牧相处的日子
我曾两度在谷牧身边工作,算起来也有近10年时间,但我们之间的交往却有近半个世纪之久。回想起来,谷牧是让我感到十分亲切、令我非常敬佩的人。在我心目中,谷牧的形象很高大,我无意评价谷牧,只是从仰视的角度,诉说一些我的感受。
1955年元旦前后,我由第一机械工业部调到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工作,成为谷牧手下的普通一兵。国务院三办(分管重工业)的机构非常精练,总人数不过三四十人,一般工作人员经常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领导。谷牧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工作务实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工作要求严格,对犯错的同志也会严肃地批评,但从未见他声色俱厉地训斥人。他和人谈话,眉眼间总是流露出自然的笑容,给人一种亲切感。
我与谷牧刚接触时,有两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我到国务院三办不久,谷牧带着秘书钟志奇和我到吉林省吉林市出差。记得有一天雪后天晴,我们去丰满水电站,路上积雪在20厘米以上,谷牧和他的老相识、当时的吉林市市长乘坐了一辆老旧的卧车,钟志奇和我乘坐一辆二战时期美军的吉普车,冷风呼呼地往车里灌。在水库大坝前下车后,谷牧看我们冻得狼狈样,诙谐地说:“冷吧!值得呀!古人把‘踏雪寻梅’当作很风雅的事,今天寻不到梅,但是多么好的雪景呀!这才叫‘北国风光’哩!而且雪后初霁是令人精神振作的景象。陈鹄,你会写诗吗?”我回答说:“不会。”谷牧又问:“那你读过古诗吗?”我说:“读过一点。”谷牧说:“说说你印象最深的。”我有点紧张,仓促应答:“能背出来的只有‘春眠不觉晓’、‘锄禾日当午’、‘煮豆燃豆萁’那几首,其余的都忘了。”谷牧笑了,似乎还要说什么,这时我们已进到厂房里,有两位工作人员迎上来了,我躲过了一场尴尬。
晚上,市长在招待所请我们吃饭,那时没有大吃大喝之风,饭桌和火车餐车上的饭桌差不多大小,总共四个人,四五个家常菜,其中有一小盘红肠很快被吃光了,谷牧说:“这红肠味道不错,再来一盘吧!”但我注意到,谷牧对第二盘红肠仅仅“浅尝辄止”,我意识到他是照顾我们两个年轻人。实际上主要是照顾我,钟志奇是很文质彬彬的。
谷牧一生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觉得他能够领导部下解决那么多棘手的问题,特别是他长期在综合机关工作,在处理复杂事物时对各专业部门表现出高度的协调、指挥能力,与他对人的很强的亲和力不无关系。
1956年夏,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国务院三办、四办、六办等并入国家经委,机构扩大了许多倍,谷牧担任常务副主任,我与谷牧工作上的直接接触就很少了。1958年秋,国家机关“万名干部支援西南”,我被分配到云南省计划委员会工作,离开了谷牧。1965年春夏之交,第三届国家建委成立,谷牧任主任,我从云南调回北京,被分配在研究室工作,又一次成为谷牧手下的普通一兵。
研究室有部分同志经常参加国家建委的文件起草工作,当时被戏称为“秀才班子”,我有幸名列其中。谷牧对机关文件、报告的起草非常重视,从不简单地倚重秘书或工作人员,而是亲自抓。他先把自己的意见对“秀才班子”系统地讲一遍,定基调、定结构、定观点、定重点,“秀才班子”主要完成文字整理。成稿过程中,要根据谷牧的意见进行反复修改,因此参加这项工作是一个深入学习的培训机会。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谷牧常和大家共同讨论,讨论中,工作人员偶尔提出一点好的见解,谷牧就会加以肯定,工作人员很受鼓舞,我至今脑海中仍浮现出谷牧说“嗯!这个意见不错”的音容笑貌。
在建委工作一年左右,“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司令部”,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我作为谷牧的随员住进京西宾馆。有一天谷牧对我说:“刚才在过道上走在叶帅后面,听到叶帅自言自语,反复念叨着‘串连何时了,罢官知多少’!大概他是看到大街上满是串连的人流而大有感慨。”我到窗口朝下看了看,复兴门外大街黑压压的人群,不但挤满了人行道,还占用了大部分车道。好在那时候汽车很少,不存在堵车问题,但铁路运输已经因为学生“大串连”而无法维持正常运营秩序了,客运列车被青年、包括部分少年学生挤得水泄不通,被迫停止售票,更谈不上正点运行,货运几乎完全停滞。谷牧当时也对这种状况深表忧虑,联系到叶帅的感慨,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紧接着中央决定由谷牧主持召开工交座谈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制定出一个指导性文件。当时教育战线、文艺战线乃至政府机关已经秩序大乱,工交战线相对稳定,但在学校造反派的鼓动、“串连”下已显现出“脱轨”的迹象。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国务院工交系统各部门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分管工交工作的负责同志。谷牧主持会议讨论并亲自抓文件起草工作。会议刚开始,“中央文革”就送来了《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要会议讨论,实际上是要会议“认可”。这个《十二条》认为工交战线“17年来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要在工交战线“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在当时的表现就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煽动群众、破坏一切。在工交战线“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必然会使整个社会和国民经济陷入更加严重的混乱局面。在当时,“中央文革”的意见几乎等同于“圣旨”,谁敢违抗?但是,与会同志毕竟是久经锻炼、考验、对党无限忠诚的老干部,讨论中大家一致反对《十二条》,认为工交系统不能乱,生产秩序不能被破坏。
有一天,周总理到会听取意见,会议室中间有一张大的长方桌,可以围坐近20个人,四周靠墙有一排座椅,也能坐下大约20个人。周总理坐在长桌一边的中间,大家很热烈地发表意见,情绪逐渐有些激动起来。坐在周总理斜对面的刘澜波站了起来,发言中有向周总理诉苦的意思,吕正操、徐今强等四五位部长也站起来呼应。周总理很平静地说:“你们坐下,快坐下,不要这么激动,这样不好!你们长时间在我身边工作,是我把你们娇纵坏了。”然后周总理讲要正确理解和对待“文化大革命”,还讲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相比,个人的利害得失算得了什么!他的一句“我们,首先是我,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胸怀”,使我终生不忘。
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文件起草班子在谷牧亲自主持下煞费苦心地对《十二条》进行了修改。对无关紧要、无碍大局的条款一字不改,哪怕文字上有瑕疵也不改,对《十二条》只改动了两三条,另外加写了两三条,最终形成《十五条》。我本人内心完全赞成《十五条》,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忧虑。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意志的时代,不是一个“有理走遍天下”的时代,而是一个说话办事都必须符合特定标准和特殊要求的时代,说真话、讲真理可能会招致飞来横祸。因此在文件接近定稿时我提出:“个别论点是否可以回避,例如‘工交战线基本上不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引申出‘工交战线不需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结论,这似乎有点不合‘时宜’,是否会犯忌?另外,少数词句是否再委婉一点,尽量不抵触《十二条》的原文。”谷牧认为:事关重大,不能含糊,要本着对党中央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说真话,要鲜明地主张工交战线不能乱,并且讲到周总理关于“入地狱”的讲话。与会同志连同我在内,对他的这番话心悦诚服,《十五条》如期上报。
几天以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由林彪主持,专门讨论《十五条》。会上,当时“中央文革”中几位极左人物对《十五条》和谷牧进行了“大批判”,要害正是“反对在工交战线开展文化大革命”,他们强调工交战线不能例外,而是更有必要“大革命”。会议开了三天,林彪进行总结讲话,他彻底否定《十五条》,“要180度大转弯”,强调要“主动地使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渗透到各个领域”。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在写作班子的小会上,林乎加说:“如果按陈鹄同志的意见改,就不会惹这么大的风波。”这时候我反而清醒了,说:“恐怕也不行,本质上的区别太大了,在劫难逃!我原来的意见是消极躲避,其实没用。”当时谷牧坐在我对面,我看了一下他的眼神,我觉得他的眼神告诉我:“你这样说就对了!”
此后不久,中央发布了“中央文革”炮制的《工业十条》,同时向社会传播林彪等人批判《十五条》的言论,在工交战线掀起了“革命狂潮”。几个月以后,中央不得不做出决定,对工交战线和各单位实行军管,这是后话。
当时,工交系统乱象丛生,工交部门领导干部靠边站、挨批斗,机关被“夺权”,无法实现有效的管理。周总理决定国务院成立“业务组”直接管理经济事务,成员由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组成,工作人员共25个人,后因种种原因,人员未配齐,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为了不受造反派干扰,防止领导干部被劫持,周总理决定让余秋里和谷牧在中南海办公并住宿,离开中南海要经周总理批准。由于种种原因,我阴差阳错地被当作谷牧的秘书,随谷牧在中南海工作了一年多时间。那段时间的工作乏善可陈,我做得最多的事情是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布的许多紧急通告,主要内容是制止武斗、制止妨碍交通、制止停产、制止各种破坏行动。这些通告由我根据谷牧的指示起草,谷牧签送李富春、李先念,最后由周总理签发。但各种事件屡禁不止,一个地方事件尚未平息,更多的地方事件闹得更大,应接不暇,于是不断地发通告。我们的工作就像“消防队灭火”。在大量的通告中,我印象最深、起草难度最大、真正发挥作用的一个文件是关于全面实行军管的决定,简称《军管八条》。
在中南海的这段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谷牧十分强调保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稳定的重要性,他认为当时全靠周总理维系局面,而周总理的处境十分微妙、艰难、甚至危险,作为助手的他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能给周总理制造麻烦。有一件事充分反映了谷牧的无奈心情。“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中央决定周总理主持不定期的“政治局碰头会”,参加人员是明显的两个阵营,一方是毛主席后来定名为“四人帮”及其同伙的一派,他们主张“打倒一切”;另一方是以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为代表的老干部,其中最年轻的是余秋里和谷牧,他们反对“天下大乱”。这两派水火不容的人在周总理的主持下经常“碰头”,这真难为了周总理,也只有像周总理那样德高望重、睿智大度的人,才能掌控得住这样的碰头会。但是,真理与谬误如此尖锐地对立,激烈的抗争终有爆发的时候。1967年2月16日下午2点,又要开碰头会。就在这天上午,谷牧被机关造反派“揪”回去批斗,罚站几个小时,口干舌燥连水也不让喝一口,弄得他疲惫不堪。下午3点左右我发现谷牧还在办公室里,我问他怎么没有去开会?他说:“碰头会上气氛越来越紧张了,前天会上为了老干部挨批斗的事开始争吵起来,幸亏总理的秘书进到会议室说毛主席来电话请总理马上过去,碰头会中断,暂时平息。今天我这副狼狈样,如果到会上去,很可能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闹起来会使总理很为难,真要闹大了,结果难料,所以我告假不去了。”但是谷牧的良好愿望还是落空了,就在2月16日下午这次碰头会上,双方大吵了起来,这件事被定为“二月逆流”,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重要事件。
1968年春,国家机关已实行军管,“造反派”的行为大体上受到了约束,周总理决定谷牧回国家建委“参加文化大革命”,住宿在办公室。大约一个月以后,李先念副总理找我谈话,让我回国家建委。回到建委后,我和谷牧在一个党支部,每天在一起“早请示,晚汇报”,“参加运动”,但是没有工作任务。大约一年多以后,总理指示谷牧到基建工程兵“锻炼”,(基建工程兵是谷牧主持组建的,他兼任政委),后又到江汉油田“蹲点”。后来恢复了谷牧在建委的领导工作,兼任国务院港口建设办公室主任,直到1975年任副总理。从谷牧到基建工程兵“锻炼”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谷牧任副总理期间,有一件事对我的工作支持很大。在邓小平的提议下,中方以谷牧为首,日方以大来佐武郎为首发起成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重点讨论双方共同关注的宏观经济形势和中日经贸合作问题,我参加过一些活动。大约是1983年,大来佐武郎向谷牧推荐日本“国际开发中心”为中国编制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工作经费由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承担。谷牧通过国家计委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办理,当时我任国家计委国土局局长。
经过认真考虑,我们决定让日方帮助编制海南岛的《海南岛综合开发计划》。工作正式启动,我请求谷牧接见日本一行十多位专家,谷牧同意了,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接见中,气氛轻松、愉快。事后我方的翻译听到日本专家议论:一是对这次接见“喜出望外”,二是“发现陈局长与谷副总理关系不同寻常”。这为我以后两年多与日方合作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回想我曾在谷牧直接领导下工作,感到很幸运、幸福,但我在工作中表现平平,因此更多的是愧疚和遗憾。我忘不了谷牧对我的批评和爱护。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一次批斗谷牧的会上,有人问:“你怎么评价你的两个秘书——李灏和陈鹄?”谷牧回答说:“李灏工作勤奋,考虑问题细致、慎重,对我比较顺从;陈鹄思维比较敏捷,工作中比较敢提不同意见。”我没有参加这次批斗会,是不止一位同志转告我的。
有一次,谷牧对我说:“陈鹄,有人说你这个人有点‘犯上’呀!”我内心不太同意,我认为自己完全没有“犯上”的情感基础和认识根源。再者谷牧说的是“有人说”,因此我没有申辩。
有一次,在机关食堂,谷牧当时在食堂参加“劳动锻炼”,在窗口卖饭,卖饭高峰已过,谷牧和我同坐一桌用餐。不记得是什么话题引起的,谷牧问我:“张学良为自己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二字人皆呼不孝’,下联是‘一生误我是聪明’,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我意识到谷牧是批评我自以为聪明、言行不够谦虚谨慎,工作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我认为批评得有道理,但没有回应,我觉得无须回应,铭记可矣。谷牧离休后,我到他家中拜望过两三次,有一次我请求谷牧将张学良的对联写来送给我,谷牧说:“可以,但是写字要有兴致,而且送你这样的对联必须写一段跋,等我兴之所至的时候给你写。”但后来我没有来得及向他索要,成为一个很大的遗憾。
不过,庆幸的是,我手头珍藏着谷牧的两件墨宝,一共14个字,写的是我父母“陈潭秋烈士遗像”和“徐全直烈士遗像”。这两幅墨宝的题写时间前后相差好几年,先是为我父亲题写的“陈潭秋烈士遗像”,多年后我又请求他为我母亲题写“徐全直烈士遗像”,并告诉了他纸张的大小尺寸,但谷牧要我将“陈潭秋烈士遗像”拿回给他做样本,以求得两个题字尽量一致。几天后,谷牧交给我五张“徐全直烈士遗像”,叫我挑选一张。我说:“我哪有那水平,您决定给我一张吧!”现在这两幅墨宝镶嵌在两幅遗像的像框里,他的墨迹成为留给我的最尊贵的纪念。我在家随时可以瞻仰,任何人都发现不了两幅题字有何差异。但是,这两幅题字都没有署名,遗憾吗?遗憾!不,不遗憾。谷牧在我心中,比他的署名重得多、深厚得多,有这样两幅墨宝,足矣!(编辑 杨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