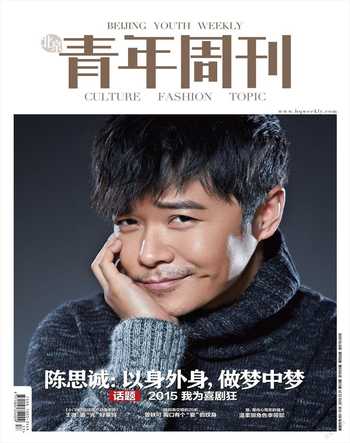陈文令 我们需要回到包浆的那个时代
张纳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人间应该是没有垃圾的,对普通人来说,把物品放错地方才是垃圾,用在对的地方,人间就没有垃圾。我小时候,一个钢笔甚至要用七八年,甚至有十几年专属的水笔,笔里面的水用完了再去装,装了再用,用了再洗,小时候我们不知道那叫做包浆,其实使用几年之后,包浆,笔就很宝贝。
“城市”,城是物质,像围墙,市是一个买卖,跟集市有关的。当下整个世界,人们都是如此的物欲横流,都要卖得好,一定让你的笔经常换的,变成一种像战争时代里的物流,甚至比战争时代运输量还大,整天浓烟滚滚的这样子,雾霾都把我快呛死了。
我们城市没有包浆,乡下也没有包浆。前不久我去老家安溪县做了一个展览。在我们隔壁村有一栋清代建筑盖得非常漂亮,红砖红墙,看得人很感动。有一个老太婆腿有点瘸,踉踉跄跄走出来,愁眉苦脸的样子,好像要跟我乞讨一样。我说,“老阿妈,你住在里面开心吗”?她说,“开心什么开心,有本事的人全都搬走了”。社会形成这样的原因,整个农村就变直了,我们小时候道路都是弯的,现在整个村庄基本上都拆光了,以前老人其实就有一种包浆的心态,我们的祖辈,就是一个破瓦一个棚子住一辈子,不舍得丢。
老太太会有一种痛,因为她身边的这些人都得了神经病了,都变态。我觉得一个正常人在这个神经病里面最后没有变成精神病的也会变成神经病,所以她脸上的笑容跑了。我的母校,安溪地质中学。有一个杰出校友——对他们来说觉得钱赚多才是杰出的。脑子愚蠢,钱多,他花了四五百万重建我们的中学,把我儿时所有的记忆,都拆的光光。
建设真的要混搭,我们以前的建筑都是理工科的人建造的,他们并不很了解美。所以我发现真的文化也要像袁隆平的水稻一样杂交才会有增长。我们安溪同样花了那么多钱,你要干预自然,自然是一去不复返,永远还不回来了,里面的山山水水就被这样子破坏了。现在所有的美术学院都有建筑系,这让我很开心。
伟大的城市要有眼睛的。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眼睛,自由女神是美国的,悉尼歌剧院也是有建筑功能的。作为当代艺术家,我们可能要创造今天的艺术,我们不能去抄袭清代的,民国的,甚至古时期的东西,它的这种转换,转换不好会容易很土气,跟这种地方性的一种文化结合的时候,要不就是从里面组合进去组合出来,需要很接地气,也要洋气。我们以前的国画都是很清楚,我画竹子、画梅花,现代的当代艺术家也应该强调一种内心的分享精神,也就是说我们安溪现在要转化成全国性,全国性转化成亚洲性,亚洲性转成半球性,然后全球性。
中国现代是一个实用工艺品横行霸道的时代,什么东西有好处什么东西就被创造出来了。不要说艺术家就是有个性就行走天下。有时候不靠着个性会显得更牛逼,这个带着镣铐的自由会通向更遥远的地方。
行为艺术家他们突然脱光光了,这样往下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艺术家不能掌握极度自由的这种权力,我们的城市规划师,我们的建筑师,我们的艺术家带有公共性就已经协商讨论了一个概念。
不能随便制造垃圾,要把垃圾使用起来,小学生、大学生、老人,男女老少,能够看到人间所有的一切,满怀一点温暖的目光去看它,不要一看就是垃圾,一看就是没用,如此功利的去看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也许会美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