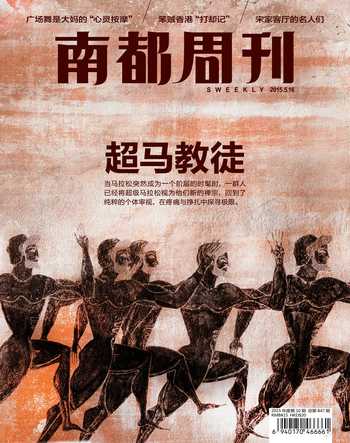制造完美人类是个噩梦
李淼
1991年上半年,我来到美国不到半年,突然患上感冒,流鼻涕不止。那时,我已经有了医疗保险,只是从来没有用过,就忍着不看医生,随便在超市里买点当时流行的非处方感冒药,无非是康泰克、白加黑之类。这样自我治疗了半个月还不见好,只好去看医生。医生一下子就弄清楚这不是感冒,是上呼吸道过敏,于是开处方给我,从此我就与过敏药结下不解之缘。
1992年我们全家去了东部,我的过敏加重了,严重到每年有一两个月呼吸不畅眼睛瘙痒难耐,早上起床眼睛被排泄物糊起来。一次,我在《时代周刊》或是《新闻周刊》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科学家马上就有根治过敏的办法了,这个办法就是改变你身体中的某个基因。
从此我盼啊盼啊,一盼20多年,总是没有盼到那个改变基因的治疗法。我多方打听,有说根本没有改变成年人基因的治疗办法,有说美国政府压根不同意通过改变人类的基因来治疗疾病。无论哪个说法是正确的,我想,这辈子也别想这种“好事”了,从此,任何人再对我忽悠基因工程什么的,我一律左耳进右耳出。
去年某一天,我应邀参加腾讯主办的一场“高层次”讨论会,忘记具体名称了。我只参加了其中的一个对谈环节。那场会有两个特邀演讲,其中之一是某基因公司董事长的。我对他关于改变肠道基因的观点很赞赏,其时我正在通过节食减肥,也近于成功了。如果能像他所说,将我的肠道菌群彻底换一次,我不是不需要节食了吗?虽然到今天,我还是倾向于控制饮食,因为适量饮食能节省资源,对于养成个人的良好习惯有好处,同时还能锻炼一个人的自控力,从而获得某种自信。在当时,我真的想通过改变肠道菌群控制自己的体重,同时还能胡吃海塞。
他又强调,他们的研究还与根治疾病有关(我就窃笑了),而且,将来父母通过改变胚胎的基因,能生出既没有遗传疾病,又貌美如花的孩子。他谈到这些时眉飞色舞,而我完全没有注意。
中场休息时,参加讨论会的安替找到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该董事长的演讲中带有可怕的东西?当年纳粹不就是利用优生学强调保持完美人种吗?再说,什么叫完美?不论是疾病也好,美貌也好,都是有一个钟形分布,通过改变人类基因去除疾病做得再好,不过是将钟形分布的宽度变窄。
我一想,对啊。比如你作为父母,肯定想生一个美丽的孩子。但如果Ta不是最美丽的,而是次美丽的,类似某个选美榜单中的第三名,另外还有百分之六十的人都是第一名,你的孩子即使美丽,和那些人比还是丑啊。
再退一步,如果通过基因改变胚胎,满大街走的都是林志玲或全智贤,是多么可怕的一幕!如果再过几年,社会认为林志玲不美了,徐静蕾才是最美的,那么又要再生产一批徐静蕾吗?这还算好的,万一他们帮你做出来的孩子,都像现在满大街上的韩国整容网红脸怎么办?
DNA结构发明人之一沃森在《DNA,生命的秘密》中提过,1941年,印第安纳等州制定法律,规定一些人不能生孩子,还提到纳粹的优生学:党卫军的军官应该多生孩子,禁止德国人和犹太人通婚,还让22万多人遭受绝育。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完美主义行动派。
桑德尔则在《反对完美》中指出:人类利用科技追求完美,貌似大众的狂欢,实则蕴藏着危机—维系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础很可能坍塌,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也会错乱。
好在,实现基因狂人理想的进程,并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令人鼓舞”。最近《纽约时报》一则消息说,中山大学生物学的一些教授试图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遭到失败:胚胎要么死亡,要么基因没有改变。看来,人类试图扮演上帝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这有点像疯狂科学家躲进地下室,进行暗无天日的实验,最后很可能造出一个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幸好,《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批评中国的科学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