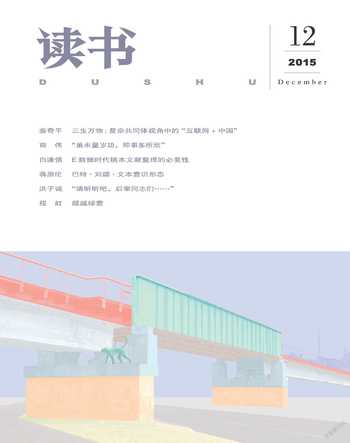追寻“不在场的记忆”
乐启良
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传统中,历史和记忆向来泾渭分明。历史学是一门有关时间的学科,但年鉴史学家总是主张要和人们的亲身经历或鲜活记忆保持适当的距离,认为这是从事科学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尽管承认历史学研究的宗旨乃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生活”,但却始终强调必须给它留下足够的回溯空间。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费迪南·布罗代尔(Ferdinand Braudel)、雅克·勒高夫(Jaques Le Goff)、勒华·拉杜里(Leroy Ladurie)等年鉴史家均不涉及现当代史的研究(马克·布洛赫《奇怪的战争》是一个例外),而纷纷把目光投向遥远而陌生的中世纪。这并非出于巧合,而更多是缘于其方法论的特殊考量。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布瓦什(Maurice Halbwachs)更是旗帜鲜明地把历史和记忆置于对立的两极:“在传统终结的地方,在社会记忆消亡或解体的地方,历史学才开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尤其是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之里程碑式的《记忆的场所》(Lieux de mémoire)出版以来,历史和记忆之间原本不证自明的鸿沟开始消失,记忆史研究开始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新领地。诺拉如是解释了记忆史在当代法国走红的深层原因:“记忆本身变成了历史,这导致每个团体都有义务通过复活自己的历史,重构其自身的认同。记忆的责任让每个人都变成了其自身的历史学家。”由此可见,记忆史学在当代史学界得以复兴的根本驱动力,实际上来源于人们追溯过去,理解当下并据以重构自身认同的现实需求。
诺拉倡导的记忆史并不是单纯意义上地追述个体、团体、族群或国家的过去。他表示,《记忆的场所》志不在此,而是要“为另一种历史敞开大门:它并不是要研究原因,而是要考察其结果;它并不是要研究记忆或纪念的活动,而是要考察这些记忆行为和纪念活动留下的痕迹;它并不是要研究事件,而是要考察它们的历史建构,研究其意义的消亡与重现;它并不是要研究实际发生的过去,而是要考察人们对过去的不断利用;它并不是要研究传统,而是要考察传统得以构建和传播的方式”。简言之,《记忆的场所》就是要研究过去在当代留下的“痕迹”(traces)以及重构、述说和利用这些“痕迹”的历史活动。
然而,并非所有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能够幸运地留下自己的“痕迹”,不计其数的人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但在当代的集体记忆里却了无痕迹。自其出版以来,《记忆的场所》受到的最多批评就是它只关注众所周知的“痕迹”,如克洛维洗礼、圣女贞德、巴黎圣母院、兰斯大教堂、拉维斯的《历史》、环法自行车赛、戴高乐……从而把法国记忆史研究变成了一部法国民族国家的纪念史。
譬如,一九八八年,热拉尔·努瓦利耶(Gérard Noiriel)就曾毫不客气地批评,在三分之一人口是移民或移民后裔,而且其世系不超过四代的法国,《记忆的场所》竟然对外来移民的贡献只字不提(在当时,《记忆的场所》只出版了第一、二卷,但后来出版的五卷对移民问题仍然涉猎有限)。他愤怒地把法国移民史研究的苍白现状斥为“记忆的不在场”(non-lieu de mémoire)。在某种意义上,努瓦利耶的多数研究(知识分子史研究除外)和诺拉的立场针锋相对,反其道而行之,试图重建“不在场的记忆”,把工人、移民、少数族裔等在当代法国集体记忆中处于“失语”状态的人群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努瓦利耶的新著《巧克力:黑人小丑》如法炮制,又为我们重构了一位曾经在“美丽时代”(la Belle Epoque)名噪一时,但却很快为法国人遗忘的黑人小丑演员的人生。
主人公拉法尔(Rafael)是法国舞台上第一位黑人艺术家。他在一八六八年左右出生于古巴的哈瓦那。父母皆为奴隶,姓名不详。“拉法尔”的名字是他们留给儿子的唯一遗产。八至十岁左右,他被卖给一个葡萄牙商人,后者将之带到欧洲。不久,拉法尔逃离至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在经历短暂而艰苦的矿工生活后,流浪街头。在此,他有幸遇到在当时享誉欧洲的英国著名小丑演员托尼·格莱斯(Tony Grice)夫妇。他们雇拉法尔为佣人,偶尔也会让他上场,临时客串马术、小丑等表演。一八八六年,拉法尔随他们来到巴黎谋生。拉法尔很快脱离格莱斯夫妇,加入处于草创阶段的“新马戏团”,并凭借在《巧克力的婚礼》(一八八八)里的出色表演崭露头角。时人因为他皮肤黝黑,而将之戏称为“巧克力”。从此,原本专门指代黑人的“巧克力”便成了拉法尔的代名词,无人不晓,时常见诸报端。
一八九○年左右,拉法尔开始了和英国小丑演员乔治·福迪特(Georges Foottit)长达十多年的合作。一黑一白的绝妙搭档成为世纪之交巴黎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明星。有关他们的报道充斥各大报纸,以他们为原型的玩偶深得儿童的欢喜。卢米埃兄弟(Lumières)拍过一部由他们主演的哑剧电影《巧克力之死》。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访问巴黎时,还专门观看了他们的表演。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五年,难以为继的“新马戏团”不再续约拉法尔和福迪特。从此以后,两人各自单演(后来也曾有过短暂合作),但从此以后惨淡经营,每况愈下,直至无人问津。一九一七年,拉法尔逝于波尔多,葬于当地的一个公墓,其墓地在今日已然不见踪影。四年以后,福迪特也因郁郁寡欢,不断酗酒而撒手人寰,葬于巴黎的拉雪兹公墓,而且其墓地至今保留完好。
“巧克力”拉法尔的人生跌宕起伏,神奇而又不乏悲剧。一个曾经出身为奴,不懂法语(他说克里奥尔语),缺乏专业训练(格莱斯、福迪特则不同,皆是出身马戏团表演世家)的黑人移民却能够在异国他乡迅速走红,变成炙手可热的明星,每月可赚八百法郎(当时法国普通工人的日工资不到三法郎),娶得法国姑娘,育有一男一女,但不久以后,其命运又急转直下,犹如划破长空的流星,归于沉寂,最终被人遗忘。
努瓦利耶认为,除了拉法尔本人从小接受黑奴文化熏陶,具有能歌善舞的本领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法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是我们理解其命运浮沉的关键因素。
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法国,巴黎变得繁华而喧闹,城市的边界不断拓展,原本人烟稀少的蒙马特地区如今咖啡馆、小酒馆、音乐厅、马戏团、戏剧院林立,成为社会各阶层流连忘返,声色犬马的最佳场所。因此,以巡演为生的英国小丑演员格莱斯夫妇携带我们的主人公来到巴黎,并驻足于此,实乃情理之中。而且,由于演艺圈的特殊性,外国演员不会和普通法国人在就业市场上产生冲突,排挤外国工人的移民政策不会波及他们,所以小丑表演人员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一八八九年,巴黎各个马戏团拥有小丑演员将近二十名,其中十五个是英国人,两个西班牙人,一个法国人,另一个就是拉法尔。
相比其他的欧洲演员,我们的主人公拥有一个不可多得的先天优势:其黑色的皮肤。当时的巴黎虽然已经涌入大量来自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和波兰等国的工人,但黑人移民却并不多见。对巴黎观众而言,拉法尔的表演充满了神秘色彩和异域情调,极具喜感。拉法尔之所以能够让他们笑得前仰后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把黑人看成一个“洗不干净”的白人。需要指出,起初,巴黎观众对初来乍到的拉法尔只是抱有一种天然的“偏见”,而不是种族主义的歧视。这一点在一八八八年《巧克力的婚礼》海报上可见端倪。除了皮肤黑色之外,拉法尔的形象自然、欢快,身体也没有任何的扭曲和丑化。而且,拉法尔在该剧中扮演的角色,更多地取自欧洲戏剧中经典的滑稽傻瓜形象—“皮尔洛”(Pierrot)。在欧洲的喜剧传统中,“皮尔洛”的形象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十七世纪末期的意大利哑剧。在经常光顾马戏团的没落贵族们的眼里,拉法尔更多代表了一个愚昧、无知、荒唐的仆人形象。
不过,在很短的时间内,巴黎观众的审美趣味突然发生了转折。拉法尔依然让他们捧腹大笑,但是,在他们的笑声当中,嘲讽、蔑视和白人种族优越感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是因为茹尔·费里内阁开始推行的殖民主义政策不断取得成功,共和政府越来越强调法兰西民族向黑非洲传播文明的“神圣使命”,文明高贵、盛气凌人的白人和落后愚昧、卑躬屈膝的黑奴之间的对立形象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法国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巴黎观众的优越感在拉法尔和福迪特长达十多年的合作中得到了体现。他们在福迪特对拉法尔象征性的斥责、侮辱和殴打中看到了白人国家统治黑人种族的合理性与满足感。巴黎的报纸在评论拉法尔的表演时,经常充斥着官方殖民主义的自负论调,而艺术家们在制作海报时,也不再正常地绘画拉法尔,而有意将之刻画成一个没有进化完成的类人猿形象。譬如,法国著名画家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就曾为他们创作了大量别具一格,但明显带有种族主义歧视的宣传海报。
然而,一桩看似和拉法尔本人毫无关联的重大事件却把拉法尔和福迪特的表演事业推向了谷底。一八九四年,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冤枉为德国间谍,但因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从中作梗,即便真相大白,法国政府也不愿承认错误,拒绝为他平反昭雪。一八九八年,著名作家爱弥尔·左拉在《震旦报》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直到一九○六年,最高法院才撤销原判,恢复德雷福斯的名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当中,法国共和派的报纸对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一八九八年成立的人权同盟更是旗帜鲜明地把种族主义视为人权的敌人。
伴随着针对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批判的不断升温,法国报纸(至少是共和派报纸)对待黑人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改口强调白人和黑人的平等。法国媒体开始称赞黑人在舞蹈和体育等领域的天赋,美国黑人舞蹈—“蛋糕舞”(cake walk)在二十世纪初的巴黎风靡一时,在美国遭受迫害的黑人拳王杰克·约翰逊迁居巴黎后也受到热烈欢迎。由于政治气候的风云变幻,巴黎观众的心理也随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令人捧腹大笑的福迪特施虐拉法尔的游戏,如今在他们的眼里已经变得索然无味,甚至令人作呕了。于是,他们不再光顾“新马戏团”,转而追捧时兴的体育运动,如环法自行车赛和拳击。
历史的吊诡在于,德雷福斯事件帮助一位深受反犹主义迫害的犹太军官洗刷了叛国的冤情,但却因为导致种族主义在法国成为禁忌,致使一位曾经在演艺圈大红大紫的黑人小丑失去了饭碗。一九○五年,日益凋零的“新马戏团”不再续约拉法尔和福迪特。两人开始了其黯淡无光的单飞表演。拉法尔后来参演过戏剧,也曾和儿子欧仁合作,让他扮演福迪特的角色,但皆以失败而告终。晚年的拉法尔不得不在法国各地以流浪表演为生,而子承父业的欧仁则因为郁郁不得志,走向了与福迪特相同的命运,因为酗酒而英年早逝。
需要强调的是,德雷福斯事件只是让种族主义在公共舆论中成为禁忌,但并没有导致它在法国的彻底消亡。而且,法国民众对黑人的认可似乎也仅限于舞蹈、体育等能够展示黑人身体优势的领域。在其他领域里,他们对黑人的歧视依然根深蒂固。拉法尔后来之所以未能在戏剧表演中获得成功,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因为巴黎评论家们做出了尖酸刻薄的评论。虽然他们不再能够讥讽拉法尔的皮肤,但却对其语言水平百般嘲弄,认为他糟蹋了神圣的戏剧艺术。
在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演员拉法尔的印象日渐淡化,直至无人知晓。但他在小丑表演中塑造的愚昧无知的傻瓜形象却以另一种方式,潜移默化地扎根于法国人的心中。在法国的某些字典和日常用语中,“巧克力”的概念拥有了一层特殊的涵义,“做巧克力,就是在做傻瓜”。
努瓦利耶在重构被人遗忘的“巧克力”拉法尔的人生时,“经常抱有强烈的同情心,甚至为时人对待他的方式感到不公”。但他表示:“历史学家并不是检察官,应当和控诉的立场保持距离,因为控诉往往会成为认知的障碍。”他认为,后殖民主义史学家的错误恰恰在于把自己变成了检察官,用控诉取代了研究,结果却由此“剥夺了失败者任何反抗和行动的能力”,从而扭曲了历史的真相。事实上,拉法尔从来不是一个消极意义上的被动者。自从逃离葡萄牙商人的控制以后,拉法尔一直保持着自由人的身份,为改善自己的命运不断努力。他追随格莱斯夫妇来到巴黎,但随后又离他们而去;他通过接受逆来顺受的黑奴角色而赚取了丰厚的收入;在一九○九年传出其死亡的假消息后,他立即用其蹩脚的法语在《时代报》上发表了一篇出自其手笔的简短文字,宣称“我还活着,我还在表演”。
但是,拉法尔的悲剧在于,无论他如何努力,他的命运始终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拉法尔的演艺生涯和人生道路,更多地取决于其周遭的评论家、艺术家、记者对其形象的刻画,取决于他们对巴黎观众之审美趣味的塑造。然而,这些评论家、艺术家、记者的政治立场,也并非全然是其自由选择的结果,他们也会受到演艺市场、媒体竞争和政治气候的左右。
在某种意义上说,努瓦利耶在重构“巧克力”拉法尔的故事的同时,为我们重现了世纪之交法国的“权力场域”,描绘了演员、艺术家、观众在民主选举、媒体自由和市场竞争的新背景下如何生活并相互影响的众生相。努瓦利耶在撰写《巧克力:黑人小丑》时,一如既往地践行其界定的历史学家的理想使命:真正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当能够‘翻译’媒体与政界的常识问题,将之问题化(problematiser),从而揭示充斥我们周围的众多话语背后的压迫形式和社会痛苦”。
对努瓦利耶而言,唯有如实地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唯有准确地再现历史人物所承受的各种权力关系,才能创造科学的知识,才能创造有利于被压迫者之解放的工具。不过,努瓦利耶清楚地知道,面对冷冰冰的市场逻辑、赤裸裸的政治竞争以及很容易为金钱与政治所绑架的媒体世界,单枪匹马的历史学家无法让自己创造的历史知识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因此,努瓦利耶在研究历史之余,开始和艺术家们合作,寻找传播专业历史知识的有效途径。二○○九年出版的《历史、政治与戏剧》即是努瓦利耶在这方面理论思索的结果。
努瓦利耶不仅在理论的层面鼓励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们进行合作,而且也身体力行。在撰写《巧克力:黑人小丑》的同时,努瓦利耶和法国戏剧导演马塞尔·博佐内(Marcel Bozonnet)创作了同名戏剧。自从二○一二年公演以来,它受到了法国观众的热烈欢迎,至今仍在法国巡回演出。与此同时,同名电影也在紧锣密鼓地拍摄。
由此看来,“巧克力”拉法尔似乎又要迎来一段传奇的故事。在努瓦利耶的帮助下,他正在走出“不在场的记忆”,有可能成为法国民众新的“记忆的场所”。
(G.Noiriel,Chocolat Clown nègre. L’histoire oubliée du premier artiste noir de la scène française, Paris, Bayard,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