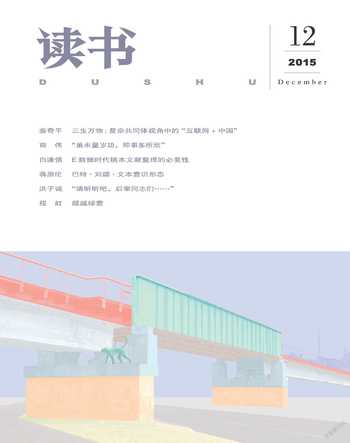一个人,没有同类,也不要紧
朱生坚
电影《刺客聂隐娘》让很多人感到无聊。
于是,忽然想起,在《复仇》里,鲁迅这样写看客的无聊—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干枯到失了生趣。
这些人是赶来看热闹的,因为有两个人,手握利刃,赤裸全身,像要拥抱或杀戮。然而,他们却只是那样站着,一动不动。最终,看客散去—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鲁迅一向讨厌看客,激赏复仇者。这都是有来历的。他改用前人的话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他写复仇、写刺客,摄人心魄,令人神往,尤其是《铸剑》里的眉间尺和黑衣人。
《铸剑》的故事骨架取自干宝《搜神记》,而在精神上与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相通,有血性,有真气。年轻的时候读史书,最让我激昂的就是古人为了一句信诺,可以二话不说,把自己脑袋割下来给人—鲁迅笔下的眉间尺与黑衣人,正是如此。后来知道,所谓血性和真气,不仅止于此。它们有各种表现形式,通过各种方式记述、传承下来。鲁迅说过,想要得到一点真见识,读经不如读史,读正史不如读野史、杂说。这是面向普通读者、青年学生的经验之谈,免得他们上了阔人的当。他当然再清楚不过,经与史,正史与野史、杂说,乃至诗、赋,实则有相互贯通的气息。司马迁写《史记》有想象,有虚构,而干宝在《搜神记》之外,有《晋纪》二十卷,“直而能婉,时称良史”。他们用不同的笔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又与屈原的“天问”异曲同工。
从先秦两汉魏晋一路下来,这种血性和真气灌注在唐诗中,散发为“盛唐气象”,这是显的一面;相对而言,隐的一面,则是在其他样式,包括志怪传奇侠客小说,其中,就有聂隐娘的故事。
侯孝贤让传奇小说中的聂隐娘脱胎换骨,拍成电影《刺客聂隐娘》。它做足了讲故事的架势,草蛇灰线,藏头露尾,像侦探片一样诱引你去还原整个故事。高智商的朋友就喜欢玩这种游戏,手脚勤快的,还绘制成图表,在“朋友圈”里张贴出来。其实,《刺客聂隐娘》的情节结构、故事线索、人物关系等等,根本就不重要。它的人物形象,与“黄金甲”和“武媚娘”之类影视剧相较之下,并不光鲜亮丽,一点都不抢眼,那些侍女站在你面前,简直就为了被你忽略掉。它的细节做得很扎实,扎实到了近乎笨拙,譬如有个插首饰的动作,笨拙到了近乎扎眼,可是这些细节根本没有任何内涵,就是细节而已。它的故事结构看起来有点复杂,要是你去把它勾画出来,那就好比高明的盗贼费劲巴拉地打开保险箱,可是里面根本没啥东西。
概言之,这部电影正因为实到够实,所以虚到够虚。诸如绘画中的留白之类的以虚为实的手法我们都见得多了,以实为虚,还真不多见。
在这部电影里,虚实之间的转换相生无处不在,就连电影的片名也是如此:为什么不直接就是《聂隐娘》呢?加上“刺客”二字,好像是为了修饰、彰显,却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视线,把“聂隐娘”掩藏起来。很多镜头几乎静止不动,有鸟飞过湖面和树林,有云气蒸腾于山峦和天空,却比静物更静止。很多画面之美,足可见造化之神功确实超乎想象,这是有眼能看的都能看到的;而在这些画面上,仿佛有些东西,却是有眼能看的人未必都能看到的—当然,也不是非得说有。
虽然处处以实为虚,这个“虚”并非真空那样的“无”,其中有真气流动—至于前面说的血性,不是这部电影所要表现的,况且也不是这个鄙俗猥琐的时代所需要的。现在的流行词里头没有“血性”,只有“尿性”,真是扯淡。
真气在天地之间,在山水之间,在人的言行与意念之间流转不息,而又始终保持安静,内敛,若隐若现,只能“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然而,“神遇”还以“目视”为前提。要不然拍电影干什么?不过,好电影不只让人“目视”看得到的东西,也会让人“神遇”看不到的东西。
可是,买了电影票来看电影的人总归更愿意看到人物,看到动作,看到情节。而这部电影太考验耐心了。经常满满一屋子的人,却没有什么动作,连声音也没有,简直是在挑战整个视觉时代。有人“于是乎无聊”,退场的退场,玩手机的玩手机。于是乎有人写文章,批评他们的审美趣味鉴赏水准等等。这是不对的。我想,他们不仅感到冷落、疏离,觉得有无聊从毛孔钻进钻出,更是受到了一种逼迫。这些静止的镜头中断故事的进度,逼迫我们直接面对一种存在。而这恰恰是我们整天对自己按着快进键的生活中避之唯恐不及的黑洞。在饱满的画面所营造的虚无之中,有一种能量巨大的实在,有“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却又沉潜、隐忍。鲁迅在《复仇》里写的那两个人,终于并未拥抱或杀戮,因为拥抱或杀戮固然痛快,不如对峙在无止尽的静穆之中。
《刺客聂隐娘》的结果也并非拥抱或杀戮。隐娘选择归隐,与磨镜少年一起去了新罗。在这里,“新罗”只是一个能指,一个符号,实则无异于自秦、汉以至唐代诗文里经常出现的蓬莱、瀛洲之类的“海上仙岛”。这些仙岛亦实亦虚,非虚非实。“新罗”也应作如是解。
说到蓬莱、瀛洲,我们知道,李白经常做的一个白日梦,就是“为君谈笑静胡沙”,然后“灭虏不言功,飘然陟蓬壶”。虽然他这些说法总是带着一点酸葡萄味道,却也接近于某些人的真实想法。另外还有一种可能:他原本就是从前人那儿学来的。一切功名利禄终将烟消云散,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皆为天地间之气运流转,非人力所能左右。聂隐娘做得到不以成败为怀,也可以不求安身之地,可是,她的一身剑术不再有用武之地,那就不如飘然远逝,葆守能量,真气伏藏。斯人已去,行迹流传。她渐行渐远,终于从画面消失,她所留下的空缺反而真真切切地揭示其存在。
聂隐娘的任务是刺杀表兄田季安。她手握利刃抵住他的颈动脉,却放弃了。她应该在此之前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作为奉命而往的刺客,她必须到这一步,才能跟师父复命说:“弟子不杀。”—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这一句,平静、坚定,无异于摊牌。本来,师徒一场,至此尚有余地,毕竟聂隐娘仍然恭恭敬敬,行弟子礼如仪。山谷间好一阵风起云涌,呼应着师徒俩的内心激荡。一转眼间,师徒交手。于是,恩断义绝。聂隐娘把师父道袍割开一个口子,扬长而去。
这个结果应该不会出人意外。谁都明白,前面重复了几遍的通关密语,“一个人,没有同类”,说的就是聂隐娘。同类,可以为友,也可以为敌—根本不搭界、没有交集的人,不可能为友,也不可能为敌。一个人,没有同类,意味着既无友,也无敌,那是真正的孤独。
这样的孤独,有一个古老的版本,在《庄子·齐物论》的开头:
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丧其耦。
所谓“没有同类”,正是“似丧其耦”的白话版。另外,也有一个较为晚近的版本,徐梵澄《星花旧影》写鲁迅:
先生也深通老、庄,胸襟达到了一极大的沉静境界,仿佛是无边的空虚寂寞,几乎要与人间绝缘。如诗所说“心事浩茫连广宇”,外表则冷静得可怕,尤其在晚年如此。往往我去拜访,值午睡方起,那时神寒气静,诚有如庄子所说“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 然似非人”。
沉静,冷静,神寒气静,正是“心事浩茫连广宇”的一种面相,以寻常人的眼光看来,却又“仿佛是无边的空虚寂寞,几乎要与人间绝缘”,正是“没有同类”到了极点。同样,尼采曾经说自己处于距离尘世六千尺的高空,那更是“与人间绝缘”的样子—然而,恰恰就是这个尼采,在令人疯狂的寂寞中,“想要拥抱随便哪一个人”。
呦呦鹿鸣,求其友音。鹿犹如此,人何以堪。聂隐娘的孤独实属迫不得已,尽管能够面对这种孤独也非常了不起。然而,问题在于,她似乎迷恋这样的孤独:青鸾舞镜的故事,好像一个东方版的那喀索斯(Narcissus)。退一步说,自恋不是问题,只是,至少要在某个时刻知道,在镜面、水面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想象中的自己,一个虚幻的同类。再者,青鸾也好,那喀索斯也好,前世留存下来的各种传奇、意象大都与我们所有人有关,指示每个人身上都有的某一方面的可能性。所以,不能因为自己发挥了这一方面的可能性,就入了戏,自以为是唯我独有的特性,不管那种意象有多么迷人。
单独一个人,就算可以“生存”,也不能进入“存在”,如果这个人不能建立与世界的联系。换句话说,完全孤立的一个人,只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聂隐娘最终选择了磨镜少年,貌似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结果仍然令人怀疑:她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是磨镜少年?小说没有交待,电影没有交待,我们也不必追根究底。大致可以肯定的是,磨镜少年的出现,呼应了青鸾舞镜的意象。青鸾是虚的,磨镜少年却是实的,而且与聂隐娘有肉身的接触。然而,磨镜少年能够解决青鸾的问题吗?
聂隐娘的孤独根深蒂固,因为刺客注定是孤独的。这根本谈不上什么个人英雄主义。现代的、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总是突出个人,而细读那些正史、野史、传奇、小说,不难发现一个悖论:在所有这些文字里,说到底,个人并不重要。这里倒是用得上《雷锋日记》的格言:“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不干。”当然,还有更加靠谱一点的阐释。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那个陶渊明,曾经突发奇想,写了一首《形影神》,构想形、影、神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是把自己一分为三,讨论个人的存在问题,他的答案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而早在陶渊明之前,有两种路向解决这个问题,简言之,一种是和光同尘,一种是仁者爱人。凡此种种,都不是与人间绝缘,而是与怨恨、牺牲、杀戮绝缘,不管这些怨恨、牺牲、杀戮打着多么华美的旗号。
一个人,没有同类,本来也不是坏事。但是,也不必迷恋于此。几次三番,用旁白说出,那就成了一种过于喧嚣的孤独。当然,这不是聂隐娘的错,也不是侯孝贤的错。
无论如何,聂隐娘与磨镜少年携手归去,孤悬海外,这个结局不好。虽然,如前所述,也不妨以这种方式葆存能量、伏藏真气。但是,脱离了赤县神州苍茫大地,终究如浮萍飘零,一不小心,会渐渐失去生机;还真不如像鲁迅所言,“在刺丛里姑且走走”,或如其诗云,“风波浩荡足行吟”,就算是一个人,没有同类,也没什么要紧。
——正气、勇气、底气和一点傻气
——从《刺客聂隐娘》看侯孝贤的“归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