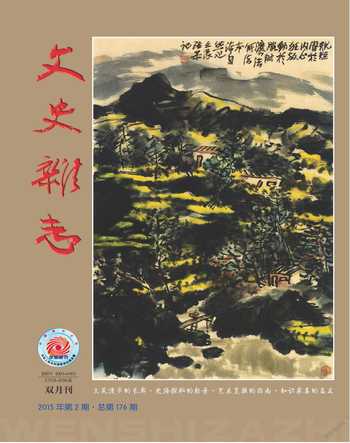唐代西蜀女诗人薛涛事迹稽沉
冯广宏
蜀人对薛涛并不陌生,因为除了成都望江楼、薛涛井、薛涛坟这些名胜寄托诗魂以外,还有刊入《洪度集》近90首薛涛诗,引人咏叹。但令人遗憾的是,史册中并没有薛涛传记,各种文献里只有些疑信参半的记载,即如女诗人的身世,还笼罩在重重迷雾中。近人研究薛涛做了大量工作,对她的事迹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可是仍有互相抵牾的地方,笔者亦欲略陈愚见,探赜稽沉。
薛涛当时的社会地位
薛涛的身份,迄今有两种反差很大的说法:一种说她是官太太;一种则视为娼妓。其实,时至今日,无论薛涛是什么身份,都无损于女诗人的美好形象。
有关薛涛身份的材料,以唐李肇《唐国史补》为最早:“有乐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涛”;唐范摅《云溪友议》称“西蜀乐籍有薛涛者”;口径比较统一。关于“乐妓”“乐籍”的讨论已很充分了,其地位大致相当于三陪小姐,是专向官僚阶层开放的娱乐圈内人物。这是薛涛同时代人的看法,我们不能不承认,元朝“七奴八娼,九儒十丐”,老九的地位还不如娼妓,又有什么办法呢?
薛涛怎会零落风尘?原因不外乎三种:一、或因唐代宗时社会动乱,吐蕃入侵西川,藩镇争权夺利,她们孤儿寡母,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走这条路;二、或因上辈获罪,连累子女当奴作婢;三、封建官僚一贯将女性当作玩物,强令应召,迫于地方官的淫威,弱女子难以反抗。史缺有间,其来由不能肯定,反正这些原因总有一个。
当今有些先生出自好心,想翻这个旧案,论证她是州官夫人,似亦回天乏力。现再举两个新证,以证此案翻不过来——薛涛有两首赠和尚的诗《宣上人见示》《赠僧吹芦管》。那个时代同和尚作朋友者多为男性,女性则恐遭物议,而薛涛这种身份便无所谓。或谓广宣和尚是个公众人物,女士赠送诗篇较为正常,那么另一个吹芦管的和尚就无法说通。第二,从刘禹锡《和西川李尚书〈伤韦令孔雀及薛涛〉》诗题可知,无论刘禹锡或是李德裕,都是从孔雀想到薛涛,对一个州官夫人不可能如此联想;可见在他们眼中,薛涛只是个漂亮的孔雀。刘诗首句“玉儿已逐金环葬”,并注明玉儿是后魏元树的小妾,用以暗喻,那么薛涛的地位就不言而喻了。
薛涛存诗半属应承
确定了薛涛这种难堪的身份,使我们更加同情她那悲惨的命运。相传薛涛一生写了500首诗,现存于《全唐诗》中虽仅88首,却也有一定代表性。笔者就此作过统计,其中酬赠诗就有43首,占48.9%,基本上是一半;咏物诗27首,占30.7%;其余就是游历抒怀的诗18首,占20.4%。可见她很大精力是用在应酬方面。这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应当是一件痛苦的事,官家女眷不可能如此应酬。《全唐诗》小传称她“历事十一镇”,果然,在这43首酬赠诗题中就有上韦令公(皋)、高相公(崇文)、武相国(元衡)、王尚书(播)、段相国(文昌)、杜舍人(元颖)、李太尉(德裕)等七人八任节度,超过了半数。88首诗中除了五律1首、七律3首和古风1首外,94.3%都是绝句,这也许与她的职业习惯有关。蜀中流行竹枝歌多为四句体,歌手们非常熟悉。
薛涛善于用典,对于不同的对象,巧妙地采用不同手法,并不千篇一律。例如高崇文是个大老粗,做的《雪席口占》就声称“崇文宗武不崇文,提戈出塞号将军”;因此薛涛《贼平后上高相公》诗里完全采用大白话,“惊看天地白荒荒”,完全不用典故。王播是个典型文人,她《上王尚书》诗用“十万人家春日长”含蓄地歌颂他,更有回味。又如《十离诗》通篇风格诙谐,为的是让主公变怒为笑,就不能再掉书袋,纯用俳体。《酬祝十三秀才》大概是送下第秀才的诗,所以她写了“诗家利器驰声久,何用春闱榜下看”来安慰他。从这些诗句中,能够看出薛涛周旋于士族之间,用心良苦。
韦皋罚薛涛赴边起因
薛涛诗里表达出遭受的最大苦难,是罚赴边地,现存《罚赴边府有怀,上韦令公》《罚赴边上武相公》各2首即道其悲哀,“罚赴边”在古代等于充军。
薛涛头一次受罚,因为得罪了韦皋。韦皋年轻时就潇洒不拘,《唐摭言》说他是前任西川节度使张延赏的女婿,可是延赏瞧不起他。在他东游时,张家送他七匹马驮着财物,而他每到一处驿站,就送还一匹,到了目的地,一匹也没落下。贞元元年(785年)他接替岳父任节度使,年仅40岁,今人公认是他让薛涛列入乐籍。韦皋政绩主要在于团结西南民族,抗御吐蕃,稳定边陲。贞元六年(790年)以前,韦皋上任不久,忙于应付吐蕃入侵,恐怕没有闲心召唤薛涛;因此入乐籍一事当在贞元六年之后,而以平安无事的贞元十年(794年)最有可能。直至贞元十二年(796年)和十七年(801年),韦皋大破南诏吐蕃,加官进爵,有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中书令”的头衔,他才能在诗人作品中称作“相公”或“令公”,直至永贞元年(805年)病故。因此薛涛此次受罚,当在公元796~804年之间。
薛涛受罚起因,今人多据后蜀何光远《鉴戒录》来推测:“涛性亦狂逸,不顾嫌疑,所遗金帛,往往上纳。韦公既知且怒,于是不许从官。”乐妓私收礼赠,这种事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否就会受罚赴边呢?笔者认为,韦皋恐怕不会为了这点小事,否则太缺乏郡王风度了;而且《鉴戒录》明记此次受罚仅是“不许从官”,并非赴边。或谓《十离诗·犬离主》有“近缘咬着亲知客”,《全唐诗》注“涛因醉争令掷注子,误伤相公(注指元稹,有误,当指韦皋)犹子,去幕”,认为她酒醉得罪了韦皋的侄子,但这更不是赴边之罪了。韦皋不会如此轻视法律;何况薛涛还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会有人出来帮她解围。因此笔者以为,其间应有政治上的原因。
薛涛很有词辩,经常在上层官僚涉及政事的议论场合中,多嘴多舌,这就犯了官场的忌讳。史称韦皋在蜀,军费开支很大,于是重加赋敛,并向朝廷封锁消息。薛涛侍奉韦皋多年,对种种弊政了如指掌,或许大胆多了几句嘴,这才碰到了地雷。她诗中自称“严谴妾”,可见问题比较严重。贞元十八年(802年)吐蕃还曾引兵攻打过维州(治今理县),她下放的地点是在松州(治今松潘),当时却去不得,诗中所说“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正是这一情况。薛涛诗又有“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之句,将了韦皋一军。官家乐妓对乡野平民唱曲,也会让节度使丢了面子;何况前边“闻道边城苦,今来到始知”两句,已经达到了受罚的目的。这样,韦皋便不得不放她了。所以韦皋赦免薛涛,似以此年的可能性为最大。
还须指出,韦皋有一首《忆玉箫》的诗,怀念旧时的情人;后来东川送他的歌姬亦名玉箫,而且和他思念的玉箫面貌相似,得到宠爱。所以韦皋对于薛涛,恐怕谈不上什么情感,仅仅爱其口才和文才而已,这才会发生焚琴煮鹤式的严厉惩罚。
薛涛再次赴边被赦
薛涛第二次赴边被赦,是在武元衡任上。由于文献无征,受罚原因不详;同时此事还存在着争论,故须将中唐蜀史作一下简单的回顾。韦皋任西川节度使时间长达20年。他死后的元和元年(806年),朝廷虽命袁滋继任,但称为“狂憨书生”的野心家刘辟却自任留后,阻兵自守,所以袁滋不敢来川。那时宪宗初立,只好任刘辟为节度副使。刘辟得寸进尺,要求兼领三川,这就惹恼了皇帝,命高崇文带领五千人马来征,经过大半年的战斗,捉住了刘辟。宪宗于是任命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崇文本是一介武夫,明知西川的位置坐不稳,不到一年就打了几次报告,要求还朝;宪宗只好让武元衡接替他。崇文离开成都时,史称他“尽载其军资、金帛、帟幕、伎乐、工巧以行,蜀几为空”。在这动乱的一年中,薛涛一定饱受折磨,如果她当时还在成都,也许高崇文就带着她到长安去了,可见她被罚赴边,乃刘辟所为。所犯何罪?可能也与政治有关。她曾希望崇文能赦免其罪,写了“始信大威能照峡,由来日月借生光”等诗句,一方面称刘辟为“贼”;一方面低头吹捧崇文;可是这60岁的武夫似乎没有理她,这才有《罚赴边上武相公》二首,转而请求武元衡。第一首诗中自比为萤,把武元衡比作月光普照,希望元衡发现自己,加以援手;第二首“但得放儿归舍去”,真是催人泪下的乞怜语。那时元衡49岁,薛涛恐怕不到三十,称“儿”是一种不卑不亢的贱称,比称奴称妾更好。史称武元衡“雅性庄重,虽淡于接物,而开府极一时之盛”,可见他是个爱才的正人君子。当时薛涛的命运可能由他挽救。看薛涛后来给他的几首诗,题称“川主”,虽着意歌颂,却文辞娴雅;因为《旧唐书》称“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施于管弦”,应该是她的一位诗国知音。
薛涛实任校书仰仗元衡
薛涛名列乐籍,相当于戴了一顶黑帽子。在封建社会如想脱帽,一要金钱赎买;二要政治翻身,其间都少不了达官贵人的援手。由于顽固势力设置种种羁绊,办成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鉴戒录》云:“大凡营妓,比无校书之称。自韦南康镇成都日,欲奏而罢。至今呼之。”所谓奏请校书,实为脱去乐籍的一种方式。以韦皋那种倜傥的性格,想来解决这个问题,倒是符合事实的,但他遇到了舆论的阻遏,从而作罢,于是这件事便落到知识型的武元衡头上。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言“武元衡奏校书郎”,恐怕不是捕风捉影之谈。李夷简给武元衡的诗《西亭暇日书怀十二韵,献上相公》,中有“琬琰富篇什”之句,琬琰明指薛涛,可作旁证。武元衡有一首咏韦令公孔雀的诗,大可注意:诗题有“座中兼故府宾妓,兴嗟久之”,那故府宾妓可能即有薛涛在内。他诗中又有“美人伤蕙心”之句,似为同情薛涛之语。其尾联“会因南国使,得放海云深”,也表露了要让孔雀(实指薛涛)重新获得自由的想法。这首诗引得当时许多诗人唱和,如白居易“放归飞不得,云海故巢深”,是赞成元衡这一想法的。
薛涛的“校书”职称,笔者认为不是虚名,而是事实。其理由是:唐代诗人咏薛涛者多称之为“校书”,如王建、司空图即是,与当时众多的男性校书无别。薛涛的酬赠诗题中唯一没写职称的只有《寄张元夫》,元稹《贻蜀五首》之一是《张校书元夫》,可见此人也是校书。由于其官位与薛涛相同,加之较为亲近,所以薛涛不写他的职称,由此可以反证薛涛实职正是校书。再者,薛涛死后由段文昌亲撰墓志,即称之为“校书”,因此薛涛被人呼为校书,并非开开玩笑而已。
薛涛籍贯和元薛之恋
这是存在争论的两个问题。薛涛籍贯与“峨眉”有关,她的诗《乡思》“峨眉山下水如油”更为坚证。《云溪友议》谓元稹听说薛涛才名,总想来川一见,苦无机会;后来经过严绶的撮合,才得相见,此事可能属实。元稹有《好时节》一诗,值得注意:
身骑骢马峨眉下,面带霜威卓氏前;
虚度东川好时节,酒楼元被蜀儿眠。
“峨眉”“卓氏”代指薛涛,有元稹“锦江水滑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诗句为证。《好时节》诗表明元稹已经与薛涛相见,只不过他身为监察,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不好吐露感情,因为那“酒楼”是被“蜀儿”占据了的。或谓严绶让薛涛到江陵去见元稹,似乎不确;元稹有《阆州开元寺壁题乐天诗》,可见他已来到阆中,前往成都并无险阻,薛涛不必远至江陵。然而元薛交好离不开严绶的撮合,则应是事实。
应当指出,当时众多诗人赞美薛涛,乃赞其才,非赞其貌,这是有一致性的,可见薛涛并非花容月貌。推想34岁的元稹爱慕年龄相仿的薛涛,亦以友情为主,两性恋情当居其次,观其《寄赠薛涛》可见。薛涛好像对张元夫有那么一点意思,她《寄张元夫》“伯牙弦绝已无声”一语,似已引为知音;而元稹给《张校书元夫》的诗则意存警告:
未面西川张校书,书来稠叠颇相於。
我闻声价金应敌,众道风姿玉不如。
远处从人须谨慎,少年为事要舒徐。
劝君便是酬君爱,莫比寻常赠鲤鱼。
完全是一套老大哥口吻,其间寓意亦颇微妙。
薛涛籍贯与“峨眉”有关,以及元薛之恋,还有白居易《赠薛涛》“峨眉山势接云霓,欲逐刘郎北路迷”可证,似乎无法推翻。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