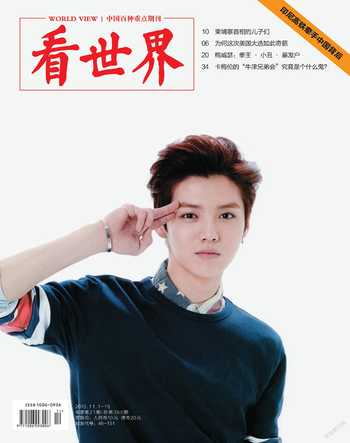为什么这么多种语言都管双亲叫“爸”“妈”
约翰·麦克沃特 李颖浩译

“狗”在英语中念“dog”,法语中念“chien”,俄语中念“sobaka”,在汉语中念“gǒu”。这几个发音都没什么共同点。当然,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对于这种面对墙就会不断用小短腿往前刨的动物的称谓,大家“各说各话”而已。
但有些词不是这样。世界很多语言关于“妈妈”这个词的发音都是mama或者辅音换成与m近似的n的nana。而“爸爸”这个词常发音papa或者与之近似的baba。而“爹”这个词常常有d或者t的音,跟前面的逻辑一样,t被认为是d的变体。也就是说,在全世界,人们普遍管母亲叫mama或nana,管父亲叫papa、baba、dada或tata。
有些人在生活中可能就发现了这种怪异的相似,但如果只是在欧洲范围内的各语言中发现这种相似性还不足以令人太惊奇,毕竟这些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它们共同的“祖先”是数千年前居住在黑海之北森林(今乌克兰)里的部落所使用的语言。所以,法语的mama和papa,意大利语的mamma和babbo,挪威语的mamma和papa,这些发音如此相似或许因为它们是“亲戚”。
不过,这种逻辑并不绝对成立。因为别说几千年,时间上有更近联系的语言都会变得互相完全认不出来。比如,威尔士语也是“古乌克兰语言”的后代,但它能诞生英语和法语都不会产生的一个小镇名字——Llanfairpwllgwyngyllgogerychwyrndrobwllllantysiliogogogoch。最近英国第四频道的气象主播念到这个小镇,又让这个冗长的名字火了一把。作为同一大语系的一员,威尔士语有很多自己独特的改变,但“妈妈”和“爸爸”二词还是mam和tad。
更令人吃惊的事实要来了,就是印欧语系以外的语言也有这个规律。非洲的斯瓦希里语有mama和baba。菲律宾的他加禄语有nanay和tatay。斐济语有nana和tata。而在令西方语言学习者最“闻风丧胆”的汉语中,居然也有mama和baba。接着,高加索的车臣语是naana和daa。美洲原住民的爱斯基摩语是anana和ataata。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州的夸萨蒂语是mamma和taata。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的比比尔语则是naan和tatah。
这很容易引起一个猜测——比“古乌克兰人”还早的、最古老的人类管他们的双亲叫mama和dada这两个词,然后从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幸存到现在。但这种猜想太理想化了,几乎不可能。语言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不仅发音会不断地融合改变,同一个词在不同地方的传播过程中也会演变出不同的意思。
拿印欧语系的老祖宗“古乌克兰语言”来说,如果我们拿今天的语言和过去的语言相比较,就能推断出久远的“古乌克兰语言”中的很多个词。这个道理就如同我们通过比较今天的哺乳类动物和它们的化石就能推断出,最早的哺乳类动物是长毛发的类似啮齿目的胎生生物。
在印欧语系中,mregh这个词本是“短”的意思。而这个词在希腊演化成“上臂”的意思(上臂比较短)。在拉丁语中则指一种像一双双交叉手臂叠加的油酥糕点。而这个词到了法国就是“肩带”的意思了。后来这些演化词都传到了英语中,这个最初意味着“短”的词这时就演化出了“手臂”(源自希腊)、“椒盐卷饼”(源自意大利)和“胸罩”(源自法国)的意思。而mregh在英语中最直接的演化词是merry。精悍的(short)往往是甜蜜(sweet)的,所以这个词的意思就变成“short and sweet”(“简单明了”之意),后来又只取甜蜜之意——也就成了merry。
按理说,像mama和dada这样的词也应该会出现类似的演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变得“形态各异”,但为什么这种事没有发生呢?
未学说话的婴儿随意发音,最简单的就是发“啊”音,因为这不需要动用到舌头和嘴唇。接着,如果要进一步发音,最本能的冲动就是合上嘴,终止“啊啊啊”的发音,这就产生了“嗯嗯嗯”的音,结果一张一合就能产生类似“ma”的发音了。
答案在于婴儿是如何开始学说话的。来自俄罗斯的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逊解开了这道谜题。未学说话的婴儿随意发音,最简单的就是发“啊”音,因为这不需要动用到舌头和嘴唇。接着,如果要进一步发音,最本能的冲动就是合上嘴,终止“啊啊啊”的发音,这就产生了“嗯嗯嗯”的音,结果一张一合就能产生类似“ma”的发音了。
婴儿的这种发音是无意识的,但是成年人可能并不这么认为。婴儿喊着“mama”听起来像是在呼唤谁,而他最可能找寻的人无非是他的妈妈。因此妈妈就将“mama”当作了自己的称谓,然后在孩子面前称呼自己为“mama”。这很可能就发生在最早的人类身上,而且发生在全世界不同语言区的婴儿与妈妈身上。这跟mregh的不停演化不一样,这种“mama”的“误解”不停地发生,让“mama”这个作为妈妈的称谓相对固定了下来。

papa或dada的形成也是因为类似的全球通行的原因。在闭合嘴唇发出m音后,婴儿会做进一步的发音尝试。他们先把双唇贴合起来,一阵后又张开嘴往外送气,这就发出了p音或者b音。另外,婴儿还会用舌头去顶上齿的背面,尤其当被喂食的汤太热的时候,这样就发出了t或d的音。所以婴儿学习发音的顺序解释了为什么亲密程度仅次于妈妈的爸爸被称为papa或baba(或tata或dada)。
类似的解释可以用在另几个“通用词”身上。语言学家约翰娜·尼科尔斯发现,在欧洲及大部分亚洲北部,“我”和“你”的发音常常包含m和t。如法语中的moi和toi,西班牙语中的me和tu,俄语中的menja和tebja,芬兰语中的minä和sinä,乃至更东方的西伯利亚的尤卡吉尔语也用met和tet。(实际上,英语过去也把“我”和“你”称me和thou。)
尼科尔斯认为,“我”和“你”的发音规律与“妈妈”(mama)和“爸爸”(tata)的规律类似,可能受了后者影响。所以m的发音用来指最亲近的意思——妈妈(mama)或我(me),t用来指亲近程度稍逊的对象:爸爸(tata)和你(thou)。
但是这两个代词的发音规律不适用于全世界,仅适用于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像汉语的“我”和“你”分别发音wǒ和nǐ,印度尼西亚语则发saya和anda这两个音,这两种语言都不符合这个规律。
除此之外,要探究其他词发音的由来,其实很难说得清——即便有一些也存在规律。如在英语中,很多有关“发光”的词都以gl开头,如glow(发光)、 glare(发眩光)、 glitter(闪光)、gleam(闪烁)和glance(反光)。还有,英语中很多关于渺小和快速的词都有ee的发音。个中缘由,人们还没有清晰确定的认识。
美国人类学家布伦特·柏林曾对600个学生做了个实验,向他们展示来自秘鲁的小众语言Huambisa的两个单词——chunchuíkit和máuts,问他们哪个是指鸟类,哪个指鱼类。学生们凭直觉选择,结果大部分都选对了。chunchuíkit指的是鸟类,有学生表示chunchuíkit的chui的发音让其联想到tweet(小鸟的啾鸣声)。
实际上,语言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很多语言现象都还解释不清楚。毕竟人类语言诞生距今已经有15万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语言改变了很多很多。不过,至少现在我们知道“妈妈”和“爸爸”是怎么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