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侠吴一龙
邹金灿
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对“人”的关注和思考。
适道,是指对道的追寻和向往。以苍生健康福祉为念,聚焦医学应有的科学精神、人文情怀,加深大众对医疗行业的认知与理解,这是《适道仁心·大医国手》开办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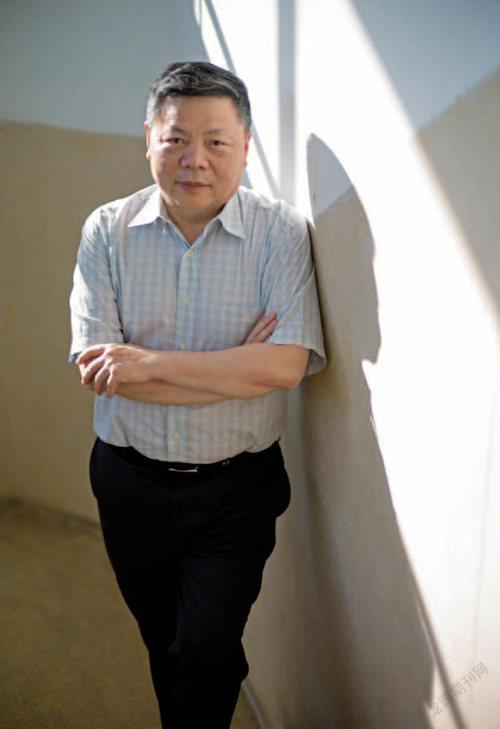
图/本刊记者 大食
纸笔之力,传承中华大医精神,人文视角,深入探寻医学与民族之魂。
2015年9月,国际肺癌研究学会(IASLC)将杰出科学奖颁给了吴一龙,以表彰他在肺癌的研究与治疗上的贡献。这个奖项由全球的行家里手投票产生,这是该奖40年来首次颁给华人科学家。
IASLC颁奖时这样说:“吴一龙教授,代表着肺癌研究历史上的中国贡献,尤其是靶向治疗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国际尤其亚太地区晚期肺癌治疗原则、治疗指南绝大部分出自中国。”
吴一龙生于1956年,现为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广东省肺癌研究所所长,还是美国外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肺癌治疗领军人物”。
得了杰出科学奖之后,有民营医院找到吴一龙,给他开出了300万元的年薪。他拒绝了,理由是民营医院是让他过去赚钱,而不能为他提供一个很好的研究平台。从医多年,吴一龙几乎担任过各个级别的行政职务,来广东省人民医院之前,他是中山三院的院长。在这个职位呆了接近4年,“这是我学术退步最厉害的时候”,因为太忙了。此后他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不要当一把手。
广东省人民医院党办副主任郝黎告诉记者,吴一龙平时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绝少应酬,即使有上面的大领导到来,碍于情面不能不出席,他也往往是来到现场、喝过几杯酒之后就离开。
奥巴马今年提出“精准治疗”计划,令精准治疗走入大众视野。在肺癌领域里,吴一龙已经专注于精准治疗十多年。这段时间里,在坊间有着“广东肺癌第一刀”称号的他,并不自得于手术的效果,而是和团队成员一起,深入攻治EGFR、ALK 等基因突变引发的肺癌,以延长患者生命。通过推进精准治疗,吴一龙希望在未来10年内让肺癌成为不再显得那么可怕的慢性病。
我们刚见面时,他看上去有些疲惫,但只要谈起自己的研究来,就神采飞扬,对待每一个问题都极其耐心,不会抛出一些外行人听不懂的术语。
“人文”,这是吴一龙在各种场合经常提到的词汇,他无时不在强调医者的人文素养。
这或许归因于他的家庭背景,“我们的父母算是小知识分子,从1949年以来一直都是在最底层,也是整天都是在担惊受怕的,因为运动一来,都是要整‘臭老九’的嘛。所以他们当时给我惟一一个要求就是,选一个不管朝代如何变化你都能够生活下去的职业。老师他们自己当怕了,那就只有当医生了。”
1977年,他参加了高考。“第一个志愿填的是中山医学院,当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当时是‘可教育好的子女’——我不知道这个词你听过没有。‘可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参加考试?不知道。等到高考前一个月的时候,邓小平、华国锋说这批人也可以考,我们才去考。”
最终他被第一志愿录取。他用带有潮汕味道的普通话,热情洋溢地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生活,“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多疯疯癫癫啊!1979年开放的时候,我们都跑到书店排长队买《白夜》啊,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呀,买了一大堆这样的东西看。”
那时的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我们在学校出黑板报。我一个很好的同学是写诗的,我是写散文的,每一期黑板报都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几个人不知天高地厚,写了一本医学史,当然了最后这本书没出版,但我们把整个医学史理了一遍。现在我会跟学生讲医学史,是得益于那个时候。”
大学时期的吴一龙,有着充沛的精力,就在校园里办了《中国医学生》这本杂志,“那些大的专访都是我写的。但非常遗憾的是,1986年反对精神污染,所有学校一定要砍掉10%的杂志,中山医学院只有这本杂志属于人文的,最后被砍掉了。”
当时的毕业生还要参加一个全国统考,吴一龙考了全国第10名。其时还是分配制度,他被分去了肿瘤科。当时的流行说法是,“金眼科,银外科,不三不四肿瘤科。”肿瘤医院就在学校宿舍的附近,他读书回来,往往都能听见里面传出来的哭声。“我当时有个小九九,就是我到外科,不知道得花多少精力才能够做出一点点东西出来。但对面那家都是死人的地方,我可能做出一点点东西,都是一个不小的成绩了吧?所以分配我去,我也乐意,没有想到要变。”
参加工作后,吴一龙有感于人们在性知识方面缺乏常识,在1983年参与创办《家庭医生》杂志。那时候,他会和同事们一起讨论稿子到凌晨三四点。“杂志有一个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叫作‘心灵深处’,专讲心理的,里面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是出自我手。我为了写这个东西,学了很多心理学的知识,补了很多课,哈哈。到今天他们都说我知识面很广,跟这些经历有关系。”
谈话中,吴一龙能随便拈出一些中外文学名家的名字来。各类文学作品中,武侠小说是他情之所钟,其中古龙是最爱,自言到现在还在看,《陆小凤》已经看了三四遍。温瑞安也是他很喜欢的武侠作家,因为其风格与古龙接近,“可惜现在不写了。”令他惋惜的,还有武侠小说在整体上的凋零,“所以将来退休,我准备写一本小说,名字叫作《医侠》。”
我问:“背景是古代吗?”
“啊不,现代的,就把我们医生的那种侠客精神写出来。”
“你对自己的定位也是一个侠吗?”
“带有一点侠的性质在里面。”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熟悉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这是《神雕侠侣》中郭靖对杨过说的一句话。大侠郭靖的着眼点,不在一己,而在人群。以侠者自期的吴一龙,似乎也与郭靖有同样的眼光。
2001年,为了挽救一位肺癌患者的生命,吴一龙率先从国外引进易瑞沙(一种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药物,当这个基因发生突变,正常细胞就会变成癌细胞。易瑞沙能有效阻止EGFR基因突变,让癌细胞不再复制),令患者病情好转。
当时,易瑞沙并不对欧美的患者起很大作用,在欧美临床试验的成功率不到10%。这并未影响吴一龙进行探究。他与团队成员发现,“EGFR在中国等东亚地区的人群中的突变发生率特别高,大概占所有非小细胞肺癌的30%,而在西方人群则少于10%。”与常规化疗相比,易瑞沙对有EGFR基因突变的患者有效率达到了60%-70%。

1988年在德国进修期间,吴一龙参加每周一次的学术报告会留影

1988年在德国进修期间,吴一龙学习第一台纵隔镜手术留影
这项研究成果震动了学界,被誉为“建立了EGFR基因突变型肺癌的治疗新标准”。但易瑞沙很贵,每位患者需要每月为之付出逾万元的费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吴一龙多方奔走,推动广州市医保局将这种药纳入医保范畴。
这件并非本职工作范围内的事,耗去了他整整两年的时间。他遇到了阻力,“第一,这个药确实是非常贵的,如果纳入医保的话,那不是医保全吃空了还付不起呀?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第二,患者不治疗可能也能活过一段时间,这药为什么要那么贵?第三,我们这边对这种新的东西呢还是了解不够。”吴一龙非常理解这种阻力的产生,“所以我当时做的第一个工作,是帮医保局去算账,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查到这个靶点,吃这个药是百分之八九十有效,然后不需要再吃其他药。我们在内部做了这个规定工作:一旦这个病人确认可以用这药的时候,在医保上其他药都开不出来。把这个东西制度弄出来,一年算起来比起过去不这样控制还节省费用了。”
在吴一龙的持续推动下,2010年,广州市将易瑞沙、特罗凯这些指向明确的药物,纳入了医保范畴,患者只要确定是特定的基因突变引发的肺癌就可以申请,此前每月付出1.5万元,纳入医保后变成只需要支付1000-2000元。现在,这个做法已经在国内多个省市推广开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医保局算这笔账的环节至为关键,而这并非是吴一龙的本职工作。“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能够只是停留在浅层次,要从深层次为对方着想:他们在考虑什么东西?有什么体系可以帮他把这个问题完善?这样办起来才能够成功。如果我当初只是口头讲,他们给你面子:哎呀这个大专家说的话,回去研究研究吧。回去研究就不下来了。但我说:可以这样这样做。这就是利用我的专业知识来为他们服务嘛。”
当时这种药还没有在中国上市,专家们在广州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会上有三分之二的老专家指责吴一龙用“假药”治疗病人——《药品管理法》规定,必须批准而未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生产、进口的药品,应按假药论处。
“但是你知道促成这一个事情的因素是什么?就是广东省的一个社保局的一个小官,他的亲戚得了肺癌了,然后我就拿他来作为一个先例(治好),哈,你看,这不好了嘛,是吧?因为中国人就要看例子嘛。”
谈起这件事,吴一龙颇有感触,“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吴一龙一天能看42个病人,再多两个吴一龙,也只是看一百多个嘛,比起中国一年60万的肺癌病人,要多少个吴一龙才看得完?但我们一个举措,一下就几千人上万人都受益了,不是更好吗?”
1988年,吴一龙赴德国进修,在那里待了一年多。德国的所见所闻,在他身上留下终生印记。他刚到那边的时候,看到医生和病人一起讨论病情,确定手术方案,大家开诚布公,各种方案如何操作、存在什么风险都列出来,然后建议病人选择哪个方案。所有的信息,医生都清楚明白地告诉病人,甚至医生之间的讨论过程,也让病人全程看在眼里。这样一来,病人就清楚知道自己的情况,以及适合哪个方案,最后的抉择权在自己。

2015年吴一龙获国际肺癌研究学会(IASLC)杰出科学奖
这种以人为本的做法,震惊了吴一龙。时至今日,他回忆起这一场景,仍然激动到哽咽,“现在有非常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特别是90年代以后,我们整个医学界陷入了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我们教导出来的医生,承受的压力非常大:要为医院做多少的手术量,才能达到这个优。就是按照工厂的方法来管理医生。手术量、经济指标,如果一个人过分强调这个东西,是不会关注到其他地方去的。就是我们会把人当成机器。”
德国之行中令吴一龙感动的还有,“我碰到过一个护士,上班时看到她受了委屈在哭。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突然间有个病人要推到手术台去了,那是一个艾滋病人啊!这个护士一听病人来了,哇,态度马上变了,从哭的就变成笑容了,还跑到这个病人面前,跟他亲吻一下,拍拍肩说,‘放心吧,我们医生非常好,会帮你做啊!’你说是不是非常动人?我每天都见到这样的例子,他们都把工作当成一份神圣的职业去做。”
甚至他所见到的德国患者,都非常信赖医生,几乎看不到什么医闹。这让他觉得,“你越是开诚布公,事情就越好办。现在我的看病风格也是这样。我们潮汕的人来,都跟我讲一句话:哎呀,千万不要告诉我爸妈得了这个病啊!我最反感这样做了。你爸妈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呢,她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决定什么,心理上我们可以一起来帮她克服,但不能瞒骗。”
德国的医疗体制也让吴一龙感到新鲜:他的导师在公立医院当主任,医院有一部分地方是老师的私人病房,做手术所得的钱,60%是归他的老师,40%才是医院的。“他们很严谨,做任何一件事情,完全不必找熟人,填表送上去,然后一切就OK了。说老实话,在德国要做到更高层次的医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等级比我们更森严,一个科室就一个教授,除非这个教授走了,才会竞争。现在还是这样,而且这个竞争是全国的,必须在他们的医学会杂志登出来说这边有一个空位置,全德国达到要求的人都可以来应聘。”
直至今日,国外的医者仍让吴一龙内心有所感触。最近,他把世界3个最顶级的外科医生请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他们分别是:前任的国际外科肿瘤学会主席、现任的主席,还有候任的。这些名医讲完课以后,就跟他们一起为病人做手术。“第二天晚上讲好跟他们吃饭的,因为病人太多了,他们就不吃饭,从下午5点钟跟我们一起做到晚上9点钟,把所有手术都做完了。这就是大牌的医生啊!他们没有想:哎呀你们对我不尊,而是主动跑到手术室说一起来做吧。”
我问:“类似的情况,在国内的医学界常发生吗?”
吴一龙摇头,“做不到,做不到。我为什么感动,这么老还是受感动,因为我衡量自己,我也做不到。所以我跟他们比,我觉得自己都很惭愧。”
1989年,吴一龙结束了在德国的进修,导师问他回中国还是留在德国。他考虑到自己能够来到德国,是因为得到德国一个基金会的支持,决定遵守契约,回国服务。临走时,导师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只要了一张CD,里面是典型德国风味的乡村音乐。
回国后,吴一龙重返中山肿瘤医院任职,头几年,“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他并不受重用,感到了失望。“那时候我就记得我老师一句话,他说当外界不理解你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争辩,你就做自己的事情。”他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把所有治疗过的病人的资料找出来,建了一个大的数据库,然后写综述。
1995年,他看到一篇英国的文献,里面总结了60-90年代肺癌治疗的状况,用了“个人资料的综合分析”这个词汇,其中有一个结论:做完手术后给病人加一个放射治疗,非但没有给病人带来好处,还带来了伤害,死亡风险增加了21%。这个“吓人”的结论,令他对这种讲究证据而非经验的研究方法产生浓厚兴趣,由是于1998年在国内率先开了“循证医学”这门课。
到了2002年,“有一个时髦的‘介入治疗’,就是用一个管插到肿瘤里面灌药物,说是效果好得不得了。我就用这方法给它做了一个重新评估,发现效果可能没那么好。发表了我的观点后,所有搞放射的人就跟我争。有一次他们在广州开大会,大概八百多人,他们的主任委员就请我去讲一讲。我刚开始非常忐忑,说我能去吗,讲我的观点出来,八百多人每一个人吐一口口水,我不是给淹死了?死都不肯去。但是那个主任委员很有料,他说你一定要去,一定要把你的科学方法告诉大家。所以我就去了。我演讲完,整整10分钟没有一个人出声。我打动他们了。”
这段经历让吴一龙得到了教益,“到现在我经常教下面的人,人生没有永远顺利的,当你不顺利的时候,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要去管人家在想你做什么事情。所以当这个时间一过去,我回头看,哦,原来人家对你不了解的时候是你出成绩最大的时候。”
与癌症跟死亡打交道了这么多年,如今的吴一龙,如何看待死亡这个话题?
他平静说道,“其实,死亡是生命的一种选择。你活着、死亡都是一种选择,只要我们尽力了,千万不要去做一些增加痛苦的事情。现在对很多到了终末期的病人,我的学生包括很多人都说:哎呀一定要想办法治疗!其实我知道我们手中的武器,到了终末期,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任何一种治疗只是增加痛苦,所以我会更倾向于让病人安静地走下去。这种理念,现在很多医生也不接受的,他们觉得好像太过悲观了。”
这种理念也得自他在德国的学习,“有一次周末,我到了奥地利,就去找贝多芬的坟墓,找来找去找不到,在一个地方耳朵突然响起了《第九交响乐》,心想肯定就在这附近了!我就找,真的就是在这附近喔!我到现在还理解不了当时为什么突然就冒出《第九交响乐》的音符在我的脑海里面。”
“看了贝多芬的墓地之后我觉得,死亡你说是很残酷吗?不是的。你看多少人在纪念贝多芬?我们这里坟墓是冷冷的、阴森森的,但人家那变成旅游胜地,每个墓碑,有名的没名的都变成一种艺术。所以我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种选择。”
(《适道仁心·大医国手》由华润三九联合本刊共同策划、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