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 如何改变命运?
邓郁

农历八九月,家乡谷里村坳口的那棵大枫树该红透了。作家东西没有回去。
我问这位长居南宁二十多年的作家,能否一起去离省会400公里的老家走走。他说时间太紧,“太折腾,下回吧。”父母相继离世之后,他每年也就清明回去一次,祭祭祖。
那棵大枫树,却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小说里。“就像彩色相片印在他的脑海。树冠的形状、枝丫的分布和叶片的浓密,闭上眼睛都能说出来。”
在他的新作《篡改的命》里,农民汪槐就坐在家门口,遥望那棵大枫树,遥望自己没能读上大学的儿子汪长尺。因为被人冒名顶替,即便超过录取线20分,即便汪槐跑到有关单位去苦求、跳楼抗争,汪长尺也没能获得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为了给摔伤的老父治病、改善家境,他只能进城打工。
东西于是想到了自己,从广西天峨县的山沟里走出来的一个写作者。他每年回农村的时候,总会看到那些高考落榜的同代人在村头遥望,遥望他们出去打工的子女。
“我就想,哎哟,这一辈子他们是改变不了了,只能重复父辈的那种生活,还面临着很多他们父亲们没有面临的问题。我比他们幸运,我是恰巧就考出来了,恰巧还有一点写作的天赋,恰巧成了一个作家。”
“那他们下一代的命运怎么改?”在书房里,东西像个家长一样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就想到汪长尺的方法——既然打工也没法真正成为城里人,不如把自己的儿子汪大志送给有权有势的人家做儿子。当对方要求他从此“消失”,他也同意,一头跳了河。
“汪长尺的命被别人篡改了,他用一种更直截了当的方式篡改了自己儿子的命。”东西说,“这是好极端的一个方式,但它能表达我的看法。”
“怎么可能为了自己的孩子就去跳河了?”对这个情节,有读者并不理解。
东西举了一个例子。“小说写完后我在广州接受媒体采访,当时在网易就看到一个消息,说是农村有个父亲,孩子生了绝症没钱治,后来他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从楼上跳下去,我孩子的病能好,我就跳。这是中国式的父爱,很深沉,也很病态。”
有趣的是,他的好几部作品,都能在写完后,找到“纯属巧合”的现实版。评论称其“对生存有警觉、对生命有痛感、对生活有同情心”。
他对汪长尺却并非都是同情。“这样的选择也是有他的投机在里面的。对不对?你连一个孩子都不要了,你想投机过去。不因为他是一个草根,处在底层,就有道德优势。不是这样。我同情他,觉得他难,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做法是正大光明的。”
城市承载着汪家几辈子的期待,换来的却是身体和精神折磨:汪长尺做建筑工受了伤,老板不闻不问还极尽羞辱。市劳动局的女科长孟璇愿意帮助汪长尺,汪的妻子贺小文为了感谢她,精心做了一袋粽子,孟璇一再感谢地放进包里走去,然而(可能是担心卫生问题)还是偷偷把粽子扔进垃圾桶,却被汪长尺看到……
和暗地里的防备和排斥共生的,还有无处不在的成见与一厢情愿的断想。因为工伤赔偿纠纷,地产公司老板林家柏和农民工汪长尺被带到了派出所,两人有一段心理活动,东西认为算点睛之笔。
林家柏想动不动跳楼,动不动撞车,社会都被你们搞乱了。
汪长尺想信誉都被你这样的人破坏了。
林家柏想是你们拉低了中国人的平均素质。
汪长尺想是你们榨干了我们的力气和油水……
“其实我们都是带着偏见看对方的,但未必就是正确的。”东西说。
汪槐负债,妻子在田间被邻居调戏。汪槐的态度竟是“在儿子没考上之前,不能做任何不洁之事。如果考上了,可以随便她”。究竟,城市有怎样的魔力,会让满身伤痕的人们依然飞蛾扑火似的钻了去?
东西抛出了植物学家蒋高明今年在环保部主办的《环境教育》杂志发表的文章《千疮百孔的中国农村》:“农村的污染很严重。他说第一就是‘令人窒息的臭味’,因为有的地方搞了养殖场。第二,地下水不能喝,因为污染太严重了。第三,害虫越杀越多。第四,河流变成臭水沟。第五,垃圾包围农村。第六,癌症患者多了。”
“就是哪怕在城市的最底层都觉得比农村强一万倍?”
东西没打磕巴地继续:“第七,农村的殡葬制度占土地。第八,勤劳未必致富。回答你,为什么一心要进城?因为务农就吃亏。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评论家陈思和说,“汪家人并非赤贫,如若他们就待在农村,日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然而汪槐把进城当成一个无比美好的理想。这就让进城成了一个象征,有了个担子。所以到最后汪长尺说,‘爸爸,汪大志的命运已经改变,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不是说我要去过一种自在的生活,而是要完成一个汪家的使命。”
现居南宁的作家田耳认为,《篡改的命》写的不是农民的尊严,而是写出底层的人在得到尊严之前,要付出的是什么。
汪长尺死后,他的灵魂回到村里。相信宿命的东西在这里安排了一个魔幻情节——投胎。
本来历尽沧桑和磨难,想在家休息一下,(汪长尺)却仍然被推搡着要奔去城里,而且竟还投到了仇家情人的肚子里,让汪长尺和儿子在下一世成了兄弟。这似乎就是宿命。然而在全书的结尾,当了警察的汪大志在明白身世后,把相关照片通通烧掉,和自己的亲人、家乡一刀两断。他终于彻底变成了汪长尺眼中的“他们”。
开车去南宁家中的路上,东西在车上放起一首《梦里家乡》,歌词出自他本人,是他“受邀”为家乡天峨县写的:
我的家是蓝色的,白云飘在河水里;
我的家乡是绿色的,森林中住着好看的仙女;
我的家乡是金黄的,稻穗摇荡在田野里……
歌词梦幻而甜美,东西对家乡的情感却很复杂。
他的好朋友、作家胡红一曾回忆,刚到南宁时,东西有个他无法苟同的“规定动作”——整日东抓西挠地去积攒旧报纸,还多次动员他把看完的报刊也送给自己。
“已经写出了代表作《没有语言的生活》和《耳光响亮》的青年作家,咋那么在乎这点卖破烂的零花钱呢?”
实在是看不过眼了,胡红一“教育”起东西来,结果反被东西教育。“他说收集旧报并非为了卖钱,都是寄给几百公里外的家乡谷里村的,那里不通公路不通电,乡亲们日子艰难订不起报刊,无法了解山外的信息。原来我们忽略了他身后的故乡。那不是我们其他人能感受得到的。”
母亲送东西到天峨县城读书,为了给儿子多留几毛钱,她硬是走30公里的路回家。东西于是写了催人泪下的散文《故乡,您终于替代了我的母亲》。
“这是一篇感恩的文章,但当我是一个失败者的时候,我是没有能力去感恩的。感恩是需要实力的,至少是写作的实力。”
他又说到汪长尺。“一个失败者的心肠往往会硬起来。当失败、绝望到极点了,你还希望他有正常心理吗?他已经麻木了。所以残酷的故事往往发生在失败者身上。”
在城里打工的汪长尺发现,饥饿时和吃饱后的选择判若两人。饥饿时什么都敢应承,没有羞耻,“连鸟仔露出来也不在乎。但吃饱了就像中产阶级。”
东西还写过一篇叫《痛苦比赛》的小说。到南宁这晚,他邀请一些作家朋友在饭店一聚。面前是一盘盘炖鸡、酱鸭、蒸鱼,还有他最爱吃的家乡腊肉。觥筹交错间,他回忆起在河池师专念书时,自己最大的痛苦就是饥饿。“最饿的时候把肚子里的蛔虫都饿死了。”他每天都注意门卫那儿的汇款单。如果有田代琳(本名)的单子,攥着那5块钱的巨款他就欣喜若狂。
记得他爱吃腊肉,如今乡下亲戚经常帮他带一点到城里。还有家乡那种小小的西红柿,酸酸的,他每年都要弄几十斤冻在冰柜里,煮面条的时候丢进去。“哪怕打个蛋花,喝个西红柿汤,一定要用家乡的土西红柿,而不是现在切不动的那种。”
这些年回老家,由头多半是带着作家、导演等各路朋友回去,半省亲半采风。若是独自回去,顶多也只是看看父母在山头的坟墓,见见健在的亲人,给一点钱——他坦承做不到牺牲多少时间来跟他们聊天。在这点上他很佩服韩少功:“他可以跟他们水乳交融地生活在一起,他能坚持,我蛮佩服。我不能,是因为我还有好多在城里的事没做完,待在村里太久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啊。就这种心理……我们是从那里来的,却变成那里的陌生人。”
家乡人跟他,就像闰土和鲁迅。“现在只有我的胃能留在老家,其他的都留不住。”这是事实,他不加掩饰。
胡红一念大学时的导师是贾平凹。“读他(贾平凹)的小说,只要坐上马桶就不对,蹲着就对了。”他也拿这个来衡量东西,“乡村瑰丽多彩,土地都有呼吸,你从他的文字里能感觉到脉搏的跳动。但城市内容写得就不如乡村那么给劲。”
东西不尽同意,“《篡改的命》其实是跨越城乡两界的,我在城里居住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乡村,今天来写汪长尺进城的感受,可能更准确一点。因为我也在慢慢地了解城市。”
三十多年前的东西进城有些像卡夫卡的《城堡》,他甚至都不知道那个土地测量员进城的动机是什么?但是田代琳们一心就想进城。到了后来才发现,城市并不是所有人都活得顺风顺水,也有三六九等。
“很多人觉得,哎呀,你写的是城乡差别。其实,真的,这个背景不重要,重要的是改变的艰难。你说,我们哪一个人今天不在呼唤改变啊?有人改年龄,有人改性别,有人改历史。汪长尺选择的是改命,我们把这个‘改’放大一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期待改变。包括爱情。但是,不是你想改变你就真的能改变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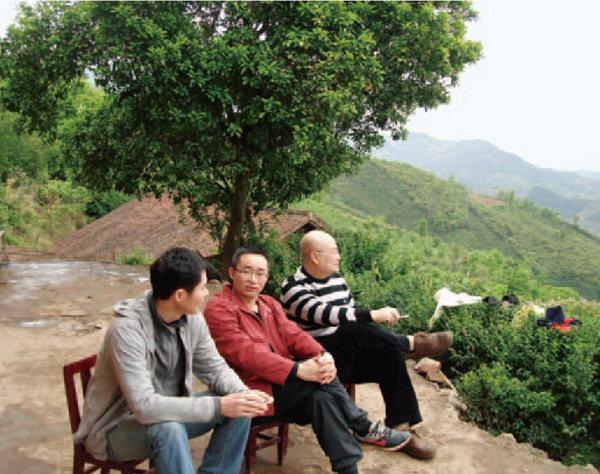
东西与章明导演(左)、作家凡一平(右)在家门口

根据东西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获第1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
给东西拍照很困难。不笑时,厚厚的下嘴唇嘟起,配合着锁眉,好像碰着什么堵心事;(让他)咧开嘴吧,腮帮是鼓起来了,脸上线条却僵硬得像是勉强说“茄子”一样别扭。只有在两个情境里,他像个领主一样自在舒展,了无束缚。
一是在自己的文字里,他善于巧妙地植入各种荒诞。《我为什么没有小秘》中的米金德发现人人都有小秘,自己不甘人后,他将寻欢作乐之事发展成为一个人的战争,注定失败。《不要问我》中的西出阳丢光了身份证件,也丢失了自己,落魄而终。《我们的父亲》中的父亲想用自己的思维方式解决孩子们现实中的困难,但适得其反,堂吉诃德式的父亲最终死在了儿女们都看得见、却都不发觉的地方。目光汇集之处,却存在最大的盲区。《后悔录》里“强奸犯”曾广贤讲述自己的故事,讲到最后你才知道他早已被错乱的时代阉割成性无能者,独自守住童子之身……
《篡改的命》里,汪长尺的老婆小文本来在洗脚城上班,后来做了三陪。开始是猜疑、心照不宣,后来,谈论小文的职业竟成了夫妻俩交流的热门话题。
好比夫妻之间谈论屁,开始还有不适感,但放多了谈多了便成自然。如果汪长尺好久不谈论了,小文会主动谈论。她谈论客人的身份,谈论客人的狼狈,还谈论客人的各种嗜好。
她一边谈,汪长尺一边讽刺,就像逗哏与捧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讽刺得越狠,她越受用,仿佛感冒时喝了一碗热辣姜汤,通过冒汗把病毒从体内逼出。而汪长尺的讽刺也仅仅是讽刺,他竟然不像过去那样生气了。他不生气,小文反而有点失落。
湘籍作家田耳刚刚调到南宁。他说广西作家普遍怪异,如果拿中国的文学版图套世界,广西大概像拉美。“东西很擅长比喻,而且往往是顺手一喻。比如说避孕套时间久了,不像是拿来用的,不如说是拿来吃的。我也有同感,我在计生办见过过期的避孕套,那种弹簧圈的。老远看上去就是像柿饼。”用邱华栋的话来说,东西的语言有种“南方的巫气”。
可能有人会觉得《篡改的命》情节过于戏剧化,余华认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东西用生机勃勃的语言写下了生机勃勃的欺压和生机勃勃的抵抗。就像多年前在东莞电影院踩瓜子壳那种声音,哗啦啦。”
照田耳感觉,现实中的东西和他小说给人的印象,很难得到统一。越是相处,他越是感受到一种悖谬。“我原以为写出这种作品的作家应该是一位愤怒之人,浑身长刺,说话咬着腮帮,随时要扯断手榴弹的拉弦扔将出去……这其实也源于认识的一些作家留给我的总体印象:性格乖张,说到文学很兴奋,顺便说及世事际遇,便充满怨怼之辞。”
东西却不悲伤愤懑。“一个快乐的人”,这也是余华眼中的印象。
二十来岁时,参加作家代表大会,田代琳便冒充别人给作家们打电话,怪腔怪调,说完自己还爆笑。这恶作剧邱华栋至今记得。
南宁的晚宴上,东西照例和相识多年的光头作家凡一平互捧互损。这是另一个他最为放松的场合。
像所有享有声誉、又能靠版税和影视编剧谋生的同行一样,东西有了一些资本,还卖了一个铺面,但最喜欢待的还是广西民族大学这套一百多平米的学校公寓。每天早上6点半,他准时到体育馆打球,中午要么下碗面,要么就步行到教工食堂吃一顿实惠午餐。“一切都很方便。我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30年前初到南宁时“低到尘埃里”的那份恐惧,而今变成了游刃有余,但为人上依然极其小心。青年作家马中才在他身边待了3年,他用“小心驶得万年船”来形容东西的心态。“比如经常跟我说,一上车就锁门,车里面不要放包和手机。”是否还是内心的那份不安全感作祟?或许。
家乡寄来的水果特产,这份给谁,那份给谁,全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有点完美主义者的强迫症倾向。“他会教你为人处世,比如找谁?应该怎么说话。我没见过这样的作家。”田耳说,“他能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从容地找出应对策略。我怀疑这也是他故意留给别人的印象,会不会是一种伪装?《没有语言的生活》里,聋哑人的孩子即使耳聪目明,也会被变态的环境呛得失语。但我知道,这小说中内含的宿命和绝望,绝对不是伪装。”
2006年,广西民大为东西和凡一平的到来,成立了文学影视创作中心,此后又将黄佩华调入该校艺术学院。当地媒体的稿件里写道,“凡一平和东西的母校河池师专,也因为出了他们两个‘人物’,年年中文系招生爆满。”
见到东西的两天,他穿着两件不同颜色的Marina Yachting的polo衫,看上去很精神,在一堆穿着垮垮的同行里显得利落、出挑。他写影视剧,写歌词,给企业做策划。“早有活得滋润的能力。”但除了一些“难以舍弃”的人情场合,他并不想让自己陷入行政事务或是无关的饭局。
他最看重的还是写作。不光自己写,还鼓励中途做生意的马中才、现在潜心戏剧的胡红一,有时间继续写小说。问起他,财富对于写作的影响?东西不光为自己,也为一帮同道开腔:“广西的作家也不是大富,就是恰当地解决了温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写电视剧也挣了一点稿费吧,但并没有影响我的写作。有人预言说东西写影视剧把自己给写坏了。他们在质疑的时候我就写出了《后悔录》。当他们又来质疑,‘他还能写作品吗’,我又写了《篡改的命》。一个真正爱好写作的人,任何东西都干扰不了他。”
“在格式化的想象里,好像贫穷是一个写作者理应承受的,富裕就非常庸俗了。我觉得,贫穷对写作的干扰并不比富裕对写作的干扰更好。”他说,“你写作的时候能不能保持充沛的情感,对世界的锐气,能不能跟作品中的人物水乳交融,这些最为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即便没有富裕干扰,写出来也就是一堆字而已。”
有位公司的老总看了《篡改的命》,问他,如果要改编,你能写剧本吗?东西干脆地回答“不写”,“我说你最好找专业编剧。我要把我50到60岁之间的10年全部用来写小说。”
“很多人会成为自己所讨厌的那个人。东西也像汪长尺一样,会具有城市人的一些特性,但他本心和当年没什么两样。他找到了如何应对世俗的方式,同时,心里装着足够远的地方。”田耳说。
(参考资料:《东西:历练之后的平和》。感谢马中才、田耳的大力帮助。实习记者蔡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