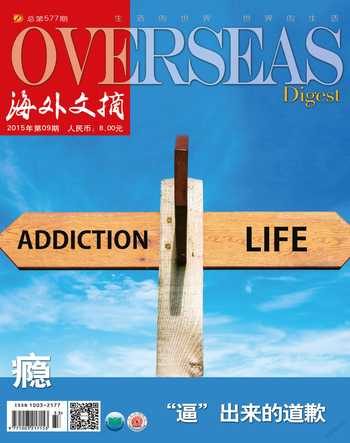布施“成瘾”的男人
山姆·基恩 苏鹰

90年代初,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辞了职,开始到街边卖炸薯片。他叫若昂,原先是一家保险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职工。他的薯片很快就大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薯片非常美味——薄、脆、色泽金黄。更诱人的是,若昂经常提供免费的薯片。只要你管他要,他就会把薯片装到盒子里给你。他经常把赚来的钱分给路边乞讨的孩子,或者给他们买糖吃。一天又一天,他空着手回到妻子和儿子的身边。
他长得很敦实,尖耳朵,弯眉毛。若昂过去是个严肃的人,倾向于把钱存起来。但1990年的一场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那年他49岁。“我离死亡很近,”他常这样说,“现在我想高尚地活下去。”他认为,给予才是他最大的快乐。对于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来说,他就像是无私的化身。

但最有意思的是,若昂全新的生活观,并非出于他意识的觉醒,而是因为中风后的脑损伤。除了其他症状之外,他还成了一个慢性失眠症患者,性欲减退,记忆力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行动变得迟缓。他的神经科医生说,他因患有“病理性慷慨”,而强迫式布施。他对于金钱无所谓的态度惹恼了家人,尤其是和他共同经营薯片餐车的兄弟。家人的指责、生意的停业、对母亲养老金越来越少的依靠,都没能阻止他的布施行为。布施可以带给他极大的快乐(若昂1999年死于肾衰竭,医生为了保护他的家庭隐私,没有提供他的全名)。
格拉夫曼的神经学实验
神经学历史上有很多案例表明,病人在遭受脑损伤后会出现异常举动。有些人不再能识别动物,或者无法正常说话,但是还能哼歌。对于神经学家来说,这些案例都给他们提供了脑损伤带来的行动异常的案例素材,让他们对于脑损伤造成行动异常有更深刻的认知,看出大脑损伤的区域负责日常生活中的哪些方面。若昂的案例也一样——研究人员希望通过他强迫式布施的案例,进一步研究常态的慷慨,了解人类为什么会有布施行为,为什么给予能让人类在生理上体验到快乐。
但是这一研究却触及到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问题。我们通常认为慷慨是纯洁而神圣的——是高尚心灵的体现,而不是脑损伤的体现。但如果给予是脑损伤的反映、本能,甚至是标志,又会如何?还有,我们认为慷慨是人类特有的属性。如果其他物种也有慷慨的表现,是不是就降低了这一行为的价值?
这些问题并不是空谈。若昂的案例表明,慷慨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类情怀”,而是深深植根在人类大脑中的一种反映。当慷慨行为占用了大脑的“高级”区域——负责理性思考的区域——就会引起动物性的愉悦中心的强烈活动,该中心通常与食物、性以及类似可卡因的毒品相关联。也就是说,渴望给予是出于基本生理需求和大脑精确反映的协同作用——这一协同作用,可能在人类进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很早以前我们就知道,慷慨和快乐有着清晰紧密的联系:全世界各种机构做过的调查均证明给予能够产生高层次的满足感,为给予者带来快乐。直到近期,科学家都还没有完全掌握,给予行为的神经学根源——为什么给予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快乐。
十多年前,西北大学认知神经学家乔丹·格拉夫曼研究给予与快乐之间的联系时,为受试者连接好功能磁共振仪器,询问他们是否会给某一个慈善机构捐助。格拉夫曼和他的团队将数据收集起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大脑中的哪些区域最活跃。
他们预想人们的大脑额叶会剧烈活动,这一区域协助群体逻辑推理,思考不同动作的行动步骤——大脑额叶的这些功能正是这一实验任务所需要的。与预想相同,大脑额叶的活动反应在了功能磁共振的屏幕上。但是令格拉夫曼惊讶的是,大脑中的愉悦和奖赏回路同样非常活跃。“我们最开始觉得,”格拉夫曼说,“这些回路活跃起来,是因为通常情况下,人们在给予的时候,会感觉心里舒服一点。但是我们不确定这一反应的强度究竟有多大。”
特别是,他的实验团队发现,中脑缘呈现出活跃状态。这一系统构成了大脑愉悦回路的重要部分,它的一系列活动刺激化学信使多巴胺的产生,而多巴胺能够让人感觉快乐。神经学家通常将这些回路的活动——很多其他物种也会有类似大脑活动——与享乐式的快乐联系起来,比如食物和性。格拉夫曼断定,给钱比收钱更能让这些回路兴奋。正如妈妈教育我们时所说的那样:给予比索取好。但是她没有意识到,神经学上来讲,给予所带来的快乐与吃软糖或躺下休息所带来的快乐,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给予能够带给人们如此美好的感觉,为什么人们不更多地布施呢?曾有调查发现,85%的美国人仅将不到2%的收入捐献给慈善组织。部分原因是,大脑的其他部分,例如大脑前叶,有时会抑制人们的慷慨行为。这可能让他们显得吝啬,也许事实就是如此。但是大脑前叶让我们看得更长远,提醒我们不要过多地做出慷慨行为。
若昂的案例向我们揭露了这样的事实:当大脑前叶失去平衡后果的能力后,就会过度热情,失去理性地做出慷慨行为。若昂的医生认为,中风导致了他前脑内侧束受损,这一结构是由大脑底部的一组神经元纤维构成的。大脑前叶从这些神经元纤维中收到信号,来监视其他区域,这也是前脑内侧束通过的地方。前脑内侧束像网络传输线一样,传输大脑中各个部分的信号,使大脑前叶抑制某些行为,以达到更长远的目标。你的大脑前叶可能会在你减肥期间,促使你少吃一块巧克力蛋糕;但若昂的前脑内侧束受损以后,他的大脑前叶就失去了对某些神经冲动的控制力——显然,也包括对布施行为的控制。
他的神经科医师里卡多·奥利维拉说,这些控制力从来不会自发产生。也就是说,若昂从来不会主动去找流浪儿,给他们钱或糖果。但是每当孩子们问他要的时候,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去拿钱包。这或多或少像是一种条件反射,就像苏联神经学家巴甫洛夫的狗,每次听到吃饭铃声都会流口水一样。
奥利维拉说,前脑内侧束受损还导致了他“惩罚机制”的失常,这个系统负责惩罚愚蠢行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系统都会介入,仿佛在对你说:如果你再这样免费发薯片,你的房子就会赔进去的。但是对于惩罚机制受损的人来说,如此长远的威胁,是没有作用的——这并不能让他们打消念头。无论他的经济状况多么惨淡,家人怎样制止,他都认识不到任何危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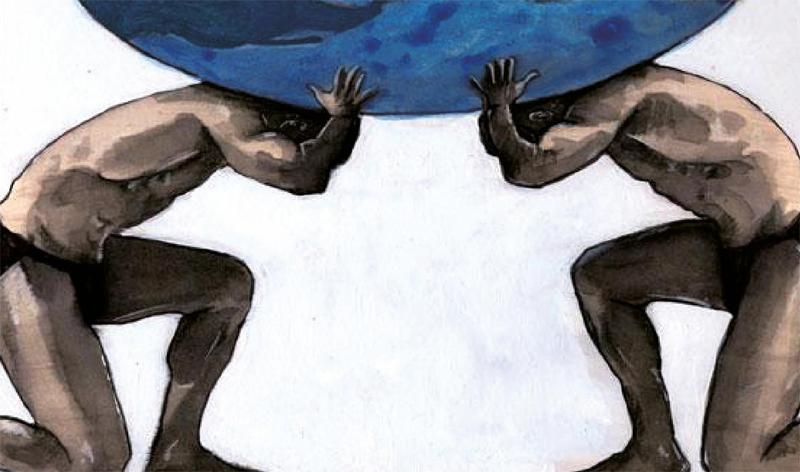
这一切又引出了另一个令人不舒服的问题。我们认为慷慨和自控都属于美德。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丧失了自控能力而变得如此慷慨呢?就像暴饮暴食的人或是无法自控的购物狂?或许慷慨有时也是一种弱点?
若昂从给予中感受到的快乐,似乎是比常人感受到的更为夸张。他的案例表明,如果没有大脑前叶所提供的抑制力,做慈善的想法会一直占据着我们的思绪。
安德鲁·李的医学实践
即便如此,病理性的慷慨,也不一定是大脑传输的问题。患有两级型异常的人,狂躁时,也会做出过度布施或其他行为,来掩饰不安或操纵他人。此外,服用药物治疗脑疾,也会引起病理性慷慨。
90年代,伦敦神经学家安德鲁·李给几个帕金森症病人开了普拉克索药方。帕金森症是由制造多巴胺的脑细胞死亡而造成的病症。类似普拉克索的药物可以修复大脑中正常的化学物质。
不幸的是,刺激多巴胺产生的药物通常会引起奇怪的副作用,例如强烈的购物欲或赌博欲。李在给病人们服用普拉克索后,发现了该药物的副作用。21世纪初,他的3个病人也出现了强迫行为,而此前他从来没有发现类似现象。有一个病人,在30多岁时,开始强迫性练习举重、赌博、购物,有一次买了60瓶剃须护理水。他毫无节制地把钱给了自己的朋友和双胞胎兄弟,而自己家却因欠费而停电了。在另一个病例中,一个女人在eBay上买了3辆电动车,虽然她根本不会用到。在她知道自己会把钱无意识地花到没用的地方时,她就把钱给了家人和朋友。还有一个58岁的自然学家,发现自己性欲猛增,并开始疯狂地写一些关于菌类的文章,有时候一写就是48小时。他还开始把三明治和钱分给他在街上遇见的“瘾君子”。他给了一个年轻女人两万英镑,一个让他的家人无法饶恕的数目。
李猜想,病理性慷慨的案例要比神经学家所估计的多,因为大多数医生没有把持续增加的布施行为算作副作用。美国科学院论文集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讲述慷慨的潜在伤害,称“利他,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品格,因其鲜有回报,而更显神圣”,但是过度给予却会毁灭病人的生活。虽然有时候他们一定程度上知道过度给予的危害,但是他们却不能控制布施的冲动。
而后,李给3个病人停用了普拉克索,他们过度慷慨的症状消失。因此他判断,他们的过度慷慨行为是用药造成的,而结论就是——一种简单的化学物,镶有氮和硫磺的碳环——让他们变成了布施“成瘾”的人。
患有帕金森的病人服用普拉克索以后,会变成布施“成瘾”的人,那么正常人服用该药物,是否也会出现相同症状呢?
他无从得知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我们中的小部分人也会出现强迫性布施。尽管如此,帕金森导致的大脑损伤依然为我们提供了病理性布施的研究线索。李说:“帕金森病人大脑中的愉悦和奖赏通路,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这就导致一些病人“享受生活的能力衰退了”。神经学家称这种症状为“快感缺乏”。这些病人并不一定感到失落,认为生活没意义,他们也没有自杀倾向。但是美术、音乐、食物、爱好,甚至性,都不能让他们感到振奋了——生活就像一潭死水。
服用普拉克索以后,他们的大脑化学物质开始变化:多巴胺再次涌流,大脑奖赏通路也活跃起来,某些活动能让他们感到快乐——虽然不一定是他们过去喜欢的活动。具体是什么活动(赌博、买剃须护理水、写关于菌类的文章)取决于他们的个人特质,以及大脑受损的部位。但是由于给予也和大脑的愉悦回路相关联,所以布施也是让他们感到快乐的活动之一。因为普拉克索能抑制大脑的控制力,所以人们会不断地重复这个令他们快乐的活动。
这个活动成为一种“瘾”,并非巧合。布施对于一些人来说,似乎是强迫性的,因为这些人渴望随之而来的多巴胺分泌——多巴胺分泌高峰就如同可卡因或安非他命(抗抑郁药物)所带来的快感。病理性布施者,是真正意义上对慈善行为上瘾的人。
慷慨行为的生物学分析
布施所带来的快乐,仅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慷慨行为还会影响你与他人的关系,尤其是接受你布施的人。病理性布施者的朋友和家人认为这些布施行为令他们困惑和尴尬。而优先布施给陌生人的布施者则会遭到自己所爱的人彻头彻尾的怨恨,尤其是当布施行为侵犯他们财产的时候。
这不同于普通的给予行为,可以拉近人们的距离。在普通的给予行为中,接受者通常很享受收到礼物,充满感激,想要报答,而在病理性布施中,接受者则不会有类似感受。格拉夫曼的功能磁共振研究还发现,布施者的膝下区域也显现活跃,该区域位于大脑前叶,控制催产素的释放。这种激素促进人类的社会联系、信任关系和合作关系;每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爱人时,都会释放这种激素。
社交奖赏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慷慨行为在人类大脑中占据着最重要的部分。解释慷慨行为,或更宽泛地说,利他行为,实际上是生物学家很头疼的一个问题。查尔斯·达尔文认为人类的慷慨是对他自然选择学说最大的挑战。想象一下我们祖先的部落。有些人是天生乐善好施的,愿意与他人分享食物和用品,而另一些人则吝啬小气。我们会认为前者是好人,但是站在生存的立场上看,这些人则是愚笨的。因为在野外,一定范围内的食物是有限的,那么,慷慨的人可能将更快地走向自我毁灭。
但是这一理论有个漏洞。20世纪中叶,生物学家开始用亲缘选择理论解释利他行为。该理论称,动物,包括人类,更容易对自己的亲属慷慨,因为亲属的基因与自身的基因更为相似。亲缘选择理论认为利他实则是被掩藏的自私:也许短期内,帮助我的兄弟姐妹们生存,会牺牲我的幸福,但是最终,这会增加我的基因被传递下去的机会。
亲缘选择理论已经成为了现代生物学的基石。然而,该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人类行为。并非因为人类从某种程度上逃离了进化压力,才塑造了其他物种。是亲缘选择塑造了人类,而不是我们自身。尽管如此,人类依旧在不断帮助陌生人,我们以后可能再也不会见到的,永远不会给我们回报的陌生人——赠予他们时间、金钱,甚至血液、器官。
生物学家用群体选择,来解释这一悖论。群体选择理论称,虽然吝啬的人比慷慨的人拥有更多生存机会,但是慷慨的群体在很多事情上会胜过吝啬的群体,例如在战争中,或是狩猎中。生物学领域中的一些领头人物也赞同这一观点,其中就包括E.O.威尔森。几十年前,他是坚持亲缘选择学说的,但是过去10年里,他开始摒弃亲缘选择学说中的部分理论。群体选择学说仍然不完善,以基因的角度看待进化的生物学家认为,群体选择学说依然有定义不清晰的地方。而这一学说在科学家当中,也颇具争议。
要想解开慷慨行为为什么会在人类物种中立足的谜团,就要研究人们在布施的时候大脑究竟有怎样的反应。格拉夫曼的实验观察到的受试者大脑膝下区域活跃现象,表明慷慨行为能够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鼓励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格拉夫曼说,这很重要,因为这样的互助关系有利于稳固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经济往来,例如贸易,一般要求人们用长时间去建立信任;也就是说,社会交往的关键因素依靠的正是人类大脑的慷慨冲动。
大脑损伤还是人性使然?
到底是大脑受损和服用药物创造了布施的本能,还是人本身就具有布施的本能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在相应刺激下,激发了这种本能呢?这一点科学家依然没有证实。
格拉夫曼认为,大脑受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个性,把他们原本没有的品质展现出来。但是杰斐逊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萨尔曼·阿赫塔尔却否认了这个观点。他曾经通过几个大脑未受损伤的实验者,研究病理性慷慨。其中一个病人给了他100万美元,作为答谢;另一个病人花费3万英镑,用私人飞机带着她从商场里认识的小男孩儿去一个主题公园。“这就像醉酒一样,”他说,“你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本身就存在于你的脑海中了。比如你喝得烂醉之后,和你的姐姐说,我恨你。酒精并不会让你生出恨意。这种恨意本已存在于你的脑海中,而酒精只是将它释放出来而已。”这与过度布施是一个道理,他说。
治疗期间,若昂的神经科医师里卡多·奥利维拉渐渐深入了解他。他和医院的护士常常收到若昂送给他们的薯片。他曾与若昂的家人深入地谈论过若昂中风前的表现。他认为若昂的慷慨本身就已存在于他的性格中。中风破坏了他的大脑回路,再加上他之前就存在的慷慨的品质,才使得他在病发后有这样的表现。他得病前后的慷慨品质没有变,只是他潜在的慷慨品质在得病后主导了他的生活。
这也是若昂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用多巴胺过度分泌或巴甫洛夫刺激反应理论来解释慷慨行为,而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是这样的理论忽略了若昂本已存在的品质:布施的确可以让他快乐,令他感到充实。奥利维拉说,若昂是他所遇到的最快乐的人。
与此同时,若昂与妻子、兄弟和儿子的矛盾,又让奥利维拉思考着另一个问题,即慷慨行为的负面影响。奥利维拉的父亲就是一个例子——他的父亲出身贫寒,是个裁缝,但是常常布施——后来奥利维拉也潜移默化地成为了慷慨的人。有时病人拿不出医疗费给他,他就为病人减免费用,这也导致了他家里的物质条件欠佳。“所以我一遇到这个病人,就想到了自己。”他说。但是从长远来看,“若昂总会让我质疑慷慨的道德价值”,若昂因为帮助他人,而不能把更多的钱和时间给予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也没有能力为他们解决问题。“你的慷慨,也许对于爱你的人来说,是一把枷锁。”
这并没有阻止奥利维拉继续布施。他觉得,人的年龄越大,越会感悟到给予的价值。他从来不觉得给予是有界线的。他说,“若昂的案例让我觉得,好与坏的界线并非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清晰。”
[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奥利维尔·里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