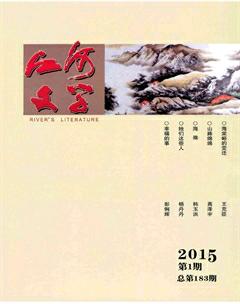皮渡河上的相思鸟
黄光耀
那年春天,我有幸从皮渡河路过,适逢星期天,他们去砍青,我也跟着一同去。
火岩天生的一道峡谷,一线苍天,两岸悬崖峭壁、林木森然,崖底就只悠悠地流淌着这条翡翠朦胧的皮渡河。相传,她是古时一条苍龙驻在火岩和烙塔两山之间的小盆地时,因天久旱不雨,被二山无情焦灼愤然凿通火岩而留下的这道辙痕,亿年万年,她便汇集天地叶滴花露,汩汩地淌成了这条绿色而美丽的河流。不信你去寻她源头,她竟是从大山脚下冒出来的呢。那地方就叫冒水洞。
从冒水洞奔泻而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就开始孕育两岸绵延几十里的郁郁葱葱的蒲竹了。莽莽苍苍的竹林,汇成竹的峡谷,竹的海洋,竹的世界,高压线就从这亭亭的翠竹间穿越而过,每到开春秋后,猛抽节或是被雪压伏的嫩竹就会淹没电线,使电路受阻。这时他们就会沿河再砍一次青,使受阻的电路重新畅通。
进入竹簧深处,十步之内只见竹不见人。耳边就只有潺潺的流水声和啁啾的鸟叫声,仿佛是我们拨动了山川的琴弦,伴唱的才是他们。阿庚在前开路,一路高歌。在歌声尽头他们找到了昨日留下的刈口。
这时只见十步开外的竹枝上,两只翡翠色的小鸟,正呼朋唤友,在欢迎我们呢。一会儿又聚了十几只,二十几只。他们红红的嘴,红红的脚,小巧玲珑,体态清秀,羽毛鲜艳,美丽异常。这鸟儿太美了!
“这是什么鸟儿?”我问后面的小向。
“红嘴雀!”
“这名字好土,为什么不叫红脚雀呢,她脚也是红红的呢。”
“那要是她身上也是红红的,该叫她红红雀啰?”
阿庚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开怀大笑。小向一时会意,竟是羞红了脸,朝前跑去。原来她正穿着一件淡紫色衣裳。还是去年六月里,我大学毕业回家等分配,曾来这里避暑消夏,皮渡河那时刚开发为风景区,我和幺叔划船进了鲢鱼洞,不料玩得正欢时,灯忽然熄灭了。我们磕磕碰碰、好不容易划了出来,几次险些坠入深潭,我顿时怒火中烧。可当船划出洞口时,却只见河岸竹篱边立着一亭亭少女,十八九岁的样子,见我们出来了,竟然羞得一脸绯红。若不是穿着一件淡紫色的衣裳,那脸蛋简直就像熟透的樱桃,煞是馋人。定是她捣的蛋……可我分明又像在哪里见过,车站?梦中?一时竟又想不起来了……后来我时常路过这里,每次都看见她目光中含有一丝淡淡的忧郁……
笑声中又震落了一帘帘水珠,那是我们砍倒下来的蒲竹扬散的露珠,像珍珠,像滴泉,像流星,一颗颗、一粒粒,坠在手中,脸上,脖子上,凉凉爽爽的,渐渐集多了,却感到冷了。我不觉一阵痉挛,身上竟凸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你歇歇吧!”她说,“冷呢。”
“有点儿!”我笑了笑,糅手,哈气。
“反正我们也是‘磨延工,不少你的!”
她嘴上这么说,行动却不同了,两个人一天要砍一两里路,这密密扎扎的竹子又是“磨延工”能够磨出来的么?
停下来,我就找了一块岩头坐下,削下一根竹管,做成了一支小笛。我吹着,轻轻地吹着,像箫声呜呜咽咽,又像在述说一个遥远而失落的梦……
“太忧郁了!”阿庚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
我无言,依旧轻轻地吹着。红嘴雀也仿佛动情动心了,又飞来几只栖息在竹枝上,叽叽喳喳地叫。河风不时拂动竹梢轻吻着河水。晨明啊,你真是鸟儿的天堂!
“他是和相思鸟说话呢,”阿庚幡然醒悟似的又冒出一句,“同病相怜!”
“什么鸟!”
“相思鸟呗!”
“这、这就是相思鸟?”
我霍地站起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书上我只见其名而不见其鸟,不承想相思鸟就是这种美丽的鸟儿!可是我的心却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是太忧郁了!”
身后又传来小向的声音。我不再吹。我默默地望着河水,掷着小石子,河面荡起一层层浅浅的涟漪。阿庚傻笑着走开了。只听小向在说:“你现在该知道这是什么鸟了吧!”
“知道了……”我想。
她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像导游一样介绍着:“相思鸟生性喜欢气候适宜,风景优美的地方。皮渡河有山有水有林,又有如此清幽的自然风光,也就成了相思鸟的聚集之地。她们爱飞、爱唱、爱跳,声音优美,能歌善舞。她们又情意深长,出没总是成双成对,归宿有如鸳鸯交颈,永不分离,故名相思鸟。本地老乡却叫他们红嘴雀,这样亲切些……
“每当春暖花开,众多的相思鸟便成双成对,含情脉脉地在山野、林间、峡谷中翩翩起舞,啼鸣高歌,情人般难舍难分。他们虽不是人,却富于情感,一旦雄雌相爱,就相敬如宾。在一对相思鸟中,如果有一只不幸生病了,另一只鸟就会非常伤心,连歌都不肯唱了。若是一对中有一只死了,那么另一只鸟也会长期不食,忧郁而死。因此,人们常常用这种鸟作为爱情的象征……人类有时候还比不上鸟呢!”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她低沉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涅槃传来似的……我好不迷惑!
太阳光又投射在对岸的山崖上了,被河谷徐徐地拉下,就像拉下了一面灿烂的银幕。我想:那片阳光是应该属于她的,我就只有这一片浓荫了!
老远老远,又传来阿庚砍竹“嚓嚓”的声响,像是在宣泄一种原始的情绪……
自从那次砍青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但我也曾去信问过风景旅游区开发的情况,还提到那可爱的小鸟。她说这鸟儿生性这种性格,变得了的么?随后才知道,阿庚也没再去找她。只听阿庚这样说过:我们无缘,她的心落在皮渡河上了!
又是一年春天。四月里,我又来到这皮渡河上,在两河口小住了一阵子。那时只有她一个人看守门市部,不再砍青,但时常上山去拾些柴火。那几天,恰巧柴要烧完了,我就邀杨娃去砍柴。沿着流水槽爬上去,在悬崖上砍了就往下抛。
突然,我听到一种熟悉而又久违的鸟叫声,四处寻觅,依稀只见那鸟栖息在一棵树枝间的鸟巢里。
但要看那可爱的小鸟,得从流水槽爬过崖壁去,崖上布满了一种青青的藤蔓,一层复一层,我只得小心翼翼地往那边挪,一步,两步,不好,左手抓住的翠藤突然“咔嚓”一声断了……我如石坠云雾中……等我醒来时,已在两丈高的悬崖之下了。
我试着挣扎着站起来,左腿一瘸,又扑了下去;我再也动弹不得了,手一摸脸,竟满手是血,本来就吓出了一身冷汗,被阳光一照,伤口辣辣的就更是燥痛了。我会不会瘸呢?那窝里有鸟蛋吗?我还在想。
“还能动吗?”杨娃从悬崖上赶下来问。
“动不了啦!”我苦笑了一下,“那是什么鸟窝儿?”
“红嘴雀的窝!”
“书名相思鸟!”
“哦!”杨娃若有所悟似的,“难怪冬天好多人捕呢,听说去广州能卖个大价钱!”
“那鸟极通人性,不能买卖,今后你见了就把那鸟放了!”
“好的!”
杨娃似懂非懂,见一个人挪不动我,就回两河口喊大人去了。
半晌,她老远老远地喊我。我正拿着随手摘下的一朵龙虾花,泪水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一滴一滴的,晶莹晶莹的,溅在花蕊上。
她爬了上来,笑了。见我没有理睬,她也流泪了,一滴一滴的,晶莹晶莹的,像雨点溅在花蕊上,也溅在彼此的心里。
“我去看那鸟窝儿,”我打破了沉寂,“杨娃说是相思鸟窝!”
“那窝还好好的!”她微微地苦笑了,“你哭什么呢?不久就会有小鸟出窝了!”
我点点头,是啊,鸟窝还是好好的。我又担心什么呢?
我住院了,伤得还真不轻,她说:“有我在你就别再打电话了!”
“你就不怕别人闲话?”我说。
“我还怕别人闲话啊!”
她伤心地哭了起来。我不再固执,这一住就是半个月,她每天早起晚睡,进进出出的,忙里忙外,不仅给我翻身,还要端屎端尿的,她好不知累的,我真是痛心哪!而有阳光的时候,她还特地打开窗子,让我听流水声、听篁竹的曳动声,还听相思鸟的啁啾声……一天,我父母忽然来看我了,后面跟着我叔伯堂兄弟们。她说:“都怪我不好!”我母亲说:“这都是命,怪不得哪个的。我算卦了,是祸躲不脱,因为你,这灾还小了呢。”然后就说起了他们来时坐的汽车翻了,好在并没有伤着他们,只是司机的手断了,一车的绿豆倒进了田里……她越发地感到内疚,竟又大哭起来……
春去冬来。一天,她寄来了她父母的信,里面夹着她的一张半身照片,很美,也很忧郁。信上写着:秀儿,你要慎重考虑……
那天黄昏,没有雪,夕阳静静地挂在西边的山脊上,总是不想掉下去,似乎还带着一丝丝的温暖。我们默默地走在两河口的木桥上,感觉沉沉的,那三四十米长的木桥,就像是要走几个世纪似的。而桥的另一头,放着两只鸟笼,鸟儿叽叽喳喳。我一惊,竟然全都是相思鸟儿!
鸟贩子却不知跑哪儿去了。我蹲下来,她也蹲下来。相思鸟羽翼扑腾,嘴额撞破,一丝丝殷红的血粘在了篾丝上。我的眼睛却模糊了。
“鸟儿也不自由啊!”我自言自语起来。
“因为人太无情了!”她轻轻地说。
“天空才是鸟儿的乐园!”我说。
“那就只有飞出牢笼!”她说。
这时我们目光相碰,彼此间分明看得到对方目光中放射出来的一股刚毅的光芒。我于是轻轻掀开了一只笼盖,一只只鸟儿飞了出来。她也轻轻地掀开另一只笼盖,一只只鸟儿也飞了出来。众鸟于是绕桥一圈,嘎嘎嘎的,又一齐向着竹篁轻盈地飞去,在皮渡河上空倏地消失了……
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随即往笼里放了十元钱,就踏着暮霭走进了竹篁,走向了那暮色苍茫之处。
黄昏过去了,夜幕降临。我们于是升起了一堆篝火,静静默默地坐着。月芽儿悄无声息地挂在竹梢上,泻下一片斑驳的银光,既是那么的近,又是那么的远。放眼而望,近山一片朦胧,只露出那黛色的山脊,与忧郁的轮廓。她静静地伏在我怀里,就像做梦似的,一脸甜蜜。一阵,河风起岸了,又掀起她柔柔的长发,她的长发就这么轻拂着我的脸颊和眼睫,让我感觉酥痒酥痒的。我便用大衣紧裹着她,她就这样安然不动地,一直偎依到天上的繁星明朗起来又暗淡下去,直至长庚星最后又变成了启明星。这个夜晚,我就这样看着她悄然入睡,呢喃梦呓,而我内心深处却没有一丝丝骚乱,就像泊着一片淡泊而宁静的月光。因为我一直都在祈求和祷告:银河啊,天上的虹桥,你就降临人间,架在这皮渡河上吧……于是我眼前就总是浮现出那个穿着淡紫色衣裳的少女,就像一只美丽的相思鸟,从遥远的天边展翅飞来……
责任编辑:邓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