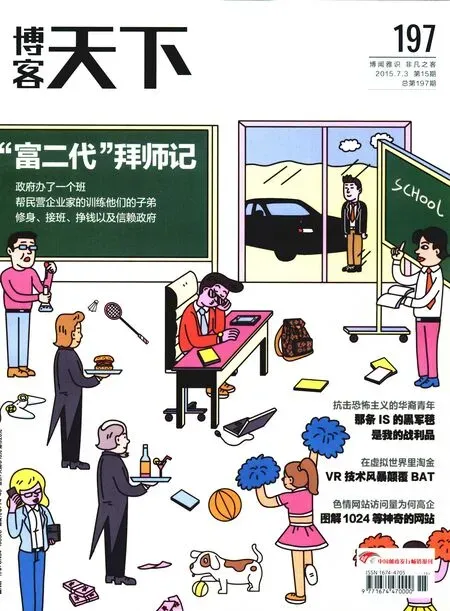他是华人,他在和IS作战
文 赵良美编辑 卜昌炯
他是华人,他在和IS作战
文 赵良美编辑 卜昌炯
23岁的黄磊刚从战场上下来。抗击IS的国际志愿者中,他是唯一的华人

志愿军的装备严重不足,他们仅有必备的枪支和弹药,没有防弹衣和头盔
“我还会回去”
尽管事先已预料到回国后免不了被警方盘问,接下来的遭遇还是超出了黄磊的想象。
当地时间6月17日下午2时45分,从约旦首都安曼飞至伦敦的航班刚一降落,自叙利亚归来的他就被冲上来的警察带走。
黄磊是英籍华人,根据英国法律,政府可以对赴中东地区参战的人员采取一定强制措施并令其报告出行计划。作为一名在叙利亚战场抗击IS近4个月的国际志愿者,黄磊一路上升腾的豪气与荣耀指数瞬间下降了很多。
晚上,他被关在警察局的牢房里。旁边有一位不知犯了何事的嫌疑犯,不停地在破口大骂,还使劲地踢门。“他们原来把我归为这一类(嫌疑犯)了。我是去帮着打恐怖分子的,结果回来之后弄得好像我是恐怖分子一样。”黄磊对《博客天下》说。
回到英国后,他终于有时间以及条件从容下来。不像之前在叙利亚前线,他的手机是土耳其号码,信号很差,很容易就突然断掉。之前《博客天下》记者与他的通话很少有超过10分钟的时候,有一次难得遇到他那边网络还不错,但由于要紧急转移,他还是挂掉了。
在警察局,黄磊接受了例行询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以后有机会,你还会去叙利亚吗?
“我还会回去。”他回答。
结束询问两小时后,黄磊被释放,但是行李还需一件件接受检查。除了去时的一副行头,他还从叙利亚带回了两样东西:一件红新月会(即伊斯兰国家的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外套,一条从IS那里缴获的长20厘米、宽15厘米的黑色毛毯。前者象征着他过去几个月的身份,后者是他的战利品。
黄磊暂时还回不了家,他被要求在4周之内不能离开曼彻斯特城区,也不能申请任何签证。此次从叙利亚辗转回国,他本是想回家安抚一下父母紧张情绪的,现在反而成了一个急需被安抚的人。
今年3月,23岁的黄磊以去耶路撒冷旅行的名义瞒着父母只身一人赶赴叙利亚,加入库尔德民兵组织YPG(People's Protection Units)。在当地抗击IS的所有国际志愿者中,他是唯一的华人。
IS是“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的英文缩写。这是一个自称已经建国的极端恐怖群体,脱胎于基地组织,以手段残忍著称,不仅屠杀平民,还多次在网上发布斩首战地记者和俘虏的视频。为免形象被拖累,基地组织曾宣布与他们划清界限。在刚刚过去的5月,IS攻占了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和伊拉克重镇拉马迪。
直到一个多月前,黄磊的父母才从中国的媒体报道中得知自己的儿子原来是抗击IS的一员。出于担心,他们不断催促黄磊回家。
黄磊对警方的做法怀有一种善意的理解。他说虽然IS是毫无疑问的恐怖组织,但在英国仍不乏同情者,甚至发生过多起英国人参加IS后回国后制造恐怖袭击的案例。英国警方对此非常谨慎,即使确认被调查者站在正义的一方,也会启动严格的监视程序。

黄磊(右)和战友在一起。自今年5月开始,他不时在新浪微博上发布自己在叙利亚的动态
回到曼彻斯特后,黄磊身上仅剩下3英镑,没钱住旅馆,只好借居在一个朋友家。比被监视居住更让他感到沮丧的是,周围的人对他做的事情大都漠不关心。他问朋友们有没有在BBC上看到自己,他们的回答都很一致:“没有。”
去一个中国餐馆吃饭,他听到旁边有一群学生模样的人在聊国际政治,但基本都与美国有关,要么就是讨论今晚去哪里喝酒。“完全不管中东和那些恐怖分子,这让我有点儿心寒。”黄磊说。
为了一个女志愿者
去叙利亚之前,黄磊自认为是一个“不关心国际动态的宅男屌丝”,不时会感受到生活的“无聊”,于是以泡吧、喝酒、打游戏来消磨时光。
转折发生在今年年初,他在网上看到一个介绍IS的视频,了解到对方的一些残暴行径,心底隐隐有一种匡扶正义的冲动。
当警察是黄磊从小的梦想,“觉得警察很正气,能帮助人”。在曼彻斯特大学读书期间,黄磊曾在英国皇家陆军服役,为的也是毕业后能当警察。
“我学的是国际政治,当完警察之后,说不定可以当第一个华人议员。”黄磊说。如果不去叙利亚,他将在今年年底毕业。
促使他下定决心去抗击IS的是一名叙利亚当地的女志愿者。他在一篇新闻中看到,在与IS的战斗中,一位女志愿者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与几十名恐怖分子同归于尽。
“这让我很有感触。我一个大男人,四肢健全,却坐在家里,对着电脑,什么都没做。我觉得做人吧,该出手时就得出手。”黄磊说。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更长远的想法:“以后我当警察的话,主要工作就是维持治安。英国现在有部分年轻人参加IS,假如我去对抗他们,说不定可以把潜在的恐怖分子击毙。”
在英国,经常能看到关于IS的新闻,不过报道的多是发生在伊拉克境内的事情。英美两国在伊拉克的投资很多,难免受到IS的威胁,关注度自然就高。叙利亚鲜有英美投资,所以关于那边的局势报道就少。在一篇讲述一个英国人到中东参与打击IS的文章中,黄磊获知YPG下属的一个“国际志愿军”组织专门招收外国人。他在Facebook上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如果有犯罪记录,就申请不了志愿者。去那里的志愿者有很多种,有负责打仗的,也有负责医疗、物资运输、种植等方面工作的。”黄磊介绍。
填完申请信息后,他和YPG约在伊拉克的第三大城市摩苏尔见面。这里距离叙利亚很近,是库尔德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当地也有YPG的军事力量。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突厥和波斯的第四大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伊拉克北部、叙利亚东北部及高加索部分地区构成的一个狭长弧形地带。其中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聚集地是遭受IS危害的重灾区。
正式加入YPG之前,黄磊需度过一段观察期。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去叙利亚。他想先实地察看一番,再做选择。
到达伊拉克后,他发现那里的库尔德地区多有美国人的帮助,实行自治和资本主义,繁华富庶,便决定到条件较为艰苦、局势也更为混乱的叙利亚去,那里可能更需要志愿者。由于叙利亚国内的机场不是被摧毁就是停航,加上没有签证,他只能坐汽车一路偷渡过去。
黄磊在六七岁时随家人一起从四川移民英国,父母对他的教育属于放养式,对他的事情很少干涉。所以,当身为基督徒的他最初说到耶路撒冷旅行时,家人并没有反对;抵达叙利亚后,他又改口说在那里帮当地的基督教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家人虽然也担心,但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
他最后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哈塞克省停留了下来,那里已有部分地区落入IS之手。
“听到他的四肢biabiabia掉下来”
哈塞克省一直是一个动荡之地,境内除了YPG、政府军,还有叛军等武装。IS进攻哈塞克省之前,在政府军的干预下,叛军和YPG签订了和平条约。目前,IS是YPG的主要打击对象。
上战场之前,黄磊接受了10天左右的军事培训,内容包括如何使用AK-47、手榴弹等。
培训结束后,他和一群新兵被一辆大巴送往前线。刚下车,他们就遭受了IS枪炮的洗礼。慌乱中,黄磊跟着大部队躲进附近的建筑物里。伴随着机关枪的“突突”声,他第一次见到了戴着黑色头套的恐怖分子。
半小时后,武器的交火声逐渐远去,指挥官号召大家往前冲。黄磊抱着一杆AK-47跟了上去,距离敌方最近时只有200多米。他本想一发一发射击,但一紧张,扣了连发,一梭子子弹全部打了出去。
他不确定是否有打中人。“当时很狼狈,什么都不知道。”黄磊回忆。
类似的场景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反复上演。慢慢地,他开始习以为常,“天天都被射击,天天都有人想杀你,必须要习惯”。
前线的作息完全以战事而定。停火时,除了挖战壕,黄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擦枪,以便下一次能精准射击。
他经常睡眠不足。“打阵地战时,每天晚上7点到早上7点去站岗,回来睡到8点就被叫醒准备武器,再回来时已经接近上午10点。”严酷的战地环境也时刻影响他的睡眠质量,“天气很热,蚊子苍蝇到处飞,太阳也非常亮,完全睡不着,如果去一个没有窗户的黑屋子的话,会被闷死的。”
3月份以来,黄磊共参加了7次大战役,小战役则难以统计。只有在小战役中证明自己的实力后,才会被派去参加大战役。大战役通常有几百人参加。
指挥官为了振作士气,会带领志愿军大声喊口号:“Team Freedom!Fighting Freedom!”
3月中旬,黄磊第一次参加大战役,进攻一个藏了40多个恐怖分子的村庄。志愿军派出5个排一百多人,开了3辆装甲车。指挥部的策略是让两个排左右夹击,黄磊所在的排从中间进攻。
不料,左边部队的13人突然全军覆没,指挥部联系不上他们,只好命令全部撤退。
“我们刚刚跑到一半,当时好尴尬啊,敌方已经看到我们,一直在射击。对进攻一个小村子来说,损失很大,况且我们占据了人力、装备优势。”黄磊说。
Y PG中的指挥官都是当地人,不熟悉现代军事的作战方法。“他们习惯打游击战,最多30多个人,大型作战时几百人,他们的管理、沟通就不行。”后来经过几次大的战役,指挥官的组织管理水平才有所提高。
战场上,死亡是难免的。黄磊曾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友在不远的地方被流弹打中,整个人瞬间被炸飞,然后“听到他的四肢biabiabia掉下来,血直接溅到我的脸上”。
丹尼尔是黄磊所在小分队的指挥官,在战地帮大家理发已经有四五年了,手艺很好。他是在帮黄磊理完发的第二天离世的。那天,他带着小分队一直往前冲,就在冲到敌人的碉堡前刚把旗子举起来时,IS突然从后面反扑,丹尼尔被重机枪扫中,当场毙命。
“感觉真的很奇怪,突然就没了,昨天还跟我说开心一点儿,一切会好起来的,今天就死去了。”为了纪念丹尼尔,黄磊决定在回国之前不剪发。
没有比目睹自己的战友惨死在眼前更残酷的事情了。不过更多的时候,他们不是死于战场,而是死于医疗资源匮乏。
黄磊的战友埃阿斯中弹被送上救护车时,还用一口不流利的英语说“smile”,大家都以为他没事的,但他最终还是死掉了,死于失血过多。“当时对我的冲击非常大。很多人不是因为枪伤而死,而是因为没有医疗兵帮他们止血。”黄磊说,战争驱使当地的很多医生去了国外避祸。
4月中旬,黄磊开始尝试做一名医疗兵。他到后方的战地医院学了3个星期的急救和护理。中途由于战事紧急、人手不足,他曾两次被叫到前线帮忙抢救伤员。
战场上,生死常在一瞬间。身为基督徒的他,上衣口袋里总装着一本圣经。他祈祷自己时时能得到上帝的眷顾。实际上,圣经还真救过他的命。一次,他边走路边看圣经,突然有一页掉在了地上,他弯腰去捡。刚低下头,就听见“嗖”的一声,3发子弹从头顶飞过,射在旁边的墙上。
“当时吓得完全不敢站起来。”黄磊说,“我没有受重伤,也没有被爆头,都是些擦伤,到现在都没有出过什么大事,可能也是幸运吧。”
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肉了
不同于政府军,YPG的后勤全部靠当地人支援,时有时无,时好时坏。志愿军也享受同等待遇。
为了与普通民众及IS明显区分开,他们统一发放的志愿军服装是深绿色,在沙漠地带非常显眼,不利于作战,而且质量很不好,“衣服非常容易破,鞋子完全不透气,袜子很厚”。
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他们没有防弹衣和头盔,每人只发了一杆AK-47和4个弹夹;好的情况下,10个人会有一台对讲机,不好的情况下,整个排一个也没有—一次志愿军进攻失败,一个小队因为唯一的对讲机出了问题,没有听到撤退命令,3名队员全部战死。
战区唯一一部军用卫星电话是曾在美国情报部门工作过的鲍尔迪带来的。话费非常贵,两美元一分钟,只有500分钟,一个半月就被大家用完了。黄磊前后打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象征性地给了鲍尔迪一点儿钱。虽然他后来有了自己的电话,却是土耳其的号码,信号时有时无。
食物以大饼为主,午饭时不时才有,“没有的话就饿一顿,等下一顿”。战事紧张时,冻得硬邦邦的大饼是他们一连数天的主食。咬不动就用火烤,再不行就找个隐蔽的地方用小火煮。
“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肉了”是挂在黄磊嘴边的一句话。每次回后方休整,他都特别珍惜能吃到肉的机会。
“环境这么恶劣,抱怨有很多,后悔倒没有。”黄磊说。恐怖分子的极端行为,让他更加笃信自己坚持的价值。仅在最近的一个多月时间里,IS就在公共场所制造了数起自杀式袭击。一次发生在军事区,当场死了6名士兵,另有多人受伤;一次,他们袭击了一家儿童医院,受害的基本都是小孩子;一次,他们开着装满炸药的货车进城,结果在城外约一公里的地方提前爆炸了……
见惯了死亡的黄磊,不想自己难得的闲暇也被沉重的末日气息所笼罩,非战斗时间,他尽可能为自己的生活找点儿乐子。他和战友们一起在山上抓过野鸡,还在恐怖分子最为活跃的半夜出去吃过烤肉。
从今年5月开始,黄磊不时在自己的中文微博上发布自己在叙利亚的动态。“我一旦战死的话,就会留下一些东西给中国人看,让他们知道中东正在发生什么。”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初衷。
为了避免暴露行踪,黄磊所发的微博大部分都是一周以前的内容。每次发之前,他会请鲍尔迪看一眼。团队的指挥官也非常支持志愿者们分享自己的动态,因为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里的情况”。
黄磊在国内开始引起关注是在5月23日之后。那天他在微博上发了几张和战友的合影,其中一张他们手持缴获的IS旗帜。配文中他写道:“叙利亚北部终于被解放了!从IS的手中,我很幸运地夺取了IS的旗帜!我们赢了!虽然只是一个小地方!”
这条微博后来被转发近两万次,评论有数千条。回想起那次获胜的经历,黄磊说他们开了15辆车上街庆祝,车上的喇叭响个不停,没有鞭炮,志愿者们就用AK-47对着天发射。
通过黄磊的微博,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的故事。微博上,他喜欢用“醉了”、“吃货”、“萌萌的”等词语记录自己的战地生活,并称国际团为“逗逼团”,不需要打仗时,他们会很放松,讲段子、做鬼脸、比试身手,或者展示自己身上的纹身。
“大家都觉得人生这么短,如果要战死,与其很悲伤,还不如快快乐乐地死。”黄磊说。
聚与散
虽然生活条件很差,但当地居民对志愿者非常友好。走在大街上,常有人邀请黄磊去家里喝茶。知道他是中国人后还有不少人找他合影。不过,他们很少进城,因为发生过IS的人剃了胡子穿上志愿者军装混进城制造恐怖袭击的案例,志愿者的营地基本都设在城外。
“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感兴趣。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形式的,非常喜欢中国。”黄磊说,那里有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他曾经待过的一个蓄水厂就是由中国援建的。墙上残留的纸张上,写有中国援建单位的名称。此外还能看到各种中文标识,如“严禁私拉电线”、“严禁明火”等。
黄磊还在一户人家里看到过大幅的毛泽东像,摆放在客厅里电视机的正上方,后面是五星红旗。浓郁的中国元素,偶尔会让他产生一种身在中国的错觉。
当地人都恨极了I S。他们称其为DAESH,与阿拉伯语“踩踏”同音,以表达自己的蔑视。
IS在当地实施无差别攻击,不仅毁灭教堂,也毁灭清真寺,斩首和屠村等行为更是频发。所以,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对他们恨之入骨。

29岁的乔丹·马特森(中)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他因不满美国政府只帮伊拉克,去年9月到叙利亚加入了志愿军
作为抗击IS的重要力量之一,YPG于2014年10月21日在Facebook上创建了“The Lions Of Rojava”主页,招募外国志愿者。应征者大多来自英国和美国,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其中不乏退役士兵,包括著名的美国退伍军人乔丹·马特森—他因不满美国政府只帮伊拉克不帮叙利亚,去年9月到叙利亚加入YPG,是最早一批加入YPG的美国志愿者之一,也是国际志愿军的精神领袖。
外国志愿者抵达叙利亚后,被统一安排在国际团。
67岁的加拿大老兵扎卡里大约是团里年龄最大的志愿者,他不愿意自己慢慢老去,希望可以以战死的方式结束生命。扎卡里身体很好,为人忠厚,黄磊从来没见他生气或者抱怨过。
30岁的指挥官阿曼曾在美军陆战队服过役,2007年参加伊拉克战争时被两个库尔德人救过,这次抱着“报恩”的心态来到叙利亚。
大卫今年27岁,来自罗马尼亚,他本想在祖国参军,但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如愿,遂加入国际志愿军。
桑德森是库尔德人,从小跟随家人移民德国,会说库尔德语、英语和德语,并在德国接受过军事训练。得知库尔德的战事后,他决定回国效力。
黄磊还提到了一位名叫迈克尔·恩莱特的英国演员。他在《加勒比海盗》、《危情谍战》、《神盾局特工》等电影中出演过配角,自称“因无法忍受IS的暴行,舍弃演艺事业前往叙利亚”,到了后从不上战场不说,还装出一副上了前线的样子摆拍一些照片和视频。
每当指挥部想送他去前线时,他就以“我还没准备好,状态不行”为由拒绝。指挥部后来想把他送回英国,他用枪指着自己的头说:“如果你们把我送回去,我就开枪自杀。”
大家聚在一起很容易就找到欢乐,但也很容易起纷争。有一段时间,志愿者们一直被追着打,所有人都很压抑,因为洗碗的问题争吵了起来。“说实话,我们也是人,还是会有情绪的,到一定程度后就会爆发。”黄磊说,最后大家聚在一起,公开指出其他人的问题后才和好。
暂时出现的不和谐只是小插曲。在前线,几乎每个人都被别人救过。黄磊谈及,在一次交战中,如果不是同行的美国志愿者拉一把,一个新西兰志愿者就被射成筛子了,“这种感觉会让我们从朋友变为兄弟”。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国际团也一样。不时有志愿者选择离开,或是因为受伤,或是因为家里有事,或是回去做休整;但也不时有新鲜血液补充进来,在黄磊离开之前,国际团又来了15个人。
“感觉有点遗憾,老的朋友都走了,新来的都不认识。”黄磊说。他曾经所在的小分队中,他是最后一位离开叙利亚的战士。
监视居住结束后,黄磊准备回中国一趟。他上次回中国,已是5年前。几个月来,他在微博上收获了不少中国朋友,粉丝数涨到了近10万。看到他要回中国的消息,很多人给他留言,说请他吃饭或是喝酒。
休整的这段日子,黄磊准备把自己抗击IS的经历写成书。他说:“写完之后就是我回叙利亚继续作战的时候。”■
(丹尼尔、埃阿斯、鲍尔迪、扎卡里、阿曼、大卫、桑德森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