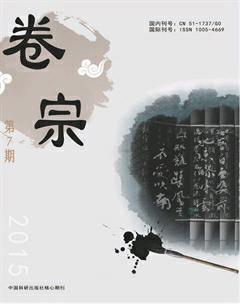网络传播与著作权保护
郑雅曼
摘 要:互联网技术的日益革新带来了以网络直播、网络同步转播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迅速发展,但由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完全按照技术特征规定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范围使得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游离于法律之外,严重影响着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的合法权利。如何规制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已经成为当下法律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扩大现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围使其可以调整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是较为合理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1 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概念与形式
1.1 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概念
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是与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厘清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概念是厘清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概念的前提。
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是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与传统的广播传播方式相比,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有着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在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下,用户可以在自己选定的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在任意一台连接互联网的电脑上上传、下载或在线欣赏作品,用户的下载行为实际触发了传播作品的过程。虽然上传作品者才是作品的传播者,但是只有在用户选择下载已经上传至互联网的作品时,作品的传播过程才真正開始;第二,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是一种“一对一”的传播行为。不同于传统广播“一对多”的传播方式,在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下,由于用户可以任意选择时间和地点下载或在线欣赏作品,因此作品的传播实际上是“一对一”的传播。例如,当网络传播者同时上传100首歌曲至互联网时,所有的互联网用户既可以在同一时间在任意一台连接互联网的电脑上收听同一首歌曲或者不同的歌曲,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在任意一台连接互联网的电脑上收听同一首歌曲或者不同的歌曲,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实现了网络传播者和互联网用户之间对于任意一首歌曲的“一对一”的传播。[1]
综上所述,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即用户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与地点上传、下载或在线欣赏作品的行为,与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相对应,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即指用户只能在网络传播者事先安排的时间或地点上传、下载或在线欣赏作品的行为。
1.2 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形式
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主要有两种形式,即网络直播和网络同步转播。
1.网络直播,通常是“由网络传播者直接到表演、赛事或者会议等需要直播的现场架设网络信号采集设备,然后将网络数字信号传输给导播设备或者平台,通过互联网将现场的情况上传到服务器,最后再发布给广大网民观看”。[2]例如201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各大媒体在会议现场架设设备采集会议信息,将其发回至所属电视台或导播平台,通过互联网将现场情况予以直播供所有互联网用户观看。
2.网络同步转播,就是“利用现在的数字与网络技术,将电视节目的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传输给电脑,使网民可以在网络上同步观看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网络电视”。[3]例如现在十分流行的PPLive等软件提供的服务就是依赖网络同步转播来实现的,用户只需安装此软件就可以在任意地点观看电视播放的节目,而无需再受只能通过电视机观看电视节目的限制。
2 现行《著作权法》对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规制困境
通过以上对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只有广播权和网络信息传播权可能进行对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制,但由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完全按照传播的技术特征对著作权的各项财产权利进行划分,导致无法规制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尴尬境地,本文以下将通过对现行《著作权法》中广播权和网络信息传播权的分析来具体论述。
2.1 网络信息传播权对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规制空白
1.现行《著作权法》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漏洞
《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规定了著作权人的网络信息传播权,根据该项,网络信息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通过以上对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定性可知,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网络信息传播权”仅调控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却无法受到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调控和规制。
就网络直播来说,虽然这项技术的应用使观看者无需亲临现场就可以观看各种赛事、会议等的现场情况,免去了地域的不同对于信息传播的限制,但是观看者并不能自行选择观看的时间,而只能在规定的直播时间收看直播节目,从本质上来说,其和传统的电视直播没有区别,只是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对于电视直播在网络上的扩展和延伸,因而不符合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特征,无法受到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调控和规制。
就网络同步转播行为来说,同网络直播类似,这项技术的应用同样免去了地点对于信息传播的限制,观看者无需通过电视机而在任意一台连接互联网的电脑上都可以收看电视节目,大大扩展了观看者的自主选择,但是观看者同样只能在传播方设定的时间而不是自己任意选定的时间收看电视节目;并且,此种传播方式针对的是所有有网络覆盖的地点,在同一时间段内,观看者看到的都是同一档电视节目,不符合“一对一”的传播特征,因此网络同步转播行为也无法受到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规制。
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必然使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呈现日益勃兴的态势,法律的空缺已经导致大量著作权人的权利被侵犯却无法得到法律救济的尴尬境地,如2008年宁波成功多媒体通信有限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虽然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判定被告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犯了原告宁波成功多媒体通信有限公司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对案件分析即可以得出,对于被告在其经营的悠视网按照原告公布的播放时间表公然在线播放热播剧《奋斗》的行为属于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按照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并未侵犯原告的网络信息传播权,法院的判决属于对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误解。[4]无独有偶,“视频网站盗播电视节目对电视台节目收视率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小觑。据工作人员介绍,对于同样一部电视剧,通常电视台每天只能安排播放两到三集,但是视频网站却会把整部电视剧直接放在网上供网民随意观看,如此以来电视台当然竞争不过网站,比如《百家讲坛》音像制品年收入最高时多达 3000 万元,现在连当时的百分之十收益都达不到,其他电视节目的收益也同样随着收视率的下降而快速滑坡”。[5]长此以往,电视节目、电影等文化市场必定会成为一潭死水,观者短期得到益处的背后是对文化市场根本性的破坏,如何解决这种无序的盗播行为是时代发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提出的挑战。
2.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漏洞归因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网络信息传播权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下简称WCT)中对“向公众传播的权利”的规定。WCT第8条规定“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第 11 条第(1)款第(ii)目、第十一条之二第(1)款第(i)和(ii)目、第十一条之三第(1)款第(ii)目、第十四条第(1)款第(ii)目和第十四条之二第(1)款的规定的情况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可获得这些作品”。通过对比WCT对“向公众传播的权利”的规定和我国《著作权法》对“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规定可以看出,两者均规定了著作权人享有通过网络传播其作品的权利,但从两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我国在移植WCT“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来规定我国的“网络信息传播权”时却漏掉了至关重要的“包括”二字。在WCT的规定中,“包括”二字表明著作权人享有通过交互式和非交互两种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权利,“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可获得这些作品”这种交互式的网络传播方式只是著作权人行使权利的方式之一,但反观我国《著作权法》对“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规定,交互式网络传播方式却是著作权人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唯一权利,对WCT内涵的误读导致了我国网络信息传播权出现的法律漏洞。
2.2 广播权对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制空白
1.现行《著作权法》下广播权的法律漏洞
通过上述对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界定,电视台、电台播放节目应当属于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但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下,部分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并不能受广播权规制。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一项规定,广播权是指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依据《著作权法》对广播权的法律界定,广播权只调控三种法律行为:第一、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的行为;第二、以有线方式传播或者转播已经广播的作品的行为;第三、以扩音器或者其他类似工具无线传播已经广播的作品的行为。即直接通过有线方式进行的传播行为因为不符合广播权所确定的技术特征因而无法受到广播权的规制。因此,若电台、电视台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直接以有线方式播放作品的行为虽然侵犯了著作权人对作品的专有权利却无法受到广播权的规制。
尽管有参与立法者指出“使用有线广播传送作品的表演属于机械表演,因此未经许可直接通过有线系统播放作品,虽然不侵犯‘广播权却侵犯‘表演权”,[6]但是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九项的规定,机械表演是指“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而电台、电视台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直接以有线方式播放作品的行为可能属于机械表演,如播放歌星演唱会视频的录像带,也可能不属于机械表演,如电视台播放电影作品的行为。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的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属于独立的《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因此电视台播放电影作品的行为属于播放作品的行为而非机械表演,但若电视台未经著作权人同意而直接以有线方式播放却并不能受到广播权的调控,也不能受到表演权的调控。
另一种观点认为直接适用无线方法传播作品的行为可以由“放映权”调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项规定,放映权是指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但并不包括将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先录制下来再通过技术设备传送到终端在电视台播放供观者欣赏的行为。[7]
因此,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立法模式下,直接以有线方式播放作品的行为只能由《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七项“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来调控,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将呈现出日益勃兴的态势,此种解决办法并非长远之计,同时,此种解决办法会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违背知识产权“权利法定”原则的可能。
2.广播权法律漏洞归因
我国《著作权法》对广播权的规定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称《伯尔尼公约》)第十一条对“广播权”的规定如出一撤。《伯尔尼公约》第十一条之二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下述专有权:1. 许可以无线电广播其作品或以任何其他无线播送符号、声音或图像方法向公众发表其作品;2. 许可由原广播机构以外的另一机构通过有线广播或无线广播向公众发表作品;3. 许可通过扩音器或其他任何传送符号、声音或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送广播作品”。通过此项规定可以看出,《伯尔尼公约》中广播权的调整范围与我国广播权的调整范围相同。这是由特定的时代背景决定的。《伯尔尼公约》于1886年签订,在当时的技术环境下,互联网远没有出现,通过无线电传播作品是最为有效也是传播范围最广的手段,因此《伯尔尼公约》只调整“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線方式传播或者转播已经广播的作品”以及“以扩音器或者其他类似工具无线传播已经广播的作品”的行为。但是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和大量普及的今天,传统的《伯尔尼公约》和直接来源于《伯尔尼公约》的我国《著作权法》对广播权的规定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广播权无法规制直接以无线方式传播作品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是法律滞后性带来的必然结果。
3 从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看网络信息传播权的完善
如何规制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已经成为当下法律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在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需要扩大广播权的调整范围,使之能够规制各种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同时建立一个上位的抽象传播权的概念涵盖所有作品传播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扩大网络信息传播权的定义,将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纳入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调整范围。笔者认为,扩大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范围来调整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是较为合理的解决办法。
第一、广播權和网络信息传播权的区别决定了只能通过扩张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范围来调整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首先,广播权和网络信息传播权出现的时代背景不同。从1886年签订《伯尔尼公约》起,广播权就已经被确定为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的一项财产权利,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广播权用于调整电视台、无线电台的公开广播行为,而网络信息传播权是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是自WCT规定了“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后才出现的一项新型权利,主要用于调整通过互联网传播作品的行为,广播权和网络信息传播权自产生时起就有着天然的差别,1996年与WCT同时达成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将广播权与向公众传播权作为表演者的两项并列的权利同时出现在该条约中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一观点,虽然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权调整的范围也为交互式传播行为,但本文主要探讨以网络直播、网络同步转播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网络环境下的非交互式传播行为,因此用广播权规制本属于网络信息传播权调整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显然是不合理的。
第二、将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纳入广播权进行调整的方案“只能在公众无法自由选择时间获取作品的情况下起作用,不能解决公众不能在个人选定的地点获取作品这种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引发的争议”。[8]由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权是指通过电视台、无线电台进行公开传播作品的权利,因此若将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纳入广播权进行调整那么权利人和使用人仍然只能在能够接收到无线电台、电视台信号的地点行使其权利,公众仍然只能在上述地点获取和欣赏作品,而公众在个人选定的地点通过互联网获取和欣赏作品引发的争议仍然无法得到解决。
第三、扩大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范围来调整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方案更有益于与现行法的衔接。我国现行《著作权法》采取了列举式的方案来规定著作权人的各项人身和财产权利,建立一个上位的抽象传播权的概念涵盖所有作品传播行为的方案势必会对现行《著作权法》造成极大的冲击,甚至可能面临重新构建《著作权法》体系的风险,虽然现行《著作权法》已经在多方面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对其进行修订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尚不完备、知识产权法律研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以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对《著作权法》进行修订的方案为宜。
参考文献
[1] 王迁.论对网络信息传播权的正确适用——兼评“成功多媒体诉时越公司案(上)”[N/OL].[2015-4-20].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a2d1f50100bx1r.html.
[2] 姚稳.数字网络时代传播权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15.
[3] 姚稳.数字网络时代传播权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15.
[4] 王迁.论对网络信息传播权的正确适用——兼评“成功多媒体诉时越公司案(上)”[N/OL].[2015-4-20].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a2d1f50100bx1r.html.
[5] 姚稳.数字网络时代传播权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8.
[6] 王迁.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构[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8,(9).
[7] 王迁.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构[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8,(9).
[8] 蓝舐婕.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归责之惑——以网络信息传播为视角论《著作权法》修订之疏漏[J].青年与社会,2014,(18).
[9] 焦和平.论我国《著作权法》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完善——以“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侵权认定为视角[J].法律科学,2009,(6).
[10] 张玉敏.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0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