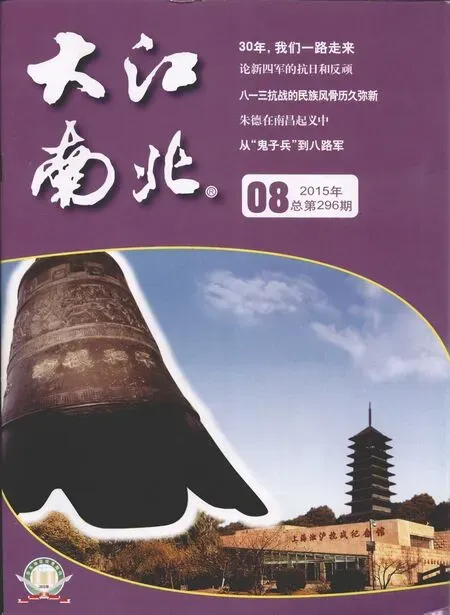缅怀妈妈叶世锜
□ 汤绍涵
缅怀妈妈叶世锜
□汤绍涵

叶世锜
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我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浩劫,我的母亲虽是一个家庭妇女,但也没有逃过这一劫。她姓叶,名世锜,生于1893年10月,缠过小脚,初小文化水平,但能看报、写信、记账,还识大体。上海沦陷,父亲失业,因租不起房子,只好寄住在卡德路(即今天的石门二路)祥福里32号舅舅家,我们一家六口挤在二层阁楼内。大哥汤纪宏1939年参加了新四军,家里靠着大姐汤群做代课老师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1941年,大姐也参加新四军去了苏北。为着抗日救国,我妈含辛茹苦,让大哥和大姐战斗在抗日第一线。
1940年前后,哥哥到江南做地下工作,他跟妈说:“我们现在做的是抗日工作,过的是供给制生活,无法养活家里。”妈妈却认为,你们抗日也不要一人在外面东躲西藏,可以到家里来,我们一起干。这样,哥哥就常回家,把家当作他的工作场所,有时约些同志来家开会,有时隐藏一些物资在家,母亲经常给他们放哨望风,也用窗台上放花盆的办法传递信号,保证了地下活动的安全。
我那时只有七八岁,在哥哥的挚友、翻译家草婴先生的帮助下,做报童,与妈妈一起卖报度日,其中还给住在上海的俄国人提供苏联报纸。有一天,母亲在卖报时被抓走,关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内,见到被抓进去的许多人中有我的哥哥,敌人要她认儿子,她始终不承认认识他,敌人严刑拷打她,她始终装傻不知是什么事。后来哥哥被地下党营救出来了,妈妈也被关了几个月后放了。这次遭遇更激励了她的斗志。在哥哥的挚友、语言学家倪海曙的资助下,我们在现今的南京西路石门路口正威药房门口,摆了一个书报摊,利用报刊、书籍夹带情报,还把三联书店送来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等进步报刊卖给进步人士,扩大了我党的宣传阵地。
原来住的二层阁楼已无法开展工作,我父亲出面在西宝兴路汉兴里三号租借了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母亲带着弟弟替地下党同志做饭洗衣,有口饭吃,没有工资,对外像个家庭。哥哥不断为新四军输送人员,还将在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人员送到根据地,妈妈给他们安排吃住,保护他们,这些青年男女也称我母亲“妈妈”“伯母”。我母亲经常主动和邻居交往,房子的右边住着民主党派领袖楚图南,左边住着一个国民党的“包打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哥哥他们把在上海刻好的抗币模板,把做武器的无缝钢管,把布匹药材及其他物资,把书报摊搜集到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新四军去。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由于隐蔽工作做得好,周围邻居和正威药房的职工都没发觉,解放后待党组织公开时,大家才恍然大悟。
邻居曾经问我母亲,你怎么有这么多孩子?妈妈总是很镇静、很大方地回答:“他们都是我的侄子、侄女、外甥,他们到上海和我儿子一起做生意,没地方住,我留他们住在我家里。”上海解放后,哥哥参加了接收上海出版系统的工作,后担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大姐回上海参加了接收中国银行的工作,她今年99岁还健在。过去妈妈接送过、保护过的同志,曾任各级的领导有:徐雪寒(外贸部副部长)、陆明(上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余瑾(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金源明(济南铁路局副局长)、蒋建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等等。
解放后,母亲积极参加里弄工作,被选上了居委会的治保委员。1950年,母亲又鼓励我和弟弟参加抗美援朝,我当了通信兵,弟弟当了防空兵,四个子女都过着供给制生活。有人问她,怎么把两个小的都送上前线,妈妈说:“把孩子交给共产党,我最放心。”人们都称呼她“光荣妈妈”,我们为有这样的好妈妈而自豪。
1965年已是73岁的妈妈,一场大病故世了。今天,我们与她离别已经50年了。她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却不是共产党员。她没有正式委任的工作,不享受各种待遇,但她忠诚老实、不求功名、不图回报的价值追求,是我们后辈的崇高榜样。
(编辑韦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