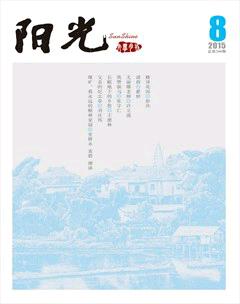清荷
翟妍
一
三月的午后,阳光很好,前日下了一场雪,今儿就一点儿一点儿地晕开了,严家院墙边的那棵小桃树在地上投下一团影子,影子下面没化开的积雪灿灿地反着太阳的银光,刺着眼睛。院子里安安静静的,有几只雀子落在那树上面,偶尔传来几声鸣叫,显得格外悦耳。清荷从屋子里走出来,痴痴地站在那桃树下面,听着那鸟鸣发起呆来。
桃树是清荷五六岁的时候,严老太太特意买回来栽在院子里的,栽在这里时对她说,清荷啊,你就认这桃树做干娘吧,你命苦,有这桃树做娘护佑着,你也能逃过这世上的劫难。严老太太那天在桃树底下摆了香炉,供了三个雪白的大馒头,清荷跪在地上就把头磕了。磕了三下,叫了三声娘。眼泪吧嗒吧嗒地就落在那桃树根下。因为她半岁时就死了娘,她娘一死他爹就有些不着调了,一颗心都泡在了酒上。她长到五六岁时,她爹喝酒喝到大口大口地吐血死掉了,所以她二婶秀春是半拉眼珠子也看不上她的,说她命硬,克爹克娘。清荷知道她奶奶心里头也这样想过,只不过心里疼着她,这样的话没说出口罢了。要不怎么会买了这棵桃树?她奶奶说,你干娘若是真心疼你,必会在三年以后结出壮实实的果子,你吃下那果子,这辈子都是幸福的人了。
那会儿清荷小,不知道幸福的人是啥样的人,只是天天望着那桃树盼啊,盼啊。盼了三四年,那桃树终于开出花来了,秀春却抱了一捆干树枝子把那桃树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秀春说,这桃树正对着她的窗,要论起来这是她地界上的东西,属她的私有财产,别人是万万争不得的。用树枝子围起来省得谁家的小孩子淘气,说不准什么时候趁着大人不注意摘走了生涩的果实。那样岂不是糟蹋了?
围在树枝子里面的桃树谢了花朵,也结出果子来了。秀春不在家的时候,清荷搬个板凳踩上去数了数,五个,一天一天地长大呢。清荷想她干娘是疼她的,哪怕吃不到,也是知足的。
桃子长到鸡蛋大的时候,上午还是五个,晌午一觉醒来,就剩四个了。秀春急眼了。鸡犬都不得安宁了。清荷吓得躲在了奶奶的屁股后,还是被秀春揪了出来,脱了脚上的鞋,用鞋底抽青了屁股还不肯罢休,她奶奶气急趴在了她的身上,你再打她,就先打死我!秀春才住了手。
桃子是清萍摘的。清萍比清荷小一岁,都是小孩子,就算清荷在清萍的口袋里看到了那颗桃核,清荷原本也是不记恨清萍的。怪就怪清萍捏着桃核在清荷面前说的那句话,把清荷惹急了,再见清萍的时候,心里就别别楞楞的。清萍说,我就想让我娘揍你一顿,凭什么薛家亚奎只和你玩过家家?
亚奎就住在严家院子的后面,亚奎他爷爷和清荷的奶奶严家老太住了一辈子前后院的邻居,说起来也算世交了。亚奎他爹个儿矮,外号薛矬子,家里又穷得很,三十大几了才娶了个傻媳妇,生了两个孩子,头胎是个儿子,偏巧腿上有点儿残疾,政策上就允许他生了个二胎,二胎又是个儿子,生龙活虎的,取个名字叫亚奎。清荷和亚奎同岁,和清萍一起去薛家玩,薛家老爹的傻媳妇特别偏宠清荷,总是把红头绳、花绫子什么的系在清荷的辫子上。那会儿清荷还小,只当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很是好看,扎在头上到处疯跑,秀春见了难免要骂上一句,说她和一个傻婆娘混在一起,十有八九也是个缺心眼儿的东西。
那会儿大人们常常逗引亚奎,你长大娶啥样的媳妇?亚奎总是秃噜着鼻涕说,娶清荷。清荷但凡听到亚奎那样答了,就笑嘻嘻地说,行,我愿意。左邻右舍都当笑话听,说小孩子就是有意思。清萍看不上清荷那没羞没臊的样儿,再说了,就是真嫁,也不能嫁亚奎那样的,她娘秀春总和她说,没人要的女人才嫁到薛家去当媳妇呢!
二
太阳还没落,薛家老大就打来电话说他打鱼回来了。清荷和严老太太说了声,就奔着薛家去了。自打清荷养了貉子,薛家老大打来的鱼就被清荷包下了。貉子那东西离不了鱼。
清荷养貉子是前年的事儿了。前年她和亚奎还有清萍三个人都从市里的重点高中毕了业,因为考大学时清萍落了榜,秀春一生气把清荷的录取通知书也撕了。撕了也就撕了,清荷本来也知道,就算不撕,这学她也是上不成的,秀春能让她读到高中毕业已经算是够贴己她了,不可能自己的闺女落了榜,还花大笔的票子供她去念书。秀春总说,羊肉贴不到狗身上的。亚奎走的第二年夏天清荷去乡上赶集,碰见了一个人,说是乡里的养貉子大户,别人都叫他“貉爷”,叫着叫着叫溜了嘴就成了“好爷”。其实他也不过四十多岁,人长得五大三粗,很是剽悍,开了一辆二手的越野,走到哪里都耀武扬威的。一张口准保是“我好爷”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天也赶巧了,是乡里组织一次养殖技术培训,本来是市里的农业部门专门派下了技术员讲解的,后来可能是乡长考虑到这一年吃吃喝喝的没少让好爷掏腰包报条子,就做了个顺水人情,给好爷一个抛头露脸的机会,让他西装革履像模像样地地坐在了讲台上,他倒也不客气,一张口就来一句“我好爷”。他毕竟是有实践经验的,远远近近又有很多仰慕他的散户,听他这样传经授教,差点儿顶礼膜拜他了。清荷也早知道养貉子是可以挣大钱的,只不过这东西风险大,老话儿不是说得好吗,家趁万贯带毛的不算,就是这样的,行情好了就发一笔,行情跌了,也免不了要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清荷他们村里还没人养这东西。清荷在台下听,那好爷也是那么讲的,是清水还是浑水,还要自己亲自蹚一蹚才知道的。
貉子是好爷赊给清荷的,赊的时候好爷说得明白,养貉子这玩意儿就是这样,三起三落的,偏赶上这两年行情不好了,我好爷这又多得出不了手,赊给你是便宜你,再过两年后行情保准涨起来,正好是你的貉子打皮的时候,到时候我好爷连本带利一起收,你也能小赚一笔。你不知道吧?从我好爷这里买种貉的散户,回收皮张时好爷我都不亏待!
就这么心血来潮的养上貉子了,为这事儿秀春大骂了她一场,说她一个丫头,不安安生生地找个人嫁了,作个啥?清荷不吭声,由着她骂,从小到大和秀春住在一个院子里,四间房子两头开门,她和她奶奶住东,秀春住西,一个屋檐下出来进去的,哪一天不挨上几顿骂?要是哪一天不骂了,清荷倒是觉得日头从西边出来了呢。她倒想也像清萍那样出去打工,一走了之呢,可她不能,她奶奶老了,越发地离不开她了,她得守着。可她也不想一辈子种庄稼,她是和亚奎一样有梦想的人。梦想,是可以带着人飞到天上去的,她想和亚奎一起飞。
清荷出了大门,向北一拐,又向右转了一个弯儿,就进了薛家的院子。薛家的院子这么多年就没变过,只是那院墙被风雨侵蚀的一年比一年矮。就像薛家老爹的个子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矮了。
薛家的人正围着桌子吃晚饭,清荷一脚跨进去愣了一下,接着有一丝惊喜漫过脸上。她看见在省城读大学的亚奎竟然回来了,正挨着他的傻娘坐着,大口大口地吃着白面烙饼。见了清荷,亚奎一口烙饼含在嘴里,先是一愣,又急匆匆地扫过清荷一眼,亏心似的又吃他的饼去了。清荷被亚奎这不冷不热的态度给弄得消沉了。想说点儿什么都被这冷漠给淹回去了。清荷接过薛家老大递过的鱼出了薛家的门脚步就凌乱了,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照理说,亚奎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见清荷前脚走了,后脚定会跟上来,送送她,说上几句什么,或者干脆告诉她今晚他们将在哪里约会。是应该约会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他在哪里她的心就跟到哪里,生怕空间的距离把心也拉远了。她总觉得他们两个是青梅竹马的,小的时候,他们总去霍林河边的芦苇垛,那芦苇一垛一垛地连绵成山,他们在里面掏一个洞,暖暖呼呼的躲在里面偷着看书,都是那些杂七杂八和学习无关的书,亚奎怕他爹嚷着让他干没完没了的活儿,放假时总是领着清荷在芦苇垛里面一躲就是一天,披星戴月回去的时候,清荷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就能听见薛家老爹破口大骂亚奎的声音,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清荷总会哧哧地笑着问亚奎,你屁股肿了吧?现在想起来,清荷是无比怀念那段时光的。尤其怀念那个芦苇垛里的洞,清荷清晰地记得,亚奎第一次说喜欢她就是在那个洞里。
那是亚奎去城里上学的前一天晚上,他躲过清萍把清荷约了出来,俩人坐在芦苇垛的那个洞口边上数星星,数着数着亚奎停住了,他在星光灿灿的夜里抓起清荷的一只手说,喜欢你,从小到大,一直喜欢!他还说等他完成学业,在城里找份工作,就和清荷结婚。那晚,靠着亚奎的肩头,清荷只说了三个字,我等你。清荷就是因为自己那晚说了那句“我等你”,才养了貉子的。三四年的光阴不能就这样白白地等过去,她要闯出一番事业来。
可刚才,亚奎对她似乎不咸不淡,清荷心口慌慌的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堵上了。
清荷把鱼丢进灶台下的一只塑料桶里,转身进了屋子,桌子上摆了一台电脑,是当初她为了和那些养貉子的散户进行交流狠了心买的。后来竟一举多得了,亚奎也买了电脑,在她的QQ好友里。她把它点开,看他的头像是她的照片,心里又踏实了很多。她放了一首音乐,安慰自己似的听着,从电脑桌下的抽屉里摸起一枚戒指,芦苇秆儿编的,好几年了,还微微地泛着黄,看起来很珍贵,因为那是亚奎送给她的,她套在了无名指上,看了又看,笑了。
喂过貉子天就黑了,今晚的约会怕是等不来了。清荷掌了灯坐在灯下看书,都是些关于养殖的书。书,在手里摆弄着,却读不到心里去,都在眼前晃动起来,晃着晃着就变成了亚奎的样子,在书本上飘来飘去。奶奶被黑夜裹着睡过去了,清荷推开房门跑了出去。她站在院子的一角看着薛家的院子灯火明亮着,很是热闹。不知谁还把过年的红灯笼挂在了薛家的房顶上,红灯笼泛着红光,挺喜兴的,清荷看见有人摇晃着从薛家的屋子里小跑出来,像是喝醉了,懒懒散散地杵在红色灯影下撒尿,清荷一转身跑回了屋子。钻进了被窝,突然觉得薛家的院子像深宅大院一样神秘莫测、高不可攀了。
那一夜,她毫无睡意。
三
天明的时候还没爬起来,听见有猪的叫声,稀里哗啦地披上衣服跑出去一看,是薛家把过年时都没舍得杀的猪给杀了,清荷忽然想起是薛家老大要结婚了。
清荷站在院角处朝薛家的院子又望了一会儿,退回屋子,忙着给貉子烀鱼,烀好了就盛在塑料桶里慢慢晾着,晾到不烫了再盛到喂貉子的小盆里,一盆一盆地端给貉子吃,貉子吃饱了,清荷把小盆一只一只地拣出来,用清水刷洗干净,摞成一摞。干完这些,清荷在肩膀上搭了一条毛巾清理貉子笼子底下的粪便。一个上午没得空闲。到中午闲歇下来了,就又想起亚奎了,胸口一漾一漾地难受着。
她出了大门,路过薛家的院门口,见亚奎双手插着衣兜众星捧月似的站在人群里,她远远地望了一会儿,觉得那人离自己遥远了,就一个人去了霍林河边。河边的冰隐隐地化开了,她小心翼翼地踩在那冰碴上,咔嚓咔嚓一声一声清脆地响着,倒有点儿让人心烦意乱的。去年的雪大,河里没来得及采下的苇子在冰面上茫茫地涌来荡去。小的时候,常常和亚奎还有清萍三个人钻到那芦苇荡里去,亚奎总是一转身就没了影子,把她和清萍丢在无垠的冰面上,非等到她被吓得大哭起来,他才会扑棱棱顶着一头的芦花从苇荡里冒出头来,说她真傻,就会哭!那个时候多好!那么好的时光就好似在昨天一样。
再回来的时候,故意兜了一圈儿,绕过了薛家的大门口,进了院子,看见清萍回来了,穿着黑色铅笔裤,葱心绿韩版小西装,深口粗跟高跟鞋,站在院子里,捏着鼻子。秀春站在她的后面,嘟嘟囔囔地说,哪还有个好味儿?这东西本来就是又腥又臭的,要是遇到个阴天下雨的,这院子简直就是不能住人了!我是拿她没辙了,她又没个妈,我总不能事事都和她计较,倒显得我小气了!她还能有几年折腾的?我就不信她不嫁人了?清萍说,这东西要是挣了钱倒也行,就怕万一赔了拉下的饥荒她可怎么还?秀春说,怎么还?自己想辙去呗!也是二十一二岁的人了。清荷老远走过来都听在耳朵里了,却装作什么也没听见似的走过去,对着清萍说,没听二婶说你要回来,啥时候到家的?清萍说,我到家的时候你正好出去了,我看见你从大门口往北一拐走了,叫了你一声呢,你都没听见!清荷说,是吗?我还真没听见呢。秀春见她们两个说话,就转回身进了屋子,门关着,秀春炒菜爆锅儿的香味还是从那门缝里钻出来,整个院子都飘着香。清萍说,真香,在外面就想我妈这做饭的手艺。清荷笑了一下,回自己的屋子里去了,清萍跟了进来,严老太太趴在窗台上等着和她唠嗑,见她进来了却狠狠地白了她一眼,嗔怪地骂她是个小没良心的,也不快点儿来和她说说话。清萍被奶奶拉扯着坐在了炕沿儿上,拽了拽她的衣服说,这么短,一猫腰就露脊梁骨了!你这个玩意儿清荷可穿不了,她整天撅着屁股喂貉子,穿这个可不好。清萍听了咯咯咯地笑,见清荷穿着一套西瓜红休闲装坐在电脑桌旁,手里摆弄着一枚芦苇戒指,也淡淡地笑着。清萍走过去,看她手里的东西,说,弄个真的戴戴,没几个钱!清荷说,这东西能自己买一个戴上吗?我等有人送给我时我才戴呢!清萍伸过手来,我戴上了!你猜谁送的?清荷说,你处男朋友了?清萍笑嘻嘻地缩回手去,你说呢?清荷又笑了笑,把那枚芦苇戒指套在了自己的指头上。严老太太在炕边上翘首望着她们,说你们俩嘀嘀咕咕说什么呢?过来坐我这儿,也说给我听听!她们俩就互相望了一下,笑了。
秀春在外面喊清萍,清萍应了一声走出去了,过一会儿又回来了,告诉清荷晚上别做饭了,和奶奶一起去吃她妈妈丰盛的晚餐。清荷说,让奶奶一个人去吧,我晚上不吃饭的,减肥呢。清萍说,那怎么行?就是不吃也要去坐一坐,让别人看了成了什么,偏偏落下你了!她奶奶也说就是,就是。清荷不好推脱了,笑着说,哪有什么别人,都是自家人!又说,那就去吧,可一旦去了就可能管不住嘴了!清萍说,那也不差这一顿,再说了,你还没我胖呢,减什么肥!严老太太突然在炕上问了一句,清萍我听说你现在不在咱们市里干了。清萍说,奶奶的消息还真灵通,我去长春了,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做大堂经理。严老太太说,呦,那不是和薛家的老二在一个地方了吗?清荷在一旁听了,忙问,你在省城,我怎么从来没听说?清萍说,我也是才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妈的,怕她惦记,其实我都在那里干了两年了,要不也不能一下子就当上了大堂经理。严老太太说,就是,你妈刚才和我讲的时候我还吓了一跳,跑去了那么远,多让人着急!后来一想也不错的,好在那里有个薛家老二,你们从小玩到大,可以相互照应的。清萍说,奶奶你说的轻巧,你以为在一个城市就可以天天见面呢?一个星期见着一次就不错了,我离他远着呢!严老太太说,哟,一个城市再远能远哪里去?清萍说,做公交车还要倒两次呢,走一趟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严老太太说,那也比没这么个人要好。清萍说,那倒是,他要不在那儿兴许我还不去了呢,我又不在乎什么大堂经理不大堂经理的!清萍侧过脸看着清荷问,他回来了,你见着他了吗?清荷心里正想着事情,被清萍这么一问怔了一下,才说,谁?哦,你说亚奎,我看到他了,你们在一个城市,怎么没一起回来?清萍说,本来也没打算一起回来,昨天是周末,我以为他去做家教了呢,下午打电话给他,他才说他要回家来的,说是薛家老大要结婚。我那儿工作忙,一时脱不开,他就先走了。严老太太问清萍,你忙跑回来干什么?清萍嘻嘻地笑,笑过了才说,我想家了呗,都走了大半年了。
秀春过来叫她们吃饭,搀着老太太往外走,清萍也站起身来叫着清荷说,清荷你快点儿啊!清荷说,你们先走,我收拾一下马上就来。她们都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清荷一个人,清荷对着那电脑看着亚奎的QQ头像哭了起来。那QQ头像上明明是她的相片,可他和清萍之间有这么多的事她竟然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照理说,在省城两年了,清萍自己不说,亚奎也是没有必要隐瞒的,可是现在听来,就好像他们两个约好了似的,她什么也不知道。她流着眼泪把那QQ关了,和他近在咫尺,却只能这么看着,虚无缥缈抓不到个影子。清萍在外面叫她,你怎么还不来?清荷哦了一声抹着泪水从椅子上站起来,那枚芦苇戒指被她的衣襟一碰掉在了地上,她一脚踩着了也没看到。
秀春的心情格外好,给庆有倒了一杯白酒,边倒边笑盈盈地说,就这一杯哟,就这一杯!庆有说,难得我闺女回来一趟,你就让我喝个痛快。老太太在一旁附和着,秀春你就开开恩,一会儿再赏他半杯。秀春开了一瓶雪花啤酒说,咱们四个女的一人来一杯啤酒,一会儿让他也喝点儿啤的,白的就那些!庆有倒是很知足,他连声说,这就不错了,这就不错了。老太太说,就是,也难怪秀春这样管你,你喝起酒来实在是没数!秀春说,可不是,你要是跟你大哥似的……话说到一半庆有咳了一声,秀春忽然觉得说漏了嘴,就把剩下的话憋了回去,看了老太太一眼,觉得她的脸上讪讪的不怎么好看,秀春紧忙笑着说,清萍,你不是说从长春给你奶奶买了礼物回来吗?快拿出来我们看看。清萍说,咦,你不提我倒忘了。就站起身去开旅行箱,从里面拿出一件长袖开身套装,富贵绒的,茄花儿紫色,上面绣着金丝线玫瑰花。老太太接过衣服,脸上讪讪的神情就散去了,说这衣服是不是太艳丽了,七十几岁的人了,有点儿穿不出去。秀春说,妈,人家城里人都这么穿,这都到三月三了,天儿也快暖和了,正好穿它。老太太嘴里说着太艳了太艳了,心里还是喜欢得不得了,脱下外衣当众试了试,对着镜子又照了照,大家都夸好,她就抹了一下头发说,今天也不是太冷。秀春忙说,妈,那就穿着,咱们吃饭,菜都凉了。
清荷站起来给老太太披了一件外衣,他们就坐下来喝酒。秀春忙着给清萍夹菜,又忙着嘱咐老太太多吃点儿,清荷心里想着亚奎,吃起饭来就一小口一小口地拈着,清萍看了她一眼说,你还真减肥啊?这个吃法?清荷轻轻地笑了一下,借此放下了筷子,说,嗯,真的不吃了,二婶的菜太好吃,一旦开了戒,肯定是要刹不住车了。秀春也不劝,当即撤了她的碗筷说,你们现在就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天天讲究减肥啊减肥啊的,我们年轻那会儿能见到点儿油星儿都不错了。老太太也捧着饭碗说,可不是,后院薛矬子年轻那会儿给生产队的食堂里做饭,生产队长让他去乡上领油,拎着油壶走到半路馋得受不了,二斤油被他偷喝了半斤,回来被队长好一顿收拾。清萍说,奶奶你可别再叫人家薛矬子,难听死了。老太太说,叫他薛矬子怎么了?这都叫一辈子了,当着他的面我也是这么叫的。再说了,你也这么叫过!清萍说,现在可不比从前!人家现在可容不得你们再贬低了,亚奎多给他长脸,出息成那样!老太太拿筷子敲着碗边子说,哟!亚奎出息了他还能长高?秀春扑哧一声笑了,说你们俩人就跟冤家似的,说说话保准能顶起来。老太太说,可不,从小她就这样,总和我拔犟眼子,清荷就不,我一说她保准不吱声了。秀春不愿意听老太太提清荷的好,就又岔话儿到薛家去,也真奇了怪了,薛家那样的人家竟能生出亚奎那样的孩子来,小时候大人们还总逗引他,问他长大娶啥样的媳妇呢,你们还记得吗?他那时候总是秃噜一下子鼻涕说,娶清荷!现在看,清荷哪还有这个命?秀春怪模怪样地学着亚奎,清荷在一旁听了,脸刷地一下红了,正好外面传来狗叫声,她借故跑了出去。
四
来的是好爷,越野车停在了大门外,进来的时候站在貉子跟前看看说,趁着天儿好,就下到各个散户家看看,你这貉子今年冬天也该打皮了,看着不错,你一个姑娘,开了你们胡家村的先河了!清荷说,那还不是借了你好爷的光。好爷说,你叫什么好爷啊,那都是那些老爷们儿闲扯的时候瞎叫出去的,你这么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和他们起什么哄?清荷说,我可不是起哄,倒觉得你这名字挺压人的呢,也不敢不叫了。又低下头去,声音细细地说,再说了,我也不知道除了叫你好爷还能叫你什么。要不我叫你好叔吧!好爷说,得得得,你打住,还“好输”,你还不如叫我“好惨”呢。我一个生意人,怕的就是“输”了,可不能提“输” !你就叫我名字,王建元。清荷说,我可不敢叫你的名字,看着你和我二叔年纪差不多呢。王建元说,看看,不让你提输,你又提,我要是输了,你也完了!清荷就笑了,说,再也不提了,再也不提了。庆有扒着门缝露出半颗脑袋问,谁来了?清荷说,王建元。庆有说,啊,是好爷呀,进来喝一杯。王建元说,不了,看看清荷的貉子,这就走了。庆有说,那就不让你了,我去接着喝,就又缩回头去进了屋子。王建元说,有一个散户建了一个养殖交流群,你在里面吗?清荷说,在里面。王建元说,我怎么没看到你?你的网名叫什么?清荷说,网名叫戛然而止的青春。王建元说,我说呢,没找到你,还以为还是清荷呢,清荷多好听,叫那么个网名,听了让人伤心。清荷笑了一下,不做声了。王建元又说,他们要搞见面交流会呢,你去不去?清荷说,我还是不去了,都不熟悉,见了面不知道说什么。王建元说,反正现在貉子一天就喂一次,去见见世面也好,咱们乡上女强人正经不少呢,去年还有一对大学生夫妻加入了进来,你要是去了,跟他们保准能有共同语言。清荷说,大学生干这个?王建元说,干这个怎么了,我好爷比他们哪个大学生差了?没念几天书,我照样抓大钱!你等着,明年好爷我雇两个大学生给我当饲养员,让你看看大学生也没啥了不起的!照样给咱土豪金打工!清荷笑得咯儿咯儿的,说,那我去!王建元说,那就这么说定了,我来接你!包接包送!
王建元走了,清荷送他到大门口,越野车掀起一浪尘土嗖的一下就没了踪影了,清荷从大门口转身回来的时候,看见亚奎从他家的胡同口里拐了出来,正仰着脸朝她这边张望着,清荷就立定在那里,也远远地望着他。这一望,就望出心中的好多回忆来,亚奎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她已经等了他三年多了。这三年多,所有的时光就是在那思念里一点儿一点儿流逝的,一开始他还给她写过几封信,后来干脆直接打手机,又后来他说长途电话费太贵了,教她开微信,可怎么都解不了思念之情,他做家教挣了点儿钱,索性买了电脑,那电脑一下子就成了她的魂魄,她的整个身心全都依附在那上面,专为等他和她说话,哪怕每天一句,一句就好!但如今这人就这么活生生地站在眼前了,却又不得相认了,那么遥远!那么遥远!
清萍吃过饭从屋子里溜了出来,看见清荷站在大门口,一径朝她走来。看见亚奎站在那边,就叫道,你站在那里傻望什么?过来,快过来啊!亚奎穿了一件加绒的红格子衬衫,也没着外衣,一边朝这边走一边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到了她俩面前,抱着肩膀,问清萍,你怎么回来了?清萍看着他,眼神腻腻的,凭啥只准你回来?亚奎看了一眼清荷,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又没说不让你回来!清萍说,你管我呢?我就要回来!清荷听他们这样说话心里有点儿难过,她说,有点儿冷,我进屋去了,你们聊着。清萍说,清荷你别走,你记得小时候我们三个总到那河边去,如今难得碰在一起了,再去走走!清荷说,我穿的少,亚奎也没穿外衣,还是不去了。清萍说,那你回去添件儿衣服,我和亚奎往前走,他也回去加件儿衣服,我们俩在河边等你。清荷还是想推说不去了,亚奎却说,就在这等儿吧,一起走!清荷只好回去穿衣服了,又快速地跑了出来,见他们俩还站在那里,清萍拨拉了一下亚奎的头发,说太长了,也不剪剪。亚奎看见她出来了,也没做声,双手抱着胳膊往前走去。路过他家的大门口,清荷说你不回去穿件衣服?亚奎说,算了,也不是很冷。
到了河边的时候,亚奎迎着微风站在那里,又晃着脑袋看了一圈儿,说,怎么没有芦苇垛了?小时候一垛一垛像小山似的,怎么突然就没了呢?清荷说,这两年雨水好,年年涨水,冬天雪又大,一直没采苇子!清萍说,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很小的时候我就盼着离开这里,我喜欢城市里的生活!亚奎你不喜欢吗?以后你也是城市里的人了!亚奎听清萍这样说,心里陡然难过起来,三个人当中,当初清荷学习是最好的,可清荷还留在这里。亚奎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说什么都怕清荷难过。
清荷也不说话,沿着河边往前走,踩着新鲜的苇芽儿,他们说的城市,离她很遥远。这里就是她的城市,弥漫了她整个童年的香气、青春的憧憬和迷惘!
清萍问亚奎就要毕业了,怎么打算的?亚奎说当然是早点儿参加工作给家里减轻点儿负担。清荷这时插进嘴来,说,大学生现在不都考研吗?说是好就业,你也去考考!清萍说,那就先工作,结了婚再考研!亚奎说,要是那样,哪还有精力!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还不光忙着过日子了。清荷说,你要是读研的话,就在学校接着读,我这貉子今年也要出手了,怎么也能挣一笔,我没花钱的地方,到时候拿给你。因为有清萍在旁边,清荷尽量说得小心翼翼的,但清萍还是十分不乐意,她说,等你的钱去读研黄花菜都凉了!亚奎听清萍这样说,突然想起小时候为了一个桃子清荷挨打的事情,那时候他一点儿也不喜欢清萍,就像清萍也厌恶他一样。那时候,亚奎家里穷,穿不上一件像样的衣服,冻得鼻青脸肿的,大鼻涕过了河就哧溜一下秃噜回去。清荷看着他那样就咯咯笑,可清萍那不屑于他的眼神却有模有样的,常常使他感到悲凉。
如今在省城里,清萍时常就去他的学校看他,话里话外总是让他知道,来省城也全都是为了他。若是他不在这里,就是天堂经理她也是不稀罕的!也该着他欠了人家的,欠了一回就怎么也还不清了,倒有点儿越陷越深的感觉。
还是清萍刚到省城不久的时候,亚奎他们同学开老乡会,本来是大伙儿轮着请吃饭,那天轮到他了,酒喝得冒了高,本来就东省西省才省下的一顿饭钱,偏偏不够了,亚奎庆幸自己记住了清萍留给他的手机号,他趁着取酒的机会给清萍打了求救电话。清萍来了,到吧台结了账就悄无声息地走了,是在照顾他的自尊心,可他的自尊心就在那一刻深深地受到了伤害,那一天他喝醉了,是他有生以来最清醒的一次醉酒。外面的花花绿绿是那么让他受煎熬!
打那以后,清萍得空闲就往亚奎那里跑,跑来不容分说,把脏衣服、被子、枕巾统统洗了,旅游鞋也刷了,袜子都不放过。看他什么东西破旧了,自己发了工资还帮他添置一些。弄得全班同学都说亚奎有一个做大堂经理的女朋友。“女朋友”,明晃晃的一个招牌,就算亚奎想不承认,清萍那样一来,他有一百张嘴也辩不清了。清萍还算有数,在家里这边还没公开他们的关系,要是被秀春知道了那还了得?亚奎一向是惧怕秀春的,好像是受了清荷的影响吧,一提起秀春总会把她和鞋底子联想在一起,一那样想,眼前就出现一个画面,秀春狠叨叨的一张脸,骂起人来吐沫翻飞。虽然自从亚奎上了大学,秀春再见他时总是笑眉笑眼的,可亚奎看了那笑却怎么看怎么难过,仿佛那笑是贴到脸上去的,再笑得狠一些都能掉到地上。
清萍的手上戴了一枚戒指,从河边往回走的一路上,清萍的另一只手一直在那手指上摆弄着,那戒指在手指上转了一圈又一圈,亚奎看着心里就不舒坦,好像她是故意的,就是要转给清荷看的。清荷也当真就看见了,眼神低低地望着她的手指,看着那枚镶着一颗小水晶的铂金戒指。他送过清荷一只,那是芦苇编制的。很多年前就在那个河边随手编了一个,半开玩笑的套在清荷的手指上,对她说,Be my lover!是不好意思说出汉语来,就用英文遮自己的脸,却没想到说的那么干脆,那么浪漫。清荷低着头,也是像清萍现在那样转动着手上的戒指,她说,我要你拿真的来和我换,那时我才答应你!然而,真的,却戴在了清萍的手指上。
其实那不应该算是他买的,可是她偏要说是他送给她的,他一时也辩不清了。是上一个月的事,是个周末,清萍给他打电话问他上午做家教还是下午做家教,他说上午和下午都有课,只不过下午三点就结束了。清萍说,那正好,正好她下午有个休假,又刚刚开了工资,想去欧亚卖场随便买点儿东西,问他能不能陪她去。他想了想就答应了。到了那里,清萍塞给他三千块钱,说是一会儿买了东西让他帮着去付款,她买了这枚戒指,很精巧,花了三千两百块,他吓了一跳,不敢去付钱,她说,你就说好不好看?他说好看。然后清萍就催着她去付钱,他怕金店的店员看他的笑话,慌里慌张就把账给结了。结过了,她把戒指套在手指上,向上一扬说,算你送我的!从此就辩不清了,是你结的款不?是!有你的二百块在里面不?他说有。就更辩不清了。
他大哥明天就要结婚了,他生怕这滑稽的笑话传到他爹的耳朵里。他大哥要结婚,十六七万元的彩礼,是他爹倾家荡产抵上去的。从明天以后,他爹饭碗里的米都要一粒一粒节省着吃。而他,竟然还有这样的情致,花去三千两百块给一个旁不相干的人买那么一个吃不得喝不得的铁圈圈套在手指头上,他解释不清的,这话儿要是一旦传出去,他实在是解释不清。即便成了大学生,他爹也照样会毒打他的,怎么能不毒打他呢?如果那话儿真的传出去了,就是他自己也觉得确实是该遭毒打的。
还是值得庆幸的,他大哥结婚那天,清萍去了,然而那戒指的事儿,有好多人问起她,她到了儿也只是笑一笑就应付过去了,她怎么也不肯说,神神秘秘地任那些女人猜。还是值得庆幸的,她们谁也没有猜到他的头上来,倒是说,清萍在酒店里做大堂经理,一定是遇到大款了,那就傍上一个!她们瞎起哄,在他家的院子里哄堂大笑起来。他大哥结婚,院子里因多了清萍,倒显得热热闹闹的!
五
清荷没去吃亚奎大哥的喜酒,那天她本来也是犹疑不决的,前一天晚上三个人从河边回来,亚奎把她们两个送到了大门口,回去了,她感觉自己有很多话要和亚奎说,可又总觉得他们之间隔了什么,亚奎转身离去的时候,竟然一点儿留恋也没有,倒像是生怕她叫住他说上几句什么,她隐隐地感觉他们之间结束了,那些躲在芦苇垛里说过的话是得不到见证的,都成了过去。那么倒霉,连那枚戒指,芦苇编制的戒指也被她一脚踩了个细碎,她昨晚从河边回来,看到它紧紧地贴在地上,细细碎碎的,像是一个生命死了,连尸骨都不全了。她捡起它,全都成了碎片,让人伤心难过,是在暗暗点醒她,他们的时代再也不会来!再也不会来!
她和王建元去参加了群交流见面会,一大早王建元就开车来接走了她,秀春眼见着她走的。她对着镜子梳头发,王建元在外面等,秀春本来正在外头喂猪,却拎着个猪食舀子跑进来,站在她的背后看她镜子里的脸,说,王建元他儿子前几年出车祸死了,他还不算老,本来可以再生一个,可他老婆偏偏得了子宫肌瘤,做了手术,竟然再也不能生了。他现在条件好,分给他老婆一大半家产就离了婚了,心里头八成是想着再娶个大闺女,生个孩子,他有的是钱,也养得起。清荷正在调辫子,听她这样说,又把头发松松垮垮地披下来,胡乱地往脑后一捋,气恼恼地出了门。秀春从后面跟上来说,大姑娘家家的和个四十好几的男人出出进进的像什么话?养貉子养貉子,别把心养野了!要是急着嫁人就早点儿说,这算什么,车接车送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和庆有图稀人家有钱,把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往个半大老头子怀里推!二十好几的姑娘了,这算什么?这算什么?严家老太隔着窗喝住了秀春,你还跟在她后面干什么?你在自家的屋子里提醒提醒她也就算了,你站在院子里嚷嚷着,怕谁听不到吗?那王建元本来兴许还没那心思,你这一嚷嚷让他听去了,也许当真就生出心思来了呢!你也是个做长辈的,本来说那些话也是对她好的,可好好的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那么难听呢?秀春把猪食舀子丢进猪食桶里,脸子上一万个不乐意,看着清荷上了王建元的车走了,她回到窗口对老太太说,你那孙女,要是真能嫁了王建元也倒好了,起码衣食无忧了。她那么年轻,比他那死去的儿子也大不了两岁,他还不当闺女一样地疼她!老太太见她越说越离谱了,就满心不乐意地回了秀春一句,清荷要是愿意,我倒不反对,她这二十几年活得样样不如意,王建元要是称她的心,我就遂了她的愿。男人大几岁又算什么,何况他又那么有钱,保养得好,看起来也顶多三十出头。秀春没趣地走了。去了薛家。
六
薛家满院子的人,清萍清清丽丽地站在那人群里,眼神黏黏腻腻地落在远方,秀春顺着她那眼神看过去,看到了亚奎站在院墙边上打电话,听了一会儿,笑一下,再听一会儿,又笑了,笑过了说上几句,点着头,好像电话那头能看到他一样,他出落得越来越风度翩翩了!她看出清萍是喜欢他的,早知道他会变成今天的样子,他小的时候她是不该那样说他的,她说没人要的女人才会嫁到薛家去当媳妇呢!她的清萍怎么会是没人要的呢?清萍是配得上他的,她今后的人生,就该是他那样的人陪在她身边的。他和她相互挽着,在城市里过那种住高楼洋房开高级轿车的日子,秀春现在相信亚奎将来一定有那个能力让清萍过上那样的日子,因为清萍天生就是要过那样的日子的。
人是多么奇怪,原本有好些好些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一直都在你身边存在着,你从来不觉得他的存在,他似有若无,可一旦心里动了某种念头,他就再也无法从心头消散了。秀春越发注意薛家了,从薛家老大春天结婚到冬天生孩子,秀春就像婆婆似的照顾着薛家的媳妇。她照顾起人家来总是振振有词的,说是前后院的邻居,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又说两个孩子都在长春,还不多亏了亚奎那么护着清萍。她这样说,是想让薛家的人和村子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亚奎对清萍是爱护着的,他心里装着她。那一年薛家老爹的光景过得不怎么好,大儿子刚刚娶了媳妇,又赶上小儿子的大学毕业季,处处需要他掏钱,可他哪里还拿得出一分钱?恰巧遇到秀春这样帮衬他,他心里感激着。他也从秀春的嘴里知道清萍挣来的工资都暗地里贴补给了亚奎,就在电话里旁敲侧击地提醒他,秀春那样小气的人,能放任清萍把钱大把大把地花在你身上,你至少要知道人家把钱花给你身上的后果。那亚奎许是被钱逼急了,家里断了他的开销,他打工又拿不到几个钱,偏赶上毕业应酬又那么多,他许是被逼得急了,就厌烦了似的甩给他爹一句,能怎么着?大不了娶了她!她不就是想让我娶了她吗!
自打他大哥结婚时他回来那一趟以后,他就再也没回来过,清荷知道他是躲着她呢。他QQ头像一直那么黑着,好像这世界上根本就没这个人了。后来还是她实在忍不住思念,从他的空间加了他的同学,人家却说,他在线的,你加他的QQ号试试。人家告诉了她一个QQ号,她加了,是另一个亚奎,她从此不再熟识的。那一刻她的心瞬时就冷到了极点,他原本就是个双面人,他把他的背面给她了,无论她离他有多近,她都看不清他的脸,看不透他的心,她在他的边缘,只能默默遥望,无论遥望多久,只会越来越远。可他一直在她的空间里黑着,舍不得删掉,每天看上无数次,看过一次疼一次。他毕了业,放弃了继续读研,
冬天的时候亚奎从省城里回来了,到市里报考公务员,清萍也回来了。两个人成双成对地出出入入,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他要娶清萍了。他们谁都不记得亚奎小的时候说过的,长大了,娶清荷!他自己也不记得那句Be my lover了,那些都不作数了!
都不作数了!
七
亚奎和清萍摆了一个订婚宴。那订婚宴在村子里已经很多年没人摆了,可秀春不干,说是不想早结婚就先办个订婚仪式。亚奎不乐意,说现在农村早不时兴订婚礼了,平白糟践了那些钱。严老太太和清荷说,秀春是不会这么轻易就遂了亚奎的,到手的鸭子怎么也不能再让他飞了,她是宁愿自己掏钱也要在人前人后摆摆脸的。她奶奶到底是经了世事的人,一眼就看穿了好多的是非,秀春真的就张罗着摆了酒席,又为照顾薛家的面子,顶着薛家的名义。亚奎和清萍订婚那天,天上的云层压得很低很低,下了纷纷扬扬的雪,落在院子里枯树上、柴垛上、屋顶上、栅栏上,盖住了村子里的每一寸土地,看起来是那么的凄迷。那亚奎也不知怎么了,讪讪着一张脸,红红的一双眼,倒好像哭过了,清荷看着他竟隐隐地心疼。她看着清萍挽着亚奎的手臂,突然觉得这世界空旷无边,给了她无垠的恐惧,她失魂落魄地想逃!逃得越远越好!可逃亡的路是那么漫长,那么煎熬!她仿佛就要撑不下去了。再以后,她对亚奎连点儿念想也不能有了,那点儿念想被清萍给撕扯没了,她的希望没了!她整个人失去了魂魄了……
夜里,她奶奶也不知怎么了,躺在炕上睡着觉,突然就一阵一阵的地说起梦话来。她说,清荷,你也该嫁人了!屋子里关着灯,黑暗拥挤着黑暗。窗外传来风的萧萧声,雪的簌簌声,狗的聒噪声,都混在她奶奶的梦话里了。那夜,所有的一切都被奶奶的梦话隔绝在这世界之外了。清荷听着那梦话一遍一遍地重复,她突然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守着黑黢黢的夜晚,蜷在奶奶的被窝里,双手紧紧地搂着她的脖子,奶奶就轻轻地拍着她,一下挨着一下,让她没了恐惧,也不知道忧伤,不知不觉就进入到那梦里去了。如今,长大了,好像再也没有甜美的梦可以做了,什么梦都会醒,就连童年的天真和纯净也在这青春驿动的季节破碎得面目全非。亚奎曾是她在这世界上最美的梦,可这一刻,他竟然在她的美梦里狰狞了,他的狰狞让她触目惊心,不认得他了,甚至也辨不出他原来的样子。童年的一切都模糊了,记忆仿佛都是虚假的,让她觉着自己从童年守护到青春的那场爱情,只不过是一场以温情开场又在悲剧中结束的梦魇。
不恨,也不爱。心如止水了,好像一瞬间老去了。清荷掀开奶奶的被角,钻了进去,奶奶的身子热乎乎的,从外往里地温暖着她。清荷伸出手臂像小时候那样抱着严老太太的脖颈,靠上前去,靠上去,听着她夹着梦话的喘息,她想,再以后,除了奶奶,她只爱她的貉子了,爱她的貉子,挣好多好多钱!好多好多钱……她要搬出秀春的院子,和奶奶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买一所有着大院子的大房子,养更多的貉子,再也不要看见亚奎,再也不要看见清萍,再也不要回忆起有他的过去……可是,黑暗里,她竟然还是流下泪水来,她真希望有一天能攥着一大把钞票,站在亚奎的面前,大声地对他说,不就是钱吗?不就是他妈的钱吗?你花了清萍儿多少钱?我加倍替你偿还……她那么痛,那么痛,痛得那么深,那么彻骨……
八
那又怎么样呢?只能锁在心里了。
她想求静的,他却偏偏又找上她。
她躲了他那么久,到底还是没有绕开他。
秀春和清萍去赶集了,亚奎看见清荷在院子里清理貉子舍,就拐了进来,清荷见了他说了一句清萍不在,转身要走。亚奎一把拉住了她,他说,清荷,我快要憋死了!这样的日子我快要憋死了!清荷挣脱了亚奎,她说,别这样,这样不好!亚奎冲着她吼,哪样好?清荷你告诉我哪样好?我他妈的就觉得这样好?亚奎紧紧地抱住了她,抱得她紧紧的!她被他木讷地裹着,木讷地说,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亚奎说,那就什么也不说,就这样抱着你,再抱你一次!可他还是说了,他说,清荷,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要的!清荷说,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亚奎松开她,看着她,说,你懂!清荷说,我不懂!越来越不懂!我已经看不清你了!亚奎暴躁起来,你懂!只有你懂我!清荷问他,就算我懂,那又能怎么样?亚奎叫了一声,清荷……清荷转过身,说,你回去吧,回去吧!
亚奎还站在那里,你还不知道吧,我公务员考试出了岔子,说到底还不是差在钱上,我笔试明明得了第一,面试的时候挑三拣四就弄出毛病来了,还不是因为我没钱,被人家给拱了!清荷背对着他,说,怎么会这样?他说,是啊,我也没想到会这样!他突然上前一步,抓住清荷的胳膊,他说,不管我选择怎样的路,你都不要恨我!清荷的眼泪滑下来了,她说,不恨你……
亚奎走了,清荷还站在那里说,不恨你……
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到底恨不恨他。
隔了一天,薛家的大嫂给清荷送鱼来,站在院子里和清荷说着话,说着说着就哭了,清荷问她怎么了?她说,你是不知道,我们家的日子现在是没法过了,这亚奎大学毕业了,原指着他能给家里减轻点儿负担呢,哪成想如今他又闹了这么一出,公务员考试出了岔子,想在乡里谋个教师当当,也是要花钱的,哪有?我结婚时过的那点儿彩礼,也是我公公东挪西借凑来的,我那时一结婚,就又都还了回去,家里哪还有钱?他又不是不知道,他大哥腿脚不好,我这也是个病身子,干不了什么活儿,要不当初也不会嫁到他薛家来。你说他这么一闹,是闹谁呢?那老的自己都顾不上自己了,还顾得上他?还不是闹我和他大哥?清荷问她,清萍那头没个打算吗?薛家大嫂抹着鼻涕说,清萍倒是想说服你二婶掏出几个钱来的,可是你二婶那么精明的人哪肯?她是有条件的,要他们先结了婚,这样亚奎又不肯了,要他个理由,他又说不出,这也就不能怪你二婶袖手旁观了,就算他亚奎是个潜力股,人家也不能放着卧兔不抓去抓跑兔!
那天薛家大嫂走了以后,清荷干着活儿又想起很多事来,说过很多次不想了,到底还是又想起来了。想起亚奎小时候看书那痴迷的样子;想起亚奎大冬天的跑出去和她玩过家家;亚奎说过喜欢她,拉着她一起疯跑在霍林河边上;那时候,他们站在这岸瞭望着那岸,水面上漾着粼粼的光波,灿灿的扎着眼睛,连着那岸袅袅的炊烟,炊烟飞到天边的红霞里,染上了绯红的颜色,那么好看,那么诱人!
人的一生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就那么几次,错过了就再也不会来。夜里,清荷又睡不着,不知怎么的就惦念起亚奎来了,她算了一下,把她的貉子皮卖了,也许正好可以帮亚奎一把,王建元说过,她的貉子皮当属上等,价钱上一定差不了。
可谁知道呢?好像就该着她倒霉似的,过几天王建元来帮着她打貉子皮的时候却说,今年的貉子皮不是价格低,是到现在还没有客商,也不知怎么了。王建元说,他祖宗的,竟然到现在还没有客商?下面的散户都是从我这儿赊的种貉,这要是他们的皮子卖不出去,我也跟着吃瓜落!清荷说,你怕啥?你坐吃三年金山不倒,我们怎么比,欠着你的不说,自己还赔了个底儿掉!王建元说,你也不用怕,你赊我那几十只貉子我压根也没打算让你还。清荷明白王建元的意思,她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男人那点儿心思她又怎能看不穿?王建元本来是个不安生的人,见了她倒总是规规矩矩的了,男人越是喜欢一个女人在她面前就越是规规矩矩的,生怕她看轻了他,生怕她以为他不尊重她。清荷对王建元还没那个意思,她不喜欢他那一身的铜臭味儿。这样一想又觉得悲凉,亚奎不也是一样吗?可她还是不喜欢王建元,没有理由的不喜欢。清荷说,哪能不还?砸锅卖铁也要还!王建元说,咱俩认识也两三年了,我的心思你就那么不明白?两三年对你来说不长,可我不行了,我都四十多岁的人了,掰着指头往五十数了,我等不起!清荷说,我哪有让你等?王建元看她生拗的样子,叹着气说,是我偏偏中了你的邪,非等不可的!那以后清荷再没见过王建元。
清荷是天天盼着王建元能过来的,倒不是因为惦记他的人,是她越发着急她的皮子能不能快点儿出手,可是左等右等王建元就是不来了。清荷等不下去了,她去了乡里,到了乡里直接去见王建元。王建元告诉她皮子有价了,来了客商,价低,很挑剔,分了三个等。又说,他妈的,几等几等还不是由着他们的一张嘴!清荷说,现在卖了还不赔个底朝天?王建元说,你听我的,压着,我那儿有库房,明年再卖!清荷说,我都这样了,哪还压得起!这样说,恍然就觉得天旋地转起来,世事是多么的变化无常啊,计划的脚步永远追不上变化的步伐。
希望,闭着眼睛的时候它还是美好的,眼睛一睁,它就没了,灭了,烟消云散了。就跟活蹦乱跳的兔子似的,在你眼前蹦跶蹦跶的招人喜欢,眨眼的工夫就蹦没了,不但不属于你了,还在老远的地方扮着鬼脸,嬉皮怪笑地告诉你,拜拜喽,拜拜喽!你能怎么着?能怎么着啊?
清荷问王建元,我能不能见见大客商,要说了算的!王建元说,你见他干什么?那人不适合你见!她说她偏要见!他生气,和她甩了脸子,跳起脚来,要不你全都卖给我!你全都卖给我,我给你一等一的价钱!看他这样她就哭了,她说你不懂的!你不懂的!他彻底发了脾气,摔了一个茶杯说,你就非拒我千里之外?你出去访听访听,我好爷对谁这么低三下四过?有他妈啥是我好爷不懂的?你不就是心里还装着一个男人吗?这不是贱吗?人家都和别人订婚了,你还当宝似的搁心里头供着!这不就是贱吗!说过他又觉得不好了,“好爷”这俩字是他自己声明过,从此不再提的。他想这句话说的不好了,他们是没希望了,清荷是厌恶他了,就因“好爷”那两个字。清荷说,对,我是贱!要不是因为贱,也不会又觍着脸来找你,我就是为了他,就是为了他!她抹着眼泪说,他公务员没考上,想在乡里谋个教师当当,上头又没人,光指着花钱往上拱,钱又没有那么些!王建元气得在地上直画圈,他都和清萍订婚了,还犯得着你操心?清荷说,我就想帮帮他,我们一起长大,他上个大学不容易!他说,上了大学又咋了,上了大学还不照样是熊包一个!清荷不吭声了,淌着眼泪,哀求似的看着他。
九
又是三五天。王建元突然给清荷打电话,告诉清荷他要宴请大客商程靖凯,他说,你想见他,你就来。
王建元请程靖凯吃饭,是因为程靖凯觉得他基本占据了这边的皮张收购市场,想在这边找个代理,自己就不再常常过来了。当初程靖凯能在这边站住脚,全凭他王建元和另一个乡的隋顺义,他和隋顺义虽说能力不相上下,但程靖凯的心里头始终偏重隋顺义,王建元知道这些年他吃亏就吃在对程靖凯的个人关心上总是比人家隋顺义差那么一步,这次为了这个代理,他不能不特别关心他一下了。他给清荷打电话,原本是不想让她来的,他是想和她说,不要你出面,见了程靖凯你的事全由我来想辙,可电话里听到清荷那空茫的声音,离他有天上地上那般遥远,他竟中了邪似的,说了,你想见他,你就来。
清荷见到了那“说了算的”。程靖凯戴了一副眼镜,穿了一身银灰色笔挺的西装,斯斯文文的。她到时,王建元和程靖凯正坐在包间里等她。见她来了,王建元就拉过她给她介绍说,这是程老板,咱们东北的貉狐交易市场整个由他掌控。程靖凯缓缓地站了起来,手里的酒杯不觉地倾斜了,泼泼洒洒地淌下来,落进了桌子上盛着红烧鱼的盘子里。王建元见了,他笑着,心里一疼,把清荷安置在程靖凯的身旁,坐下了。
酒喝到一半,王建元半醉着跑去上厕所,屋子里只剩下清荷和程靖凯两个人,他们无话可说,就那么静默地坐着。她歪着头,看着窗外,天上挂着阴霾,又阴又冷,屋子里的空调开得不好,她似乎冷了,裹了一件堆领羊毛衫,领子往上一提遮住了半张脸,程靖凯捧起一碗茶向前欠了欠身子用一根指头把那领子往下压了压,露出她的整张脸来,对着那张脸,他喝着茶,微笑着。清荷左手抓着右手,垂着头,她说,你什么时候去看看我的皮子?他把茶碗放下,手搭在椅子两侧的扶手上,手指头轻轻地敲着,微微侧着头,看着她,过了一会儿他说,王建元都说了,你的皮子好,都是一等一的好东西。清荷猛地抬起脑袋,好东西你咋还不收?他嘴角轻轻一挑,又端起茶碗来,慢悠悠地喝上一口,用舌头把喝到嘴里的一片茶叶推到唇边,吐掉,方说,好东西太多了我也要不起,现在生意难做。清荷咬着嘴唇说,我急着用钱。程靖凯从椅子上站起来,裤子有些堆上去了,他抖了抖腿让裤子垂下来说,钱这玩意儿现在谁都不多!他晃了晃腕子看了看时间说,这个王建元怎么去了这么久?又说,今儿,不太有心情说生意的事儿,要不明天你来和我单独谈?如果我们谈得好,一等,兴许我就要了!他笑着,意味深长的。
那天傍晚,回到家的时候,她坐在电脑旁,漫无目的地点着,突然听到清萍在隔壁里哭,严老太太从秀春那屋回来时叹着气说,最初她就不该,这会儿倒又想起哭来了!亏得我老了,看穿了又能说什么?现在人家宣布退婚了,花她的钱一分不少还回来了!她早就该看明白的,他能攀着你往上爬,就也能甩了你攀上别人!这回好了,又攀了个更高的枝儿,听说是市里一个领导的女儿,到了儿把那公务员考试的事又弄成了……她的手一抖,碰错了鼠标,亚奎的QQ号不见了,听着隔壁的哭声,她蓦然抬起头看着窗外,窗外的阴霾都压到她的心头上来了,飘起了雪,落在地上厚厚的一层,把院子里那棵桃树压折了枝,她自己也被冻得再也化不开了,再也化不开了!
过了一夜,那雪竟然铁了心再也不停下来了似的下着,她起床后,早饭也没吃,对着镜子梳妆,画眉,涂了胭脂、口红,高高地绾着头发,她一出门,那素洁的雪更是衬出她艳丽的样子,她像婀娜的花朵,在那冰天雪地里绽放,再任由那冰雪肆意地枯萎她……
她敲开了他的房门,进去了,程靖凯在等她。
站在他面前,她被冰雪冻僵的脸这一刻微微发起热来,红晕开了,渐渐滚烫着,把腔子里那些无处撒怨的怒火都烧到脸上来了,她说,我那皮子值多少钱?程靖凯叼着香烟,脖子梗着,看着她,他说,一等一的东西,价钱当然差不了!她说,把钱先给我!程靖凯啐了烟头捻在脚底下丢过一个皮包说,都在这里,你看值多少完事了你自己拿!
清荷笑了一下,她背对着程靖凯解扣子,一枚一枚地解,解得泪水淹没了脸颊,把那胭脂洇花了一片,找不出她本来的样子了。他从后面抱住她,把她摁在了床上,抵上去。锥心的疼痛让她的牙齿刺进了肉里,一股鲜血顺着她嘴角缓缓地淌下来,淌下来,在那一床褥子上洇出一朵刺眼的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