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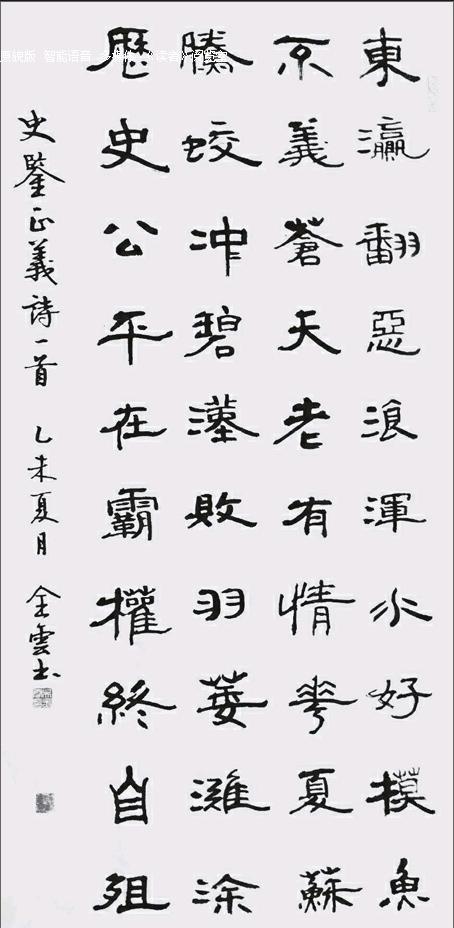
梦见蛇
暴雨下了三天,我三天梦见了蛇。白蛇、青蛇、花蛇。它们潮湿,滑润,没有气味,带着与生俱来的冰凉,相互缠绕,游离,然后悄然远去。
一个临近中年的人为什么有那么的梦?梦是不是灵魂在黑暗里游走,寻找可能的人和事?
大概在二十岁的时候,我常常梦见蛇,梦见蛇变成女人,有村里的新媳妇,有大学校园里蓬勃发育的女同学,也有画册上光洁的明星偶像。蛇暗喻了女人,也昭示了朦胧青春的身体冲动。而今,四十岁的我为什么还在梦见蛇?
周公解梦中,关于梦见蛇有多个说法,大多的注解是梦见蛇多数是吉兆,但也有不好的状况。比如梦见一对蛇:很快会分家。女人梦见蛇:自己和孩子都会病倒。梦见蛇钻进洞里:家里会被偷窃或被劫。梦见蛇咬自己妻子:是不祥之兆,会遇到忧愁不幸。梦见蛇捕捉老鼠或青蛙,会有不幸的消息。
我梦见蛇从来没有遇见过好运。我不祈求有什么好运。正如我不窃喜发意外之财,艳遇妙龄少女。我期盼的是平淡和安静。这种感觉在四十岁的时候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迫切。我日复一日的做梦,大概就是寻求现实生活之外的释放。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是压抑的懦弱的。在生活的游戏规则中,没有一个人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所以只有梦是无限延伸的,梦中可以飞翔,可以变异成羽毛成花草,可以抚摸明星,可以追杀仇人,也可以看见自己的强悍和灵巧。而我的梦都是些什么梦?我在梦中说梦话,拖着自己的肉体在夜空里游弋,我有解脱也有惊恐。但为什么总是梦见蛇?
这样的梦我给妻子说过,连续几个早晨,太阳刚露头,我就在洗漱间给妻子反复地描述我的梦,我描述的很累,妻子听了则不以为然,妻子说,太阳出来之后,把梦说出来就没啥事了,你这是胡思乱想。后来的情况是,梦越来越多,有蛇也有游走的狐狸和晃头晃脑的田鼠,梦套着梦,我在梦里希望太阳出来,长梦结束……我讨厌沉睡不起的肉体,挂着风筝一样的梦在飘摇着上升……
太阳出来了又消失了,梦醒了,但身体依然是困乏的,像走了一条漫长的夜路。
暴雨变成了小雨,雨淅沥沥地下着,我在清晨的电视新闻里看到汛灾,在中午的时候听到大河溃坝的消息。这些确切的消息对于我而言是职业般的恍惚。我恍惚洪水肆虐的场景我曾在梦里梦见过?还有那些木然的表情和撕心裂肺般的哭喊?我不清楚在平静的生活里,谁给我安放了这些漫长而又交织不休的梦?
路上有积水和梧桐树叶,雨下了七天,潮湿的感觉使得人心里发痒,似乎要长出阴晦的苔藓。阳光出来了,六月的阳光很直接地照到了大地上,冰凉的植物们抖擞着绿色,将五颜六色的花朵托举在路边的花坛中。一度幽暗的城市在艳丽的阳光下完整地裸露了出来,包括远处的山和近处的土塬。
雨后的草地是最美的,像松软的肌肤,雨后的草地上有了许多的落叶,六月的阳光似乎也一下子穿过肌肤达到了内心,阴雨散去,睡梦褪去,内心被阳光召唤,一切澄静了起来,生活所有的意义都是美丽的。这样的行走有些惬意。
但是一位少女哭了,她长得并不漂亮,脸上还有明显的几块雀斑,她在美好的天空下抹着眼泪迎面走过,哭得稀里哗啦,整个脸都涨红了起来,她因为什么在哭?越哭越激动?
天气这么好,她却一路哭着。路上的很多行人只是扭了扭头,没人围观也没有规劝。只有我扭着头回看着少女远处的身影,猜想着她痛哭的种种可能。但愿她遭遇的只是一场梦,梦醒了,一切都会过去。
去铜川的香山寺,看到一个香客的留言: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东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样的留言,让人心生触动。但是生活中谁无闲事?即使无闲事,也有正经事挂心头的。有事总是劳累的,也是劳心的。
我是那么羡慕不做梦的人,我羡慕他们闲散地游走和踏实的睡眠,羡慕他们的日常生活表里如一。
她走了
三台闹钟摆动着,在墙上,在书柜里,在桌子上,滴答的声音长短不一,间隔不一,像流水又像心跳。我坐在屋子里,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是那么虚无又是那么急促。
她走了,知道吗?她走了。那个散布消息的人闪动着密细的牙齿,眼角跳动着细微的皱纹,她有种事不关己的眼神和表情,她像兔子一说完后就迅速地消失了。在六月炎热的天气,那个散布消息的人嘴里充满着韭菜的气味,也透露出一丝的冰凉。
她走了,其实就是她死了。黑夜来临,嘈杂的世界里,我离开办公室,乘坐一辆公交车由南向北,黑夜覆盖着这座城市,也覆盖着我疲倦的神情。万劫不复的黑夜,覆盖着所有的生灵和大地。黑夜里,空气开始变得湿润,充满着不为人察觉的惊恐和喘息。
我眼前一直浮现着她那像孔雀开屏般的彩色裙子,想起她亮晶晶的眼睛里风情万态,想起她在镜子前一遍一遍描眉和打粉。我也会想起她小巧的若隐若现的乳房,在夏天,她挺拔的乳房吸引着许多男人的目光。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我听见她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
她总是穿着裙子,酷寒的冬天里她也喜欢穿着短摆的裙子和长筒袜,衬托着她淡然的笑容。她的发型简单,不是束起来就是用发卡盘起来。在我的印象中,她的头发总是那么顺溜地一丝丝地飘动着,衣角平整地摇摆着。作为一名年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她似乎不是那么热衷社交和应酬。她总是沉默寡言地待在演播室的一个化妆套间里,在化妆间的镜子前一遍一遍描眉:或许是先描眼皮,或许是先描睫毛,也有可能先描嘴唇。总之,在日复一日的时间里,她职业地化妆是漫长的,她在化妆的过程中目睹自己的容颜带上职业的面具,然后默记一些职业的台词。很多时候,她在化妆间翻阅报纸和杂志,她喜欢看的是电影画刊和文学期刊,而不去楼上的办公室。我也记得我去过化妆间几次,我看见她在抱着一本小说看。她的头发刚刚盘起,化妆盒整齐地放在身边。她有一个特别大的挎包,总是鼓鼓囊囊,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她主持的是一档晚间情感节目,属于访谈节目。两张苹果绿的沙发相对摆放着,数十盏聚光灯下,她对坐着那些需要倾诉的人坐下,倾听、微笑、惊讶、询问。倾诉者总是义愤填庸,带着伤感和烦恼。她认真地听着,很多时候,她只是个倾听者。在她的旁边,有心理医生和专家团队。关于化解这些矛盾和痛苦的药方基本都是大家共同讨论制定的,说透了,这些药方是为节目制作服务的,对于倾诉者有多少帮助,她或许是清楚的。有一次节目结束的空挡,她表演了小提琴,悠扬凄婉的琴声中,有人流出了笑容,有人流出了眼泪,那天我才知道她是学音乐的。我在她的博客里也曾读到过她写得一篇文章,怀念外婆家的枣树,写得情真意切,很是细腻。endprint
关于她的事情我还有一个细节记得清楚。就是在她的化妆桌前常常有一大簇的紫色玫瑰,好像从不衰败一样。一大簇的紫色玫瑰让许多暗恋者心生惭愧,自觉放弃了无所行动的追求。后来我知道有很多人追求过她。但她喜欢的是大学一位男同学,男同学后来出国了,她似乎一直在等,但她的那位男同学回来后留在上海。
对于她我所知的就是这些。她的工作和生活似乎一直很简单,她的年龄多少?她是否有男朋友?我一无所知。后来,就传出她得了一种可怕的病。我和同事们去她的住所看望她。去了后我们知道她的病其实就是常见的乳腺癌。那时间的她戴着一顶墨绿色的贝雷帽,面容有些憔悴,但依然很是干净。她知道我们要来,准备了大樱桃、水蜜桃和甜梨。她有些局促不安,不知道说什么话题好。我们闲言碎语地说了一些话后就没话说了。我们都明显地发现,她的一边胸部明显的塌陷了下去,同事低声说她做了乳房切割手术。她没成家没有小孩,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同事们嘀咕着,谁也猜不透她怎么回得了这样的病。
她的房间里有大片的粉红色,床单、窗帘、墙壁、吊顶灯。她的房间里有着许多的英文书籍和所有女孩子们喜欢的熊娃娃。一架钢琴好长时间已经没用了,她的房间里水仙花也正在枯萎。书房里挂了她大学的照片,那时候的她比较瘦小,留着短发,在一群人中,她的两只眼睛特别有神。
在她不大的房间里,我发现她画了不少的油画,小小的书房里堆满了小玩具。交谈中,她还是忍不住对女同事说她做了无数次的检查,骨刺了6次。她的身上有无数的针眼。她说着止不住低声哭了起来。她摘掉了帽子,她的长发已经不存在,稀疏的发丝像哀伤的老妇。她似乎一直是虚弱的。
她时好时坏的消息已经离我们远去,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了。我们忘了她,因为她主持的那个节目因为收视率不高的原因也被叫停了。
就在那段时间,她的病情恶化了,胸腔的积水越来越多。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她的另外一些事情,有人说她和化妆师曾经有过一段不长不短的感情纠葛。那个化妆师其实并不好看,也没什么特点。她和造型师好上的消息是造型师的老婆最先发现的,造型师常常不回家,以工作的理由不回家,其实是和她在一起的。但造型师没有离婚,他有一个6岁的孩子。他爱着自己的孩子也喜欢她。但他给不了她太多的东西。她大概是清楚的,她也没和化妆师吵闹,后来就平静地分手了。
现在,她死了,关于她的流言停止了,剩下的似乎都是惋惜。我想起她在幽深的化妆间里读书,想起她办公桌前一直没有凋谢的紫色玫瑰。
怀念她,其实是我一直在忘却她。每一个逝去的人总会被生者偶尔想起,她是触动了我的情绪还是情怀?我无法言说,我只觉得一个美好少女的感觉在我的印象中渐走渐远,或者说一个幻想时代结束。
小李搬走了
先是一台挖掘机,然后是几台铲车和卡车尘土飞扬地开进开出。在六月炎热的一天,响彻着巨大声音的大型机械塞满了二府庄狭窄的巷子。像要宣战一样。机器巨大的手臂刺向了房屋,菜市场大棚,小吃店,快意地破获弥漫着尘土,尘土几乎弥漫了整条街道。
有很多人看戏般地围观,也有很多人诅咒着。阿丽穿着一年四季不离身的睡衣睡裤,嗑着瓜子唾沫飞溅,鄙夷地看着那些挖掘机,并大声地喊着:我就不搬,看谁敢把我家拆了。阿丽的喊叫是孤单的,也是虚张声势的。因为村里很多人都搬走了。
拆迁的事情其实很早就流传开了,说是临近马路的老建筑都要拆。城市在旧貌换新颜,高层楼房正在成为新城市的标志建筑。临近市区主干道的二府庄自然在里面。但二府庄人多,村子人多势众,要求也很高。拆迁的事情一度搁置了下来。没想到,前些日子,巷子里张贴了许多政府告示,说马上就要拆,而且确定在了6月份。巷子里也悬挂了很多黄色条幅,说是支持政府拆迁暖人心,建设美好家园人人有责。阿丽那天就站在白纸黑字的告示前,大声地喊,没有谈好条件,就要拆,简直是胡闹!
阿丽是二府庄门面房最多的一户人家,她家的楼下,有米线店、小商店还有一家粮油店等等。楼上住的也就是这些生意人。有人给阿丽算过帐,说阿丽家一年有二十万元的收入。阿丽窃喜地笑笑。两只没有悬挂奶罩的奶子晃荡着,像她怀抱的小狗两只耳朵在颤动。
小李就在阿丽的楼下开着一个面馆,早晨卖油条胡辣汤,中午卖各种面食。一口大铁锅在早晨里是滚烫的菜油,中午是翻滚的面汤。小李的生意似乎一直不错,经常挤满了食客。人多的时候,很多食客就自己套袋子,尽管拆迁的机器大肆轰鸣,他的店门口也刷上了大大的拆字。但是小李一直在卖着面,他的妻子则在一边撒葱花,香菜和红萝卜条,绿色的芹菜。来他店里吃面的人每天很多,尽管有很多的尘土在蔓延,但不少的人还来这里吃饭。大家喜欢的是小李家的面做的实诚,肉给的多,一碗不仅能吃吃饱还能吃好。小李家的油条也好,炸油条的油几乎两天就要换,自制的胡辣汤里,豆腐条、牛肉丁、面筋块、海带丝一样不少。一碗胡辣汤两根油条吃的无比舒坦,早点卖的豆腐脑也很有特点,一种是卤汁的,一种是五香的,柔滑顺口。小李瘦而精干,和妻子两人跑前跑后,从没雇过服务员。两个人分工明确,食客虽多,但秩序井然。一些熟人自己端碗捞面,自己倒面汤,小小的一间面馆,成了大家最温馨的记忆。
现在,挖掘机在工作着,钢铁销毁着水泥,水泥解构着砖块,废墟一堆一堆地呈现着,像是一场地震留下的满目疮痍。玻璃碎了,门框被挑了出来,水泥墩里的钢筋也被剔出了出来。在废墟的一边,树立着新村建设的宏伟蓝图:鳞次栉比的高楼,宽阔的马路和繁华的商业街铺。按照规划的蓝图,二府庄将真正成为城市的商业新区,村民们将过上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不再用蜂窝煤路,不再扛煤气罐,不再为污水横流愁眉苦脸。
但是修钥匙的老刘会去哪里?补鞋匠老王会去哪里?还有盘着土炉子烤大饼的李师傅一家会到哪里去?他们一直租住在二府庄的城中村里,在民房的楼下起早贪黑地做活,在楼上睡觉做饭。如今,他们会去哪里?
一群鸽子依旧在盘旋着,这样的场景我曾经在黄昏里常常看到。那是老张在二府庄楼顶饲养的一群信鸽,每天黄昏,老张总是摇着一面红旗,招引着鸽子们返回。然后提着一瓶酒去修钥匙的老刘铺子里扯闲话,他们说着家乡话,叽叽喳喳,像一群迷恋缝隙的麻雀。路过的人听不懂他们的谈话,但觉得他们热闹,生活得有滋有味。他们聚得多了,人生的感悟也就多了。有时候,老刘就会把这些话写在黑板上,放在铺子门口。endprint
老刘的粉笔字写的好看,有些话是值得琢磨琢磨。但又多少人理会他们这伙人呢?
拆迁开始了,他们的酒喝得更多了。酒瓶子不用扔垃圾箱了,直接扔到了那片废墟上。他们曾经是小李家面馆的常客,冬天的时候,不烧开水,就去小李的面馆舀一碗热乎乎的面汤喝。
小李搬走了,阿丽也是要求搬走的,她虽然叫喊的厉害,却有着虚张声势的孤单。在强大的拆迁中,她必须搬离,带着自己与生俱来的身份,演化成城市新居民。
一声鸟叫
老家的黑夜是沉寂的,后半夜的雨声就是在沉寂中一点一点大了起来。滴答滴答,雨水敲打着树叶,瓦片和屋后的大片麦地。一种淅淅沥沥的感觉就弥漫在心中。后半夜也起风了,雨水大概是打到了窗户上,我无法深睡,躺在床上,感到清凉无比。
在这样的雨夜,我听到了不远处的一只鸟叫,它的叫声像从一堆石头里跳出来的,又像是从树顶上的一簇树枝里掉下来的。有些急促焦虑,甚至有些恐怖。我无法描述那样的叫声,因为我对那样的叫声充满了厌恶。小时候,我听母亲说过,如果后半夜听到一种奇怪的鸟叫,那就是村里有人要去世了。我为此一直紧张着,记得有一年麦收季节,村里一下子死了两个老人和一个壮汉,扰乱着村里人夏收的心情。那一年,雨声似乎也多,人们提着镰刀进不了麦地,很多人家的麦子就在雨水中发了芽。在心急如焚的等待中,人们在大雨中挖掘坟墓,埋葬着死去的老人。记得那个壮汉无亲无故,他一个人住在村子打麦场的一个角落,家里连个像样的家居也没有,真的是一贫如洗。后来他被卷了凉席埋在了北边的乱坟里,埋他的晚上,就有很多鸟在叫,叫的人心里发憷。
迷信的村庄因此演绎出很多的传说,其中,就有人说她好几天晚上就听到了怪鸟的叫声。但是我没有听到。我听到的是布谷鸟的叫声,是麦黄鸟的叫声:算黄算割,算黄算割。麦黄鸟的叫声,像刀子一样交割着庄稼人的心。在麦黄鸟的叫声中,我一直在心里猜,叫走老人和壮汉的那只怪鸟,它是一只什么模样的鸟?栖居在什么样的树上?它为什么要在农忙的季节叫走他们?
今夜,我又听到它的叫声,它的声音刺破着黑夜和雨声,短促破碎。离开村庄二十年,在这样的雨夜,突然听到这样的鸟叫声,我已经没有了童年时的恐惧。但是猜想和迷惑还在,我轻手轻脚地掀开窗帘,想看看这样的鸟声从什么地方传来。夜色凝重,雨声磅礴,湿气弥漫,我无法循声张望,只能在黑夜里对着鸟叫的方向猜想。我看到一棵高大的梧桐树在风雨里摇晃着叶子。在我的张望中,鸟叫声渐渐清晰悠长了起来。有了简短的停留。我大致感觉到,这样的声音就在东边的邻居家,几年前,他们就搬出了老院子,荒废后的老院子里生长着许多的树木。也招引着各种蛇虫怪鸟…….
天亮的时候,这样的声音终于清亮了起来,雨还在下,树木从黑夜里显露了出来,房子和田野也显露了出来。一夜之间,麦子似乎比我昨天回来时黄了很多,核桃树上的核桃好像也长大了不少。一夜之间,村庄湿润,生机勃勃。
我看见了一只鸟,它花白相间的尾巴是刚刚长出来的,毛茸茸的头部上还沾带着巢穴里的枯草。它在一棵不大的桐树上笨拙地跳来跳去,有几次险些掉下来。但它停止了叫声,它晃动着脑袋,张望着雨夜之后的村庄。它其实就是一只喜鹊,我想昨夜的叫声是不是它稚嫩的声音?昨夜,是它的母亲被雨水带走了,还是它在栖息的黑夜里看到了人们无法看到的诡异一幕?
少年的背影
6月1日,我在八里村嘈杂的人群里尾随着一位少年穿越油味浓烈的集贸市场。我只是一个好奇者,我跟随着一位少年行走,是因为他洁白的校服后面,用签字笔写满了潦草的语言。比如:栗柯霏,我喜欢你;比如:张大力,我叉你妈;物理老师是摊屎。这是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流行的价值观是实用主义和成功学。嫩模、干爹、奢侈、微信、道德、夜店、成名、闪婚。我所好奇的少年这件服装,是不是也是一种流行?还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我叛逆?他为什么要这么明目张胆地涂写一件校服?然后毫无顾忌地穿着这样的衣服在大街上行走?
我知道少年所在学校就在不远处。学校是所初中,教学质量不怎么好,但管理严格,似乎也很是刻板:比如中午校门关闭,学生们只能游荡在校外,很多孩子吃零食,相互追逐打架,有些躲在拐角处抽烟。夏天热的时候,一些孩子就坐在花坛护栏上打瞌睡,冬天就是抱着胳膊晒太阳。城市的家是回不去的,回去了父母也不在,父母们都在忙碌着,早餐也是顾不上做就在外边卖。可能也是年龄的缘故,孩子们大概也不是愿意回家的,不愿意听到父母和长辈们的唠叨。
儿子不到九岁就开始叛逆、顶撞。看得出来,他有一些紧张和压抑。这样的感觉来自身体的变化和教育的观念。世界在他的脑子里似乎就是个转动的地球,就是楼房和川流不息的车辆,就是父母为挣钱弯腰为一次昂贵的消费争吵。他还不懂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没完没了的作业,程式化的课外手工制作,不能有任何差池的背读和考试后的反思总结让他多了沉默。我不清楚这样的成长是否有拔苗助长的嫌疑,但是孩子明显的活力不足。每周我都计划好带他外出比如跑山,去公园游玩,去和楼下的孩子做游戏,但是每周都有做不完的作业和参加不完的课外兴趣补习班。我们脱离不了这样的成长怪圈,我曾尝试着抵制,但无济于事。每到孩子做完作业的时候,我就会给他讲我小时候放学后,去和同伴们在野地里疯玩的事情,讲我割猪草时发现草丛里有蚂蚱还有甜瓜的故事,孩子面目表情地听着不以为然地反驳着。这是不同时代的心灵感觉,我所描述的场景和乐趣他无从体会。他正在庞大的应试教育体制内被复制,无力抗争。
青少年时期是敏感时期,行为和人生的观念已经萌芽。但青春在不知不觉间变得病态而残酷。暴力的膨胀让他们叛逆,而我们总是用自己固有的视角和思维看待他们。
看到少年的背影,让我想起我的鲁莽无知的少年时代,不知天高地厚的青春岁月。尽管那样的生活没有管理,但内心的寂寞和冲动时时涌现。一个叫刘三娃的大孩子带领着我们打架、偷瓜、下水摸鱼。那是个无羁的年代,我们冲撞父母,蔑视村里的壮汉。为一些恶作剧满心欢喜。其实那样的恶作剧就是烧了别人家堆在地头的柴禾取暖,就是在放学的路上,合伙收拾了一个经常给老师打小报告的同学……
乡村的生活是单调的,但我们的内心是丰富的。因为大地上万物在生长,天空里白云在翻滚,池塘里有蛙鸣,夜空里有繁星。田边的野花随便采,地里的甜瓜尽饱吃。有天真和忧伤,就在田野里狂跑大声地哭大声地咒骂。乡村是巨大的又是与世无争的,与世无争的生活衍生着封闭和贫穷,而贫穷产生的怜悯会成为一种相互关怀的温暖。在乡村,人性是绵长而宽厚的。那么,城市生活又是怎样的一种成长环境?物质大于精神?我不得而知,只是觉得人的视野太小。可以想象的空间太小可以宣泄的地方太少。只有坐在3D影院,才有惊奇和兴奋。在一本刊物上看到一篇文字:中国的城市少年几乎都是在同一种大环境下成长的。他们幼年时以号啕大哭来表达自己不能实现的想法,等到成了少年,就选择沉默和叛逆。他们很少把自己与父母的矛盾告诉别人,但更不愿对父母讲述自己的苦闷。他们在人前会违背自己的心愿,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通常都是基于同一个理由——那是父母喜欢的。
我不懂得这一代的的少年,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思维和观念看不透这一代孩子。每个孩子的成长遭遇都不尽相同,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机遇也各不相同。我的孩子正在成长,面对他们的沉默,我选择的可能也是沉默。因为就像一颗种子,它在花盆里生长和在田野里生长有着明显的不同,顺其自然。让他们在自己的环境里遭遇人生自然遇到的事情。去体会去承受去感悟……
少年一路招摇走过,他的憧憬是什么?梦想是什么?走在他的背后,我猜想过他的面孔,他的激荡内心。我也猜想起我曾经的少年同学,那些风一样飘过的青春岁月,沉浸自我无法自拔的那些漫漫长夜……
但这仅仅只能猜想。少年一路走过,旁若无人地穿过市场,穿过马路,消失在人群之中。留下我,杞人忧天般的发呆。
◎马召平,1973年生于陕西岐山。中学时代起发表作品。出版有散文集两部,诗集三部。获得过柳青文学奖、鲁藜诗歌奖、孙犁散文奖等。系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