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无葬身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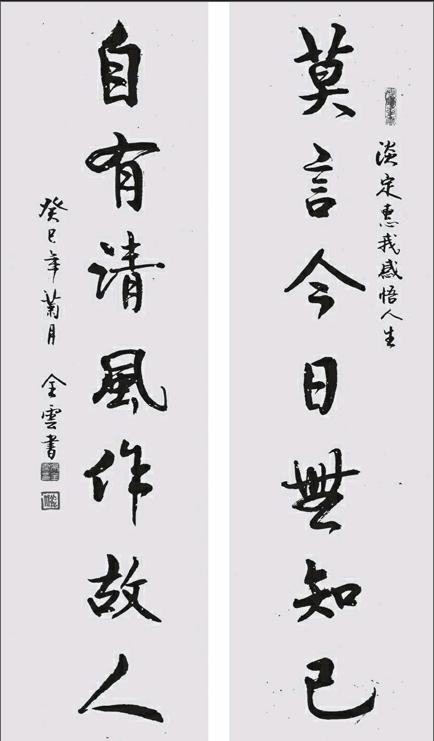
我与爷爷素未谋面。
爷爷在他四十九岁那年为革命光荣英年早逝了。关于爷爷的这些故事,我都是听奶奶说的。若与民政局等相关部门记录备案有出入,则以官方相关记录为准。作为爷爷的直系亲人,我们拥有谈论及缅怀他的权利,或许也只有此权利。
奶奶在说关于爷爷的故事时感情是复杂的,她的眼神总是闪烁着令人不解的光芒,在她慈祥的目光照耀下,让人感觉这一切并非遥远。仿佛就是刚刚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身边的事情,当然奶奶也有说到落泪的时候,一般到那时故事也就快要结束了。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说着同一个故事,现在我几乎都能完整地背诵下来了。
和大多数革命军人一样,爷爷也生活在一个很落后的乡村,落后的让人觉得美,美的让人想哭。那里的山秀气的让你不敢靠近,那里的水清纯的像个害羞的姑娘。
爷爷十六岁的时候,家里就准备让他与村里的一位姑娘成亲了(那个姑娘却不是我奶奶)。这是遵循乡下早婚早育的风俗。爷爷在那之前并没有看过他的新娘。那时侯大概流行所谓朦胧美,所以,一般在成亲之前男女是不得见面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双方的家长代办。那时侯的结婚是纯粹意义上的结婚,结婚者只负责结婚,除结婚以外的其它事宜,一律概不负责。
在我看来,爷爷在那时对男女之间的事应该还不甚知晓,只是觉得结婚像一场戏,一场每个人都将去演一场的戏。前人怎么演后人照着去演就是,至于这戏是否好看该如何去演以及作为主角该带着怎样的情感入戏——都不是他考虑的问题。
爷爷结婚的前一天上面突然来了人,据说是来招兵的,是领导,他们在村干部的陪同下来到爷爷家里,然后就把爷爷带走了,带到镇子上的一个党支部里。
那里摆设说不上豪华,但很别致很干净,然后那些领导都开始给我爷爷做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做就是一天一夜。他们给爷爷讲了许多听起来很伟大的故事,那里有领导新中国解放的英雄事迹,他们不厌其烦地讲,爷爷也不厌其烦地听,爷爷说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故事,听着听着爷爷忽然潸然泪下了,然后他们又对爷爷说现在正是祖国需要你的时候,我们打退了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又来了,战火已烧到了鸭绿江边,你愿意看到中国又回到解放前民生凋敝生灵涂炭的样子吗?乡亲们整天心神不宁,魂不守舍,四处奔逃,弄不好还得遭受鬼子的屠杀……
爷爷仿佛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保卫祖国的使者,祖国的未来和自己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仿佛也看到了鬼子那副蛮横像,满脸杀气,手持刚枪向着乡亲们冲过来,见人就杀,十恶不赦。爷爷忽地站了起来,那几位领导用温和的眼光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爷爷用袖子擦了擦眼角涔出的泪水,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有点紧张地看着身旁的几位热情的叔叔阿姨。
“我要参军!”
哗哗哗哗,身边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让我们为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鼓掌!”
哗哗哗哗,又是一阵掌声。这时,屋里不知什么时候又来了许多人,他们一起为爷爷鼓掌。
最后他们要爷爷填一张表,爷爷把表顺着看了一遍,又倒着看了一遍,然后他说:“我不会写字。”
“那我们帮你填吧。”领导们热心地说。
“你家的地址是哪里?”
“青山镇龙潭村。”
“你父母叫什么?”
“父亲某某,母亲某某。”
“你的婚姻状况?”
“明天结婚。”
“明年结婚?”
“不对,是明天结婚。”
“啊?明天结婚?”
“那你怎么办?”
“不知道。”
“其实结婚呢,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你现在还年轻,要以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为重,以后有的是好姑娘……”
“嗨!”
“我们明天要出发了,把你送到朝鲜去,你有什么想法?打算怎么做?”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说的好,那就这么定了,你的父母,我们会做妥善的安排,这你放心,你是光荣的,共产党万岁!抗美援朝志愿军万岁!”
“共产党万岁!抗美援朝志愿军万岁!”里面的人又激情高昂低喊了一边,爷爷也跟着他们一起激情高昂地喊。
第二天一早,在一个由各色人群组成的队伍的欢送下,爷爷和几个青年出发了,他们膀子上都带着红花,身穿崭新的军装。在锣鼓喧天的欢送队伍中,有人哭,有人笑。笑的是那些懵懂无知的少年,以及一些憨厚的像土地一样的乡亲;哭的是爷爷及和爷爷一样的青年的亲人。爷爷的母亲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死死拉着儿子不让走,说是这一走就永远见不着面了,可爷爷最终还是走了。那些个领导们又劝了爷爷的父母们一番,说是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是在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是正确的,保家为国是伟大的光荣的。他们还要父母们笑一笑,说这样光荣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笑才对,哭哭啼啼儿女情长成和体统。可父母们就是笑不出来,不得已最后还是苦笑了一下。爷爷始终默默无语,尽管他的心里也许很矛盾,但他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哭还是笑。
爷爷他们在城市的一个临时警备军事区里进行了短期的急训,爷爷那时反应特别敏捷,跑的特别快,在那个编队里很受重视,说是一个好料子,要好好的培养,爷爷身上具有山里人的朴实与憨厚,教官们都很喜欢他,他很快就被提升为班长。爷爷很高兴,他长这么大还从没尝过当官的滋味呢,但在部队里官可不是好当的,志愿军纪律严明,训练也特别的辛苦,但爷爷毫不在乎这些,他心里想着自己可是个班长,要带好班长的头。
两个月过后,爷爷他们就奔赴朝鲜战场了。听说代军的是彭德怀将军,爷爷也有幸见过了,爷爷说彭司令个子不怎么高,但很威武。
一路都响着嘹亮而有雄壮的歌声: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
过了好多天,军队开到了鸭绿江边,这里是真正的东北,寒冷的空气笼罩着一些年轻或成熟的脸庞,他们坚定的目光把雪地刺的异常单薄,江上结着厚厚的冰层,连军车和坦克可以平稳地行驶在上面,就像行驶在马路上。爷爷他们有时坐车,有时跑步,感觉也不太累。
一路的风景对于军人们来说只是形同虚设,他们中除了有少数诗人气质的,会发点感叹之外,其余的大都在摩拳擦掌,把刚枪擦的油亮油亮,特别是爷爷,他被领导们说的特别恨美国鬼子,他恨不得马上就冲进美国军队大营里,把他们杀的片甲不留。
踏上朝鲜的国土感觉又不一样,爷爷那时候就是不明白朝鲜人为什么老是把东西顶在头上而不把东西放在肩上,那样头压的不痛吗?朝鲜人和中国人长的几乎没什么两样,但他们说话就是听不懂。朝鲜的迎军队伍摆的很长,比家乡的送军队伍长多了。并且朝鲜人特别客气,为军队送来了许多东西,爷爷还获赠了一双布鞋,一块米糕。
开始的一些日子,志愿军没有立即赴战场投入战斗,还得继续熟识地形,训练的强度更大,但这样的日子比起打仗来悠闲的多了,毕竟还不用顾忌有生命危险。
但过了不多久,爷爷他们就要上战场了。爷爷说美国鬼子的武器很先进,志愿军死了很多人。爷爷的战友也死了好几个。特别是上甘岭战役,打的太艰辛了,连续几天都没有合眼,战士们一个个双眼通红,嘴唇干裂,手跟蟾蜍皮似的,身上带的水早就喝完了,没办法就喝马尿,爷爷他们的那一个连在一次冲锋时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在美军飞机大炮的轰炸下,爷爷身边已经没有任何人了,爷爷的身边是滚滚的硝烟。眼睛被呛的几乎蹦出眼眶,喉咙里窜着烈火,爷爷还在战场上狂奔,嘴里喊着“同志们,冲啊!杀啊!”但此时已经没有人应,忽然轰的一声,一颗炸弹就在爷爷身边爆炸了,爷爷昏死了过去。
爷爷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他不相信,以为自己在做梦。
“你没死,付启文同志,你只受了点伤。”医生说。
爷爷看了看自己,又摸摸自己的胸口。“伤?我哪里受伤了?”爷爷没有发现自己的伤口,他也没有感觉到哪里痛。
“你的脚趾头被碰断了一只!算是小残废了。”
“哈哈!脚趾头啊!哈哈哈哈!脚趾头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大不了的?少一个脚趾头我照样去杀鬼子!”爷爷兴奋地喊着。
“好了,启文同志,你先休息一下,上个战役同志们打的都很辛苦,不过尽管辛苦,现在总算是打胜了。”
“胜利了,我们胜利了!”爷爷兴奋地跳下床来。
“你先躺在床上,你的脚还没好呢!”一个营长关切地说。
“我没事,我没事!你看,这不好好的吗?”爷爷又跳了几下。
“你这小鬼呀!”营长摸了一下爷爷的头,笑了。
“启文同志,你在战场表现出色,考虑到你反应敏捷,领导决定以后调你去当岗兵,负责站岗放哨,你觉得怎么样?”
爷爷没有说话。
“启文同志,怎么不说话?”
“我……我……我想去战场,杀美国鬼子!”爷爷实在忍不住了,他鼓起勇气大声地说。
“启文同志,不是说只有打仗才是对祖国贡献最大的,其实站岗比打仗要难的多,岗兵要求战士要有非常高的警觉性,这一点你具备,组织相信你!叫你去站岗这是组织的安排,你应该感到荣幸才是,再说,站岗也有仗打,说不定还得打许多仗呢!别看平时岗兵就那样站着,但一发生特殊情况哪一次不是岗兵最先打的,启文同志,明天调队!”
“是,营长!”爷爷又被说的动心了,他很激动。
自那以后,爷爷就开始站岗了,也曾上过几次战场,但他的主要任务还是站岗。岗兵真的是最辛苦的,叫你站在哪儿,你就得站在哪儿,哪怕是油锅里,你也得下去。朝鲜的冬天特别的冷,有时候爷爷就站在桥下的河里,一站就是一个晚上,爷爷说那水凉的刺骨,可以让你失去知觉。有时连续几个小时站在河里,下半身在冰里,上半身在地面,真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旁边的战士们也都一样,死死的站在哪里,不说一句话,一个个都像僵尸一样,一直到有人换岗才小声的说上几句,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没有忘记话是怎么讲的,才知道自己她妈的还没断气。
爷爷的身体那时受到了极度的摧残,严重的风湿病使得他的腿不再有以前那般敏捷灵便,以后遇到冷天他的身上会起许多大包,像长满了无数个拳头似的。
期间队伍里流传着许多光荣事迹,比如救朝鲜小姑娘的罗盛教,为军队的利益活活被烧死的丘少云等。爷爷对他们很崇敬,因此他常以为自己做的一切不算什么,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应尽的义务,但爷爷常说假若他遇到那样的“机会”,他一定也会“把握”的。
朝鲜战争结束后,幸存的战士们凯旋而归,爷爷也是其中一名,回国后,领导们说由于爷爷年轻,表现出色,要他留在队里,爷爷又沉默了,因为他那几天晚上天天做噩梦,他一闭上眼睛自己的亲人就来到身边,他看见自己死去的爷爷奶奶从坟地里爬出来拉他回去,然后惨叫着说他要不回去这一辈都回不去了,爷爷自那以后也生过几场病,(主要是风湿病)但他自己不明白,他还有点迷信,心里想着一定是自己不孝的缘故。有的战友打探到了谁谁将会留队的小道消息,他听说有他的名字时,沉默了许久。
过了几天,朝鲜战争庆功会召开了。
“下面宣布留队的战士名单:胡长有,张四旺……付启文”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
“报告团长,我要回家!”爷爷突然站起来,小声地说。
刹那间全体沉默了,没有人知道爷爷是怎么想的,许多人想留队都留不了,这小子怎么这么傻?最后,还是团长最善解人意,他走到爷爷身边。
“小伙子,是不是想家了啊?”
“是,非常想!现在仗打完了,我要回去报告我的父母,我还要好好的孝敬他们!”爷爷哭着说。
“好!说的好!志愿军的好战士!志愿军嘛,既然是志愿来的,当然也可以志愿回去!”
“付启文同志,你要确实想回家,那就回家吧,只是考虑到你是个人才,部队才留你,绝没有勉强你的意思。”
“谢谢团长!”
“那你有什么要求?”
“我只要求部队好好的培养我的儿子(爷爷当时在行军途中捡了一个孩子,八岁,那孩子管爷爷叫爹。)我们那里是山区,教育落后,希望部队把他培养成一个人才!”
“好!别的没有了吗?”
“没有了!”
爷爷他们还参加了几个仪式,无外乎就是些授勋章、发证书了等等,这些爷爷看的很淡,在他心里,只想着,现在美国鬼子投降了,祖国人民安全了,自己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此时他只想回家。
回家后爷爷被安排在区武装部工作,爷爷担任部长,相当于与现在的公安局局长,但由于爷爷没有多少文化,除了写的好自己的名字,认识零到九之间的阿拉伯数字之外,其余的几乎不认识,合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斗大的字认识不了两箩筐。许多文件都得由别人来念给他听,他甚至连签字也不知道往哪签,干了不久,爷爷便觉得自己不适合当领导,他想辞职回家当农民,可政府并不同意,他们说要是真的干不了部长,也可以调到别的部门工作,否则上面怪罪下来,说他们虐待志愿军功臣将士,这责任可是谁也担当不起的。没办法爷爷又调到区里的粮站当站长。
当站长后的爷爷比较轻松(一般的账目都是由会计管),但麻烦也正是由此而来,爷爷当站长后不久,便赶上文化大集体,那几年全国闹灾害,苏联又逼着中国还国债,地方政府浮夸风厉害,老百姓被饥荒逼的妻离子散,四处一片凄凉,饿殍遍野。
爷爷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不忍心看着乡亲们就这样饿死,善良的爷爷终于“下令”将区粮库打开,把粮食分给社员,这一措施,没有一个人赞成。
“站长,这样搞不行,把粮食分给人民,上面若查下来,我们谁也担当不起呀!”一位干部说。
“什么担当不起?你们担不起我担的的起!人民饿死这么多,这里得粮食怎么不能分给他们吃!这叫救命啊,知不知道?人民的命就不重要吗?”爷爷气愤地说。
“那也不行啊!上面有指令,要把粮食上缴给党中央!你那样做叫玩忽职守,是违法行为!”另一位干部说。
“玩什么葫芦指什么首尾?违法?违什么法?法是谁定的?法律规定人民不准吃饭吗?法律规定人民要饿死?”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国家啊!为国就是为人民啊,现在叫先为国家服务,再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员的宗旨。”
“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人民服务?没听人民这样说:‘社员吃半斤,走路用棍子撑,干部吃四两,走路咚咚响!许多干部就会说空话说大话,但实际上自己不知道吃的有多肥!”
下面一片沉默。
“都不说了?”爷爷反问一句。“咋都不说了?”
还是没有人应声,一片寂静。
“那我宣布,开粮库,叫社员来领粮食!”
“这——不妥吧?”
“什么不妥?妥的很!”
说完爷爷快步走出会议室,亲自走进粮站的广播室喊社员来领粮食。
这一喊可不得了,社员们像疯了一样向粮站涌来,区领导也闻讯赶来了,但为时已晚,人群已把粮站围的水泄不通领导们只有在外面吹胡子瞪眼——干着急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爷爷把粮食分给社员。
爷爷被捕了,但所幸没有坐牢,政府念他曾经有功,没有过分的深究他的责任,但他们也从此事件里看出爷爷实在不适合当官,就随他自己的心愿让他回家当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并叫爷爷回去好好的反省,说不定哪天组织需要他,他还得回来。爷爷心想正和我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我当不了官,你们非叫我当官,我就是想回去当个普通社员,那样还可以孝敬父母……
就这样,爷爷结束了他短暂的政治生涯。
爷爷回到家里,父母们并没有怎么责骂他,因为他确实为社员们作了件大好事,那次开粮库不知道救了多少人,一天到晚来爷爷家感恩的人络绎不绝,他们说爷爷那时只知道傻傻地笑,还是很少说话。
回到家里几天后,有一天,来了一个老奶奶,说要给爷爷提亲,父母们也说是啊,文子也不小了,都这么大了,上次本来都要结婚了,又从了志愿军。媳妇在家等了一年,没有消息,都以为他死了,第三年便改嫁了。
他们帮爷爷介绍了一位姑娘(就是我奶奶),提亲那天,家里准备了十斤大米,五块“光阳”(即银元),父亲跟媒人一起来到奶奶家。
“你说启文,他今年多大?”奶奶的父亲问。
“也不大,不过二十四五岁。”媒人说。
我家姑娘今年才二十,不过这倒也没什么,俗话说的好,男大十岁不算大,女大十岁叫妈妈,但听说他是一个残废军人,前不久又被革职了。你是知道的,我家以前可是不差(是富农),奶奶的母亲说。
“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来了,你家以前是富农,这可是有资本主义尾巴的,现在就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呢!看你们还吞吞吐吐不答应的。说实在话,说不定马上就要打倒你家了,还不赶快粘点革命的光?叫你家姑娘与他成亲,那其实是在救你们!”
听媒人这么一说,奶奶的家人便不敢再奢求什么了,仔细一想也是的,现在政策变了,家里也确实是不安全,前不久就上交了不少钱不少粮食,说不定哪天来抄家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好吧!”奶奶的父亲先答话。
“那好,就这么定了!”邵老大,这次你家姑娘可有福了,启文那小伙子又聪明,又能干,还有过光荣历史,这样的人哪里寻啊,以后小两口可有好日子过了……”
至于奶奶,那时候的婚姻全是由家人定(这一点中国已解放多年了,但婚姻还是没有解放)。家长说什么就是什么,叫你嫁给三条腿的蛤蟆,你就不能嫁两条腿的活人。
但奶奶听说爷爷是残废军人,她心里总有一丝不满:“嫁给一个残废人,那我可不干!”
“不干?不干也不行!小丫头片子,不懂事!”奶奶的父亲厉声说。
奶奶怕了,她后悔刚刚说了那样的话,奶奶说她的父亲很厉害,长的彪悍凶猛,连鬼都怕他,说有一次她的父亲晚上喝醉了酒,经过一处叫鬼吊胫的地方,(传说那里经常闹鬼)便听见一群没有下巴颏(鬼都是没有下巴的)的人一阵哭喊:“邵老大来了!邵老大来了,快跑啊!快跑啊!”经父亲这样一训,奶奶便什么都不敢说了。
“我嫁了他就是。”奶奶说这话时大概是一脸无奈,当然这是我猜的。
“其实你爷爷并没残废,要说残废也只残在脚趾头上,这哪算什么残废啊,你爷爷长的和你一样傻气,你呀,长的很像你爷爷,特别是你走路的后影(背影),简直是一个模子(就是一样的意思)。当然这是奶奶嫁给爷爷以后才知道的,奶奶因此偷偷的笑了好多回。
奶奶和爷爷过了一段比较幸福的生活,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即我的大伯父,二伯父)但好景不长,浮夸风愈演愈烈,饥荒以更快更猛的速度像病毒一样蔓延,平时走路时几乎每个人都拄着根棍子。爷爷的大儿子在十岁的时候溺水而死,二儿子在四岁的时候因为吃不下树皮饿死了。但那时候爷爷奶奶却来不及伤心,在饥饿的逼迫下人不但会丧失理智,连最起码的亲情也会默然视之。那时候死个把人根本不值一提,和现在死一只鸡一条狗没什么区别,那年我的爷爷奶奶还没把亲情完全丧失,他们选了一处较为偏僻的地方将自己的儿子埋了,这在当时已是很负责的了,因为埋一个人是很费体力的,更何况找一处很偏僻的地方!之所以要偏僻,是怕尸体被饿狗扒出来分着吃了。
奶奶说爷爷也曾因此而伤心难过,但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又何尝不伤心呢?只是没有力气去伤心罢了,那时候的人们连伤心的自由都没有,就是偶尔伤一下也会力不从心。
饥荒过后不久,他们的第三个儿子我爸爸出世了,一家人又皆大欢喜了一下,因为总算没有绝后。爷爷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养活好,要不一辈子就什么都没有了。说到底爸爸还算幸运的,没赶上饥荒的年代,要不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那时当然还是大集体还是粮食不足,但总算是有的吃了,他们的儿子也可以喝上稀饭而不至于饿死。
有两件事在此不得不提一下,算是两个小插曲:
一次奶奶叫爷爷拿工分去换粮食,可爷爷这一去竟一天一夜没有回来,第二天提着空空的带子回来了。奶奶问他称的粮食在哪里,爷爷只做着一些奇怪的动作,他用手不停地比划,好像在表示他做馍馍吃了。奶奶不相信,一个人怎么可能会两顿吃掉十几斤粮食,但无论奶奶怎么问,爷爷就是不说话,他哑了。当然,奶奶知道他是装的,便也没有再追究什么,因为她知道爷爷肯定又把粮食分给本村的一位没儿没女的老太太了。家人也只有饿两天肚子。
还有就是红卫兵来到爷爷家,要把爷爷拉出去当右派打,要把爷爷戴高帽子游街。那天当十几个年轻而又顽皮的红卫兵来到爷爷家,喊着口号打倒爷爷的时候,爷爷真的生气了。他左手拎着砍柴刀,右手拿着根大木棍,像刺秦王的荆轲一样怒发冲冠,奶奶说那是爷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那么大的火。
“走资派,跟我们去游街!”红卫兵嚷着。
“你们说什么?谁是走资派?”爷爷愤怒地问道。
“就是你,你当年把国家的粮食分了,你怂恿个人主义,你就是走资派!”
“放你妈的屁,我是走资派?要不是我把粮食分给你们父母吃,现在有你们吗?你们的良心都她妈的被狗吃了?”
“别说了,反正你就是走资派!我们要打倒你!”
“我要是不跟你们去呢?”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们就先打你一顿,再把你绑着抬去游街!”
“小兔崽子,你们敢?老子当年在战场上可以杀美国鬼子,今天照样可以杀你们这帮混球!今天哪个来动老子一根毫毛,老子就不跟他客气!不相信你们放马过来!说着爷爷把砍柴刀一挥作了个不知是砍柴还是砍人的动作。
这下红卫兵可给吓蒙了,他们没想倒爷爷会真动刀子,一下子吓的跑的老远。
“你们给我站住!别以为老子跟那些教书先生一样听话,任你日弄!老子反正一条命,还是捡来的,命不该死,现在老子反正也活够了,社会竟由你们这帮狗日的日弄,这还成什么世道!狗日的!整天吃饱了饭撑的没地方放闲屁是吧?
爷爷的话还没有说完,那帮小子早就跑的无影无踪了。隐约可听见他们骂爷爷“这个老家伙,真不是好惹的!”
“早就听说他以前是志愿军,不好惹,你们不信!”
“妈的,跟老子撒野!早晚我们收拾他!”
这些话又被爷爷听见了。“小兔崽子,你们说什么!要收拾老子,那你们来啊!老子在鬼门关等着你们!”爷爷又追了上去。
“快跑,这老儿真的会撒野,当年他可杀了不少鬼子,说不定他真把我们砍伤几个,那可吃大亏了!”
“对,还不跑快点!他砍了你,说不定你都没办法,他还认得不少大官。”
“都给我滚!滚!快滚!滚的越快越好!妈的!”
这是这个地方第一次红卫兵被“右派”吓跑的经过,奶奶说爷爷就是自那次勃然大怒后病倒的,这一病就卧床不起,附近的大医小医都求遍了,还是无法使爷爷康复。家里花完了所有的积蓄。能卖的也都卖了,最后实在没什么可卖的了,奶奶哭着对爷爷说:
“老头子啊(这是农村的习惯称呼,其实爷爷当时只有四十多岁。)现在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可怎么办啊?”
“那就不要给我治了,我的病是在朝鲜就得的,心脏和肺都有问题,治也没的治,你带着孩子好好过吧,最好再去找一个合适的男人嫁了,要不你一个人怎么养活这个家啊?”爷爷是坦然地说。
“废话,那怎么行啊?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帮你治!”(可那时候还有锅可以砸有铁可以卖吗?)
“唉……”爷爷叹了口气。
隔了好半天爷爷才开口说话。
“老婆子啊,你哭什么哭啊?总是有办法的,可我一直不想开口,就怕给国家添负担,现在人民这么穷,饭都吃不上,我怎么开得了口啊?”
“怎么开不了口啊?你当年打仗都有勇气打,现在治病就没有勇气了啊?啊?你就等死啊?你死了可好,我们娘俩可怎么过,啊?”奶奶放声大哭。
“这个……也是,那你去把我的小箱子拿来,把里面的退伍证拿去找县里的领导,那里有我的战友,看看政府会帮点什么的,当年政府也说要是以后我有什么困难,可以跟组织说,政府会考虑的。”
奶奶抓着爷爷的退伍证像是抓着救命的稻草,奶奶开始找到乡政府,乡政府的领导说这事他们没法处理,管不了,说上次爷爷对红卫兵无礼他们还没追究责任呢。
奶奶又找到了区政府,区里的老领导都调走了,现在是一些年轻的他们根本不认识爷爷,他们叫奶奶去县里,也许县里会管的,但也说不定。
没办法,奶奶只好去县城,奶奶不识字,还不知道县城往那走,东奔西走,问张三问李四,总算找到了县政府,这次县里的领导们态度很好,因为里面有爷爷的战友,他们叫奶奶马上把爷爷接到县城的医院里治疗,至于医药费,不用奶奶担心。
就这样爷爷被送进县医院接受检查,检查结果一出来,所有的人都傻了眼。爷爷患的是心脏病加肺癌,没得治了!领导们下令说继续治,尽量治!接下来爷爷就住了几个月的院,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可病情却丝毫没有好转,反变的更糟更坏。一开始他们都瞒着爷爷说没事的会好的,但后来却又不得不跟爷爷说了。
“启文啊,我们也尽力了,国家也为你花了不少钱,可你这得的是绝症,你可不能怨党不关心你啊!”爷爷的老战友流着泪说。
“我得了绝症,那你们怎么不早点说?花了这么多冤枉钱!值得吗?!”爷爷又生气了。
“值得!值得!怎么不值得呢?你为国家做了贡献,国家不能不管你啊,以前不跟你说也是为你好,好让你好好的养病,把病治好,谁知道现在……”老伙计说不下去了。
“没什么的,不就是死吗?老子不知道死过多少次了!我马上出院,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老头子还是那么豪迈。
爷爷回到家里不到一个月就死了,但奶奶说爷爷死的时候没有闭上眼睛,原因是这样的:政府本来给了不少安葬费,但经过区里乡里村里队里一道道关卡剩下的就没有多少了。最后生产队只送了块粗糙的木头板子来,给爷爷当棺材。
“不是说给我买口好棺材吗?怎么只有一块板子?!这板子怎么也不推光堂(平的意思)一点?我躺在上面怎睡的着啊?!这还不如当年死在战场呢!这么不光堂,我怎么睡哦,这么不光堂,这么不光堂……”
爷爷只是一个劲地说他躺在这粗糙的木板上睡不着,睡不着,说着说着就断了气,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块粗糙的木板,一直没有闭上,他的眼里噙着始终没有流出来的泪水。
奶奶说她知道爷爷哭了,一定哭的很伤心。奶奶还说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看到爷爷哭,她一直以为爷爷是没有泪水的。
可有一件事情爷爷不知道,如果知道会这样的话,他更会说还不如当年死在战场上——他死后连一块葬身的地都没有。
事实是这样的,当年正逢人民公社大集体,当时的土地都属于国家,并且正逢粮食快要成熟的季节,爷爷死前交代自己中意的那块土地上当时正长着茂盛的庄稼。当时生产队谁也做不了主,就报告村里,村里也没人做得了主,就上报到乡里,直至最后报至县政府,经有关领导批示才让爷爷下葬,此时爷爷的尸体已放屋里好几天了——已经臭了……
爷爷死时他的儿子——我的爸爸才十二岁。那天他去了离家很远的小河里捞虾,说回来给爷爷吃,因为爷爷喜欢吃虾,可爷爷吃不上他儿子捞的虾了。奶奶说爸爸把那些虾放到爷爷的铺草里一同烧给爷爷了,不知道爷爷吃到了没有。
关于爷爷的故事说完了,奶奶曾不止一次和我重复讲着爷爷的故事,每次讲完后,她总会哭一场,而我就准备一张手纸,轻轻地帮她擦去泪水。
◎许多余,1983年生于安徽金寨。作品散见《北京文学》《天涯》《延河》《草原》《边疆文学》等。曾入围《财富人物》“2010中国80后作家财富榜”“2011中国作家精神富豪榜”等。现居合肥,自由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