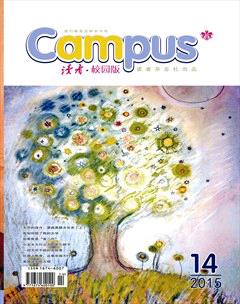那个迷书的少年郎
胡子龙
我十一二岁时迷上了课外书。但家里没书,连小人书都没有,我只能向有书的小伙伴借阅。
一个没有一本课外书的人,要想经常借到课外书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星期天,我好不容易借到的一本书忽然又被要回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小石桥边闷闷不乐时,一个在江尾小学上五年级的张姓大同学走近我问:“听说你相当喜欢读课外书?你一个三年级的学生,读得懂吗?”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他说:“跟我到我家去,我借你课外书看。”我实在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突然降临,但还是跟着他去了。他家在村南染布巷道里。他把我领到一个小阁楼上,从谷仓上抱下一个红漆箱子,打开,是一箱的书。看见如此多的书,我眼睛里就像伸出了无数双小手,恨不能把这些书都立即抓到怀里。他找出比较薄的一本递给我说:“你先看这本吧。这本容易读,读完了这一本,再给你换一本。”
我捧着书,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就从他家跑出来,一口气跑到村外小沙河边洋草果树下的草坪上,在暖洋洋的阳光里贪婪地读起来,把晌午饭都忘记了。到太阳落山、冷风骤起时,我已经读完三十几页。这是一次何等新鲜而畅快淋漓的阅读!这本名为《欢乐的海》的书,虽然很薄,但已经不是我之前接触过的小人书,而是当时我们那里人称作“大书”的那种书籍了。随着书页的翻动,少年的情感思绪生出了欢乐的翅膀,飞出村坝子,飞过万水千山,飞到祖国浩瀚的南海,飞到西沙群岛,看到了洁白的海浪,银光闪闪、活蹦乱跳的海鱼,朵朵白云下掠浪飞翔的海鸥,银色的沙滩上慢吞吞爬行的海龟,挺拔苍翠的椰子树林,充满热带岛屿风情的渔村和勇敢的渔家少年……这是我接触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我用一个月将《欢乐的海》读了五遍。读第二遍的时候,我把不认识的字用铅笔记在作业本的封二、封三上,然后去问老师和生产队的会计、记分员,边请教边给生字注音。一个月时间我就学会了课堂上还没来得及学的两百多个生字。这样,当我从张哥哥家借到第二本书《闪闪的红星》时,阅读就很顺畅了。接下来是《铁骑》《吕梁英雄传》《红岩》等。我认真地读完一本,还回去,再借一本。一本比一本厚重。而从他手里最后借到的《欧阳海之歌》,已是上下卷的两卷本了。那一年,到他家里还书、借书,成了我少年生活里的一件无与伦比的乐事,以至于三十多年过去了,隔月隔年,我就会在梦中走进张哥哥家那个小阁楼。成年的我站在阁楼里那个谷仓旁,和张哥哥一道,从那个红漆木箱里,翻出一本又一本纸页已发黄的厚书。梦中的那份喜悦和幸福,丝毫不亚于当年。
张哥哥家存有的几本文学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个遍,我的汉字认读能力突飞猛进。进入四年级的下学期时,我掌握的汉字,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很多初中生。一个三四年级的学生能够通读砖头样的“大书”的消息,成了村里的头条新闻,我成了很多学生家长夸赞的对象。一些家长从箱子、柜子里找出珍藏的书籍,让他们的孩子抱着来找我,请我带着读。什么《大刀记》《连心锁》,什么《林海雪原》《欢笑的金沙江》,什么《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等,这正中我的下怀。通过所谓的“带读”,我读到了一本又一本的文学书。
少年时期如痴如醉的课外阅读,开启了我的心智,开阔了我这个乡村孩子的视野,使我在少年时就萌动了文学创作的强烈愿望。在读了6个月的初中就不幸辍学后,我跌跌撞撞地开始了文学创作。如果说,今天的我勉强算得上是一个文学拨浪人,那么少年时代阅读到的一本本书,就是最初载着我驶向文学海洋的一只只帆船。
(郭旺启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5月8日,Getty Images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