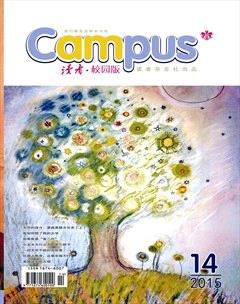告密者
闫晗
我生长在一个打小报告的环境中,从小学开始,就经常被迫写字条检举不守纪律的同学。初中二年级时,班主任突然公布了一个李光耀式的禁令:不准带瓜子进入教室。我是第一个“躺枪”的,虽然我那是禁令之前两个月的事,虽然只吃了几粒,虽然我并没有把瓜子皮扔在地上。我窝窝囊囊地点头承认了,然后表面平静却无限腹诽地接受了惩罚,扫了一个月的地。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告诉了我检举我的人是谁,那是一个座位跟我隔着一条过道的短发小姑娘,长相、成绩都平平,我俩无冤无仇,我对她几乎没什么印象。她说她看见了就要说出来,并且认为自己很正直,我竟无法反驳她,只是隐隐约约觉得有哪里不对。
高中的某一天,我也面临了类似的处境。学校禁止学生在校园里骑自行车(老师可以),只能推着走,我和住得近的师姐在一个晚自习之后,可能出于一时的叛逆之心,或是着急回家,抬腿上车往前溜了一段,恰巧被教导主任瞥见。他大喝一声,从夜色中冲过来拦住我们。师姐一个激灵,本能地迅速上车骑得飞快,消失在夜色中。主任只揪住了我,然后开始审问逃脱的那个同学是哪个班的,是谁。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主任暴跳如雷,在办公室里与我僵持了一阵,终于放弃,怒气冲冲地对我说:“别人骑车扣5分,你得扣20分!”
惯于做良民的我当晚失眠了,恐惧、愧疚、怨恨的情绪纠缠着我,不过最后的结局也不外乎被嘲讽一番,被罚擦了一阵子黑板。第二天傍晚见到师姐,她很紧张地问我后来的事,得知我没供出她来,长舒了一口气,愉快地骑车走掉了。
这两件事算是我波澜不惊的学生时代里的大事。多年后,我看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三傻大闹宝莱坞》,都有要求学生检举揭发的情节,可见服从权威还是选择义气是全世界人民都会面对的处境。沈佳宜主动站起来抗议老师这种挑拨同学关系的做事方式,一下子摆脱了柔弱校花的形象,让她的爱慕者们对她多了几分敬畏。而《三傻大闹宝莱坞》中的拉杜被校长以开除相威胁,要求供出作弊者,面临的选择是被动而迫切的。虽说家境贫寒的他考上大学不易,但出卖朋友等于否定了他做人的意义,拉杜最终选择的是从窗口跳了下去。当然,他只是摔断了腿,却震慑了校方,也保住了自己的尊严。这一摔竟让他的人生开阔了起来,他从此无所畏惧,成为一个有尊严、被人敬佩的人。
我不知道那些揭发别人的人后来过得怎么样,只是突然很庆幸,当初自己没有当一个告密者。
(王文华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15期,康永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