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们,学习一下莎士比亚
马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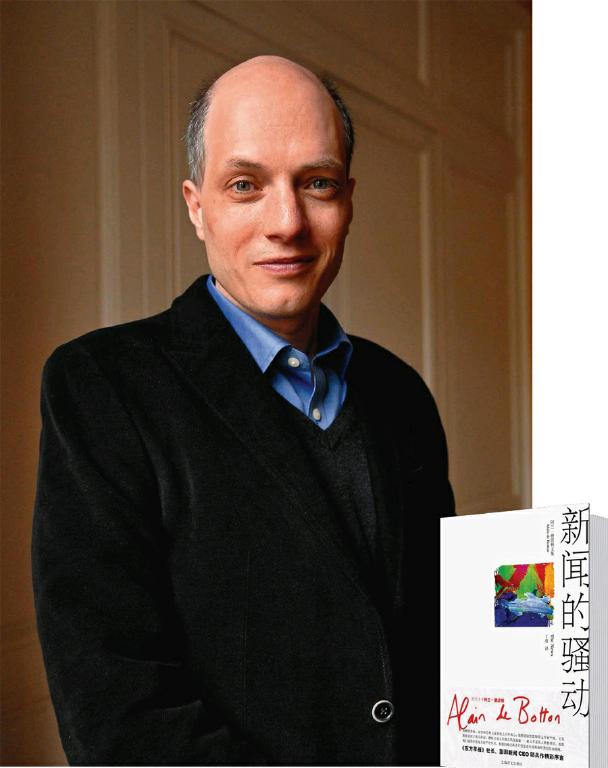
阿兰·德波顿和他的著作《新闻的骚动》
“教堂尖顶那朵无人问津的浮云,拿着注射器温柔贴近病人胳膊的医生,灌木篱笆下的肥胖田鼠,敲打白煮蛋壳的孩子和一旁满眼慈爱的母亲,胆大心细巡视海岸的核潜艇,研制出首个新型引擎样本的工厂,以及虽百般挑衅却仍能保持克制和宽容的伴侣。”——这些日常生活中较为正常、平凡、正面的部分,绝少有可能出现在新闻里。而那些离奇、罕见、黑暗的事件,则大有可能被用来填塞广告与广告之间的那些版面。翻开19世纪的欧美报刊当能明了,“反常性”原本就是商业报刊的金科玉律;此刻登陆任何一个新闻门户网站,任何人也都能领会:“反常性”今日仍然是、并将永远是、最能吸引关注的新闻元素。
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写了一本《新闻的骚动》,把新闻产品与新闻界的弊病一一针砭。以他一贯的生花妙笔,虽然并未使用新闻学那些少得可怜的理论术语——譬如“议程设置”、“新闻价值”、“框架”、“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把关人”、“刻板印象”、“拟态环境”、“选择与遮蔽”、“媒介素养教育”——却也鞭辟入里、条分缕析,足以让新闻学教授们汗颜,同时让新闻编辑部的主编主笔们蹙眉,没办法,德波顿是站在受众一边,立场决定了矛头所向。
在德波顿看来,政治新闻读起来枯燥乏味,数字和专门知识令人困惑,将权力人物拉下马来固然带给大众一时的满足,但是新闻媒体往往不能引导公众将注意力投向更为严重和隐匿的政治-社会的结构缺陷。新闻报道倾向于将事件按照特定的模子框定,削弱了受众从其他角度进行深层思考的意愿甚至能力。国际新闻更是八股而干瘪,以国家的外交及经济关系为优先,因此只忙着告诉受众:该与谁为敌、和谁贸易、或怜悯谁,一味呈现对方的黑暗面,既不报道对方的生活常态和人情细节,也不促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经济新闻充斥着各种数据、术语与图表,令很多平民读者云里雾里,很多属于“投资人新闻”,新闻界的无数人力被用来帮助投资者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的钱应该投给哪些公司?多数的经济报道并不提供附带政治因素的经济教育,原因不外乎两种:或者因为新闻自身亦感觉困惑或烦心,或者因为新闻也是现状的受益者。
大概因为以上三类硬新闻做得极差,受众才会一窝蜂地去关注另外三类新闻:名人新闻、灾难新闻、消费新闻。不过即便是这三类“可读性”甚强的新闻,也并不令人满意。在名人新闻方面,德波顿指出,崇拜的冲动是人类心理中一种根深蒂固的重要特性,与其压制人们对名人的痴迷,不如将这种冲动引向最明智、最有成效的方向。在一个组织完善的社会里,最具知名度的人,应该是那些体现和巩固了最伟大最高尚的价值观、最能造福社会的人。可惜当今的名人新闻大有问题,且不说“成功人士”的遴选标准是否得当,由于对普通人没能给予必要的尊重和关注,必然导致普通人对“成功人士”的羡慕嫉妒恨,一旦名人爆出丑闻,便会引爆最尖刻、最仇恨、最分裂的抨击。灾难新闻大概又可以划分为个人悲剧、意外事故、自然灾变,新闻或者失之于太过血腥详尽的细节,充斥着观淫癖的趣味;或者失之于短平快的讲述方法,拒绝在受众中引起更广泛的共鸣;或者失之于煽情、惊悚、宏大场面的营造,让大众在戏剧性中沉溺,忘却了那些与各自生活更紧密攸关的事务。最有趣的是,灾难新闻虽然喜欢报道谋杀和爆炸,对于人类的正常死亡却抱着毫无助益的胆怯态度,它倾向于将死亡描述成一种掀起高潮的奇观,但是对于作为日常现实的死亡却从不问津。至于消费新闻,大约是新闻中最“软”的一部分,通常倾向于报道三件事:第一,市场上有什么商品;第二,这些商品售价多少;第三,这些商品有何优缺点。在德波顿看来,它完全没有抓住关键,这个时代之所以变得独特,是因为人们想要通过物质消费来实现复杂的心理抱负,因此消费新闻本应巧妙地引导受众,去追求最能满足人们内心深处对于圆满人生渴求的物品和服务,以及相关的精神活动。
书名既然叫《新闻的骚动》,作为题眼的是这样一段话:“我们的生命承载着种种幽闭负担,比如与自我共处,比如不断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潜力,比如费力地说服身边寥寥数人倾听我们的想法和需求。而新闻尽管多有负面,却恰能帮助我们摆脱上述负担,可能越是惨烈效果越好。阅读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只是聚焦于自身的忧虑和疑虑。”
受众总是对的,不对的是新闻界。德波顿指出,公众对于硬新闻兴趣淡薄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公众特别肤浅或鄙俗,甚至不是因为事件本身空洞乏味,而只是因为新闻呈现的方式不够引人入胜。自然,记者和编辑们又很容易陷于另一个极端——“记者和编辑都倾向于认为,任何事件的重要性都是由其离奇性和反常性所决定的,这基本也就等同于其表现出来的可怕、血腥和残忍程度。”不不,新闻可以关注“反常”,却又不能只停驻于“反常”;新闻可以可怕、血腥和残忍,但同时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德波顿举例说,言及从“反常”取材,古希腊悲剧堪称重口味。比如女主为了惩罚出轨的老公杀了亲生孩子,比如男主犯下杀父娶母的罪行自我惩罚刺瞎双目,又比如丈夫祭献了女儿、妻子为报复而通奸并最终杀了丈夫和丈夫的新欢,剧目分别是《美狄亚》、《俄狄浦斯王》和《阿伽门农》,按照最后这部里女预言家卡珊德拉的话说:“血在滴答。”不过,当代的编辑记者与古希腊悲剧作家的差距在于文学技巧和道德情怀。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认为,只要有高超的剧本和艺术性的舞台呈现,只要作者心怀善意、触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即便这些故事情节残暴粗野,却具备重要的教化功能。德波顿觉得,当代的新闻记者都该向索福克勒斯那样的大剧作家学习悲剧技巧,不是引导公众做简单判断、而是引入成熟明智的思考。
德波顿夫子自道说“撰写此书的工作带有乌托邦的性质”,而他最为干犯新闻界众怒的是,在书中的这里那里不断呼吁记者们向文学家学习:“如果新闻编辑室里坐着托尔斯泰、福楼拜和索福克勒斯,也许媒体就能多提供一点东西,说到底,《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安提戈涅》的故事原型,也是新闻事件。”更过分的是,他提出:“或许可以要求新闻报道学习一下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故事讲得好,其中的心理、社会和政治主题,超越了故事本身的时间与地理背景,构筑于永远不变的人性基础上,因此可以属于无数的世纪。在编辑记者们看来,如果说德波顿对于六类新闻报道的批评颇能点到穴位,最后开出的药方却太有江湖郎中的风格。这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吧,新闻与文学毕竟社会功能不同,使用方法不同,生产方式不同。且不说别的,莎士比亚一生传下来的戏剧只有37部,当代企业化运作的新闻编辑部恐难容得下一生只写37篇报道的记者。至于原汁原味的莎剧里那些黄色粗鄙的连珠妙语,以及玄幻浪漫的部分,恐怕也难逃今日编辑大人的法眼。
浸淫于文学界的德波顿信奉文学的主要原则: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超越时空的永恒主题,因此他对于新闻界的程式化与碎片化大为不满。为了解决新闻带来的无谓骚动,他暗示大家:与新闻报道的暗示恰恰相反——其实没有什么事情真正算得上是新奇、值得讶异或者恐怖至极。是啊,《传道书》里有类似的“新闻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他建议我们偶尔该放下新闻,从每十五分钟刷一次屏的焦灼中自我解放,同时出于对人性的理解他又诚恳地表示,在一个如黑格尔所说新闻成为宗教的时代里,要是某人真能离开新闻漩涡一整天,只倾听窗外的雨声和自己的心声,其持戒水平当直追高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