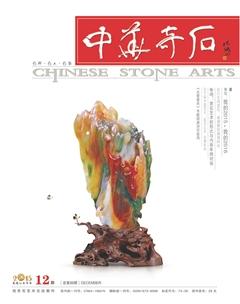捡石、玩石随想
廖尊谦

台湾新竹的捡石活动始自日据时期,这可以从早年日本水石杂志中曾刊登多方石质上好、坚硬润腻、色黑如漆且清滑如脂的黑石,以及梨皮石和变化多端的油罗石瀑布景石,让我们得以觑见早年赏石以山水景观石为主流。当然,日本人也带来了去芜存菁的切底石观念,刚开始就以黑石及油罗石为主。
笔者捡石即开始于此潮流的中后期,故当年觅石以切底景观为主、以大为美。溪床上时见三三两两的人群,手拿铁撬杠、凿子、捆绳、扁担等工具,谈笑声中以铁撬翻转大石,若属游罗石,过大的就当场凿切,若是黑石或是可合力扛抬的油罗石,则众人以绳结捆绑妥当,一路摇摇摆摆自溪床蹒跚接力抬上溪岸停车处,再合力抬上车,载到裁切处后置水中以水平定位,再循水线画出切割线,以机器切台加水切石。此风潮过后,赏玩原石逐渐成为主流,赏玩切底石的石友日渐萎缩成小众,最后淡出历史舞台。
自大石切起至标准石,再至小品石的过程中,石头底部包台比例仅二分的原石,原本可以做台座予以包覆,却在切一刀好做台座的流风下,不需切也切它一刀,也造成了今日新竹地区景观石难得一见的后果。
笔者三十年前自雅好民艺的同好处识见雅石,至今仍沉迷其中。初捡石以关西镇内马福、玉山溪系为主,后慢慢扩及其他溪流。镇内石友间将当地各溪黑石石质的优劣顺序做了排序:一锦山,二玉山,三沙坑,四马福。而这些溪流大都汇流至沙坑溪,再经凤山溪出海。而笔者皆从各处溪流出海处探索至源头,在那疯狂岁月中,空闲时多在关西,几乎可以算半个关西人了。
多年捡石下来,也遇到不少危险。早年石友捡石大都结伙同行,因穿越林地及溪畔多见蜂窝蛇踪,同行可互相照应。记得曾有一日在马福溪觅石时,于转角处小石旁骤见一白色蠕动,倒退几步细看才发现那是一条红眼白蛇,正在吞噬一条小鱼,显然见到人它也吓了一跳,昂起头来,血红的眼睛闪着妖异的红光,下一刻便吐出小鱼溜走了。捡石遇到蛇是常有之事,穿越竹林时,盘卷在树干上的绿色竹叶青蛇会突然蹿下袭击人,然而这红眼白蛇最令人印象深刻。捡石是种休闲活动,应注意安全,激流亦应防备。就曾有石友在强渡时发生被水流吞没的憾事;亦需随时注意周遭的变化,曾有友人在高深窄壁间捡石时,忽见上游陆续漂来竹叶杂物,遂赶紧催促大家上岸登高躲避洪水,不一会儿大水汹涌卷涨,当时若未上岸,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故新手捡石宜与熟知路况的老石友同行,一来有个照应,二来也可避免今日捡了明日还回去之事的发生。
人经常对于周遭环境全然无感,匆匆如过客,也经常无视周遭美丽的风景。可是在溯溪寻石时,捐弃了浮华世俗,去尽繁华,追求一种素朴宁静且回归内敛精神本质的回响。双脚踏在不受外来尘嚣负赘干扰的空间中,会不知不觉中放慢脚步,光影在身上流动变化,听鸟叫蛙鸣、溪水潺奏,观绿意盎然,那是和自然的美丽邂逅,是天地造化孕育下一种抚熨褶皱人心,进而与和谐美感舒畅共沐的享受。在抬头见山、低头觅石;抬头睹人、垂首捡石时,这山这人俱在山环水覆天地间,瞬间时空交异,潋滟光影浮动,浮光留白中遇上水土锈沁的石头与流动的水波,仿佛传达出生命变动,缓缓溢流的水波代表时间仍不停的进行,而石上的锈迹土印、水洗的光滑面,却传递出时间流动带来改变后生命的状态。
闭目静待大自然中,伸臂大口地呼吸,似可得到一种吞天之气、吸地之力的感受。而人可从捡石、赏石活动中汲取一种生活的甜度,这美好的甜度能让人在遭遇困顿挫败时,心中仍保留那些甜度的记忆,这让人产生眷恋美好生活的意念,故能更有尊严且镇定地面对困难,并不轻言放弃。这不仅是生活美学的发现,也是另一种生命美学的启发,以之对抗真实世界中的外来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