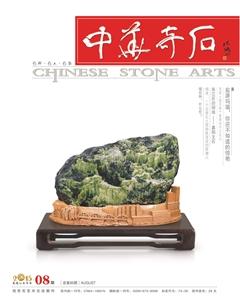赏石随笔
王永奎
三十多年前艺术大师吴冠中先生在写给当代学者何新的信中谈到在艺术领域要攻那个“内容决定形式的毒瘤(按:是当时那年代的思想症状)。”这是上世纪“文革”结束后80年代中国大地上兴起的一场空前美学热潮中十分有艺术觉醒、呐喊警示意义的话语。经过那次美学思潮的洗礼,至少在学术思想领域“形式在艺术审美中的本质地位”当该确立,不应有什么怀疑。当然要说这种艺术哲理的根基能植根于民众有多深,这恐怕是大打折扣的。因为当今社会是“决定论”、“名利观”、“成功学”大试拳脚的年代,艺术被“冷落、被遗弃”一点也不奇怪。要不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土豪”“前赴后继”地“勇往直前” 而不受阻挡呢!令人欣慰的是石界新一轮的启蒙和反思在《中华奇石》杂志这智慧的平台再一次引发。
这次思辨的题目是“赏石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去年的思辨则是“发现的艺术,还是表达的艺术?”尽管这些话题的结论在学术层面已是属常识性的了,但在石界却能引起关注的波澜,正反映着石界的现状和需求。不由使我想起法演禅师《只履颂》中相似的类比:“祖师遗下一只履,千古万古播人耳。空自肩担跣足行,何曾踏着自家底。”石界“人人都光着自己的脚却争着去扛别人的那只鞋”(更何况不是达摩的那只鞋),确已成为见怪不怪的风景。对此,杨靖女士的一番话:“纵然我们现在还无从或无力立即为当代赏石建立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执着者的……勇敢反思和真诚争论,”已为开创石界的新局面作出“最扎实和可贵的工作”是非常中肯的。
但我所考虑的是是否还存在着一条认知感悟上相对而言的捷径和通道呢?不妨抛砖引玉:这就是“艺术感悟中的路径”问题。我以为牵住了这个“牛鼻子”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艺术路径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就是“赏石是何物”之思考,亦即对艺术的属性和本质的理解,我喻之为“属性观”。第二就是对人类哲学、美学史的整体性的把握,从而能否站立到一定的视野高度,我称之为是“整体观”。这是赏石人行进在艺术之道上必须要掌握的两个方法论。否则你就难以摆脱“瞎子摸象”的困境,有时亦或只能是“隔靴子抓痒”,解决不了赏石艺术实践的任何问题。
先来说第一个方法论,即“属性观”的问题。
这反映人类社会的进步其实有着两种不同属性的“认知”:一种是科学范畴的认识论,其属性是概念性、逻辑性、他律性、公利性(通常意义中的“有用”)诸特征(称之为“决定论”的认识论)。另一种即艺术、哲学、宗教范畴的悟性(智慧之性),其特征就是非概念性、非逻辑诠释性、自律性、非公利性(“无用”表象中隐藏着更大的“有用”)等属性。称之为“艺术论”的属性(归类为“非认识论”的知性)。但由于石界在自身建设中存在着许多的先天不足,因此艺术思绪对石界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整体来看石界得了严重的“(艺术)营养不良症。”石界总体理论构建是建立在产业性认识论的思考框架中的,它在本质上是去艺术性的。石界在“决定论”的掌控下已经实施着对“艺术论”的全面“驱逐”,但是这种局面只会引发石界新一轮艺术审美启蒙思潮的到来。为了给这一思潮推波助澜,就让我们重温一下历史上的哲人、伟人、思想家、艺术家们,他们是如何看待艺术和审美的“属性”特征的:
“美不属于决定论的世界,它脱出这个世界而自由地呼吸”—— 别尔嘉耶夫;“美不是别的,而是现象中的自由”—— 席勒;“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对于它,音乐并不是一个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的肯定”—— 马克思;“美学就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纯粹的人类现象。在这一领域里,一切超越似乎从一开始就预先排除了;不可能有逻辑的或形而上学的解决办法,只有人类学方面的解决办法”—— 卡西尔;“艺术总是可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来,因此,艺术的条件也就决不会是预先设定的”—— 塔达基维奇;“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 鲁迅;“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庄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 老子;“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 王国维;“你们的孩子,不是常常热中于弄烂泥,骑竹马,折纸鸟,抱泥人的么?他们把全副精神贯注在这等游戏中,兴味浓酣的时候,冷风烈日之下也不感其苦,把吃饭都忘却。试想想看,他们为什么这样热中?与农夫的为收获而热中于耕耘,木匠的为工资而热中于斧斤,商人的为财货而热中于买卖,政客的为势利而热中于奔走,是同性质的么?不然,他们没有目的,无所为,无所图。他们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即所谓‘自己目的,这真是艺术的!他们不计利害,不分人我;即所谓‘无我,这真是宗教的”—— 丰子恺。
……
通过和上述先哲、智者们的对话,我们的观察视角和结果是否能得到些改变呢?比如对观赏石的鉴评标准问题、科学赏石的理解问题、自然美的属性问题、形式美的属性问题、石展的评奖问题……
禅诗中有言:“多少人来看明月,谁知倒被明月看。”在艺术缺失的日子里,石界“看不懂明月,反被明月看”的尴尬也只能无奈地存在下去。
方法论之二,即“整体观”问题。
就是你能否站到人类哲学史、美学史的整体性角度的视野上去看问题。有了这种视野,你的审美“头颅” 将会变得无比的高贵(生命的自由维度所促成),你的洞察也会无比地深刻(生命的自由维度所造就)。否则你也还是无法摆脱“瞎子摸象” 的困境。例如站在美学史整体性视野上你会很自然地得出“美学的历史并不是同一规定和理论的世代相传”这一常识性的结论式判断。还例如只是在十八世纪(1747年)艺术才被统一为巴托“美的艺术”(即音乐、诗、绘画、雕塑、舞蹈、建筑和修辞这七项内容),现代艺术内涵得以确立。
你的审美趋向(一种内在自律)就不会非常轻易地被外物和他律捕获、拘泥而“成法”,被稀里糊涂地局限于某一时代的审美内容和形式中去。因为对你起影响的观点可能有些早已是被分离出艺术和审美的范畴,有些即使仍属审美的范畴,但也未必是艺术发展史整体性上的视野。正如席勒在《论美》一文中所言:“似乎错误可能就在于,把与该理论相符合的那种美的部分当做了整体的美本身。”
托马斯·阿奎那说:“重要原因的效用不能由次要原因的估量的作用来衡量。”比如对古希腊的文明怎么看,马克思就说过非常深刻和富含哲理的评述:“古希腊的文明是人类的儿童时代”,成人的人类拘泥停留在那里就突显稚嫩了。如此这般就可避免“错拿鸡毛当令箭”,发生“以偏盖全”的误判、误导此种尴尬。我们的视野一定会更加开阔和豁达。也正如文学幽默大师林语堂所言,我们才能避免去当“富有灵感的白痴,”也不会去当“稀里糊涂的天才。”
为了清晰和方便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愿意引用和上述禅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现代诗人卞之琳《断章》中的名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是一首多么令人清新神往、富含通透“棒喝意义”的哲理诗!(恕我执意地把此爱情诗硬要看成是哲理诗)(注)!“桥上”和“楼上”就是哲学、审美史上局部视野和整体视野、次要原因和重要原因的区别。以“桥上”所见的风景去充当“楼上”所见的风景,这就叫做“断章”。石界中“断章”这样的事比比皆是,一言难表,有待和石友们共同去分辨(先辨后辩,底气就足效果会好),将有改造石界蒙昧现实的促进意义。因为“必须超越自己,才能洞察未来”,这是石界进步的必由之路。“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石界艺术之春天,也只有在争辩和觉悟中才能获得。
如果广大石友都能掌握上述两种方法论的思辨武器,那么石界中艺术的正能量就会慢慢积蓄。托马斯·阿奎那又说:“点灯优于仅仅发光,把沉思的真理传播给他人优于仅仅自己沉思。”石界需要更多的“点灯”人,而不是“吹灯”者(我视仰仗“决定论”者是对赏石“艺术之灯”的“吹灯”者)。那么届时石界中的“(完全版)理论家”也好,或是“半个理论家”( 沪上石界的一种调侃)也罢。他们的言谈可得要三思了!那时石界的进步一定是质的进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上只是积累于心间的有感而发,也许可能还是“桥上的窥孔之见”,并非是“楼上之观”,亦或“看风景的人在摩天大楼的楼顶看你”。再感而发,故诚请坊间内外有识之士明鉴和指教!
注:此诗相传是当代诗人卞之琳对其爱恋之人,有着“民国最后一位才女” 之称的张充和女士的爱情诗。诗的后两句是“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于当地时间2015年6月17日在美国逝世,享年102岁。
——石界抗疫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