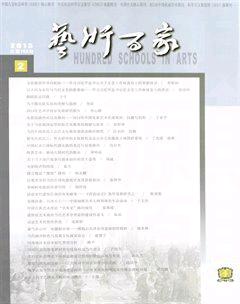明清青楼题材绘画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摘要:明清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中青楼题材绘画最盛行的时期,与早期此类题材绘画作品不同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具有人文意识的启蒙思想的觉醒,明清时期青楼题材的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出现了新的特征。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不仅仅只作为背景、群体出现在画面中,她们作为个体的个性和尊严开始得到了关注和刻画。文章将明清青楼题材绘画分为两类分别进行了解读与分析,印证了明清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缓慢过程。
关键词:明清绘画;青楼题材;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Understanding of Female Image from Paintings Taking Blue Mansion as the Material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FAN Yin-hua
(School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明(1368-1644)、清(1636-1911)是程朱理学影响最甚的时代,也是“妇德观”思想映照在图像中最为明显的时期。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明清二代青楼题材绘画的繁荣似乎是与此观念在图式上的一种对抗。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促使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呈现出愈加鲜明的世俗化气息。
妓女作为向男性提供声色娱乐和性服务的特殊群体,大部分时候她们都是画面故事的配角,往往是作为一个群体和性别出现在画家的笔下,她们的个性特征常常被忽略,她们的面貌、服饰都是雷同的。她们的身份、情感都不是画家所关心的,她们的出现只是为了刻画画面中的男性形象的需要。明清青楼题材的绘画作品中大部分女性都是以此种方式出现。
目前,我们在明代表现青楼题材的绘画作品中,能够找到的相对较早的作品是郭诩《东山携姬图》和《琵琶行图》等。
在中国艺术史中,唐寅因其独特的知名度,可以算作是表现青楼题材最有名的画家。他常用的“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巷里醉千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章都意在表明自己以游妓为荣耀、玩世不恭的人生观。这与他考场舞弊案后颓废自弃、终日寄情于声色不无关系,落魄才子遇风尘美人,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所以唐寅喜欢表现青楼题材。明王世懋在《王奉常集》评说:“唐伯虎解元于画无所不佳,而尤工美人,在钱舜举、杜柽居之上,盖其生平风流韵多也。”唐寅科场失意后,一度非常痛苦悔恨,“方悔昨朝搬鬼戏”、“何须苦苦用机谋”、“富贵荣华莫强求,强求不出反成羞”等等,都是他用来表达痛悔内心的诗句。其友祝枝山为减轻他的痛苦就带他到风月场所中“散心”,唐寅本是性情疏狂之人,从此,他便经常出入于声色场,借此来麻醉自己。因而,在唐寅的人物画中有不少是描写他所熟悉的声色场所的生活的。为了生计,唐寅还应人所求作过大量色情画,正如清沈德符说:“工此技(按指画春宫图)者,前有唐伯虎,后有仇实甫(英)。”可见不是虚名[1]。
《孟蜀宫妓图》是唐寅人物画中的代表作,此图立轴,绢本,设色,纵124.7厘米,横63.6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画又称《四美图》,由明末汪砢玉《珊瑚网·画录》最早定名,沿用至今,据说画面表现的是五代西蜀后主孟昶的宫廷生活,描绘的是四个宫妓的生活情态。但蜀后主王衍曾自制“甘州曲”歌,形容著道衣的宫妓妩媚之态:“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沦落在风尘。”此画当改为《王蜀宫妓图》为是,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孟蜀宫妓图》里的仕女虽然盛装打扮,身穿华丽的长褂、修裙,但没有生活的背景作衬托,此图用线细如铁丝,挺劲而富有弹性,施色妍丽而不失古雅,衣服上的花纹和她们佩带的饰物刻画精工细致,人物形象端庄娴静,人物安排顾盼相应、疏密有致,最能代表唐寅的人物画的成就。唐寅题词云:“莲花冠子道子衣,日侍君主宴紫微,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斗绿与争绯。”并有后记,曰:“蜀后主每於宫中裹小巾,命宫妓道衣,冠莲花冠,日寻花柳以侍酣宴,蜀之谣已溢耳矣。而主之不挹注之,竟至滥斛,俾后想摇头之,令不无扼腕。唐寅。”下钤“伯虎”、“南京解元”朱文方印二。后记中唐寅表达了对于孟蜀宫妓的“摇头”和“扼腕”,但是宫妓的悲惨境遇又不是唐寅的这首题词所能概括的。画面中的女性都是缠足的,所谓“三寸金莲”,这在唐寅这样的文人看来是一种美,然而对于女性而言,这是一种肉体的摧残。唐寅只是对孟昶骄奢淫逸的生活进行了揭露和讽刺,对女性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但是他认识不到,他所代表的封建文人的审美同样对女性是一种压迫。妓女之悲的深重,是连唐寅这样的风流文人都无法理解的,这不免使这些妓女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1]
《陶谷赠词图》也是唐寅此类人物画作品中比较有名的一幅,选题别有深意。此图立轴,绢本设色,纵168.8厘米,横102.1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陶谷(穀)赠词故事见于《南唐近事》记载。陶谷(穀)(903-971),字秀实,邠州(今陕西彬县)新平人,是北宋初的一位大臣,受命出使南唐时,对南唐君臣居傲无礼,激起了南唐众臣的愤怒,于是暗中谴派宫妓秦若兰到陶谷所住的驿馆去卖唱,以美色诱使陶谷堕落色网。事毕,陶谷写词《风光好》一首赠蒻兰:“好姻缘,恶姻缘,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第二天,陶谷在宴会上又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当秦蒻兰出现时,顿时羞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此图即描绘陶谷在旅舍赠词于秦蒻兰的场面,前者闲坐于席塌之上,旁置笔墨纸砚,暗示他已写完赠词;榻前红烛摇曳,说明此时正是深夜。他双眼直勾勾地对着秦蒻兰,右腿支起,以掌击膝,呈现出打节拍状,当是随着秦蒻兰的演奏而吟唱。画中有诗题曰“当年我作陶承旨,何必尊前面发红”,显然,唐寅画这幅画的目的并非是表现秦蒻兰的才情,也非是描绘她出色的容貌,只是借陶谷讽刺当时士夫阶层中的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假道学。唐寅传世作品中存有大量此类借物言志的人物画,其中不乏描绘青楼女性的作品,但我们从中更多能看到是文人画家们“自恋”式的情感抒发。
曾以画供奉内廷,得赐“画状元”的“江夏派”倡导者吴伟,是戴进之后的浙派名将,他也画过多张反映青楼故事的画作,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武陵春图卷》和《歌舞图》。
吴伟《歌舞图》,立轴纸本墨笔,纵118.9厘米,横64.9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据画幅上唐寅墨款“吴门唐寅题李奴奴歌舞图,时弘治癸亥三月下旬,李奴奴十岁”可知,圈中翩翩起舞者是青楼歌舞妓李奴奴,年方十岁,她娇小玲珑,能歌善舞,四位男士正围坐一圈,欣赏她妙曼的舞姿。其中一位,可能身份比较高,他手托下巴,身旁有二女妓陪坐,一女手持快板,另一女则心不在焉地笼袖而坐,李奴奴当是根据她快板的节奏来跳舞;顺时针第二位男子则面带狎笑,身姿后仰,陶醉地看着舞女;第三位男子仅见背影,然其低首状十分清楚,当也是注目于舞者;第四位则文质彬彬的模样,神情也颇为专注。明代中后期青楼文化的兴盛,吴伟、唐寅等许多仕途失意的画家纷纷饮酒狎妓,试图以酒和色来摆脱失意的郁闷,在纵情中忘却暂时的苦闷。从画幅上方有明祝枝山、唐寅、九华遗士、金庭居士、七一居士、髯九翁六家题跋来看,此作获得了众多文人雅士的青睐。
明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思想界出现了新的动向,文人或多或少的平等和自由思想,形成了对封建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冲击。这些青楼题材绘画作品中的妓女形象也出现了新的特征,在一些作品中,她们不再作为花瓶和载体出现,她们作为人的个性和尊严得到了关注和表现。《武陵春图卷》则当属此类作品。《武陵春图卷》,纸本,墨笔,纵27.5厘米,横93.9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吴伟画艺精湛,曾分别于明成化和弘治年间奉召进京供奉宫廷。但是由于其本人孤傲的个性,最终仍被排斥出朝廷,黯然返回江南,郁闷不得志的吴伟,和唐寅一样,常以饮酒狎妓遣释自己苦闷的心情,因此他们对于青楼女子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也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对于这些女子的无限同情。武陵春本是词牌名,宋代著名女词人曾经写有《武陵春》词。吴伟画中的武陵春,是当时金陵秦淮河的一位名叫齐慧贞名妓的艺名,她能诗善歌,善于鼓琴,并能谱曲,富有文采而有识见。武陵春身陷青楼而保持内心纯洁的心灵,且对爱情仍抱有忠贞不渝之志,据说她与傅生相爱五年,后傅生获罪被徙,慧贞倾其资财营救不得,竟忧郁成疾而死。同时代的金陵著名文士兼画家徐霖写小传歌颂她,吴伟亦深深为之感动,遂援笔作此《武陵春图卷》,以示对齐慧贞的同情与敬仰。画面中,武陵春托腮低首,另一只手中拿着手卷,沉浸在对于傅生无尽的哀婉思恸之中。有意思的是,武陵春身后的石桌上,铺满了笔墨纸砚和古琴,正是暗示了吴伟对其多才多艺的赞叹与感慨。
清代画家陈清远的《李香君小像》,画面上有其题画诗“生小秦淮绝食姿,谁知侠骨在蛾眉。欲将心赠侯公子,只唱琵琶绝妙词。谁上风烟草不春,肯放玉质污流尘。歌残一部桃花扇,羞煞前朝二姓臣。”陈清远对李香君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对于这样一位有绝世之姿又深明大义的奇女子,陈清远表达的不仅仅是赞扬,还有对“前朝二臣”这类人的戏谑,凸显的是李香君作为一种理想寄托的形象。在这里,女性不仅作为平等的人被人同情、被人理解,而且作为一种楷模受到男性尊敬、让男性汗颜。这幅作品有改派仕女画的风格,衣纹刻画的钉头鼠尾描是改派绘画的典型特征。画面中的李香君正捧读书卷,微露悦色,人物形象的才女气质流露无遗。
这些明清青楼题材的绘画作品充分表现了男性文人由于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带来的妇女观的进步。妇女地位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作为男权文化和社会制度的直接受益人,男性文人的妇女观的转变是艰难而又缓慢的过程。在封建道德和传统文化的压制下,人性的觉醒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文明进步的步伐是谁也无法阻挡的,社会的进步必然导致人类自觉意识的苏醒、女性观念的进步。(责任编辑:徐智本)
参考文献:
[1]范银花.旷古才子情——略论唐寅的人物画[J].东南文化,2002,(08):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