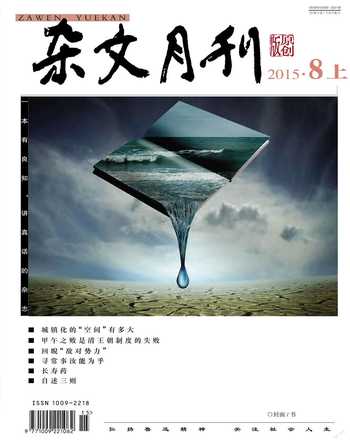莫言说吧
张晓辉
在《说吧莫言》这本散文随笔集里,莫言还真是说了一些真话、人话、内心的话,甚至是雷倒众人的话,不像他写的小说,有点“玄”还带点“虚”,有时要借助他人乃至动物表达自己的心声。故而读这本书还真有点“真刀实枪”的感觉——
他在《酒后絮語》中说:“官员的腐败,是所有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本原因。官员腐败问题得不到控制,制假卖假问题解决不了,社会风气堕落问题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解决不了。连那些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它们的天敌,也是腐败官员。”
在《狗的冤枉》里给某些“牛人”画像,画得生动、形象、逼真:“经过几十年的淘汰,这些‘牛们多半解甲归了田,但也有一些爬到了一定高度,靠着囫囵吞枣学来的那几百个汉字,靠着几十句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者们挂在嘴上的空洞术语,统治着他管辖的部门。这些由‘牛变成的老虎,张口就是‘觉悟‘党性‘组织原则‘作风纪律‘关怀培养,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这些话的真正含义,鹦鹉学舌,瞎叫而已。其实他满脑袋瓜子都是《官场现形记》中那个带着老婆给巡抚大人煮馄饨的小官儿的思维,他对下属颐指气使,对同级脸上带笑脚下使绊子,对上司呢?那就是一只活生生的哈巴狗了!”
在涉及“文革”及“有关人士”上,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突然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打右派的继续,也可以说,当时的作协领导人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推波助澜者,文革初起,他们心里还不知道该有多么高兴呢,但没想到自己也被放倒了。这可是不幸中之大幸,如果这些人在文革中不被打倒,如果他们还浮在上水头,他们整起人来,比‘四人帮还要狠。”进而指出:“大家只批评当时的政治背景,很少涉及到对人性的分析。我看电影《莫扎特》,其中那个阴险嫉妒的宫廷音乐师,就让我联想到作协系统的领导人,那颗被嫉妒的邪火烧灼着的灵魂是多么痛苦啊!还有电影《巴黎圣母院》中那位主教,与作协的领导人是多么相似啊!”(《说老从》)
在《郁达夫的遗骨》中,他更是掷地有声:“我不知道那个用手扼死郁达夫的日本宪兵和那位用刀切断张志新喉管的中国公安哪个更好一点。我也不知道那些在战争时期残杀中国人的日本士兵和那些在‘文革时期残杀自己同乡的中国‘革命群众哪些更坏一些。我认为我们应该痛恨的是战争和发动战争的人,以及至今还不承认有过这样一场侵略战争的人。”
在谈及自己的遭遇时,他有愤怒,也有坚韧的顽强:“因为一部《丰乳肥臀》和‘十万元大奖,使我遭到了空前猛烈的袭击。如果我胆小,早就被那些好汉们吓死了。我知道他们搞的根本不是什么文学批评,所以也就没法子进行反批评。我知道他们一个个手眼通天,其中还有那些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一辈子以整人为业的老前辈给他们出谋划策并充当他们的坚强后盾,我一个小小的写作者哪里会是他们的对手?但我读了鲁迅后感到胆量倍增。鲁迅褒扬的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我没有资格学习,但我有资格学习落水狗的精神。”(《读鲁迅杂感》)
在《虚伪的教育》中,他直抒胸襟:“因为虚伪,我们口是心非;因为虚伪,我们亦人亦鬼;因为虚伪,我们明明爱美人,却把美人说成是洪水猛兽。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虚伪,形成了习惯,使我们把虚伪当成了诚实。”
在《雪天里的蝴蝶》里,他袒露心怀:“我真正的朋友,就像雪天里的蝴蝶一样稀少,而那些恨我的英雄就像夏天里的苍蝇一样多……我是宁愿做了狗屎去肥田,也不愿意被做成脂粉去涂抹英雄们的面孔。”
在关于“作家”和“写作”上,他如此放言:“时至二十世纪末,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不会再去充当吹鼓手或是枪手,他应该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他的写作,他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他苦苦思索的应该是人类的命运,他应该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高密东北乡”的“圣经”——日文版,〈丰乳肥臀〉后记》)
最后,他不无谦逊地说:“我对自己的写作,一向是缺少自信,惟一自信的是:我写作的态度是真诚的。”(《我写作的态度是真诚的——〈莫言短篇小说全集〉前言》)
这些精粹的语言或片段,犹如暗夜中的火光,照亮了主人也照亮了我们。
说吧莫言,我们继续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