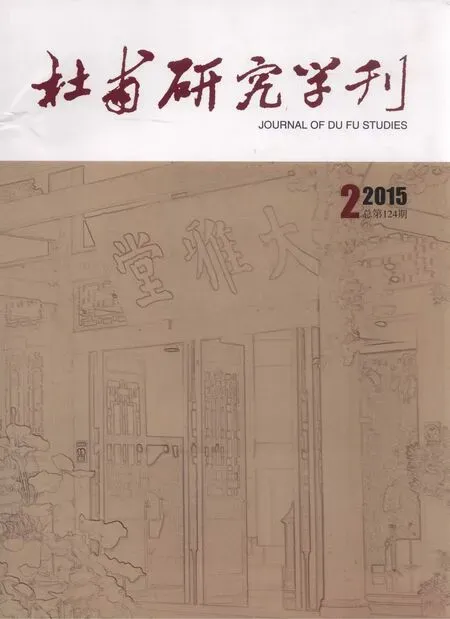杜甫《收京三首》作年考辩
卢本德
作者:卢本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王洙编刊杜诗以来,历代杜诗注本几乎都认为《收京三首》写于至德二年(757)、或乾元元年(758)安史叛军东奔、肃宗皇帝收复两京这一时间段。三首的每一首到底作于何时,学者不无异议。但是,这个传统的编年,一千年来几乎一直被普遍认可,应该算比较确定,不能轻易推翻。
然而,宋代学者蔡兴宗(即蔡伯世,生卒年不详)在他作的杜甫《年谱》(或作《诗谱》)曰: 《收京三首》,王洙等“编作凤翔行在诗(即至德二年间诗),尤为差误”,将该组诗看为杜甫在阆州得知代宗皇帝收复了西京的广德二年(763)春写的。蔡生或许误会了旧说(一般来讲,学者认为该组诗写于杜甫到鄜州省家时作,不是在凤翔行在作),但是无论如何,笔者认为该组诗的内容确实有几点与至德二年、乾元元年间的史实不相符合。在这几点上,蔡兴宗的广德二年编年似乎更妥。
《收京三首》原文如下:
(宋百家本作收京四首,附《收京》(复道收京邑),按,此诗作于广德二年无疑)
仙仗离丹极,妖星照(一作带)玉除。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这两句,一作得非群盗起,难作九重居,一作得非群盗杀,之作九重居)。暂屈汾阳驾,聊飞燕将书。依然七庙略,更与万方初。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羽翼怀(一作慙)商老,文思忆帝尧。叨逢罪己(一作巳,误)日,沾洒(一作灑涕,一作洒涕)望青霄。
汗(一作江,误)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杕(一作枤)杜,归(一作福)及荐樱桃。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一作同)送喜,无乃圣躬劳。
一、叨逢罪己日
笔者之所以开始怀疑这首组诗的写作年代,是因为不清楚“罪己日”的含义。《收京三首》其二有“忽闻哀痛诏”之句当中,所谓的“罪己日,”应该指“圣明朝”所下诏令的内容吧。问题是,杜甫说的诏书是否存在?一些很有权威的近代学者,比如陈贻焮先生在他《杜甫评传》、萧涤非、张忠纲诸先生2014 年新出版的《杜甫全集校注》,在这个问题上接受仇兆鳌的说法,认为杜甫指的是至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壬申(即757年12月13日)肃宗所下的《御丹凤楼大赦制》。
但是,这个说法有较为明显的问题。《收京三首》其二的首联明确表明,诗人得知这个诏令时,并不在长安。关于这个问题,仇兆鳌曰:
此当是至德二载十月在鄜州时作。诗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此明是在家闻诏。按肃宗于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甲子,即位灵武,制书大赦。二年十月十九日,帝还京。十月二十八日壬申,御丹凤楼,下制。前后两次闻诏,故云又下也。是时公尚在鄜州,其至京,当在十一月,年谱谓十月扈从还京,与诗不合,当以公诗为正。至于上皇回京,十二月甲寅之赦,又在其后,旧注错引。
仇兆鳌提出年谱“与诗不合,当以公诗为正”的原则,很有道理。问题是,仇兆鳌自己在别的地方也承认杜甫曾经说他“十月扈从还京。”比如《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的“法驾还双阙,王师下八川。此时沾奉引,佳气拂周旋”几句,仇注曰:“奉引,公为扈从。”杜甫此时扈从,也可以旁引另外一点证据,乾元元年《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其一曰:“去岁兹辰捧御床,五更三点入鹓行”、其二曰: “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至德二载冬至是在十一月六日左右,从肃宗颁布《御丹凤楼大赦制》到那一天,只有八天。既然鄜州离长安有两百五十公里左右,赦文要往、诗人要来,这八天时间显然太短。
第一位反驳以《御丹凤楼大赦制》为“哀痛诏”说法的应该是洪业先生。洪业认为,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公元757年12月8日)肃宗到达长安之前,杜甫早已回到了凤翔扈从皇帝还京。洪业因此在《唐大诏令集》找了比较早的诏书来填补杜诗“哀痛诏”的空白。与独立研究这个问题的台湾学者廖美玉一样,洪业找到了肃宗在至德二年十月颁布的《收复西京还京诏》,其原文如下:
圣人有作,弧矢爰兴。历代已来,征伐靡废。自敌人已死,馀孽犹存。所统蕃人,多以利合,亦有因事,便被胁从。朕誓雪国仇,余无所问,中夜痛愤,志安苍生。其假息偷生,据城自守,鼎鱼幕燕,何以喻慈?广平王及各诸将分队夹攻,迎军破败,横尸遍野,积甲如山,二十里内,可知多少!其中逼迫,同被杀伤,言念於兹,良深悯悼。今兵马乘胜,便取东京,平庐节度兼领契丹五万,又收河北。天下之事,计日可平。缘京城初收,在安百姓,又扫洒宫阙,奉迎上皇。以今月十九日还京,应缘供顿,务须减省,岂忘艰弊,当别优赏,宣示百姓,令知朕怀。
洪业、廖美玉把这道诏书看为杜诗提到的“哀痛诏”,并非是不可能的。但笔者还是有点怀疑。若杜甫真的是与肃宗一起回长安的,他恐怕是不可能在鄜州羌村听到这道诏令。上面已经提出,羌村(即今陕西富县)在长安北边两百五十公里左右,离凤翔有三百多公里,而鄜州与长安、凤翔两个地方之间,山川重阻。这道诏书也不知道何时颁布:肃宗是九月最后一天才得知广平王李俶已经收复了京师,即使他在第二天立即颁布这道诏令,估计诏书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传播到鄜州(而且鄜州是个小地方,当时还属于危机的状况,传播可能会慢一点);再说,杜甫听到了诏令之后,他也需要走十来天才能到长安,何况是远在凤翔。从朝廷得知京师被收复的时候,到肃宗亲自到达长安的那个日子,仅仅二十三天。洪业与廖美玉要我们相信,肃宗颁布这道诏书之后,诏文被尽快传播到杜甫所在的鄜州,而此后,诗人赶路到凤翔、长安之间去扈从肃宗还京,而这些都在短短的三个星期之内,应该说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但也不是很大。
即便如此,笔者还是认为洪业与廖美玉这个说法的最大问题不是时间,而是该道诏令“哀痛”之意并不强烈、“罪己”的内容基本上是找不到的。其实,这一点也是理所当然:安禄山反叛是在肃宗即位之前,肃宗与杜甫所责备的杨国忠从来就不是同党,而且肃宗即位之后没有很大的、公认的失政 (虽说杜甫已经对他有些不满),所以他毫无理由在收复京师的时候责备自己。按,“罪己日”是含有典故的,《左传·庄公十一年》曰:“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如果说“罪己”的意思只是“不罪人”,那么以仇兆鳌、陈贻焮、萧涤非诸家所引的《御丹凤楼大赦制》为“罪己”大致可以说得通。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杜甫不可能是在“天涯”听到的。

更重要的是,郭子仪收复了京师后,代宗下了几道含有自责的诏令。比如,在广德二年二月二十日戊子(公元764年3月27日)颁布的《南郊赦文》,代宗曰:


自凶孽乱常,王室多难。干戈不息,今已十年。军国务繁,关辅尤剧。念兹疲耗,久困征科……征人不息,勤戍斯久。丁壮疲弊,老弱困穷。光武有言,头须为白(按,后汉书载光武帝《勑彭书》曰“每一发兵,头须为白”)。戢藏锋刃,牧养元元。方面重臣,宜悉朕意。应诸州团练将士等,委本道节度及诸防御使等审与州府商议,如地非要害,无所防虞,其团练人等,并放营农休息。寇戎以来,积有年岁,征求数广,雕弊转深。自今已后,除正租税及正敕,并度支符外,余一切不在征科限。
杜甫在《释闷》一首中已经说了“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应该会见到代宗返京之后的举止而稍微感到欢喜。
笔者以为,《南郊赦文》有可能就是《收京三首》所指的“哀痛诏”。但即使这道诏令不是杜甫所说的,代宗在这个时间段所下的现存诏令基本上都很相似,罪己之词往往而有。比方广德三年正月的《改元永泰赦文》:

这道诏令太晚,不可能是杜甫《收京三首》所说的。但是,它能代表代宗广德二、三年间诏文的共同主旨。而这些主旨与肃宗至德二年收复两京之后的诏令截然不同。杜甫所听到的诏令也有可能已经遗失(《唐大诏令集》平乱部没载广德年间诏书,按例当时应该有),但无论如何,较至德年间的诏书来讲,广德年间的更可能含有“罪己”的内容。
二、归及荐樱桃
较旧说引的肃宗皇帝《收复西京还京诏》、《御丹凤楼大赦制》两道诏书,《南郊赦文》还有一个优点:它颁布季节(即二月,春天)与《收京三首》其三中的“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杕杜,归及荐樱桃”四句更为契合一些。广德元年冬、二年春,杜甫屡次往来颇为偏僻的阆州、梓州之间,离长安有五百多公里,一路都是山,信息传播很慢。虽然郭子仪早在广德元年十月二十一日(763年11月30日)收复了长安,代宗在十二月十九日(764 年1 月26日)返京,杜甫当时写的几首诗证明,他等到春天才听到这个消息。《巴西闻收宫阙送班司马入京》一首曰: “剑外春天远,巴西敕使稀,”可以确定杜甫在春天才“闻收宫阙”(但应该注意,这首诗有的早期杜诗刊本阙,或许是伪托的)。同样,杜甫写《城上》一首时,诗人还未听喜讯,就写了“风吹花片片,春动水茫茫。八骏随天子,群臣从武皇。遥闻出巡守,早晚遍遐荒。”《伤春五首》下,宋代《九家本》载早期注文曰:“巴阆僻远,伤春罢,始知春前已收宫阙,”虽然注文不一定是杜甫的原注, 《伤春五首》中的“烟尘昏御道,耆旧把天衣。行在诸军阙,来朝大将稀”几句、“再有朝廷乱,难知消息真。近传王在洛,复道使归秦”几句,都可以证明诗人等到至德二年深春才得知京师早已被收复。赦文一般传播得很广泛,杜甫在偏僻的阆州由《南郊赦文》而得知这个消息,也不是不可能。
相反,旧说引的《收复西京还京诏》、 《御丹凤楼大赦制》两道诏书与《收京三首》其三的春景不甚相合。该首仇兆鳌注曰: “宫阙已收,贼壕可铲,赏功荐庙,即在来春”,这一点,廖美玉赞同,说第三首都是“预设之词”。杜甫在收京之前写《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云:“家家卖钗钏,只待献春醪”,而在到达京师之后写《腊日》 (腊日是农历十二月八号)曰:“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好像都是以春喻中兴、更初之意。那么,说他在《收京三首》是预想春天的事情,大致可以说得通。但是,我还觉得这个解释有一点令人不满意。按,《月令》当中,天子“羞以含桃,先荐寝庙”是仲夏(即五月)事。杜甫自鄜州到达长安的时间应该在十月下旬左右,到明年五月份还有半年多。若是杜甫听到的诏令是洪业与廖美玉所引的《收复西京还京诏》,他就会知道肃宗本来打算在十月“十九日还京”。笔者因此想不到他为什么会说要等两个多月才开始铲贼壕,等六个多月再赏功荐庙,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春天、夏天还会有“万方频送喜”的事情。另外,若是杜甫、肃宗、朝廷、功臣都在十月份要到达京师,“归及荐樱桃”句中的“及”字写得似乎不是很准确。

因此,笔者以为黄鹤、黄生之说显然不如仇兆鳌、廖美玉这种比较主流的说法。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黄鹤、黄生这些很有眼光的学者提出这样勉强说法是有理由的。若是这组诗果然是在至德二年冬写的,第三首整篇(除了第一句之外)都是预设之词,包括尾联的“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注家这里多引《诗经·硕人》:“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意思好像是杜甫焦虑皇帝会因为需要接见万方使者而觉得累。如果这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说,章法实在很独特。笔者因此以为,将《收京三首》看为广德二年的作品是个较为简单的解释。与其说第三首是预想几个月之后的情况,似乎不如看作是杜甫在远处想象当时在长安举行的典礼。此时,杜甫已经有一次经历过刚收复了京师的春天,所以他知道皇帝“应”怎么赏功臣,也记得当时收到的樱桃(此事,参见《野人送朱樱》一首)。其实,这样看第三首,似乎更有意味。
三、天涯正寂寥
再说,这样看第三首也更符合第二首的语气,特别是首联的“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要是把这组诗看为至德二年间的作品,总觉得诗人说自己“甘衰白”、以鄜州为“天涯,”都有一些夸张。其实,杜集中没有别的诗文把鄜州或者接近的地方号为“天涯”、 “天边”等。虽然至德二载冬杜甫因为替房琯辩护而受罪的事件已发生,对于肃宗已经感觉有点失望,但是他毕竟还要返朝为官。到羌村省家本来就是短暂的事情而已,诗人在此时不应该强调“贫病他乡老”(763 年杜甫在梓州时作的《广州段功曹到得杨五长史书功曹却归聊寄此诗》中语)的意思吧。
说起第二首,旧说这边也另外有问题。据《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的内容,可以断定至德二载,杜甫在《收复西京还京诏》颁布之前已经听到了唐军快要收复京师这个消息,应该已经有心理准备。那么,第二首的“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中为什么会用“忽”字表达突然、吃惊的意思?再说,下句中的“又”字也一直对于旧说是一个难题,众说纷纭。之前下的“哀痛诏”或以为指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甲子肃宗即位时颁布的赦文,或以为是天宝十五年八月一日玄宗下的《銮驾到蜀大赦制》。这两个解释并不为不可能,但是,至德二年十月的《收复西京还京诏》毕竟不是赦文,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到它的时候杜甫会联想到这两道诏书。
反而,若是我们将《收京三首》看为广德二年的作品,这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杜甫觉得“哀痛诏”来的很“忽”是因为他在偏僻的阆州,好久没有得知朝廷的消息了。诏令为什么“又”自圣明朝下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这是唐朝第二次收复京师。杜甫在远处还记得当时扈从皇帝还京、含桃荐庙事等等,却这次他在“天涯”似的阆州(杜诗中对于广德年间所在的蜀、巴,“天涯”、 “天边”这样的代称经常出现)“贫病他乡老”。笔者以为,若是把这组诗定为广德二年的作品,我们不难以看出第二、三首喜中含悲。
四、难题

但即使蔡说能解决旧说的几个问题,它也有一些缺点。最明显的应该是第一首颈联,“暂屈汾阳驾,聊飞燕将书”。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燕将攻下聊城……齐田单攻聊城岁余,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燕将见鲁连书,泣三日……乃自杀。”安禄山基地在古燕国土,将自己的皇朝号作“燕”,以“燕将”指叛军在长安的领导,甚合。但是,把该句看为广德年间所作,估计也可以说得通。杜甫在《渔阳》一首又用了同样典故,曰:“系书请问燕耆旧,今日何须十万兵。”这里,典故含有双重意思:一方面确实是地方相合,另一方面是胜利很容易,不需要用很多士兵就可以打败敌人。而这方面,较至德年间,皇帝已经在外快两年了,似乎与吐蕃陷京、郭子仪收京的情况更合:

郭子仪不战而胜,很符合用鲁仲连的策略来表达,而且吐蕃陷京仅仅十二天,皇帝在外的确是非常短“暂”的。
其实,这样看此联,也可以免除传统说法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暂屈汾阳驾,”是指玄宗还是肃宗?若是该诗写于至德年间,“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应该指玄宗,而“依然七庙略,更与万方初”应该指肃宗,那么,“暂屈汾阳驾”指谁?在这个话题,注家众说纷纭。此外,不妨注意一下,宝应元年春(762)郭子仪被封汾阳王,吐蕃侵犯之前闲废日久,杜甫曰“暂屈汾阳驾,”用《庄子·逍遥游》尧“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一事,是把郭子仪视为藐姑射之山的四子之一吗?此处笔者不敢肯定,但无论如何,杜诗广德一、二年间屡次体现与“汾阳驾”相似的说法,比如《释闷》当中的“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湖城”和《城上》“八骏随天子,群臣从武皇。遥闻出巡守,早晚遍遐荒。”
另外一个难题就更复杂一点。第二首颈联,“羽翼怀商老,文思忆帝尧”的“商老”(即秦末汉初四皓)、“帝尧”指的是谁呢?用蔡说,的确有点难以落实。其实,旧解也是众说纷纭,“商老”或为裴冕、杜鸿渐、或为郭子仪、或为李泌、或为广泛指扈从老臣、或为天宝年间保护李亨的诸人;“帝尧”,或为玄宗(因为让位给肃宗)、或为上古帝尧(说肃宗文采相似)。众说,很多都可以说通,难免感觉有点含糊。今按,用“商老”典故的杜诗总有六首,除此诗外,都泛指乱世中贤隐者,好像都没有具体时事对象(参见《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洗兵马》、《闻惠子过东溪》、《北风》、《幽人》等诗)。或许这一例也是如此,用“商老”指在外的贤人,比如杜甫自己。首联说诗人“衰白”在“天涯”,颈联提到“商老”,应该不会完全偶然了吧。
用“商老”比喻自己年老在外的情况,并非全无根据。广德一、二年间诗屡次表现出返回朝廷的希望,比如《伤春五首》其三“行在诸军阙,来朝大将稀。贤多隐屠钓,王肯载同归”、《巴西闻收宫阙送班司马入京》“黄阁长司谏,丹墀有故人。向来论社稷,为话涕沾巾”(此或求汲引)、《奉寄章十侍御》“朝觐从容问幽仄,勿云江汉有垂纶” (盖为反言)。广德元年,代宗招房琯回长安,拜他为特进、刑部尚书,又废了程元振,杜甫也许此时开始希望自己或他的朋友可能会有机会再次入仕。那么,“羽翼怀商老”有可能是说杜甫希望收京后代宗肯带“隐屠钓”的贤人“同归”。那样,“文思忆帝尧”或许没有时事对象,简单说皇帝所下的诏书的“文思”让杜甫忆念写《尧典》的帝尧。以之对“怀商老”,杜甫或表现他希望为像尧的皇帝出仕作老臣。我承认,这个解释固然不能确定,但是在该组诗的逻辑结构上,不逊于旧说种种解释吧。
五、结语
最后,不妨提到一下诗体问题。杜甫奔走秦州前,以政事为主题的律诗很少(姑且不谈隐微地提到政事的诗),基本上只有《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一首与一些赠答诗(比如《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 《送灵州李判官》等),而这些大部分为排律,不完全一样。此时,杜甫写政治主题一般是用古诗的,而除排律外,其律诗一般提到政治话题就含糊一点,比如《对雪》的“战哭多新鬼”、 《送灵州李判官》的“血战乾坤赤,氛迷日月黄”等等。具体讨论政事的律诗,杜甫入蜀后才真正形成。前面几次提到的《伤春五首》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例子。
笔者以为这一点证据可以支持蔡说的可能性,但是,与上面提到的几点同样,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该组诗写于至德二年还是广德二年,我想,可能没有确凿的证据,两种观点都可以说通。我承认,我自己还是有一点先入为主,觉得如果至德二年的编年可以说通,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将此组诗看为此时作。笔者这里只不过是想证明旧说确实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蔡说也是可以成立的,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
注释:
①蔡志超校注:《宋代杜甫年谱五种校注》,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版,第40 页。

③陈贻焮著:《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56—360 页。
⑤按,这个日子有异说。《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等本子云十一月壬申,但至德二载十一月没有壬申。此据《资治通鉴》改。
⑥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458 页。

⑧William Hung 洪业著:《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年版,第120 页。
⑨廖美玉撰:《论杜甫之收京三首》, 《东海中文学报》1982 年2 期。
⑩宋敏求编,洪丕谟点校:《唐大诏令集》卷123,学林出版社1992 年版,第60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