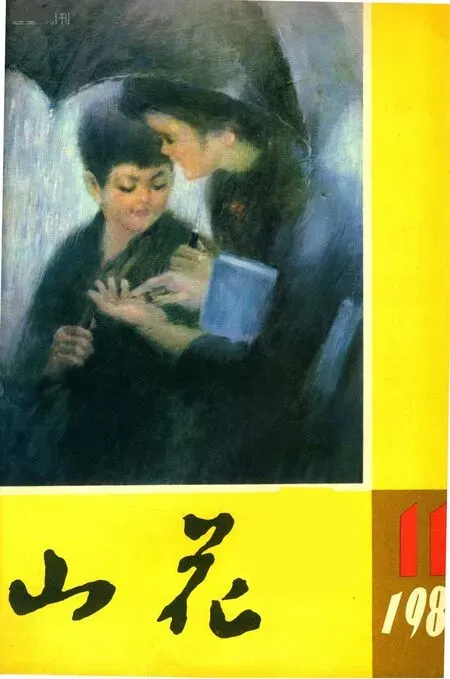哈拉哈河的硝烟记忆(外两篇)
郭雪波
哈拉哈河的硝烟记忆
它,就那么流淌着,静静的,哈拉哈河。
苍茫的大兴安岭,如慈母挤奶汁从其西坡摩天岭溢出它时,便赋予了一层神秘色彩,一则悲悯故事:说很久前,西岭上一个叫达尔滨的猎户少年为保护幼弟与狼搏斗而死,其母为唤醒儿子不停地挤出自己鲜奶洗他眼睛,传说母亲乳汁洗眼可让儿子复活,那位母亲就这样不停地挤呀洗呀,开始流出的是奶,后来流出的是血……最后她昏倒在草地上。不久被一阵哗啦啦的流水声唤醒,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正从她身边流过,丈夫告诉她,达尔滨终未能睁开眼睛,但她感动了长生天,把她挤出的奶汁变成了这条悠长的河流,儿子达尔滨漂在河上流向了遥远的天堂。这就是哈拉哈河的故事,一条由母亲乳汁酿成的河。
哈拉哈,人们解释是“哈拉哈拉克”词的简化,意思为“屏障”,因河的西岸比东岸高出很多如一条屏障。可我愿意这样解释,哈拉哈这词是“哈日哈”的变音,遥望之意,母亲在遥望远逝的儿子归来,也隐喻母亲拿乳汁洗儿子“哈日哈-尼都”——视觉眼睛,这应和了那则古老动人的传说。
或许,母亲的奶水是诚挚炽热的,哈拉哈河从摩天岭达尔滨湖起源后,从三潭峡到金江沟约二十公里长的河段冬季不结冰,成为闻名的不冻河,零下三十度河面上依然升腾着柔曼的淡雾,透着夕阳的余晖;或许,母亲的乳汁是圣洁的,不便太久地晒露在外,哈拉哈河流进阿尔山火山熔岩地段后,河水突然不见踪影,变成一条暗河,完全潜入地下,人们只听见潺潺流水声,却不见河水在哪里流淌。你会突然觉得,这条河似乎在跟你捉迷藏,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轻轻唱着歌,像一个少女吸引你去追逐她,捉住她。
离开了熔岩地带,哈拉哈河便开始如摆脱羁绊的小鹿般在草原上奔驰了,又汇集苏呼河和古尔班河等支流,由东向西浩浩荡荡流入蒙古国境内去了。在那片广袤富饶的草原上,她孕育了蒙古哈拉哈部落,至今执掌着蒙古国,史书也称那里为哈拉哈-蒙古利亚。它又是条很执着的河,寻寻觅觅,依地理蜿蜒而去自由奔流,从那里又拐向北方,中间在新巴尔虎左旗的阿木古郎镇南成为中蒙界河,注入贝尔湖,而后又经乌逊河转入呼伦湖,再经达兰额莫勒河汇入著名的额尔古纳河,归向最终的目的地大海。
“一条河的经历,即是一部史书”。
这是我静静站立在哈拉哈河岸上,面对着一片叫诺门罕-布日特的地方时,脑子里突然出现的词句。七十五年前,有个叫双喜的十七岁蒙古男孩,骑着马来到这里打了一仗,他参加的那场战争史书称为“诺门罕战役”。这个十七岁男孩,本该呆在八百里之外的老家库伦旗乡下,第二年到十八岁时迎娶十七岁的媳妇,过个普通百姓过的平常日子的。可偏偏遇上被赶出北京皇宫的溥仪被日本人又扶上马搞出个满洲国,从东蒙地带抓来偌多蒙古青年当他的“伪满国骑兵”,他就懵懵懂懂被征来了,往他怀里塞了一杆短马枪,又牵给他一匹马,为一位叫德勒格的副团长当勤务兵。当他寸步不离地跟随副团长后边,冒着滚滚硝烟,驰骋在这条哈拉哈河岸上时,才发现眼前的这条河与他老家的养息牧河是多么的相似啊!一样的长着茂密的芦苇草,野鸭在游进游出,水清澈得如镜子,鱼在水里嬉戏时连家狗都看得发呆,美丽得都让人心疼。当一发炮弹炸飞了河里一群野鸭时,他才从想家的思念中猛醒,感觉到这是在打仗,日本人在同河对面的蒙古国军和苏联红军在玩命,拉来他们这些“满洲国骑兵”垫背,叫他们在蒙古同胞间相残。这时他的父亲般慈爱的团长德勒格正在朝他吼,你小子,别再想没过门的媳妇了,快躲在那棵树后头,把脑袋放低点!
这是1939年夏天发生的故事。日本东京大本营正为“北进”配合德国合围苏联,还是南下太平洋打美国而犹豫不决时,哈拉哈河对岸蒙古国边防军过河来放牧,当时国界有争议,日本人便以此为借口,拉开了诺门罕战争的序幕。这里地名全称叫“诺门罕·布日特”,诺门罕是“诺么”一词的变化音,意思是经书,早先有一位喇嘛从西藏来此念经传佛而得名,布日特是小水泡子。谁曾想,多年后在这个诵经拜佛的和善安宁之地,跑来两个毫不相干的国家日本和苏联,流血打仗,撕裂了这里美丽的草地,硝烟弥漫了蓝色的天空,河水在战火中呜咽。
那位十七岁青年双喜,很多年之后离开人世时也没搞懂这是为什么,“诺门罕战役”历史意义又是什么。他只知道,日本人让他们朝河对岸蒙古同胞开枪,他们这些伪满骑兵不情愿,都朝天放空枪,对面的蒙古军人也如此。日本人很坏,打不过对面那个叫朱可夫的苏联将军,死了上万人,急眼了,就让那个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往这哈拉哈河里投放鼠疫和炭疽病菌等细菌,结果没毒着对面苏蒙军,反而让自己1340名日军染上伤寒赤痢和霍乱,军医和敢死队员被自己细菌传染亡命达四十多人。历史真的很吊诡。
十七岁小骑兵双喜的团队,遭遇就惨了。不能真打,又瞒不过日本人,骑兵团开始“溃败”,开小差,甚至整排整连地脱离战场,有的干脆投到对面去了。日本人欺骗从战场“溃散”的骑兵团官兵,只要回来不追究,官复原职等,结果回去的人都被秘密枪决了。十七岁的双喜跟随父亲般的德勒格副团长,从轰隆隆的坦克阵中左冲右突,最后向河对岸奔驰时,一发炮弹附近爆炸,他从马背上摔落下来,晕过去了。醒来时已经是黑夜,团长和军队不知在哪里,一双眼睛一时什么也看不见,脸上淌血,耳鸣不已,头如炸裂般的疼。恐惧中他不管东西南北地狂跑了一夜,天亮后继续向南边的方向跑,他只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南边,在遥远的南边。
很多很多年后,他对他的儿子——我,不无愧疚地这样说,从那次,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般的团长德勒格,再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当“逃兵”东躲西藏也没有再回去,只知道他是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布敦哈拉根屯人,就这些了。我安慰他说,没有关系,只要有人名地址就好办,我帮你慢慢打听打听。很多时候,我真分不清偶然、赶巧、机缘这几个词的区别在哪里,冥冥中总觉着有个看不见的神般机运安排着一些事情让你遭遇。又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我被下放到那个科左后旗锻炼,离开时带走了一套当地地方志《旗志》,当时也没有读它,后来写《青旗嘎达梅林》时需查阅资料,便翻开了那套厚厚上百万字的科左后旗《旗志》。于是奇迹发生了,上边一处人物栏里赫然记录着:德勒格,科左后旗布敦哈拉根人,诺门罕战争时为伪满洲国兴安师骑兵团少校副团长,于1939年7月8日带领部属杀死日本官兵数人,同旺吉拉上尉一起投奔苏蒙红军。后二人同蒙古国上尉宾巴一起受蒙古人民革命党派遣,潜回内蒙古东部地区开展推翻伪满洲国革命活动,不幸被捕,被杀害于新京(1941年)。
我掩卷长叹。得来毫不费功夫,只可惜,此时老父已上天堂有几年,无法再告知他的父亲般老团长的如此经历和悲壮结局了。人世两茫茫。
哈拉哈河在一旁静静流淌。一切都远去,如她的清流。
斜阳暖暖地照着,习习凉风吹过时带来了草原的花草清香,远处有牧歌传荡,雪白色羊群在哈拉哈河岸上悠闲地吃草。老鹰的影子从空中掠过,无边的空阔让它的身影变得那么渺小,一个黑点。四周很安静,都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有只小翠鸟落在近处树上久久不肯离去,也不啼叫。
我甚至有些怀疑,难道这里真的发生过那场战争吗?那场决定二战趋势,导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辞职、前线总指挥小松原因败病死、参谋长冈本双腿被斩断、日本人被迫停战求和、承认诺门罕之役是“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的大战,真的在这里发生过吗?
可是,似乎一切并未远去。旁边高高矗立着一座纪念碑:诺门罕战争纪念馆。造型恰如一部从不合起的立体书卷,一本无比厚重的史书,远近还摆着好多破旧坦克残骸。战史资料如此评介这场战役:致使日本放弃“北进”转而“南下”,确保苏联东部安定全力迎战西边纳粹德国,迅速扭转战局,在莫斯科战役关键时刻抽走远东20个亚洲师投入欧洲战场,起到了扭转乾坤的决定性作用。相对于二次大战其他战役,诺门罕战役虽说是不为经传的战事,但它对二战局势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南下”偷袭珍珠港,不但失去了与德国在远东会师的机会,使自己陷入不能支撑的太平洋战役,并将美国拖入战争使得二战格局由此发生根本性逆转。
哦,是的,可能是这样。只是对于这些,那位十七岁小骑兵双喜毫不知情也并不在意,逃回家第二年便如愿娶了十七岁的我娘,过上普通农牧民的平常日子,只是遭遇每次运动时都要好好交代一番而已。如今,他的儿子我,站立在自己父亲当年十七岁时奋战奔驰过的哈拉哈河岸上,心中不免感慨。战争是人类权势集团的游戏,流的却是普通百姓的鲜血,尤其是大好青年人的鲜血。人类种族的血液里,总流淌着一股邪恶的血,在一定轮回的时候这股邪恶的血便要冒出来。望着纪念馆门前那座大警钟,我似乎隐隐听见东边和西边的磨刀之声,牙齿在黑暗中吱吱切磨之声。
从暗黑的纪念馆走出来,突然感觉外边的太阳那么的灿烂,和平的草原那么迷人。
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安宁生活如蜜般在这里流淌。
可是我似乎依稀看见,一个十七岁男孩骑马挎枪在远处奔驰,炮火中不知呼喊着什么。
我身上一阵颤栗。
那片神秘的历史后院
呼伦贝尔,历史的后院。大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如是说。
在茫茫草海和围栏铁丝中,乘坐的越野车左冲右突时,我犹闻从嘎仙洞出发的鲜卑铁骑向中原方向呼啸而过,去开辟魏晋辉煌;淡淡岚雾中时隐时现的额尔古纳河克鲁伦河缓缓流淌,我依稀看见一个英雄的身影,一个奔忙的身影——那是正在为统一北方诸部而奋战的铁木真;还有东胡火光,柔然猎鹰——在眼前一一闪过。
我们的三辆车,驰过一片因雨水汪洋而成为沼泽的鄂温克人牧场之后,便在这历史的后院中迷失了方向。若有若无且算做是一条路的那个痕迹,早已悄然隐没在疯长的小羊草紫花苜蓿针茅草丛中,消失在从天上下来滋润它们的甘露水泽下。带路的那辆车,业已陷在乌泥中爆胎遗留在后边,继续前行的两辆车此时面对茫茫四周,迷惘而更不知去往何方了。就如面对历史,面对经前人无数次反复重修过的历史,再知识渊博的史家都会感到手足无措一样,我们一行草原人因寻一座古迹而却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在这茫茫的被称之为历史后院的自家草原上,迷失了方向。头顶上有鸿雁飞鸣,似在发出嘲笑。
只能说,这历史的后院,实在是太大,太浩茫了。苦了我们这些幼稚的历史后人。
不像希腊神殿,用工匠石泥,把自己的历史竖起来,至今残缺地显摆在那里。
不像中原文化,以诗词歌赋,把三五千年历史书写在秀岩绝壁或祠庙古籍之上,虽修之再修依然斑驳中显出灿烂。
而草原游牧人的历史在哪里?
历史的后院,竟然几乎看不到历史的痕迹。没有高竖的断壁残垣,没有烟熏的千年古刹,白云千载空悠悠。只有漫漫的风吹过,长长的雁阵飞过,原上的草绿了又黄了,黄了又绿了,马蹄铁上刻留了无尽的风霜。是啊,游牧人似乎不屑于动石弄泥封赏自己,也不擅长编写史书抒发自己,编了再修修了再编不断往复好辛苦。游牧人也就偶尔在岩壁上,酒后拿马刀刻划几下,记一记射的虎养的鹿放的马,或者荒草中丢弃两个不识岁月的扁脸石人罢了。如此写意式随便,就已穿越了数千数万年的风尘。
哦,游牧人的历史。就像风一样自由,雨一样自然,散漫于天地之间。
正因如此,伯赞老才称之为历史的后院吧。前院讲厅堂,后院讲储藏。储藏在岁月风尘中,不显山不露水,无声无息。
斯仁巴图教授是个土生土长的鄂温克人,人谦和又有诗人的气质。他下车向一座雪白如云朵的蒙古包走去,准备把我们从这后院的迷茫中解救出来。那家的狗冲他一阵叫后突然摇尾巴了。回来后笑咪咪地告诉说,这是我弟弟家,那个送他出来的脸蛋紫红少妇是他弟媳。她朝西南方向比划,我们也看懂了。
车在他勤劳的弟弟和弟媳围起的铁丝网草场上,转了几圈出不来,草原上如今全被这种铁的蜘蛛网罩住,好似无边的迷魂阵。同样是鄂温克人的旗文联主席苏伦高娃笑他,是否回去再问一下你弟媳?她是个很有智慧的年轻女性,斯仁巴图依然温和地笑答,不用,前边那座包是叔叔家,拉上他直接带我们去就是。苏伦高娃下车去拉开了围网栅栏门,车如出洞的兔子,直奔已从雾中显现的巴音乌拉山而去。不必劳驾他叔叔了,因为那座神秘的小山前面就是此行的目的地。它,不仅藏在后院,还埋在后院的地底下。
此时,耳畔犹响古曲: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公元1221年春,也是这样烟雨迷濛的天,一个身影在这里踽踽独行。
他是关内道家丘处机,长春真人。西行觐见西域作战的成吉思汗前,先来这里拜见监国铁木格-斡惕赤斤,领取西行路条符牌。史书记载他行程:“渡河(哈拉哈河),北行三日。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帐下。七日见。复自斡惕赤斤大帐西行五日,乃至呼伦湖。”。斡辰即斡惕赤斤,乃成吉思汗幼弟,在老家侍奉老母守护祖宗火种。他是老“嘎达”,蒙古人把最小男孩称“斡惕赤斤”,准确发音是“斡特根”,《蒙古秘史》把“特根”拼写成“赤斤”是有误。“斡特根”还有一层含意是“承袭灶火最小儿子”。因而受宠,称他为“早行睡的,晚行起的”,封赏的领地广,属民达万户。
如今,丘真人的足迹和那三座王宫金帐,皆已湮没在历史风尘中,一片汪洋都不见。巴音乌拉山前的辉河南岸,茫茫绿草滩上,连个城池残垣都未能留下。斯仁巴图教授默默告诉我,其实并没有消失,都埋在地底下。
果然,一条鼓凸的绿色草岗式脊背,绵亘方圆几里,环如龙脊。中部草洼处,有狼洞和盗墓贼挖留的深坑,依稀可见古瓦碎陶。唯一见证历史的似如大殿柱子的底盘,尚露在苦艾丛中,由生铁铸就锈迹斑斑,风蚀虫啃后布满麻坑。如一本沉重无比的帝国史。无人知晓古城何时颓然沉埋于地底,也无任何片字记载。战火?还是斡惕赤斤作为东部叔王们首领,曾南征高丽及参与灭金,故而整个部族南迁弃此而去?现在只能想象,丘真人拜见斡惕赤斤和国母诃额伦夫人时这里是何等金碧辉煌和隆重热闹。
把历史埋在地底,倒是符合后院的称呼。走过就走过了,做过就做过了,不纠缠往日,无论辉煌或没落。依然故我如牧草般绿了黄了黄了绿了,与大自然同在,这就是大开大合的北方游牧人,一切性情使然。其实,历史沉在地底挺好的,更显其珍贵和神秘,省得多事的后人为各自利益翻来覆去地修,搞得面目全非,无真实,就无真史。
苏伦高娃捧出蓝色的哈达,把哈达献给历史。谁有资格对浩瀚历史评头品足呢?凭个人短短几十年修为评判数千数万年历史,洋洋洒洒论证对错是非,这显然有些虚狂。
此时,随风传来悠扬的蒙古长调和呼麦歌声,如来自远古的声音。
是斯仁巴图叔叔家在歌颂丰美的季节,我心为之一喜。呼麦,这一保留原始因素的古老吟唱,它是来自民族记忆深处的远古的回音,记载历史和文化,就是一部用音乐记述的人种史和民族史。
北方游牧人的历史,如那马刀刻划的岩画一般,也已深藏在呼麦声里。史书描述这声音“高如登苍穹之颠,低如下瀚海之底,宽如于大地之边”。《诗经》讲北方部落之“啸”,唐时称“啸旨”,皆指这呼麦矣。
听一首呼麦曲吧,胜读十年史。在这片神秘的历史后院,会如醍醐灌顶。
额尔古纳河这岸
额尔古纳河从黑山头脚下匆匆流过。很恢弘,从天边浩荡而来,向北方一泻而走,去与百里之外的石勒喀河汇合,像一位要去赴约的小伙子,激情澎湃。它等待的就是这场旷古的约会,渴望着一次伟大的蜕变。由此开始,它摇身一变就名曰:哈尔穆仁——黑龙江。从河到江,就如由螭化龙,穿越的是千万年的亘古洪荒。
匈奴后的东胡一支蒙兀室韦以及后来的蒙古人,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摇篮。
从大兴安岭西坡起源,获得人类第一次命名,叫海拉尔河。西流到满洲里附近折向东北,被它滋养的属民再次给它更名,从此郑重而形象地称之为额尔古纳河。就如家里的少女长大了,从昵称改叫正式大名了。海拉尔意思为化冰雪之河,可解“爱哭”之意,缘自从高高的兴安岭带下的冰凌一路融化之故吧;而额尔古纳这词,是额尔“格”纳的变音,意思为回头或回旋,因为水大时河水倒灌入呼伦湖,然后又掉头向东北,固而称之为回旋之河——额尔古纳。好比少女出嫁一阵哭泣,踏上远路后,频频回头望故乡,显出百般的不舍之态。蒙古人给自然界万物起名,都颇有诗意,如称北极星为阿拉坦-嘎达苏,意思是金色的钉子,钉在北方天空闪着金光指引方向;北斗七星则叫道依乎尔-道伦敖都,意思是弯曲的敲钩钩;而三星就直接叫它古尔本-诺海——三只狗,当成自家养的三只牧羊犬了。
我们在这岸,陪伴着出嫁的少女额尔古纳河,一同奔向黑山头。
河的这一侧,平阔如茵的大草原,宽厚地守护着她;而那边的岸上,则逶迤莽莽的山岭起伏迷蒙,如只贪婪的卧虎在觊觎着她。前人的无能,也许喜酒喝多了,护嫁保航时居然把那边岸广袤的陪嫁地给弄丢了,让人偷走了。本来,河的两岸都是蒙古人和其它兄弟族人的故土,如今只能隔河相望,心中不免生出些许的凄然。
额尔古纳成为界河之后,这边的岸,从未断过那边贼人的惦记。
十九世纪的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从河的那岸潜入来一名大盗,偷偷溜进黑山头脚下的那座古城遗址。此盗贼名叫克鲁泡特金,以他为首的一伙俄国人多次窜入黑山头遗址等地,盗走了无数的珍贵文物。学他们榜样,其后人科兹洛夫也于1909年潜入西边额济纳旗的唐古特古城喀拉浩特废墟,发现一个神秘洞窟,里面装满了古老的艺术珍品、徽记、神奇壁画、祭祀原始文物、以及大量的古代手抄本,统统被盗光,并向世界第一次公布喀拉浩特古城遗址而闻名于世。历史的后院,那会儿是盗贼的天堂。皆因主人孱弱不善守护造成的。
我们的车在奔驰。旁边那座神秘的黑山头,在巍峨地耸立着,如一位忠诚的卫士守护着它脚下的成吉思汗二弟哈撒尔古城遗址,与南边数百里远的老弟斡惕赤斤的古城遥相呼应。很不巧,前方葛根河桥的涵洞遭洪水冲塌,车辆过不去了,我们心里一凉。塌方处正在填石土,但徒步还是能爬得过去。我们便弃车徒步穿越,决定到对岸再雇个车。这时一辆摩托从身旁飞驰而过时,听见一句熟悉的科尔沁蒙古语。我喊住他们。原来,这小两口就住在古城遗址旁边,名叫喜宝,牧民。他和媳妇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暂时放下到黑山头镇与朋友聚餐的事,用放在对面的小车先把我们送过去。族人的心还是热的,也好沟通。喜宝对古城遗址很熟悉,他和姐姐家的牧场就在遗址旁边,喜宝十多岁时就从科尔沁老家投奔姐姐来这里生活,成家立业。
开过一段泥泞的土路,就到了。喜宝把车停在遗址东侧。这里静悄悄,没有游客,连个人影都不见,这倒出乎我的意料。喜宝推开用铁丝拴的栅栏门,前边的辽阔草滩上流着葛根河,不远处是得尔布干河,遗址就在二河流入额尔古纳河的沼泽地的东部草地上。背山面水地势开阔,位处大兴安岭与呼伦贝尔草原交接险要处,可攻可守,是扼守北方的门户,进出草原的咽喉。原古城分内外城,土筑城墙,外城则呈方形,占地面积约三十五万平方米。有护城壕,设城门和瓮城,中部偏北有一座大型宫殿遗址,花岗岩圆柱基础排列有序,随处发现黄绿琉璃瓦残片和青砖古陶,也曾被风吹出来过龙纹瓦当及色泽艳丽的绿釉覆盆建筑饰件,可想当年在这里坐落着一个何等金碧辉煌的宫殿。如今一切已烟消云散,地面上除绿草覆盖之外,其它什么都不见了。
八百年的历史遗址,安静地躺在地底,除了那位祖先被蒙古人统治过多年的俄国盗贼外,几乎无人打搅过这里。没有如织的游人,没有随处丢弃的垃圾和震耳的喧哗,也没有见什么人往树和图腾柱上刻写到此一游。年轻热情的小老乡喜宝,从七八里远的家提来一桶酒,供我们祭祀用。作为哈撒尔的科尔沁部落后裔,我很郑重地向祖先古遗址祭拜。哈撒尔王后来也与老弟弟一样,随帝国的繁盛南迁,在嫩江流域及至西拉木伦河一带游牧,繁衍了后来的科尔沁十旗部众。科尔沁词意是神箭手,因哈撒尔王是著名神箭手,受成吉思汗赏赐而得此名号。
我问喜宝,这里没有人看护吗?听了此话,他的微黑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原来这附近住有他们五六家老牧户,自动看护古迹,很多年了,去年突然说要保护古迹,把他们全都迁走,挪到东边七八里远的地方。政府安排了一个老头,自己的人,住在后边一栋旧砖房里。喜宝笑说,那老头,你就是把整个遗址挖走,他也不带出来的。说着,他带我们去旁边小山包看被盗贼挖过的旧坑。
我在小山包西侧,发现一处新挖的大坑,倒不是盗墓,而是挖的沙石砬,用拖车拉走的。喜宝一见忍不住吼出一句骂娘,说前几天还没有呢,死老头不知看什么呢。我说,备不住就是他自个儿干的。他听了愕然。
守护,变成公家事后反而形同虚设。好在这里已没什么可偷的了,除了砂砬。
寄托八百年前那段磨不去的风云历史,现成为后人的精神家园,这样足已。后人只在意对祖先的记忆。离别时,我拿出酬劳答谢喜宝时,他脸红了,憨憨地摆摆手。
这期间喜宝的电话一直在响,耽搁的时间有点长,显然媳妇和朋友在催他。他只是憨憨地回一句,亚布吉-白那——正走着呢。离开时,他认真关好栅栏门,还不忘跑去找那位酣睡或醉酒的老汉,说几句。他是个很有心的小伙。到了镇上,当他从车上跳下向小饭馆飞跑而去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念:他是祖先冥冥中安排来接待我们的使者,八百年后,我第一次前来这里拜谒,他的出现并非偶然。那个飞奔的身影,如只雄鹰在展翅。
额尔古纳河这岸,古风依然;历史的后院,守护者的雄风也依然。
历史是有记忆的。虽然都埋在草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