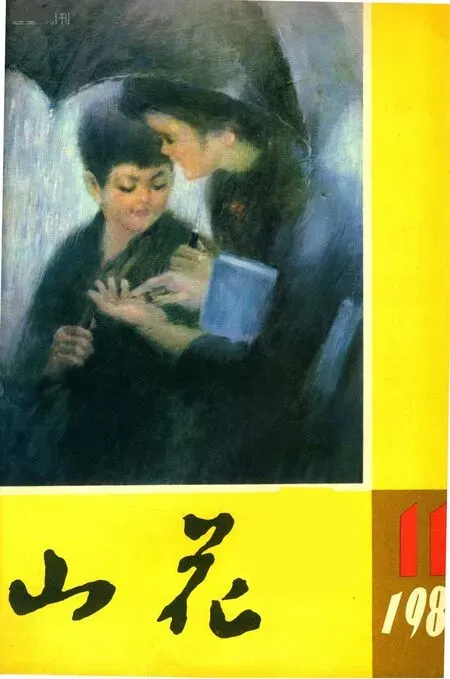拯救
陈希我
乡下人老想当城里人,但这些年有点倒过来了,城里人老往乡下跑。摘果子的,捡土产的,他们说这是“绿色食品”,还有买鸡鸭的,还有到乡下建房子的。城里商店里卖的东西信不过,城里的水信不过,城里的空气信不过,城里人与人的关系信不过,他们像难民一样逃到乡下。据说户口要落在农村还很难。有专家还担心,城里人大量涌到乡村,会毁掉乡村的青山绿水。
在草根爹眼里,青山绿水却是穷山恶水。没有生计,他倒想去城里落户。但也做不到。草根的爹就在乡下养“绿色鸡”。“绿色鸡”是他编的词,就是土鸡。不用饲料养,用饭菜养。不是圈养,是放养。卖的价格比吃饲料的高一倍。城里人纷纷来买,这些来寻找拯救的城里人,倒把草根家给拯救了。他们有时还拖家带口,城里的小孩瞧着活鸡,稀奇极了,他们从没有见过活鸡,鸡都是在电视或图片上看到的。瞧着他们追着鸡的样子,草根总觉得他们很傻。
城里人傻,还因为他们好骗。其实草根的爹也用饲料养鸡,不然成本太高了。城里人竟然也买。点着卖鸡的钱,望着客人远去,草根爹总要叹一句:
“真是‘钱多人傻啊!”
这些年,来买鸡的人手头更凶了。不是一只两只拎走,而是好几只,有时候一装就是一篓子,说是做“百鸡宴”。草根知道“百鸡宴”,一群群人虎狼一样吃着鸡的尸体,就着酒,脸上满是油。他们一点也不去想鸡有多疼。想到这场景,草根就在心里判这些人下辈子当鸡,被宰被吃。吃珍稀动物要判刑,吃狗,有爱狗的人来救,还会被谴责,但吃鸡好像就理所当然。
来买的人说,他们是开会所的。他们不怎么讲价,只要货好就行。草根的爹知道,会所一道菜比一般餐馆高出好几倍,来消费的也不计较,反正花的是公款。草根的爹不说“钱多人傻”了,说:
“谁都不是傻子啊!”
只有一只鸡从不喂饲料。草根还专门抓了虫子喂它。草根专门给它开小灶,起初爹不答应,骂他,但他不管,爹就随他了。那是一只公鸡,被草根养得体格健硕、鸡冠鲜红。它浑身羽毛光亮,阳光一照,熠熠发着五彩。它报晓起来,简直就像将军在发号施令。和它在一起,草根会觉得自己不再微不足道。
这只鸡也只认草根。他摸别的鸡,别的鸡不安地躲开。这只鸡不躲,安安静静让它摸,身体是顺柔的,不僵硬。天黑了,草根有时把它抱出来玩。它眼睛看不见,就定定站在他脚边。他的脚动,它就也动,完全凭感觉。他脚到哪里,它也到哪里,完全信赖他。草根觉得它就像一只狗,那么忠诚,那么聪明。当然草根起步时,会把脚步放得慢慢的。他知道它毕竟不是狗,没有狗那么灵敏,他体会它的难处。
草根不开心时,就会去找它。把它端置在椅子上或桌子上,跟他相对。他向它倾诉,它通人性,会把脖子靠过来,然后把身体偎在他身上。草根觉得好温暖,鸡的身体暖,比人身体的温度热上好几度。
它越长越大,草根的爹给它做了一次手术。草根不肯,但爹坚持要做。草根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手术?爹说,做了能更快长大。草根后来才知道,那叫阉。但阉的是鸡的腹部,爹在鸡腹下割开一个洞,把一小粒东西取出来。鸡果然更迅速长大了。它身体越长越大,但它的鸡鸡却越来越小,竟至于好像都没有了,成了一个洞。相反的,草根的鸡鸡却越来越凸显。草根常会去抠鸡那个洞,探寻消失的鸡鸡缩到哪里了。这是孩子好奇的天性,喜欢探密,比如掏鸟窝、探蛇洞。草根很小时也对自己的肛门好奇。渐渐的,草根将手指深探进鸡的洞里,他自己的鸡鸡就会变大起来。这时候他会感觉莫名的心焦。
草根以为自己心焦,是担心鸡被卖掉。虽然土鸡长得慢,但这只公鸡长得快。它越是长得快,就会越快被卖掉。鸡总是鸡。而且它又那么抢眼,单是那红鸡冠就抢人眼目,老远就看得见。为了不让买客挑走,买客一来,草根就将它藏起来。那鸡也很乖,不会发出一点点声音,只跟草根四目相对。这又像他们在玩“躲猫猫”,倒也有趣了。但有一次,一个顾客挑来挑去,就是没满意的。他说是要挑一只祭祀用的,要特大特肥的,草根的爹就想起这只鸡来。那一刻草根刚好被妈喊去,只把鸡用稻草掩住。结果鸡被他爹找到了。草根听到鸡叫,奔出来,那鸡已经在顾客手里了。顾客掂量着,转了转。爹自夸道:
“领导,这可不是大种鸡,可不是吃饲料的!”
顾客道:“我不是领导。”
草根认得,这人是领导的司机,经常代领导来买鸡。纠正了多少遍了,爹还是叫他领导。“这么大,哪里找?可是一口饭一口饭喂出来的啊,领导!”爹说。
草根平时见领导的司机都害怕,这下顾不着了。他大叫一声,扑过去救他的鸡。他叫着这鸡不卖,他爹喝道:
“不卖?留着做祖宗!”
不由分说,爹就开始捆绑。把鸡的脚捆上,塞进网兜里。鸡的脚趾从网洞伸出来,瞎抓着。网兜被爹提着,鸡整个身体腾空,完全使不上力气。草根悔死了,自己刚才怎么跑开了!
顾客又欣赏鸡,然后点钱,接过鸡,就往一辆车走。那车草根认得,四个圈的,是“奥迪”,官车。眼看鸡就要被带走了,再也见不到了,草根心中一裂,又要冲上去。妈把他抱住。
“再不卖掉就老了,谁要?”妈也在他耳边说,“鸡不中留,鸡总归是鸡……”
他拼命挣脱。他觉得没有鸡,他就不能活了。其实他原来对鸡的感情并没有这么强烈。鸡只不过是鸡,他玩的鸡。不知怎么的,现在突然感觉跟鸡生死相依了。但他被妈的胳膊捆得死死的。
他明白再反抗也没有用了。钱已经算过了,顾客越来越走近他的车。他猛一激灵,据他以往观察,顾客总会把鸡放在车的后备箱。他装作想通了,服从了,手插口袋,浪荡着步子向那车挪步。他转到车的另一侧,再趁客人打开后备箱那一刹那,打开车后座的门,爬了进去。他要跟着他的鸡。只要他在,鸡就还有救。他猫在后座跟前座之间,他个头小。客人没发觉,启动了引擎。
一路上他想着怎么救他的鸡,过不去后备箱,有椅背挡着。后来他才知道汽车后座位的椅背很多是可以放下的,可以直接通到后备箱。而且,那后备箱还可以从里面打开。要是他早知道,他的鸡就直接得救了。他没办法到后备箱去,又不敢弄出动静,只能眼睁睁让人家把他和鸡载到目的地。司机去开后备箱时,他溜出来。司机提了鸡,回头撞见了他,幸好不是在他出来时,客人只觉得他脸熟,稍微愣了愣。客人太忙了,没多寻思,扣下后备箱盖,把鸡提进门。
这是一个豪宅,领导的家果然是领导的家。草根从侧面围墙爬进去,里面更是豪华。厅堂上还摆着供桌,上面已经摆上了一些供品。最抢眼的是一个猪头,煮得半熟,装在盘子上。猪向前伸着头,眯着眼睛,嘴角向上翘,显出笑的样子。草根知道猪头呀羊头呀狗头呀一旦煮过,都会显出笑的样子,所以大人骂嘻皮笑脸,总是骂:“煮熟狗头!”
草根见多了杀猪,村里响起最大声嚎叫,就知道是杀猪了。猪被人拉出来,猪不肯走,人就前面揪它耳朵,后面提它尾巴,将它硬拽到屠场。有时候猪叫得太凶,有的猪还会咬,就拿绳子从它嘴里贯穿进去,再转出来,打几圈,那嘴就闭上了。猪被拽着,四脚几乎架空,但猪毕竟比鸡重,人没法把它提起来,不好放到案板上。人也有办法,用一根棍子抬住它的肚子,它就到案板上了。
屠夫端着装着一半水的盆子过来,放在猪头部那端的地上。几个人合力把猪的身子侧过来,屠夫在猪脖子上探索两下。猪毕竟笨,不比鸡灵敏,这时候大多很麻木,安安静静的。等到起刀扎进,才又挣扎,但为时已晚。血像泉水一样涌出来,淌在那盆子上。有时还撒出尿来,有时尿还冲到盆子里,跟血混在一起。猪渐渐不动了,只有脚在颤抖。屠夫拿勺子在血上舀,舀掉面上的泡沫。
这还没完,烫水,刮毛。为了好刮毛,还有用打气筒往猪身体里打气的,猪被打得圆滚滚的。开膛破腹、掏下水、大卸八块,然后才有现在这样被斩下来的猪头。猪怎么可能笑?哪怕是猪依然顺受,像牛。草根见过杀牛,牛那么大块头,那么大力气,却不反抗,任人摆布,它好像懂得自己要被杀,只流着泪。这更让人不忍。好在牛肉不能当供品,要供牛,得供全牛。所以现在人就都不供牛了,牛才被赦免了死刑。
草根从小跟牲畜玩一起,对所有牲畜被杀掉吃掉都很反感。他爱它们,但人却只想吃它们。还要让它们表现出笑脸来,好像它们很愿意被杀被吃一样。他最讨厌肯德基,那广告还把鸡描绘成欢快的样子,挺着脖子,昂着脑袋,翘着嘴,撅着屁股,喊着人们去吃它。有的鸡的广告,还给鸡胸上挂上大红花,让鸡叫:“为丰富人民群众餐桌贡献力量!”鸡会这么叫吗?贡献?凭什么要鸡做贡献?草根还曾听一个人恬不知耻地说:
“没有人吃,它们有机会活吗?”
敢情它们就是倒霉,倒霉的就该倒霉,吃的吃得有功,被吃的还应该感谢吃的人,如果没有吃的人,那么你连现状都维持不了。
更搞笑的是,那些说是用来祭神的猪呀鸡呀,最后都送进人自己的嘴里。他们要特别膘的,说是为了神,其实是为自己。
那个猪头,额上也被扎了一朵大红花,英雄花。好像它是光荣的英雄一样。草根记得他爹有一张老照片,那是爹很年轻时候,也被戴上英雄花,说是种田大户,其实他把自己口粮都贡献出去了。爹回忆说,那一次乡领导还对他说:
“我们太需要你这样的英雄了!”
爹在心里说:“凭什么我当英雄?你来当呀!”
英雄,就要牺牲。草根最初以为“牺牲”是指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后来才知道,它原意是牲畜。但他不知道,祭祀原来还用人的,叫作“人祭”。人割舍的东西越珍贵,就越虔诚,那么割舍自己当然最虔诚。“人祭”有火烧的,水溺的,活埋的,刺喉沥血的,砍头的,还有把人剁成肉,蒸为肉羹。草根后来从书上看到,玛雅人害怕太阳毁灭人类,还用人的心和血来喂养太阳,寻求拯救。起初奴隶主和奴隶都争相把心挖出来祭太阳,后来奴隶主不愿意牺牲了,就让奴隶当牺牲品。再后来,谁也不愿意当牺牲品了,只让牲畜去当牺牲品。还要做得冠冕堂皇,这草根知道。他的鸡鸡冠通红,连大红花都不需要扎了,所以这户人家执意要挑它。但杀了草根的鸡,就等于杀了他。他宁可自己去当牺牲品,也不能让鸡去当。
草根紧张找他的鸡,鸡体积小,但他的鸡有鲜红的鸡冠。他很快发现了,它被丢在天井的墙脚。一起被丢在那里的还有两只鸭子。它们都被捆绑着。天井上人进进出出,各做各的事,洗东西的,切东西的,还有抬东西的。一个年龄稍大的女人在指挥,她穿得极为高级。“放这放这!”她叫。
“王总,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做。”一个稍微年轻些的女人说。
草根不知道这“王总”是谁,应该是主人。那么那个稍微年轻的女人就是客人了。又叫对方“王总”,应该是王总的手下。那么就是来帮忙的。那些人应该都是来帮忙的,他们彼此好像也不太认识,这给了草根混入的机会。待王总一走,他也装作帮忙的,趁一群人搬桌椅,他搬了张椅子接近他的鸡。他要把鸡偷出来。鸡见到他,眼睛一亮。他担心它发出声响,正要给它作手势,有人擦身而过。是那个稍微年轻的女人,她手里端着两份水。草根知道,那是盐水,血在盐水里容易凝固。一份装鸡血,一份装两只鸭的血。
女人把碗放在地上,开始围围兜。她就是女屠夫了!女屠夫围好了,就去摆弄菜刀。她要动手了!草根心里发紧,得赶快把鸡救出来。他挡在鸡前面,但那女屠夫避开他,就向鸡鸭伸手。她的手背皮肤粗糙。草根血往头上冲,如果她抓的是鸡,他就强抢。只能这样,虽然他都不知道该怎么逃出去。那手碰到了他的鸡,鸡闪开,好乖。那手好像也并不执意要逮鸡,就伸向了鸭子。鸭子被抓在那手里,鸡躲过了一劫。
鸭子伸长脖子大嚷。鸭子就是比鸡笨拙,两下就被制服了。它脖子抻得那么长,刚好方便人家下手。揪下脖子上的茸毛,拿刀,一划,血自来水一样流出来。然后女屠夫把刀在它身上擦了擦,一别脖子,将脖子当绳索盘住翅膀,丢一边。好在还有一只鸭子,但难说那女屠夫接着还会选鸭子。草根不顾一切先把鸡拎起来。那女屠夫回来再逮,竟然没留意少了鸡。她只向墙根伸手,理所当然逮的是鸭子。
她一转身,草根就要往外跑,先转到侧面墙边,然后翻墙。但他被一个人挡住了。
“挡道!”那人骂。
草根一看,正是那个去买鸡的男人,领导的司机。他一吓,把鸡给撒了。
“大人忙着……”那人继续嘟哝。他跟草根打个照面,又一愣,他认出了草根。
“怎么是你?”
“我爹叫我来……”草根只能敷衍。
“怎么?”
“鸡抓错了!”草根索性道。
“怎么可能!”男人道,“我看中的就是这只鸡,红红的鸡冠。”
他寻找鸡,好在鸡已经被草根撒下,它在地上。“怎么丢这里?这鸡我可是千挑万捡的!”
他把鸡拎起来,向大家炫耀道:“瞧,难得见到这么膘壮的!这可不是大种鸡,吃饲料的有什么意思?刚才专门拎给厅长看了,厅长也惊奇,说神肯定会喜欢的。”
他又对那女屠夫:“夫人也说喜欢!”
“王总?”
“你当然要叫‘王总,你刚去人家公司,要改口过来!”
“我看你呀,最好也改口!”女屠夫小声说。
“也是,”男人说,“‘王总比‘夫人霸气。夫人,不,王总还说,不过意我们两口子都来帮忙。我说,这有什么?应该的!我是厅长的兵,你是夫人的兵!”
“就你会说话!”女屠夫说。草根明白了,这一男一女是两口子。但他没闲暇管这些,他说:“不是……”
“什么不是?”
“不是这只!”
男人饶有风趣道:“你怎么知道我要哪只?”
草根灵机一动:“这不是最好的,还有一只,那才叫大,又大,又肥!”
那男人现出贪婪的神态。“那你爹怎么不早说?我都跟他说了,这是最最重要的祭祀,领导的祭祀!是给神吃的,神没吃好,领导就完了!”
女屠夫赶忙制止他。“你是不会说话!”
这下又变成不会说话了。
“我爹忘了!那只真的很棒,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草根诱惑道。
“算了,来不及了!”那男人说,把鸡丢给女屠夫。他丢鸡时还显出嫌弃的样子,他心里想着另一只鸡了。这又让草根不满,他不能容忍人家轻慢他的鸡。
鸡被丢向女屠夫时,扑腾着翅膀。草根想,要是它能飞就好了。飞出天井,飞上天空。鸡本来应该会飞的,像鸟一样,但是现在的鸡都不会飞了。这是人豢养的结果。人不会飞,所以也让鸡飞不起来,才能控制它,吃它,太阴险了。草根没有想吃这鸡,但他把它养得这么大,它也飞不起来。这样想着,草根又怪罪自己,爱它就是害它。自己哪里是爱?只是自私。
女屠夫没接着,鸡摔在地上。鸡竭力要站起来,但它的脚被捆着。如果脚没有被捆绑,就是不能飞也能跑。人要抓住鸡是不容易的,鸡灵活,人笨。鸡小,人大。鸡矮,人高,人猫下要来就更笨了。但草根很容易抓到鸡,他个头小,更重要的是鸡会迎向他。鸡期待着他来救,跑几步就扭头瞅他。草根当然不能辜负鸡的期待,他像足球守门员一样弓着腿,瞅机会。一旦鸡投入他怀抱,他就紧紧抱住鸡突围。他相信只要他抱住鸡就能突围,虽然他还没想出突围的路径。但问题在于现在这鸡根本跑不了,它腿被捆绑着,它只能在地上打滚。也许正因为它根本跑不了,他才无须去想逃跑的路径,所以他才自信自己能够逃跑成功。
女屠夫没有把鸡拎起来,直接在地上下手了。边上的人帮她拿来盐水碗,放在鸡面前。这些帮凶!女屠夫一只脚踩上鸡翅膀,另一只脚踩上鸡脚。草根替鸡觉得疼,他叫起来:
“疼!疼!”
女屠夫抬头,问他怎么了?才发现他眼睛瞧着鸡。女屠夫释然了,还笑了笑。她竟然还笑!草根道:
“要是把你脚拿去踩,你疼不疼?”
女屠夫道:“孩子,这鸡是你养大的吧?”
草根点头。
“所以才不舍得。”女屠夫说。
难得她还懂得草根心思。她把踩在鸡脚上的脚松开些。鸡脚一直卯足了劲,被她这一松,像弹簧一样弹了出来,把装着盐水的碗踢翻了。不仅踢翻,碗还破了。这草根没料到,他也觉得神奇,这鸡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也许它真有特异功能。对,就是有特异功能!他又叫:
“你看,你看!跟你说就是不听!”
女屠夫愣住了。草根看出他的话起作用了,继续说:“这不是一般的鸡,很神的!”
女屠夫明显畏缩了。人毕竟很迷信,搞祭祀的人绝对迷信。草根要更加一码。
“我们家都不敢杀它!所以才养这么大……这么老……它是鸡魔!”
草根猛然想出“鸡魔”这吓人的说法。他忽然发现鸡用冤枉的目光瞧着它,好像在说:“我怎么是鸡魔?难道你一直把我看成魔鬼?”他也觉得污蔑鸡了。在女屠夫愣神当儿,他甚至去想,自己这么说鸡,把鸡救出来了,以后怎么面对它?他还悄悄向鸡使眼色,让鸡明白这只不过是吓唬那女屠夫的。
那女屠夫真被吓住了,道:“什么鸡魔!”
“真的!”他更煞有介事。
“无稽之谈!”
“我说的是真的!”草根又道。他杜撰起在这鸡身上发生的神奇事来。他调动起自己道听途说的知识,电视上的传说,动漫上的情节,再发挥想象,添油加醋。女屠夫听着,脸色有点发绿了。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她叫:
“怎么在神面前讲这个!呸!”
“真的!真的!”草根更大声道。
“还说!”女屠夫生气了,“你这孩子到底怎么了?你爹怎么管教你的?你有爹管还是没爹管?”
“好了没?”这时候那司机,也就是她丈夫又走了进来。他瞧见女屠夫还抓着鸡。“还没杀?水都开了!”
女屠夫下意识瞧瞧边上冒着蒸气的灶。
“一只鸡也搞不定!”男人又说。
“谁搞不定?”女屠夫应,“两只鸭都杀过来了!”
草根以为她一定会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告状都是他在干扰。但她没有说。她明显想推诿,但终究没有说他,只说:
“先烫鸭好了!”
“烫鸭有什么用?鸭又不赶着供,晚上酒席上吃的。鸡是要供的,要是来不及12点前,误了厅长的事,看厅长怎么收拾你!”
“厅长也这么迷信!”草根说。
“谁不迷信?这祭祀的事。”那男人说。
男人这话,好像又勾起了他老婆的迷信心理,她说:“可是这鸡好凶啊!”
“凶怕什么?祭品正需要凶!凶才强大,有力!越凶越好!”
现在草根后悔自己说鸡凶了。确实,祭品最好强壮,过去还用野兽献祭的。他连忙说:“不是凶,是神!”
“神?”
“怪!”
“怪力乱神?”男人哈哈笑了起来,“那刚好收了它!”
他把鸡接过来。这个男屠夫!他就站着,别鸡的翅膀。女屠夫很搭手地把鸡脚抓住,倒起来。男屠夫又把鸡头别过来,用抓鸡的手的拇指摁住鸡头,让脖子顶出来,就去揪脖子上的茸毛。那些细细的茸毛,草根平时经常小心抚摸的,被他粗暴揪下,丢在地上,地上丢了一撮撮,鸡的脖子亮出了红嫩嫩的肉,还有鸡皮疙瘩。他又感受到鸡的疼了。他更知道,接着要发生什么。他冲过去,控制住男屠夫的手。男屠夫惊,叫:
“你干什么!”
“不行!”草根叫。
那男屠夫好像明白过来。“不就是要钱吗?要加钱?”
草根摇头。但转念想,如果说加钱,也许对方会放弃。就又点头。那男屠夫却道:
“加钱就加钱!”
真是财大气粗。草根懊悔了,又摇头。男屠夫道:
“差多少?给你!不就是钱吗?”
这就是有钱人普遍的德行。有钱人就是没良心,只认钱。草根没有退路了,他只能拼命摇头。
“不要钱?”那男屠夫问。
“这鸡不卖!”草根直说了。
“不卖?那养它干嘛?养着玩?”
“就是!”
“那为什么要卖我?玩我?玩我们领导?告诉你爹去,我们领导可是一手遮天。领导一生气,你爹那养鸡场是非法的,就得关闭!”
草根想最好关闭。关闭了,就没有鸡被买走被杀了。“关闭就关闭!”他应。
那男屠夫调侃道:“去问问你爹肯不肯!”
他把草根手甩开,就去拿菜刀。女屠夫递来那只杀鸭的菜刀,还带着血,还有鸭毛。男屠夫接过,就向鸡脖子去。
“啊!啊!不要!不要……”草根叫起来。他扑上去,直接去逮男屠夫手上的菜刀。男屠夫叫:
“干什么!危险!”
危险就危险!草根想。他把另一只手也伸出去,一并握住。一边仍然制造声势地叫:“啊!啊!”
“放手啊!”那男屠夫叫。女屠夫也分出手来帮他,一手仍抓着鸡脚。鸡脚扑腾,趁机起义。但鸡的脚被悬在半空,好像使不上劲。鸡急切地瞧着草根,草根知道鸡的所有希望都在他的手上。他拼尽吃奶力气,但是边上其他人也来帮了。他们人多。她们都是女人,却没有同情心。这么多女人合着掰他的手。他的力气运不上手指,渐渐撑不住了。他惨淡地瞧着鸡:我快不行了!我只是小孩,他们全是大人。我只一个,他们这么多个。如果爹妈在就好了,但爹妈会向着这些人的。一边卖鸡,一边买鸡,他们是同谋。大人们全没良心。只剩下我一个人保护你,但我不行了!实在不行了!草根不敢正视鸡了,他知道鸡目不转睛盯着他,他一下也不敢看鸡。他感觉自己的手指已经被掰开好几根了。他已经被掰掉一边手了。他听到了鸡的哀鸣。可怜的鸡!最可怜的就是鸡!他索性抽出那只被掰开的手,重新发出进攻,支援那只还守住阵地的手。也许是这手松了一下,重聚了力气,一上阵,特别有冲击力。它直击那拿刀的手,刀被震,刀锋一闪。
“刀啊!”男屠夫叫。
草根以为刀要剐到自己了。这他无所畏惧。他把自己生命置之度外,他可以和鸡一起死。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不怕死。他曾经设想过,如果他爹发生危险,他敢不敢去救?不敢。如果是妈?想来想去还是不敢。怎么鸡发生危险他却敢了?也许那一切并没有实际发生,只是想象。但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对鸡比对爹妈亲。爹妈只是概念上的亲人,鸡跟他是耳鬓厮磨、肌肤相亲的。他已经习惯于每天要抱鸡,不摸它,他就感觉不到活着的快乐。如果能以自己的死换取鸡的活,那更好了。他又开始进攻。
“刀剐到了!”男屠夫威胁。
他意识到刀离他很远。那么,就是要剐到鸡了。刀就在鸡脖子前,在争夺中,刀不小心就会剐到鸡脖子。他迟疑了。这一迟疑,他的手就被大家扯开了。
好在他的一只手还守着。他又一次冲锋,但又被拉住。他一次次冲锋,但一次次被牵制住。他的手被他们牵制着,就好像游泳,怎么也无法游到对岸,水是空的,又是有力的,他的脚是虚脱的。遥不可及,遥不可及……他无力了。
在这种状况下,他忽然去怪鸡了:你也出把力呀!我这是救你,你总不能等我救吧?这可是你的命啊!你不是也有爪吗?你的腿被绑着,但你的爪还能活动,你有指甲,尖尖的,长长的,不像鸭子有笨笨的蹼,你要发挥作用呀!鸡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加快转动起它的爪来。其实它原来就一直在转动着爪子,企图划到人。它当然知道自己救自己。但是它整个脚被控制着,人头避着,爪子根本扎不到人,只在空中张牙舞爪。
鸡的武器被架空,草根的武器被牵制,刽子手的武器抓在手上。草根知道自己这方毫无胜算,只能回过来求人,不要杀鸡。男屠夫道:
“不杀?拿什么祭?”
女屠夫也说:“这祭祀很重要的!”
“我知道,我知道……”草根只能先承认对方,以此缓兵。“但这样祭了,会有祸的!”他道。
男屠夫笑道:“还是这话!”
“真的!真的!”草根道。
“祭还会有祸?礼多人不怪!神仙不打送礼人!”
“这鸡神了!”
“不就是特别凶嘛!”
“踢破碗了!”草根突然说。他让男屠夫瞧那被踢破的瓷碗,它被收拾在墙根。他又去望女屠夫,渴望让女屠夫出来证明。但女屠夫没有出来说。男屠夫说:
“这有什么?我一踢也破!”他做出要过去踢那碗的样子。这下女屠夫出来制止了,小声喝:
“别乱来!”
眼睛还警惕地睨了睨边上的人。男屠夫真是夏天的知了,越捏越叫:
“就是嘛!破瓷发财啊!”
“说是这么说,但是破总是不好的!”女屠夫说,“你不在意,厅长不在意吗?王总不在意吗?又不是你祭祀!”
男屠夫说:“那总不能向厅长汇报吧?那不成了我们不会办事?”
原来他们也是在敷衍,欺上瞒下。哪里是为厅长着想?他们看似对厅长忠心耿耿,其实是假忠。他们只忠于自己。那么,厅长祭祀,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当然,草根也听说过,领导倒了,司机也完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要维护领导。但同时他们更要维护自己,所以那女屠夫说:
“你会办事?别的可以敷衍,这个可不能。到时候出了事!巡视组就要来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草根好像听明白了。他灵机一动,他就是要把他们戳穿,他就是要利用厅长心虚。厅长忌讳了,就会有转机了。他大叫起来:
“厅长,厅长!”
女屠夫慌忙把他嘴捂上。捂有什么用?捂就没事了?草根死命摆头,摆脱那捂他的手。
“我要告诉厅长!”他叫。
那手又慌忙捂上他。那手跟着他摆,他再挣脱不掉。那边男屠夫又动作了起来,刀口眼看凑近了鸡脖子。只要再接近,就碰到鸡脖子了。如果不采取措施,鸡就死了。死而不能复生。草根冷静了,不叫了。他只哼哼,急切地哼哼,让对方觉得他有什么要事要说。女屠夫松开手。
“让我摸一下总可以吧?”草根哀求,“最后摸一下!”
这要求合理,女屠夫接受了,让男屠夫等草根摸一下。男屠夫说:“你快点!”
草根点头。他走近鸡,鸡好像感觉到他走近,身体松弛下来。他温柔地摸鸡脖子上的毛,那长长的像阳光四射的毛。鸡身体柔顺了,好像得救了。它不知道这是向它最后的告别。这让他更加难受。他把脸贴在鸡的肚皮上,哭了起来。
今天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他想,自己能做的只能是尽量不让它疼。他向女屠夫提出,女屠夫说:“好好,不疼!”
这许诺让他宽慰。毕竟是女人,心软,有爱心,像妈妈一样,也是鸡的妈妈!但是操刀的是那个男屠夫。草根又求男屠夫:“不要让它疼!”
“好,好——!”
那男屠夫拖长声音应。这好像敷衍,但也可以理解成加重语气。草根明明知道这是敷衍,但他仍让自己相信这是在郑重承诺。不这样又能怎样?鸡瞧着他,好像在寻问他,相信他的判断。于是他又怀疑男屠夫是在敷衍。再审视男屠夫,男屠夫把头无奈地摇了摇。这是不耐烦。但至少他被我烦得不得不按照我的要求做了。这也好。
他于是又得寸进尺了,又要求:“要轻轻的!”
“肯定轻轻的!”女人说。
“好,好——!”男屠夫也说。
男屠夫应着,又引菜刀。刀锋逼近了鸡脖子。幸好鸡头被别在后面,它的眼睛被男屠夫的手挡着,它看不到刀。草根去跟鸡聊天,这样,猛然一下,就结束了,鸡不觉得疼。“就好了!”他对鸡说。他眼尾瞥着刀。刀碰上了鸡脖子,那嫩红的肉。鸡叫了起来。但竟然没出血,根本没切开口子。男屠夫“啧”了一声。他伸长手臂,往边上的花盆沿磨刀口。他要把刀磨得锋利!草根阻止:
“你答应轻轻的!你答应的!”
“是轻轻的嘛!但刀口这么钝!”
这逻辑听起来像耍赖。但再想想,刀钝了,就快不了,确实只能重割。割不开还得再割,一次次割。草根曾见到一次杀鸡,钝刀口像拉锯子一样,最后把鸡脖子都快锯断了。他只能让男屠夫去磨。男屠夫一来一回磨了两下,说:
“这下快脆了!”
快脆,也就是快速干脆把鸡杀死。但没办法,长痛不如短痛,干脆地死总比折腾半天才死好。既要温水炖青蛙,又要快刀斩乱麻。男屠夫又引刀向鸡。草根闭上眼睛。鸡又叫,草根睁眼一看,鸡脖子开了一道口。但仍然没有出血,但草根能体悟到那非常疼。鸡当然要拼死挣扎。草根把鸡抱住,他没有去制止刽子手,他没有理由,只能接受命运,他也只能让鸡接受命运。但鸡也要挣脱他。它瞪着他,好像在说:
“你出卖我!”
原来鸡根本没有领会他的苦心,根本没弄明白他跟刽子手苦心谈判。当然,牺牲的是鸡,又不是你,你凭什么代表鸡?但是我是真替鸡着想的啊!草根觉得这时候他就像领导,鸡就像群众,一点都不体恤他鞠躬尽瘁。唉,群众总是不能理解。“不是,不是……”他想向鸡说明,但是鸡听不懂,也没有时间了。换位一想,就是听得懂有时间,它又怎么会认同?把你放它的位置上,谁会愿意失去生命?什么道理都没用,活命才是硬道理。
但问题是你已经抓在人家手里,翅膀死死钳制着,你还能逃?愿意死得死,不愿意死也得死。愿意死,死得轻松,不愿意死,死得折腾。你作为鸡,反正要被杀,只有两种死,一种是好死,另一种是好死而不得。草根就对鸡说:“没关系,就一下!一下就好了!”
鸡却一昂头,好像在说:“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是鸡呀!”草根说。他知道自己答得没道理,简直拙劣。但大家不都这么认为的吗?这时候他觉得谁都认为的就是有道理的了。谁都认为吃鸡理所当然,鸡就是养着吃的,那些号称有爱心的爱狗的人,他们也吃鸡。
鸡又一昂首。草根知道鸡又在质疑:“那么多鸡,这次为什么偏挑我?”
是的,但谁叫你长得膘壮?就只能先你了。祭品就是要挑膘壮的。人家看重你,不也是你的光荣吗?戴英雄花!他脑海忽然冒出这场景,一系列场景:猪戴着英雄花,鸡戴着英雄花,他父亲作为种粮大户戴着英雄花,电影里上前线的军人戴着英雄花,还有他小时候,学校里那些学雷锋积极分子戴着英雄花,当时他和大家一起起哄,但现在,在这严峻时刻,这场景变得崇高了,一点也不搞笑,一点也不荒诞。即使你不信,至少,在必死前提下,当祭品总是光荣的吧?你是为崇高事业献身的,“重于泰山”。
“你会很光荣的!”他说。
但鸡仍然挣扎,鸡毕竟是鸡。草根又检讨自己:当然要怪我,我把你养得这么膘壮,是我不对!我知道,是我坏!我坏!他对鸡说。现在后悔也迟了,你已经膘壮了,你已经被选中了,你已经捏在人家手里了。愿意献身,献身得光荣,不愿意献身,也得献身,还可耻。当然现在不是给鸡说理的时候,只能哄:
“就一下!只是划一下,划一下就放开你了。然后,我给你好吃的,好玩的,你会得到很多……”
这是哄骗。但是为它好。人生不就是一场哄骗吗?不知不觉把生命哄骗掉,这就是菩萨普渡众生。草根这么想着,觉得自己义无反顾了。他继续骗,他又对男屠夫说,说给鸡听:
“只划一下,是不是?”
男屠夫不耐烦道:“是啦!”
“你听,是不是?就划一下!”
鸡脖子一偏一偏的,好像在指它的伤口,好像在说:“已经划一下了!”
“我知道,我知道。再一下!”草根说,“好不好?”
鸡不答应,它的脖子摇来摇去,但它又不是鸭,脖子不长,就那么点回旋余地。那男屠夫又把它的头往后压。鸡又大叫。
“你看,不听话,就会这样了!”他威胁鸡。他简直是叛徒。“听话!听话……”他哄。他越过男屠夫的手,瞧被别在后面的鸡的眼睛。鸡竟然流泪了。他从来没见过鸡流泪。他想起他见过的那只被宰杀前流泪的牛。都说牛比鸡通人性,但这鸡也很通人性。通人性就懂事,懂事,也就是说它清清楚楚知道自己面临着什么。那更可怜了。草根心都碎了。但是没办法了,接受吧!认命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为鸡拭去眼泪。他摸鸡的头。他听见鸡还在嘟哝:
“我不要……”
“听话!听话!”他继续安慰。安慰着,哄骗着,他感觉慵懒,这种老生常谈让他慵懒。他在慵懒中等着男屠夫下刀。男屠夫终于下刀了,鸡又挣扎。他立刻意识到自己错了,自己不该慵懒。鸡哀求地望着它,好像在说:
“不行啊!实在不行啊!求求你!求求你跟人说一下,我不要……”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
这确实非常难,草根被夹在中间。他哪边都搞不定。他只能继续慵懒,安慰鸡:
“没关系!乖,乖乖!就一下,只一下!”
鸡的脚一摆一摆,草根知道它在说:“我不要……”
“没关系!”
脚摆得更厉害了,已经完全不再张牙舞爪,已经彻底缴械。这动作甚至显得有点优雅,一种放下武器讲道理的优雅。草根有机可乘了。
“只是划一下,就放你下去……”他记得小时候打针,大人就是这样利诱的。
“真的?”
“真的!一下,就没事了!”
“好吧!”
但鸡冠仍然挺挺的,草根知道这说明它仍然梗着脖子。这样,刀下去,它会感觉强烈,会很痛的。他去抚慰它脖子,脖子柔顺下去了,但它仍发出细丝般的声音:“咦——咦——”那是细弱的抗拒,是顺从之下的不顺从,是不顺从之下的顺从。草根听着,心都被刺穿了。这是温柔地杀它,它是听话地被杀。它的爪子拳得更紧了。是我害了你!给你下套,骗你,我太阴险了,太卑鄙了!不能再想了,不能再拖下去了!他让自己的心硬起来。他瞅男屠夫,暗示他下刀。男屠夫领会,又割了一下。
鸡又挣扎,叫:“疼!”
“我知道,我知道,疼!”草根对鸡说。
但是鸡仍然挣扎。
“我知道很疼啊!”他又说。
他蓦然悲怆起来,悲鸣:“我怎么不知道很疼呢!”
鸡并没有体谅他。
“要不肯,他们火起来,那才会死!”他转而威逼,“他们很凶的!”
好像它不反抗就不会死似的。简直卑劣。人就是要它死的,他却骗它不会死。“就划一下!啊?”他继续哄。
鸡忽然得知自己原来不会死,停住了,瞧他,好像在问:“真的?”
“真的!”他答。
“你保证!”
“我保证!”草根道。但他马上想,我怎么能保证?他看鸡,顺从了。它的鸡冠软了下来,盖住了半只眼睛。外国电视里把人杀死前,往往在人家眼睛蒙上布。这是文明,文明地处死,文明地杀戮。也许眼睛蒙上还真让人安宁,看不见悬崖,把命运交出去。鸡抽抽搭搭,不再挣扎,把一切交给了他,他是它最信任的、唯一可托付的。
那么我就是导致它死的罪人了!我也是刽子手。但我又能怎么办?罪人就罪人吧,只要鸡不那么痛苦地死去。他觉得自己是悲剧英雄了。不,也许更像“替罪羊”。村里有个教堂,信教的人常说“替罪羊”的故事。这就是拯救者的命运,功罪在一身。草根觉得自己境界不一样了。
但他其实又实在不能承担罪的重压,那个“替罪羊”有圣母,而他世界中的母亲和女人只是要卖鸡或杀鸡的。那“替罪羊”背后还有上帝,但他没有。他周围的人只信自己,只信自己活,活是绝对硬道理。也许鸡也根本不信他,它自始至终就知道自己肯定要死,它只不过要他负疚、负罪。那他更不能承担了。他必须把责任推给别人,那要杀鸡的人:
“你也保证!”他对男屠夫。
男屠夫不耐烦,不应。女人为他保证:“好,好!”
“现在人说话都不算话,不讲诚信!”草根忽然又去纠缠这个问题,又好像不愿意继续下去,要反水。
“你有毛病,跟鸡说……”男屠夫道。女人制止了他:“添乱!”她啐男屠夫。
“你也太纵容他了!”男屠夫对女人。
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太过分了。他对鸡:“你听,他们怪我了,我被他们怪了,但我是为了你!”
女人对男屠夫道:“你要办事还是吵架!”
这是什么意思?办事?办什么事?这是他们的黑话,人的黑话,草根觉得自己听不懂。他让自己感觉听不懂,在寻思,实际上是在维持糊涂,是在装糊涂,在延误。在他寻思之时,男屠夫挥动手臂,一阵风过,鸡又大挣,但它已经叫不出来了。
血像喷泉一样射出来。
草根冲男屠夫喊:“你怎么这样!果然说话不算话!没诚信!”
好像原来他就没有答应让鸡死。真的只是划一划,但男屠夫说话不算话。草根被骗了。他后悔莫及,哇地哭了起来。他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了,因此只是失误。但他同时又把一切罪责揽在自己身上。只有这样,他才认可自己。也只有这样,他才能跟鸡捆绑在一起,他的痛也才能在被虐之后产生更大的痛,从而得到慰藉。
鸡拼命挣扎。它什么也不顾了,它已经不再相信草根了,你骗了我!不再相信救世主,它只相信自己救自己。它扭动脖子,竟然从那男屠夫手上扭脱出来。草根以前只知道鸡的脖子灵活,没料到那细细的脖子还这么有力。它一个腾空,立刻翻身过来。也许正因为它翻身,血才会往上喷。草根不知道,他也惊呆了,他从来没看到鸡血像喷泉一样往上喷的,它不知道是鸡先翻转过来,还是血先喷出来的。
鸡竟然从男屠夫手中挣脱了。但它也只是在地上打滚。男屠夫又去抓它,草根抢上前去,但鸡先被男屠夫抓在手里。
男屠夫显得烦躁,血喷了一地,他已没心思再放血。他把鸡脖子扭过来,在翅膀上打一圈,摔在地上。鸡扑腾着,脚在抽,仍然那么有力。但草根想很快抽动就会减弱了。
“你们会报应的!”草根叫。
男屠夫嘲弄地瞥了他一眼,就要去洗手。草根向鸡奔去,还没到,鸡竟然站了起来。它的头竟然从翅膀里挣脱出来,被打在一起的翅膀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松开了。
它瞪了男屠夫,又瞪女人。草根叫它,它也不理,它也瞪着他,侧目。这时候草根才了解什么是侧目。它站得不稳,它也顾不得站稳,就走了起来。它的脖子上还开着口,胸前还流着血。它走到哪里,血就滴在哪里。男屠夫又要回来重新捆它,草根大叫起来:
“不要动!我告诉过你们,它是神鸡!”
大家都有点发怔,草根知道起了作用,他更大声叫,他要把那个最迷信的厅长叫出来。
厅长果然来了。瞧着鸡。它走得踉踉跄跄,但却很挺拔,顶着红鸡冠。它的红鸡冠并没有褪色,简直是飘扬的红旗。它走着走着,竟然有点矫健了,竟然有点骄傲了。厅长对着它,不自觉随着它动,或者说是躲着它。鸡走一下,他就愣一下,也走。它走左,他就走右。鸡踱着圈,厅长绕着圈,其他的人也随着厅长战战兢兢走圈。这有点像舞台上的戏,一个英雄镇住一群敌人。一边是鸡,一边是所有的人。包括草根。
鸡忽然像是笑了一下。令人不寒而栗。厅长一抖,问:
“谁弄的鸡?”
“是我……”男屠夫嘟哝。
“杀鸡儆猴……谁出的主意!”
男屠夫吓得简直要跪下去。“不是我……是夫人,不,王总让我去买只鸡,最大最壮的鸡……”
“馊主意!”厅长说,“快放了!”
“放生……”那男屠夫机灵,用了个吉利的说法,“对对,放生!放生也是积德,救苦救难……”
草根觉得可笑。这些人到底信不信神?也许他们根本是什么也不信,他们只信自己,对自己有用的就信,杀还是放,都看对自己有利没利,是救自己还是害自己。对司机来说,领导倒了他就失势,对职工来说,老总倒了她就失业。他们都是栓在一个利益链上的蚂蚱。他们根本不敬神,只是怕神。平时领导看上去很可怕,想着都可怕,但他们也有怕的时候,他们愿意只是这样!怕得跟孙子似的,他们不怕时就穷凶极恶。
“我替你放生!”他叫。他跑过去,把鸡抱起来,就往外跑。他要以最快速度抱着鸡跑开。虽然鸡被割开了血管,虽然它没救了,它要死,但他仍然抱它走。他担心厅长反悔,跑得飞快。他跑出时,被那个厅长夫人撞见了,她叫他,他装作没听见,只管跑。她叫:
“小偷,小偷!”
“别喊了!”厅长喝住她,“你能干什么事!”
草根抱着鸡,一口气跑回家。鸡竟然还没死。他找到兽医,把鸡的伤口包起来。那伤口竟然渐渐合在了一起。爹知道草根又把鸡拿回来,骂他,他申辩说是领导让他抱回来的,爹啐:
“领导是傻子?”
爹说要等领导司机再来时,再把鸡还回去。草根祈祷着司机不会来。那司机还真的再不来了。没多久,草根从电视上看到那领导的照片,说是因为贪腐被抓起来了。他跟爹说,就是这领导。爹说:
“原来是贪官!贪官的鸡,也不要还他了!”
草根禁不住想:也许真是没有鸡祭的缘故,所以厅长才被抓了。但他当然不信这些,他的教育告诉他,这些是迷信。他相信是厅长被抓,是他自己腐化堕落。
但大人们传说,其实厅长并非最大的贪官,他只是牺牲品。有一天,草根跟爹妈聊起那天厅长说的“杀鸡儆猴”,爹哈哈大笑了,说:
“你想杀鸡儆猴,猴想杀猴儆猴。猴子很聪明的。我去吃过猴脑,抓猴时,笼子里的猴子都想拼命把别的猴子挤出去,献给人吃。这是个互为牺牲的世界。不过力气最大的反被我们挑上了,就因为它最强壮。”
草根没明白爹的话。但那厅长认罪态度很好,报纸上登了厅长的忏悔:“我忘记了革命的初衷: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
这话唤起了草根内心久违的崇高感。爹的话,他就听懂了一句:这是一个互为牺牲的世界。但在还没有成贪官的厅长那里,在认罪的人那里,牺牲却是一种崇高。他觉得厅长的话是真的。
这崇高感很神奇。鸡的状况也呼应了这种神奇,它不仅没有死,体格竟然恢复了。
草根每晚都要抱着鸡睡。他经常做噩梦,梦见鸡被杀,他拯救鸡,刀硬生生要插入鸡的脖子。醒来时,发现自己的鸡鸡挺立,像祭着敌人头颅的旗杆。
城里的会所纷纷关闭了,来批量买鸡的少了,草根的爹的生意也不好做了,鸡场就倒闭了。一手遮天的厅长倒了,按说草根的爹的鸡场应该就没有威胁了。草根的爹又反过来怪草根当初不该把鸡救回来,没顺从了厅长。不救,鸡当成了祭品,那么厅长就不会倒。厅长不倒,会所就不会倒,鸡场就会很兴旺,他就可以千秋万代养鸡卖鸡下去。但兴旺的鸡场,也千秋万代有着死亡的鬼哭狼嚎。草根的爹委实很踌躇。
鸡卖光了,最终剩下这只公鸡。每当爹瞧着这鸡,这鸡就会身体抽搐,偎到草根怀里。草根明白只要在家里,鸡就在劫难逃。一个晚上,他抱着那只鸡出走了。他到了一个山上,跟鸡一起生活,像私奔。
他又做噩梦,是他爹要杀这鸡。这是幸存者,和他经历过生死的,他当然要救它。他抱着它东躲西藏。但他爹好像把这只鸡给忘了,再没提它。草根只能回忆着梦中的惨烈,感觉自己是从战场硝烟里回来的士兵,那般落寞。
草根渐渐不再做噩梦了,于是连接他和鸡的纽带渐渐地松弛了。后来他也回家吃饭睡觉了,得空回来陪鸡。后来没空时候多了。鸡开始不满了,说他不像当初那样爱它了。
确实。其实草根的忙无非是玩。他感觉自己像一只实在关不住的野狗。有一次,他逛到村里的教堂,里面在唱诗,那旋律,草根总觉得不像外国的,带着当地的腔调,倒像本土的民谣。他走进去,蓦然望见布道台中央那个“替罪羊”耶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手掌上的铁钉铮铮可见。他想起鸡脖子上的伤痕,想象着上面还插着刀。
他觉得疼了。他跑回山上,跑到鸡身边,抱着鸡痛哭。他想像那些教徒一样,真心诚意匍伏在鸡跟前忏悔,求他宽恕。正是它的受难,使得他生命有了意义。它是他的救赎。
但是鸡不是羊,它只是鸡。它不肯任人摆布,不任人宰割,也不任人寄托。它特别明白,他其实也在利用它。它扭身走开。他拉住它:
“要不,你也割我一刀!要不你啄我,啄我!”
他亮出自己的脖子。鸡不理睬他,用刚踩过鸡屎的脚踢他,把他的救赎之路踢得满是鸡屎。
草根也没耐性了。他也不是教徒,他只是普通人,一个也吃鸡的人。他想:我为什么要求它宽恕?你还是我救的,你才应该感激我!“没有我,你能活?要没我救你,你早被贪官当祭品了,早成了人家的盘中餐、嘴里肉、屁股拉出的屎了!”
鸡也咯咯顶嘴:“你别救啊!别救啊!”
草根想,当初真不该救这鸡。鸡就应该被杀,被吃。现在没人可以杀这鸡了,他不能,也不能把它交给别人。不能杀的鸡,不能献祭的鸡,不能成神的鸡,拿它怎么办呢?“活像烦死的老妈!”他冒出这比喻。不知什么时候,他开始懂女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