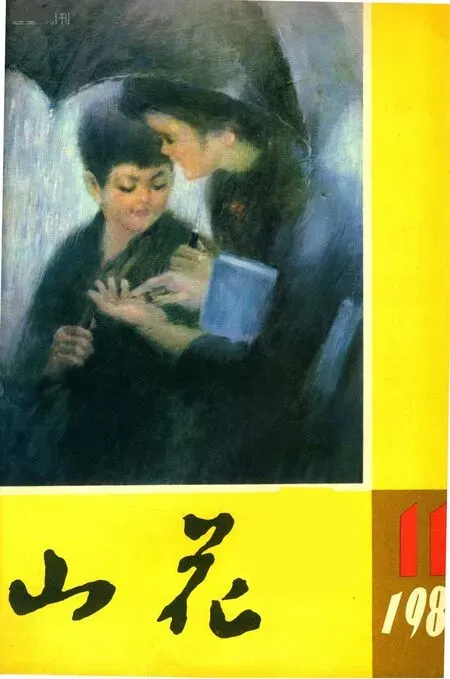桐花
何大草
李小山的爸爸给一位老爷爷专职开车。
每天早晨,他骑车到贡米巷25号的市委机关行政处,然后把伏尔加开出来,载了萧秘书,进27号家属大院的门,曲里拐弯,驶过锅炉房、长满牛筋草的大坝子、几排核桃树掩映的小平房,还有一片白果林,停在大院底端的一座独立小院前。黑门终年紧闭,门上还有一扇小门。八点差十分,小门打开,老爷爷走出来,佩了毛主席像章的藏青色中山装,没有帽徽的毛料黄军帽,肚子大凸着,微微打着颤。他的夫人端着他的包,像端着一只黑漆的点心盒。他走到车门边,回头接过包,对夫人笑笑。老爷爷面善,不笑也像是在笑。笑了,躬下身,就钻进车去了。
伏尔加出了家属院,就轻快地跑起来。可能是去隔壁的办公楼,也可能去下边的一个局、一个厂。
伏尔加亮铮铮的,跑在灰扑扑的街道上,宛如一匹漂亮、优雅的马。
李师傅爱惜车,总把它里外擦拭得一尘不染的。车门一开,老爷爷总能嗅到一股干净、爽洁的气息。他深吸口气,仿佛这比早晨的空气还要清新些。
但李师傅更爱惜、敬佩的,还是老爷爷。老爷爷除了平易近人,还关心萧秘书的女儿萧小红,李师傅的儿子李小山,他记得两个娃娃的生日,必送小礼物,两块巧克力,两小袋大白兔……两个娃娃同年、同月,今年十岁生日,各得到两本《十万个为什么》、连环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李小山对孔老二没兴趣,却很快把《十万个为什么》读完了,还开始读第二遍。不懂的,他就请教常识课老师。这老师是返城知青,一个造反派头头的儿子,满脸小疙瘩,李小山不懂的,他也不懂,还拿指头戳着李小山的额头说:“不要读迂了!白专典型。”
明代的亲王府,有条很宽的壕沟,民间俗称御河,在主城区腹心绕个圈,向南流入濯锦江,再向南流淌一百三十里,到江口镇汇入岷江去。李小山的家,就在御河边:
后窗推开即见河水,开了前门,就是西御河沿街。说是街,更像细长一条巷子,两排女贞树,门口拔地而起一棵巍巍老泡桐,树影罩了半条街。冬天,泡桐枯枝如铁,进了三月,枝头突然鲜花怒放,成串、成串,白中透紫,姹紫粉黛,粉嘟嘟、透亮,把人的眼睛都映得亮堂堂。
不过,阴天是多数。本城窝在盆地中央,自古安宁,聚人气,聚财气,也聚云、聚雾,阳光天少有。西御河沿街地势低,墙根、树根,爬满了青苔,不下雨,屋里地上也是湿湿的,暗暗的。屋顶有一块玻璃亮瓦,一柱光落下来,静得像古代,日子在发霉。解放前,这儿是有名的棚户区。
街坊邻居中,李小山找不到同龄的玩伴:大的正在乡下当知青,小的还穿开裆裤、吊着清鼻涕乱窜。下午三点半放学,他没参加文工队排节目,也没参加批判组出墙报。萧小红拉他参加故事组,宣讲批林批孔,他也没有去。时间长得没尽头,人无聊,就会像一根蔫了的豆芽,等着风干,变成一把灰。然而,他不是。他把红领巾摘下来,团了塞进裤兜,光脚下御河去捞东西,酒瓶子,罐头盒,一串钥匙……有回捞起一尊砸了头的领袖石膏像,就像捞起一块烧红的铁,赶紧扔得更远些。
河水潺缓,若有阳光,也是粼粼好看的。然而,水很脏,两岸的人家都把脏水泼进御河去。河水飘着腥气,像根烂肠子。鱼是少见的,倒是喂金鱼的红线虫很多,随手一揪就是一团,在手掌心蠕动着,男娃娃觉得好耍,女娃娃感觉恶心。
李小山养过几条金鱼,都被红线虫撑死了。
暴雨前,御河上几千只灰燕低空盘旋,捕食蚊子。雨后的晚上,青蛙嗒嗒嗒嗒地叫,焦灼得揪心。李小山就拿了电筒沿岸抓青蛙,手电一亮,青蛙就闭了嘴,愣愣地,束手待毙。他读了《十万个为什么》,要实证条件反射,就用两分钱的铅笔刀,在青蛙的小腿上切个口子,然后指尖拈紧向上一撕!青蛙已经死了,整张皮撕下来,毕露出肉、筋、血,还在痛苦地抽搐。
他母亲见了,不敢看,喃喃骂道,“作孽啊……”
父亲直接就甩了他一耳光。
李小山、萧小红蒙老爷爷安排,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念完五年级,接着念初一,俗称戴帽子。要到初二才能正式进中学念初二、初三,然后是高一、高二。那时学制短,中小学共十年。
夏至过后的一天,李小山的父亲回家很晚,饭菜都凉了。他头上缠了绷带,浸出一大块血迹。母亲见了,吓得呜呜哭。李小山恨恨问,“爸,哪个敢打你?”父亲道,“算个×。”
他下午载了老爷爷和萧秘书去肉联厂跟造反派对话,话不投机,一大群人舞着小红旗和赶猪棒、杀猪刀冲进会议室,高叫“打倒!”“打倒!”局面大乱,造反派头头也控制不住了。李师傅替老爷爷挡了几棒,萧秘书得空死活把老爷爷拖进了汽车。
“痛不痛?”母亲问了句废话。
“不算痛……也很痛。杀猪匠嘛,又不是杀青蛙。”
李小山不知咋的,嘿嘿地,傻笑了两声。
星期天,老爷爷请了萧、李两家人去吃晚饭,是表达谢意的意思。李小山的母亲在被服厂做工,心细,胆小,咋也不肯去,说去了是站、是坐、该说啥不说啥,弄不清楚,饭也吃不饱。只好父子俩去了。到了才发现,萧秘书也只带了萧小红。
这是李小山头一回走进27号家属大院。说是大院,其实是院里有院,两扇铁灰色大门后,一条弯曲小道把八九个小院串起来,宛如一根藤上结满了小瓜。院里树多,蝉鸣铺天盖地,森森然,而又生气勃勃。他看见人家的窗户都挂了帘子,木门外加了纱门,有的种了牵牛花,向日葵,还有的种了玉米,苞谷穗子已然黄了,偶有几只鸡踱过……看着都是好看的。
老爷爷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孙孙一大堆,家里却安静得出奇。来开院门的,还是萧小红,眨眨眼,一脸笑,似乎是这儿的常客。独立的小小院落,也像大天井,铺了砖,不见泥,寸草不生,只摆口大木桶,种了一棵绿黝黝的树,李小山不认识。萧小红得意地说,“《十万个为什么?》白看了吧?它属于第十万零一个问题。”
“你得行,那你说。”
“无花果。”
听着像是外国名。李小山把这棵树多看了会儿,树叶是格外绿,绿澄澄发黑,但也没看出别的啥名堂。
萧秘书在书房陪老爷爷说话。李小山的父亲下厨帮忙。环小院一圈,好几间屋子,都是空空的,再没别人了。李小山正纳闷,听见父亲叫他。
“小山,快叫奶奶。”
他嗯了一声,却没叫出口。
父亲挽了袖子,围了围腰,有点谦卑地躬着身子。边上站了个妇人,年龄跟李小山的母亲差不多,也可能略大两三岁,那“奶奶”二字在他嘴里打了几个转,终于还是吞了回去。
“咋没礼貌呢?快叫奶奶啊。”父亲急了。
“别吓着孩子了,老李。”那妇人微微眯了眯眼,像微笑,然而并不是。嗓音厚实,是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平静,好听,但严肃。季节虽已入夏,她深蓝的衬衣外,还罩有一件灰色的毛背心,袖口、领口,扣子扣得严严实实。下身倒是裙子,但裙摆一直落到了脚背上,隐约看见一双皮拖鞋,一双黑色的尼龙袜。这就衬得她的一张脸,格外的白皙。
李小山有点怕她,不觉就退了一步。
她伸出手去。“来,小礼物。”是两支英雄牌钢笔。
萧小红接过来,立刻在手心上写了几个字。“谢谢奶奶。”她笑眯眯的,补充一句,“好好写哦。”
李小山手碰到她的指尖,觉得好凉,一种夏天背阴处的凉。“谢了。”他咕哝。
“谢谁?”他父亲厉声问。
“奶奶……”很模糊的两声。李小山的奶奶去世多年了,他没有见过她,只看到过一张模糊的照片,她膝上坐着还是幼儿的李小山父亲。
“不谢。”奶奶说。“成绩好吗?”
李小山不吭声。
“我全班第二。”萧小红说。
“哦……那第一呢?”
萧小红拿一根指头指了指李小山。
“是吗?”
“向毛主席保证。”
奶奶眯眼看了看李小山。“很骄傲。”她说。
“骄傲啥!”他父亲又急了。“这娃娃胆小,见了奶奶就嘴笨,不敢多话……何况,他成绩是好点,可白专,动手能力差……”
“他不差啊,”萧小红替他辩护。“实验课解剖青蛙,他好厉害,全是一张张整皮揭下来,贴了一门板。”
李小山父亲气得脸煞白。
奶奶目光如刀,盯着他。“是真的?”
李小山埋了头,脚尖在地上默默画弧线。
两只菜花黄的蛾,绕着无花果树慢悠悠地飞。
“是真的?”奶奶重复问。
“嗯。”
奶奶的眼睑轻微哆嗦了两下。小院中一下子冷寂了下来。无花果的树叶在微风中嚓嚓响。良久,她说,“今天的鲤鱼你来剖。”
李小山剖鱼时,奶奶支派萧小红去书房给老爷爷斟茶,他父亲去屋檐下洗菜,她自己则站在身边一声不响地看着。那是条一尺六七的灰色鲤鱼,肉质饱满,生命顽强,肚腹白得像抹了层白胭脂,正有力地呼吸着,尾巴拍在案板上,啪啪作响!
但李小山握住菜刀,十分镇定。
他一手拈住鱼尾,倒提起来,刀刃随即贴了上去,刷、刷、刷……倒刮鱼鳞。鱼身愤怒摇摆,还发出叽叽叫声,像个撒娇的女孩。然而他运刀如风,均匀、有力,鱼鳞跳了起来,扇面洒开,像一群透明的银箔,纷纷扬扬,哔哔作响。刮完了这一面,他再刮另一面。两面刮完了,他弯曲了食指,伸进鱼嘴,把鱼腮一一抠出。这时候,鱼似乎断气了,但肚子却在一点点胀大,宛如临近爆炸的气球,他等的就是这一刻:菜刀瞄准鱼肚中央一条隐约的凹线,一刀横切,鱼肚吐出一声叹息:一汪黑血缓缓流满菜板,仿佛永远流不完……这时,他才略感异样,侧脸看了看,奶奶已经不见了。
萧小红后来问过李小山,“想不想晓得奶奶的事情?”
李小山说,“可以。”
“那你要保证不说给任何人听。”
李小山说我保证。
“要向毛主席保证。”
李小山说,“不。毛主席管不了那么多事情,接见外宾时,显得很老了。”
萧小红大怒。“你太反动了。”
李小山说,“那你去工宣队告我嘛。”
“工宣队算啥?我直接给毛主席写信。”
李小山哼了一声,懒得理她。
她还是把所晓得的事,都告诉了李小山。就像她平日有了一块绿豆糕,一只苹果,一只梨,总愿意跟他分享。她说,老爷爷的儿女,都是他跟前妻生的,离婚后,他们都随母亲搬出了27号家属院。这位母亲不是黄脸婆,不是受气包,很不简单的,她小时候缠小脚,就大哭大闹过,不依不从。十六岁参加八路,在晋南打过游击,能骑马放枪,做队长时,手下有三十多号大男人。后来她去延安学习,遇见了老爷爷,由一位大首长做媒,把窑洞布置成新房,就成了红色的伴侣。出席婚礼的客人中,有一位后来做了元帅,将军就更多了。全国解放后,老爷爷的官运并不亨通,因为,他遇见了现在这位奶奶。
奶奶是南京人,父亲是银行家,母亲是姨太太,很多姨太太中的一个,父亲叫她老四,后边还有老五、老六。母亲在姨太太中、她在一群兄弟姐妹中,不算受冷落,也远不是受宠爱,有一点落寞。抗战爆发,日本兵攻破南京城前夕,她正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念英文系。父亲给了她一口藤箱,就随学校流亡到了成都华西坝。
从此她再没有见到过父母。
坝上当时有五所大学,她换学到了华西协和大学念医科。大四时,她去川南的雅安实习,医治过一位川军中校,他中了一枪,子弹穿过左脸颊,留下一个突兀的咬痕,很有英雄气。还没有毕业,他就捧了玫瑰来华西坝求婚。顺理成章,她就嫁了。婚后才晓得,他的枪伤是擦枪走火所致,跟血染沙场没一点关系。何况,他是军需官,从没打过仗。好在他除了嗜酒、嗜赌、偶尔嫖妓,并无大的恶习劣迹。他染过梅毒,传染给她,好歹打针吃药,梅毒是断了根,却再不能生育了。临近解放,川军起义,她算是起义军官的妻子,与新社会相安无事。丈夫从军需官,改做了粮站的副站长。
有个秋天,副站长带人下去视察庄稼收成。晚上喝了很多苞谷酒,他抱着一棵板栗树呕吐,先是吐光了酒饭,后来就吐五肝六脏,再后来是吐命:一头栽在呕吐物上,呜呼了。
奶奶料理完后事,依旧提了那口藤箱,辗转来到本城,在王府正街的一家小诊所做了大夫。也是合该有事,老爷爷有天晚饭后散步,从贡米巷走到正街上,风吹来,被沙子迷了眼,揉几揉,居然红肿了,痛苦不堪。他摸索着,敲了街边诊所的窗户。诊所已经关门,但奶奶没事,还在里边读闲书。
她一手轻轻拨开他的眼皮,一手拿蘸了清水的棉签,小心翼翼扫出一粒沙子。他一下子舒服了好多。
“可能是煤渣,有棱角的,再揉,就伤到角膜了……以后再不敢了,啊?”
“……”她的手,声音,都有种夏天的薄荷凉。
他付钱,她不收,没用药,也说不上治疗。他就随口问她读什么书,她说了,他一脸茫然,就把书抹过来细看,全是英文。老爷爷和老婆都是马背上打天下的英雄,刀枪在手上玩得轻如鸿毛,可拿一支笔,却重如城门闩,吃力得很。
老爷爷回了家,心里再没把这女大夫放下。过些日子,他把这小诊所划入了市委机关,成了行政处下属的医务室。很多人在背后议论纷纷,但他不理会,反正也没听见。下了班,他总要干咳着,去医务室让她摸摸脉,测量下血压。顺带说说话。他来得再晚,她总在,好像就是在专门等他。有天,她等来的是老爷爷的老婆,第一针织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
她扇了她一耳光。还把医务室砸烂了一半。
老爷爷和老婆离了婚。
奶奶和老爷爷再婚后,提了一个要求,去四川医学院,即从前的华西协和大学,完成医科学业。老爷爷没答应,他说除了这一点,啥要求都答应。然而,奶奶啥要求也没有了。
她辞去了医务室的工作,退入了老爷爷的家。
李小山初次见到她的那个夏天,她已经幽居在家二十年了。
1977年10月,高考恢复。李小山和萧小红16岁,刚在念高二,但学校推荐了他们参加高考,说是积累些经验嘛,考不上无所谓。这倒是,高考中断了十年,文革前的老三届毕业生堆成了山,都拼老命要挤过窄门呢。录取率低之又低。
结果出来,李小山居然高高地中了,收到四川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这学院是老牌,重点大学,很不差了。但中学校长大喜之余,建议李小山放弃,等高中毕业再考,必能拿下清华。李小山也觉得可行。但他父亲劈头一通骂:“人不要贪心。贪心没好报。李家八代睁眼瞎,总算出了一个读书人,知足吧。”母亲也劝:“听爸的话,贪心不好,知足好。”他挨了骂,也不辩解,认了,那就读吧。
萧小红也收到了通知书,是南充师范学院,她两把就撕了。
次年春天,七七级入校。李小山收拾好一包衣服,一包书,一床捆好的棉被,插了一卷草席。临行前一晚,父亲说,应该去给老爷爷、奶奶告个别。
父子俩是吃了早晚饭过去的。天色还亮,也很暖和,主客就坐在寸草不生的小院中喝了会儿茶。萧小红没人叫她,也主动跑来凑热闹。她父亲已经提拔为办公厅副主任,萧家一年前已搬入27号大院,是老爷爷亲自给找的一套带红漆地板的平房,便于萧副主任的工作。
老爷爷更胖了,颇有倦意,但心情舒畅,气色好,嘴一直张着,乐乐呵呵的。他胖大的身体坐在藤椅上,把椅缝都挤满了。
奶奶还是瘦瘦小小,穿了高领黑色羊毛衫,还罩了一件灰色的开衫,手大半缩在袖里,只露出几个指尖。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也是苍白的。
气氛比较沉闷,幸好萧小红话多,就她一个人叽里咕噜,还不时站起来,绕着无花果树踱一圈,说自己下回就考戏剧学院的戏文系,做剧作家,写一出当代的《雷雨》。老爷爷笑道,“好,好。”李小山父亲也赞叹,“还是小红有志气。”
奶奶点点头,看着李小山,问他:“你觉得呢?”李小山没听说过《雷雨》,就叽咕了声,“夸夸其谈。”
萧小红不依了,跳过去揪住他的头发,要他道歉。
奶奶的眼睑轻微地跳了两跳。
李小山说,“好,道歉。”
“你这个乏味的现实主义者。”萧小红噘噘嘴,饶了他。
奶奶送了他一个笔记本。是她亲手装订的,牛皮纸封皮,内页是一沓厚实而轻的白纸,不是纯白,有点米汤色,亚光,略涩,手感极舒适,宛如一册素朴、雅致的线装书。
李小山说着谢谢,双手接过来。他父亲说,“请奶奶给小山题句话吧。”
奶奶又把笔记本拿回去,去书房用蘸水钢笔竖着写了两排字:
春天是最好的季节。
十七岁是一生的春天。
没有落名,也没有日期。
萧小红伸头望了一眼,咕哝道,“我们还没有十七呢。”
奶奶盯了她一下,眼睛刀子般一闪。
萧小红立刻闭了嘴。
奶奶随口问了句,“家门口的泡桐开花了吧,小山?”
李小山微微一惊。奶奶咋晓得自己家门口有棵老泡桐树呢?他回答不出来。这些天忙着下户口,转粮食关系,一系列入学手续,而且莫名的,情绪有些郁郁,埋着头进,埋着头出,根本没抬头看一眼泡桐树是不是开花了。他就老实说,“我……没有注意到。”
奶奶眯着眼,笑了。这是他头一回看见奶奶是真的笑了。她微笑道,“是有一点呆。”
奶奶手订的笔记本,李小山始终没用上。不是不喜欢,也不是舍不得,是用不上。他用了许多灰色、黑色塑料皮的笔记本,大开,半寸厚,横格,纸张光滑,经得起磨损、摔打,而且,还有一点关键的,很便宜。念完了本科,又保送读研,毕业留校任教,给大一上尸体解剖课,同时就在本校在职读博。平日除了上课,就泡在实验室、图书馆,吃食堂,睡单身寝室。
图书馆外有一块荷花池,他有天晚上出来,星空睛朗,听到鱼在莲叶间窜动,莲杆被撞得啪啪响。他忽然起了童心,脱了鞋袜,要下水捞鱼。但,脚指头才一伸到水里,就抽了口凉气,咕哝声好冷,算了,就缩了回来。
奶奶的笔记本压在了箱底,起初可能是有点珍藏的意味,后来就近乎遗忘了。
他没有再见到老爷爷和奶奶。
父母已经退休,从西御河沿街搬到了三洞桥一处市级机关的宿舍。还是老房子,然而是楼房的底层,小三居室,有厨房、厕所,阳台外有块小花园,可以种花,老俩口种了茄子、丝瓜,开出繁繁的紫花、黄花,看着是喜人的。他节假日回去陪父母住几天,父亲总念叨要他去看望老爷爷和奶奶,但他拖着,提不起兴致。父亲骂他没良心,他不反驳,只觉得言过其实了。研究生毕业的次年春节,他是要去给老爷爷和奶奶拜年的,但腊月二十九被老同学拉去喝酒,大醉后躺了两天,迷糊了三天,也就罢了。
萧小红第二次高考的成绩,总分相当高。填报志愿前夕,她父亲跟她长谈了一夜。她放弃了做剧作家的梦想,填报了中央财经学院。毕业后去了广州,后来是深圳、香港、美国。头两年,她跟李小山偶有明信片往来,之后各自没了音信。
十余年间,李小山只见过到她一次。那是个春天的午后,忽然燥热了起来,他感觉到倦意,懒懒的,就上街去溜达会儿。大街空荡荡的,车和行人都没了影子,空气中飘着嫩叶的清香,这是好闻的;也是让人倍觉春困的味道。锦江饭店国际商场的橱窗前,站了个年轻苗条的女子,白色喇叭裤,黄色蝙蝠衫,手腕上搭了条纱巾,像是在等人,也宛如刚从橱窗走出来的模特儿。
他走拢去,两人一对视,都立刻认出了对方。“李小山。”“萧小红。”友好的,老熟人口气,不是久别重逢的惊喜。
“留校了吧?”还是萧小红话多些。
“是啊。”他点点头。
“应该是讲师,在评副教授?”
“嗯,是。”
“有女朋友了?”
“嗯。”
“而且是师妹?也留校,同一个教研室?”
“是啊。”
“等分配到一套两居室就结婚?”
“嗯。”
“最后一个问题:还计划好了,结了婚,但要等完成一项国家级课题再生小孩子,是吧?”她脸上推出两丝假笑。
“是呀……你咋猜到的?”他有点迷糊。
“还用猜吗?这么乏味,想都想得到。”
“那,你是咋过的?”
“我?”她吐了一口气。“也挺乏味的。”
萧小红抬腕看了下表。
李小山就跟她告别了。
深冬,是个星期天早晨,李小山熬了夜,还在熟睡。父亲的电话来了,叫了声“小山……”,半晌不出声。
李小山迷糊应了声,话筒搁在枕边,保持着睡意。
“奶奶死了。”
他从没见过爷爷、奶奶,生下来他们就死了。开玩笑,还能再死一回啊?“哪个奶奶?”他咕哝了一句。
父亲破口大骂。“哪个奶奶?你说还有哪个奶奶!奶奶对你这么好,你这个没心肺的。”
他一下清醒了,是老爷爷家的奶奶。“爸,对不起,我……”应该给父亲说道歉,说句哀悼的话?这未免滑稽了吧。可说什么呢?他还没想好,父亲又说话了。
“奶奶留了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不接受任何人的吊唁……遗体捐献,供医学研究。”
“奶奶很伟大。”
“不用你来表扬她。”
“……”
“奶奶在遗嘱中,还提了个条件,必须由你来解剖她。”
“这……咋个可能呢?”
“奶奶给你写了遗言。你回来看吧。”
“……”
李小山晚饭前回到了父母的家。这是一月的傍晚,空气又冷又湿,底楼的阴暗又让冷添了些僵硬感。屋里没开电视,也没开灯,父亲就黯黯地坐在沙发上等他。母亲则缩在厨房中,锅、碗、盘子、碟子,不时传来冷冽的声音,像夏天的冰块在杯子里碎裂。
那张写了遗嘱的纸,跟奶奶手订笔记本的内文纸一模一样。遗嘱的字迹,也和笔记本上的留言相同,蘸水钢笔,娟秀,坚定,而且新鲜,宛如刚刚写下的。
小山,我活了一辈子,一生一世,是个无用的人。
死了,把遗体捐出来,是想为国家、为你,做一点有用的事。
请你亲手解剖我,在尸解课上给学生们做示范。谢谢你。
小桐
李小山感觉脑子空白,很不真实。“小桐?小桐是谁?”
“就是你小桐奶奶啊。”父亲唏嘘道。
“老爷爷,他还好吗?”
“他还好,昨天上午还在打门球……都以为他会先走的,结果是奶奶。”
“奶奶得的是啥病?从没听爸说起过……”
“不晓得。都说不晓得,组织上打了招呼,不许乱猜、乱说。”
“乱说啥?”
“别乱问。”父亲瞪了他一眼。“奶奶上午还去菜市场买了菜,回来给老爷爷炖了雪豆、蹄花汤,凉拌了折耳根青笋丝。然后,她在沙发上睡一会儿。这一睡就没有醒。”
“……”
李小山快想不起小桐奶奶的模样了。这会儿浮现出来的,是裹住全身的灰和黑,灰黑中一双微眯的眼睛,轻微颤抖了两下的眼睑。
晚饭是热腾腾的。母亲端上来一大碗笋子红烧牛肉,文火煨熟的,肉、筋、干笋都极为软和,汤汁收进肉菜之中,嚼来极有滋味。还有一盘撒了干辣椒末的油酥花生米,一碟清爽、脆蹦蹦的跳水泡萝卜。父亲几乎没动筷子,李小山则胃口大开,吃了两大碗饭,还喝了一杯母亲斟的枸杞酒,出了毛毛汗,一身通泰。
饭后,父子俩坐在沙发上,无话可说。一个还饿着,一个撑圆了肚子。母亲想开电视机,可不敢,就对儿子说,“你上街转转吧,消饱胀,顺便给我带一包盐巴。”
李小山在街上转了一个时辰,发现自己走到了西御河沿街上。御河已经填了,准备盖楼房。老街在等待拆迁。自己旧家的门前,那棵老泡桐还颤巍巍站着,高出了街灯一长截,但还能看见枯枝如铁丝一般,冷黢黢,托举着夜色。泡桐树在三月开花,花谢了再长出阔绰的绿叶……等到深秋,叶子黄了、落尽了,春天的花梗、花托,还一串串留在枝条上,像一个一个的铁疙瘩。好多年了,李小山没这么仔细地端详过老泡桐。
尽管夜色深灰,如黏了厚雾,但他还是看清了那些小疙瘩。看得很清,甚至可以挨个挨个数出来。
风在街道里嗖嗖吹。一个小东西飞来,他一下子迷了眼。起初,以为是粒小渣,或小虫,小心揉了揉,居然没有了。街灯下,无数的小虫子飘舞出好看的椭圆形,那是南方冬夜的细雪。雪中有雨,冷彻、干净的雨夹雪。
李小山在泡桐下伫立了很久。雪花落在他的头发上,也落在睫毛上,转瞬化为清水,簌簌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