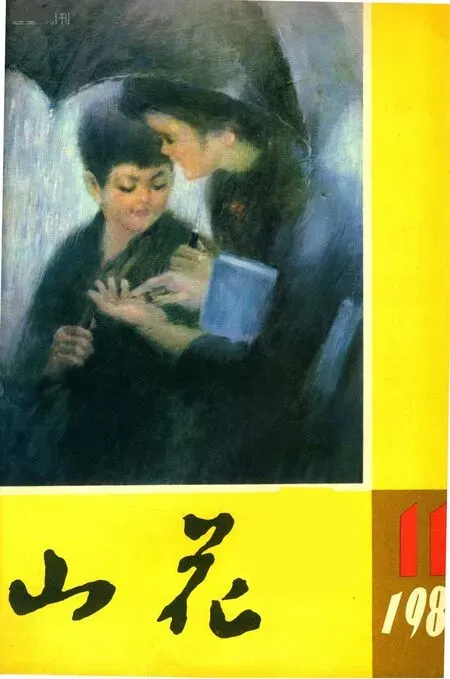追忆史铁生
时间具有魔性,转眼史铁生离世四年多了。史铁生在世时,我曾发表《我眼中的史铁生》一文,后来他去世,这篇文章又被人翻出来,被数家报纸杂志转载,但题目却被改成《史铁生和〈我与地坛〉》。我能接受这种改动,原作的题目从“我”的视角出发,难免狭隘,而改动的题目给人一种客观感,也显得不容置疑,无形中抬举我了。
不止一人看后对我说,没想到你是在他活着时写的,怎么看上去就是一篇纪念文章?有人干脆就认为是一篇怀念逝者的新作,这或许是史铁生个人的特质所至,他散发着生死一体的气息,身前身后,仿佛分别不大。
2010年12月31日那天清晨,刘庆邦和另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史铁生凌晨三点多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下意识地转移情绪,将自己置身在忙碌之中,好像一细想就会确立这个事实,但他的形象还是顽强地冒出来,一个接一个,我一次次地截断它,不让过去的岁月复原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当晚,上海《新闻晨报》一位女记者打来电话,说要采访一下我,我感到她有些气促,也许因为激动她显得像个新手,提问有些零乱,问题也极为普通。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提问,问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是否感到意外?我说很难受,但不觉得意外。一个月前我梦见他不太好,可能这也是个预兆。虽然我知道报纸不会登梦魇一类的细节,但我还是习惯实话实说。
那个梦很短暂,就是史铁生的上半身,像证件照,却是有呼吸的照片,他像过去一样笑着,突然间脸面变黑,没有任何过度,惊悸之下就发现他变模糊了。
很凑巧,次日刘庆邦有事打电话找我,我就顺便问他史铁生的状况,刘庆邦说前不久看到过他,还可以,就是瘦了点。我听后竟有些惶恐,也有些自责,好像自己干了件坏事。想起陈希米曾在一月份时写信告诉我,说史铁生肺炎刚见好。她的信总是不长,短句,明确,不拖泥带水。一年了,我也没再听到希米说史铁生有什么危情,刘庆邦的话也使我放下心来。我想,如果病情真有什么反复,他的轮椅车也会越过这个坎,继续无碍地跑上长长的一程。这一年我和他们联系甚少——退休生活使我进入另一种状况,我也不再有出差去京的机会,与文坛也似乎隔了段距离。可这真不应该呀,如果我有足够的警惕心,这个梦后,我应该去京看他们。
2011年的年初,天好像莫名的阴着,或许是我们心冷着。我不是刻意地拒绝接受这个现实,却是如失亲人般的恋恋不舍,要说疼痛,那是一种钝痛。我们共同的朋友严亭亭打来越洋电话,她因宗教信仰而显得平静,但依然能感受到她的忧伤,她说史铁生的去世,不单单是文学界的损失,更是我们这些人的不幸,他的友情是无可替代的。严亭亭真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想到他,不仅仅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更像孤岛上遇到的同类,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每次去京,上他家,就是一大乐事,他走了,心里就空了一块,去北京的动力也减了一份。
史铁生去世后好一段时间,我还是无法集中心力回忆相关的时光,不知为什么,一想就有股力量跑来截断,好不容易想真切了人就变得难受。有人劝我再写一篇纪念史铁生的文章,我想这样好的一个人,不知结了多少善缘,有多少人要借文字去追述那些时光,我怎能在这时候挤进去占有一席之地?史铁生曾有遗嘱,要把器官捐赠出去。这样的大善定然趋于光明之境,我相信愿力会起作用。我能做的,就是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祝福他。
现在,我能比较平静地回顾与他交往的点滴了,说起史铁生,我的思绪很容易回到1978年的时光,有人称此段日子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那时我尚年轻,正在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学习,用春光明媚来形容周围的氛围并不为过,看到的文字和听到的音声都带着一种自由与浪漫,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就在那一年,我听到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邓丽君,一个是史铁生。一个是从里面往外掏情感,一个从外往心里反观。这是我的简约感受与理解。同学播放了走私的邓丽君磁带,我第一次听闻到这类缠绵入骨的歌声,确实感到世界很新,记得几个岁数大一点的女同学迷得眼睛发亮,排队买饭都在哼唱邓氏歌曲。而关注史铁生却是小范围内的事,那时史铁生还未出名,班里有几个同学与史铁生交往甚深,比如刘树生、晓剑,据说他们经常去史铁生家聚会。七年后我做《上海文学》编辑,也开始跑这个地方,它就是雍和宫大街26号,站在院门口能闻到南面飘来的藏香味,往北不远则是地坛公园。他说住在这里好像一个宿命。我觉得这个位置确实有些象征意义。当然这是后话。当年,我只是从文字上认识他。也应该说是因缘吧,从刘树生那里读到了一本内部读物,好像是崇文区的文学沙龙杂志,还有一些装订的油印册子,里面就有史铁生的文字,一开始我分辨不清,因为有两个写作者,都名铁生,只是姓不同而已,但很快地我分辨出来,史铁生的文字更见个人风采,它们干净纯净,极具思辩色彩。同学告诉我,史铁生是个双腿瘫痪的残疾人,我很惊讶,文字中看不出啊。敬佩之余,我生出见他的想法,同学也答应有机会带我去见他。很快地我离开了北京电影学院,一直没机会见史铁生,直到1985年我从美术电影制片厂调到上海文学杂志社,负责京津地区的小说编辑工作,才终于名正言顺地和史铁生见面了。
以前发表过的相关文字在此不再重复,我只想说约到史铁生的第一篇作品是篇小说,名《毒药》。他的文字有种魔力,看的时候自然生起一种阳光缕缕透进幽暗的异域氛围,我不自觉地进入其中,好像身处这个看上去平常却又隐含着悬念的小岛。小说故事简单,说的是一个以养怪鱼为荣的小岛民众,在追求这种荒诞的名利中,生活的本质被颠倒了。一个养鱼屡屡失败的人只想求死,结果一神医送他两颗毒药,吃了可以无痛苦地死去,但面对大海时他突然想开了,反正早晚要离开这个世界,还不如先去外面看看,毒药就这样赐予了他多活一刻的信心,在他九十岁时,他回到小岛,想谢谢恩人,可是那位神医却不认他,还问他看出小岛有什么异样没有,他看到人们欢天喜地,争相猜测谁能成为新一届的鱼仙。直到神医点拨了他,他才发现原来岛民们都得了不孕症,神医请他带走仅存的两位孩子,后来两个小孩抢了他的毒药吃了起来,他大惊中才发现原来它们是两块口香糖。结尾好像有一声喊,“救救孩子”,不同的是,这不是狂人的心声,主人公非革命志士,他甚至是恍惚的,行走都是隐蔽的,他和他要找的人,个人史都是模糊的,但时代背景荒谬。而且它不仅是要救救孩子,更是要救救自己。小说的布局是智谋的,人物的对答竟有戏剧语言的韵味,可能和我学过戏剧创作有关,对台词有份本能的敏感,它需要一种精凝的内在动作。这离不开史铁生的文字修养,更是他化身其间的关系。奇怪的是这篇小说似乎不太被人提及,是因为寓言体小说不如现实题材的份量重吗?也许作为编辑,我本能地偏爱它吧?上海文学两年一度的小说奖中也有它,史铁生很高兴,来上海领奖时,还和李锐一起,各买了一盒西点,送给我和卫竹兰编辑。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打开盒子时,他凑过头来看,还夸张地咽了下口水,嗳,上海人手巧,点心都做得这么漂亮。
那是1988年的事,我独自去北京接史铁生来上海领奖。这里有两个细节需要更正某些误传。一是有人写文章说,我去北京时陪史铁生一起游地坛,其实相反,他以几近请求的声调对我说:姚育明,我想陪你去地坛走走,不知你愿意吗?人们习惯性地以为总是编辑陪作家玩,没想到史铁生偏偏不以为自己是什么角色,他动机单纯,地坛于他浑然一体,他希望与人分享。谁陪谁,虽然一字之差,似乎也无伤大雅,但在我的感受中却不一样,这和史铁生一贯为人着想的习性相符。还有人赞我,说当年姚育明独自接史铁生回上海,一个人把轮椅车扛上扛下,还把170斤重的史铁生背上背下,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场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女汉子,我真有这个力量当然好,可我不想掠人之美,当时同行的是蒋原伦教授,我忘了他是嘉宾还是理论奖得主,但记得他是个低调的人,是他背着史铁生上车下车,我则是用力提着轮椅而已。中途停靠站,他也要背史铁生下去透透风。他们两人各怀自在,让我看了心里感动。
一开始我每年或隔年去一次北京,每次都能看到史铁生,他不像别的作家,会往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跑,他就像一棵树,扎根在那个小屋里。第一次看到陈希米差不多也是那个时段,不是1989年年底就是1990年年初,她正陪史铁生从地坛回来,那个小门上的帘子,像过去一样被一双手掀起来,但不再是父亲苍老的手,而是一双女性的手,揭开了温暖的一幕。记得史铁生给我写信,说到和陈希米结合的事,有几句话说得幽默,他说陈希米也是你们上海人,一分钱记得很清,一元钱常常不知去了哪里,非常适合娶来结婚。听到这个消息,我寄去了一条床单作为贺礼,那感觉就像邻家大哥有了好事,自己也会跟着喜庆。
1990年年底,史铁生把《我与地坛》的稿子寄给我,让我意外而又感动,之前不久我还问他有没有写什么呢?他一点口风也不透,他的散文给了我莫大的惊喜。当时编辑部想把它作为小说发,除了次年一月号缺重点小说稿外,他们认为小说重于散文。我很不乐意去劝说史铁生,这是明明白白的一篇散文,怎么就能以小说论呢?但是身在兵营由不得自己,我不得不打电话给史铁生,幸亏史铁生没有商量余地,他说如果你们为难,不发也行。我很开心,知道编辑部不至于为此而失去这篇好稿。
编辑部后来以“史铁生近作”之称发表这篇散文,发表之后的影响不用我多说,很有意思的是,那时各种选本选它,散文选刊选它,小说选刊也选,甚至故事类的选本也选,台湾也将《我与地坛》编入教课书中,听说这是大陆唯一一位作家的作品入选。从这个现象来说,它的文体具有非常宽泛的因素,与其说这是散文写作的一场革命,不如说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一种境界坦露,它出于最真诚最光明的心地。
可在我印象中,《我与地坛》竟没得过什么散文奖,结果无意中看到有人说它得过1992年上海文学小说奖。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作为责任编辑,这么大的忘性,确实很不称职,也许是我在潜意识中自动过滤掉了,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把它当小说来读。史铁生不承认它是小说,我同样不认为它是小说。
前年我给某校高三学生上散文课,这帮曾经气走前任老师的散漫学生,对《我与地坛》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还对我说,老师,你见过史铁生,真幸福。
是的,每一个与史铁生交往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一份心的热度,权且用这个词吧。
读过《我与地坛》后,我有了写史铁生的冲动,无意间和副主编周介人谈起这件事,他问你准备给谁,我说想给解放日报,他说写好后给我看看。《我所认识的史铁生》很快完稿了,他看后说谁也不要给了,我们自己发。我当时有点不敢相信,因为以前有过规定,编辑不能在自己杂志上发表文字。这篇散文由此开了编辑在本刊上发文字的先例——真是借了史铁生的光啊。
一般我去北京之前,都会打电话或写信给他们,问有什么事要办,史铁生除了托我寻觅废名的《桥》外,从没为其它物事麻烦过我,记得有一阵他对禅宗文化感兴趣,也一直在搜集废名的文字。作为一个贤妻,陈希米则直截了当,她说你带些那史吃的东西过来吧。她称史铁生“那史”,听上去像“那厮”,我会忍俊不禁。虽然她曾在电话中数说史铁生这个那个,我现在都想不起是些什么芝麻绿豆的事了,只记得她的娇憨口气,他比我大嗳,他就应该让让我。实质上她对史铁生的照顾很费心血,她实在心疼史铁生,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的,所以,我给史铁生带些海泥螺、腌制肉、多味豆腐干甚至上海玫瑰腐乳之类,也只是为了让史铁生的嘴巴有些许味道。
没几年,上海文学杂志社陷入经济危机,周介人说没钱出差了,甚至有一次还让我们少写约稿信,好节约些邮票。还记得编辑们反对时他流露的羞愧神色,现在想来真是不忍,周介人去世后,蔡翔也为钱的事头痛。那时编辑都很知趣,不会主动出差,我去京的次数也在减少。好像是1998年,我去北京,刘树生和我同去史铁生家,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刘兄家。史铁生就说,讲好了,下次你来,住我家。我说不用不用,我能找到住的地方。陈希米大概以为我客气,补充说,你不嫌弃就住那个小间,很方便的。我说我当然愿意住你们家,好和你们多聊聊,可是没必要麻烦你们呀。史铁生又说,姚育明,只是对你哦,我们从来没叫过其他编辑住我家,这样你可以省下住宿费了。我向他解释,是刘兄和朱大姐硬不让我住外面,其实我住宿的钱可以报销的。史铁生这才松了口气,也许他也听闻了杂志社的窘迫吧?此时史铁生已有了三年的透析史,写作数量开始减少,他的经济生活并不宽裕,却为编辑的几个小钱着想,想让人不感动也难。
2001年我有私事去北京,在史铁生家遇到了钟晶晶,听说钟晶晶是陈希米的西北大学同学,钟晶晶的丈夫又和史铁生同年插队在陕北,两家人关系甚好,但钟晶晶依然像学生聆听教授之言一样,表情认真,坐姿恭敬。史铁生在小保姆和希米的帮助下,起身坐到轮椅上,他把车摇到客厅门口,指着书橱对我说,看,刘易斯送我的。他的脸上闪着小孩子似的快乐。于是我看到了一双大号的耐克鞋,好像是蓝白色。记得我当时说,刘易斯真幽默啊。认识史铁生的人都知道,他根本不会为这一类话伤感或反感。史铁生只是眯着眼笑,一副很享受这种况味的神情。他喜欢刘易斯由来已久,总算满愿了。
我虽然也笑着,但心神不安,他明显地黑了,瘦了,看上去有些疲软。陈希米看上去也有些憔悴了,她像过去一样,话很少,动作很快的走来走去的忙。
没想到这次见面,史铁生主动给我一叠手稿,它就是六七年后出版的《记忆与印象》的第一部分,共八篇。他说我相信你懂我写的一切。原话我不能确定了,但大意就是对我的信任。
意外地得到史铁生的稿子,就像当年得到《我与地坛》一样,体会到他对我的抬爱,不免感动,但这一次的心情不像那回轻快,我抑制住沉重的心,祝愿他能顺利地完成系列,早点出书。离开他家坐上公共汽车,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第一次为史铁生涌动起悲伤的心潮。
之后一直没去北京,直到2004年王安忆请史铁生来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正好我的美国朋友格格来上海,她希望我能转达自己对史铁生的仰慕之情,她说我没别的奢求,就是想请史铁生吃顿饭。
史铁生哪缺饭吃,到处都是吃请,根本应付不过来,但他善解人意,答应抽一个晚上和格格见面。格格也是个心善的,她说不要劳累史铁生,就在宾馆里吃。
在银星假日酒店的那顿饭,与其说是宴请,不如说是请史铁生观赏饭菜,他微微前倾,仔细地看了菜肴说,哎,眼睁睁地看着这一桌好菜,却不准你吃!简直是一场刑罚!依然是那样宽厚的微笑,脸色却黯淡,也明显瘦了,这顿饭吃得我们很不好受。格格小心谨慎地让他尝尝汤的味道,他用嘴唇沾了沾小勺,品味着,嗯,真好吃。过了会儿,又含了口水,却没咽下,片刻又吐出来。哎,哪怕让我多喝几口白水呢。多么低的奢求!我们看着他,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来。史铁生察觉了我们的感受,反过来安慰我们,我就喜欢看你们吃,你们吃得越多我越高兴。
吃饭其间我们闲聊了各种话题,其中讲到人的面相问题,史铁生指着我对格格说,你看她,永远不见老。我说不是不见老,而是早就老了,我二十多岁的时候额上皱纹就很深了。他说那不算,许多小孩天生就有额头横纹,女人老不老要看嘴边的皱纹,连颈上的横纹也不算。我当时真有些吃惊,没想到老史兄还懂这些,更奇怪的是他的表情和说宗教类的话题一样诚恳。我被他说开心了,神色肯定好看,要不陈希米还说,姚育明心态好,脸上老有光。格格说,她整天听经坐禅的,精神气自然足。我说嗳呀,在这里尽听好话了,可是在佛友中经常受批评,比如师父来讲经,我因为妈妈生病不能前去,就有人说我不精进。史铁生略微倾了倾身子,姚育明,你不去是对的,修佛首先要讲孝道,一个不孝顺的人修什么法都是入魔道。我说老史兄,你怎么说得像佛经似的?佛就说父母恩重难报呢。他又呵呵笑起来,嗳嗳,不能这么说,我一凡夫,就是闲话,谈不上圣言。
在吃饭的过程中,他掏出只有半截的烟来抽,但只是一口,然后就掐了,过一会又点上。他像做错事一样地看着陈希米,嗯,我知道,烟也要少抽。又对我们说,其实真喝一点肉汤也没关系,是我自己不敢,希米够累的了。
看着陈希米,我心里也生疼,她的变化同样大,明显的疲惫,眼袋也出来了。我把包里准备好的红珊瑚给陈希米,告诉她,我的心意全在这108颗珠子上了,每粒珠子拨动时我都念过好几遍观世音菩萨。她笑了,虽然疲惫神态依然未褪去,但那嘴角带出的笑意依然坦然无邪。这是小小的短暂的轻快。她捏在手里问,怎么戴呀?格格蹲下身,认真地在她手上套了几圈,陈希米举起手腕,眼神里又闪出娇美的小女儿态,好看吗?
虽然话题始终轻松散漫,但史铁生明显的黝黑和陈希米黯淡的枯黄,让我和格格不忍心畅谈下去,格格主动表示散席。她抢着推轮椅车,感慨地对我说,别说写作,就是对付这种生活,也不容易呀!
一靠到床上,史铁生就叫我把冰箱里的粽子之类带走,他说全是人们送的,他们根本吃不了,而且他们也不想再带回北京,太重,去给你们兰天吃。
他还记得我女儿的名?让我高兴。记得有一年,他给我寄自己画的贺卡,向我以及我丈夫拜年,写到我女儿名字时后面用了个括号,里面是个问号。我后来告诉他,没错,就是这个名。他还真记住了。
2007年5月,我去京领一个编辑奖,结束后去看史铁生,他家坐着几个作家,正围着他聊天,聊了一会他想起什么,指着书橱对我说,姚育明,有人送了我几块贝壳化石,你去挑一块。化石有五六块,我挑了块最小的。结果,有一个作家说,我也要。话音刚落,几个人蜂拥而上,小孩似的抢起来。史铁生坐在轮椅车上呵呵地笑,这一比不就比出来了,哪像姚育明,挑最小的,你们呢,挑最大的!听了史铁生的表扬,我很受用,而其他的人也不惭愧,他们嘻嘻哈哈的,竟然一块也没给史铁生留下,透过那种氛围,完全可以看出史铁生平日与朋友们相处的随意和大度。我没意识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但我也确实发现他的眼神有微妙的变化,过去他的眼光是有温度的,看你一眼,就温暖到心里,很慈悲。几年不见,他那沉稳的眼神里明显有了遥远空茫,好像魂魄已住到那里,现在只是分身来应对这个世界。
2008年我打电话给史铁生,告诉他,自己要退休了,七月底将正式离开杂志社,希望在走之前,再发一篇他的文字,以作美好的留念。他告诉我,现在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一时没东西给我。他的口气充满歉意,也有真心的叹惜,我真有点不习惯你的退休,看来要适应一段日子了,又提到在整理一本书,准备出版。我忘了是哪本书了,只记得当时问他里面的文章发表过没有,他说基本都发过,然后他有点不确定地说,你看看我的自序行不行?就是有点短。我很高兴,短无妨,哪怕数行,只要是史铁生的东西,没有差的。《原生态》就这样到了手。在这篇二千多字的散文中,他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原生态非状态,而是生命的最初心态和神态。为此他还举例,比如为了人民是原生态,为了赢得人民就是非原生态,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有信仰是原生态,为了指挥和拯救别人是非原生态,为了爱情是原生态,为了父母以及媒人是非原生态等等。我有些意外,原来他并没有如我所想的那样,魂魄远离尘世,只参生死大事了,他还挺现实主义的呢。不过,虽然他的分辨令我忍俊不禁,但我还是觉得举的例子削弱了他的观点,也经不起严格求证,用什么来证明生命的最初的心态是零呢?好在结尾中的结论比较圆满,他认为原生态并不都在历史和风俗中,也不在一时一域,它们只存在人的心里。我知道史铁生也是接触过一些佛学书籍的,对一些基本教义不会陌生,我觉得《华严经》里的“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能说到根本上,它准确地解释了世间的各种人生现象,用不着举一些例子,然后再为例子注明,为注明再举例子这样补缺了——说服众心并不容易。但我没和他交流看法,又不是哲学讨论,再说真要论起来我也论不过他,编辑编好稿就是了。我只是发自内心地感谢他对杂志社的支持,以及对我多年来的支持和关爱。他也很高兴,说你喜欢就好。他的口气如释重负,我很熟悉他的为人,经常帮人解难。后来我在网上看到,这篇散文进入2008年中国散文排行提名榜了。我知道,许多人和我一样,期待着他的新文字。
史铁生去世后,一位和他们关系密切的朋友告诉我,说史铁生已经皈依了基督教。我没去陈希米处求证,他已告别这个尘世,生前有什么信仰也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他的眼光一直没离开过生命的问题:原罪、忏悔、救赎、苦难、爱。他的眼神很真挚,也深邃,这和他长期的思考有关,也和他热爱生命有关。
我从来没和他讨论过佛教的教义,事实上我对佛教教义也不甚了解,我关注的只是受用。但他曾主动对我说过,他说我的腿成这个样子,按照佛教的说法,应该是前世的造孽,后世我承担这个果,只是这个因果谁能说清?
我没有接他的话题,这个题目太大也太具体了,面对一个兄长般的朋友,怎么说都是错。随便什么宗教,随便什么说法,只要能慰藉史铁生,我都以为是好的。而他平日里处处流露的悲心,以我凡俗眼界,又怎知道是在什么果位?记得有一次我对他说,有过很糊涂的时候,把轮船方向盘看成法轮,还觉得风车饰件也像法轮,他笑着拍了拍身下的车轮,说我也是法轮常转。
是啊,从我认识史铁生以来,他的车轮就一直圆融地转着,他首先破除的是自己心中的障碍,他的思索就是他的足,前景辽阔,无所障碍,在这种前行中,他成就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