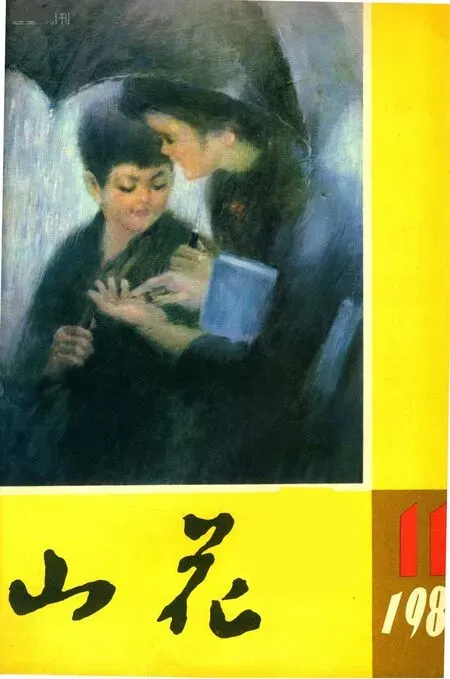放声嚎啕
杨献平
天旱得狗把舌头放在阴凉地,蚂蚁把自己藏在虫子的尸体下面。太阳照得远近山川散发出浓郁的焦糊味道。我和我老婆在上塘地干活,和这村里其他人一样,一大早,吃了饭后,就挑了铁水桶,扛了头,背了化肥和种子,抡着双脚到田里。虽然旱得掘地三尺还是干土,蚯蚓都死绝了。点种下去,说不定还能滋些青苗儿,再碰上点好雨水,秋天还能有点收成。要不点种,连根草都收不来。一家人光靠买着吃,不要半年,家当就要底朝天了。
挑了几趟水,裤裆里都湿漉漉的了。我坐在树荫下一块扁平的石头上歇着。地下边还是地,别人家的,他们家能动的也都来了,从河里挑水的挑水,在地里刨坑的刨坑,撒化肥点种子一个人能成。再下面地里,是曹爱玲一家。那是一个要强的老妇女,都快六十岁了吧,还像年轻时撅着屁股干,就像一只老母鸡,两腿都被泥巴泡得生锈了,还一个劲儿地满地找食吃。旁边撒化肥的是她二儿子媳妇,邻村人,脸寡瘦,长而窄,下身和上身长度基本相当。脑袋还不大灵光,基本的人事还知道,再深一点的就晕头胀脑,不知深浅多少了。
曹爱玲常说,要是俺家里条件好点,俺二小子就不会找这样的媳妇了。说完,黑脸乌云低垂。不久,这话传到她二儿子媳妇耳朵里,狼狗一样窜出来,三步蹦到曹爱玲院子边大喊,你说啥啊你个老巫婆,俺难看你以前不知道,咋还八抬大轿把俺娶到恁家来!曹爱玲出门就应嘴,声音也大。回敬说,早知道你长得丑,还傻得不透气,俺三万块钱买个驴回来也比你好使!
村子不大,我就住在曹爱玲家对面。按辈分,我叫她婶子。她丈夫张远见是远近乡村公认的老好人,遇事不开腔,按曹爱玲的话说是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尖石头砸脸上也不吭声。
正月还没过,武安那边修公路招工,曹爱玲就让他背着行李卷出去干活挣钱了。那时候天还很冷,风在东边山岭上把去年的茅草尘土刮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夜晚从门槛下面蛇一样钻进人的被窝里。春天到后,人把大粪驴粪羊粪肩挑背背地运到地里,就巴着个酸枣脸看天,嘟囔说老天爷,该下雨了啊!
可无论人怎么虔诚,把脸给太阳烤焦,天还是蓝的,而且蓝得叫人绝望;阳光烈得像五百年没见过水。不几天,刚眨巴出来的嫩草蔫了,一头刨进去,再勾出来,就是一股白烟。到三月中旬,人知道,再不点种下去一年就只能喝清水了,只好用水桶从河沟挑水到地里,用水瓢一个坑里倒一点,先润润种子产房,心里想,老天爷再杂种,也有做好事的时候。
我回身捡起扁担,铁钩子刚挂上水桶的铁梁,突然有人大喊大叫,而且很凄惨。我心慌了一下,到地边一看,那边山岭上有人打架。那山岭不高,可是从河沟到上塘地必由之路。我脑子正在根据声音判断谁和谁在打架,却听到正在刨坑的曹爱玲一声尖叫,既而破着嗓子大喊说,打死人了啊!打死人了啊!
确是曹爱玲二儿子张爱平和人打架。准确说,是被人打了!
一方爷儿仨。爹叫张二柱,他大儿子张再,二儿子张军。三人都比张爱平年岁大,最大的大三十多岁,最小的大四岁。张爱平又不是武林高手,张二柱爷儿仨一人一脚再加一拳,张爱平就是铜陀螺也挡不过来。
曹爱玲兔子一样从自家地里窜到五百米外的山岭上,中间还有一道浅沟。张二柱爷儿仨早就走了,张爱平歪着身子半死不活地躺在草堆上。曹爱玲又扯着嗓子哭喊,打死人了啊!打死人了啊!一边抱着张爱平一米八几的身子摇晃,嚷嚷着让他站起来,又朝上下田地喊,俺孩子被人打死了啊,谁来帮帮俺?
上塘是一大片旱地的统称,生产队时候合着,全村人养种;包产到户后,这家一片那家一块,都分到了个人名下。张爱平和张二柱爷儿仨嘶喊乱打那阵子,村人都和我一样站在自家地边观看,打完了,张爱玲哭喊着叫人帮忙,除了我,都转了身,抡头的照样抡头,挑水的挑起铁皮桶吱呦呦地往河沟走。
我也正要转身,曹爱玲却喊说,老三,俺该咋办啊?
我惊了一下,看了看上下田地。张爱平的媳妇腆着个大肚子,坐在田里乱骂说,操他娘的张二柱,打死俺爱平了啊!我冲曹爱玲大声说,报案吧!曹爱玲好像听到了,抱着张爱平继续俺的儿啊啊啊哭。过了一会儿,又扯嗓子喊自己儿媳妇说,赶紧叫恁娘家兄弟来帮忙啊!这时,张爱平媳妇才从地上爬起来,顾不上拍打身上的灰土,沿着一边小路踉跄着往邻村娘家走去。
曹爱玲把电话打到派出所。听了她急如暴雨的哭诉后,那边声音年轻、雄壮有力:这还得了,他妈的,光天化日之下……简直是,必须严惩!曹爱玲还满嘴哭腔,连声说,就靠您了啊!电话又说,你放心吧!这事儿必须严肃处理!曹爱玲还想说些话,可厚嘴唇撬动了几下,又咽了回去。
曹爱玲二儿媳妇几个兄弟从邻村赶来,把在草上歪躺了一个多小时的张爱平半抬、半架着送到马路边,一台三轮车突突而来,然后沿着新铺的柏油马路向下驶去。他们是要去乡卫生院。那是村人看病,尤其是乡邻间出现肢体冲突的必到之地。通常,乡卫生院检查后,会有个报告单出来,也作为派出所调解、处罚和赔偿的主要依据。院长是本地人,医生也就他一个,另有老婆管账兼取药、卖药,唯一的护士是他姐姐的女儿,亲外甥女。
蝉房乡统共两万多人,就一家卫生院,门庭自然若市。院长姓张,也是本地人,因为掌握着众人生命身体,威信比乡书记乡长还高。可谁也不想平白无故得罪人,尤其是打架斗殴,给一方治疗了另一方背后骂娘;派出所又用检查单做调解的唯一依据,受伤的一方希望开得严重点,占便宜的一方则希望不要开,或轻描淡写。照实写不行,弄假也不行,都得罪人。
张爱平和曹爱玲到了乡卫生院门口,说要检查住院。院长老婆倚在大门口,斜着身子嗑瓜子,见这么几个人来,眨巴眼睛说,咋了?摔了碰了还是?曹爱玲心直口快。院长老婆一听,赶紧说,哎呀,这样儿啊,赶紧去市人民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咱这边设备差,根本看不出来个啥!
曹爱玲好像没听懂,说,先给俺孩子看看有啥大事没?没得俺就放心了,要是有大事,俺再去市医院。院长老婆还想说点啥,张爱平老婆扶着他已经进到门诊,躺倒在检查床上。院长老婆一句话没说,脸跟穿了几年的布鞋底儿一样,又黑又滑。院长上前扳眼睛摸伤口又脑电图地检查了一下,说是轻微脑震荡,腰部、后背部分淤血,骨头没事。曹爱玲长出一口气,一家人在一间小病房里闷坐了一会儿。儿媳妇突然说,娘,俺饿了!
看着儿媳妇提回来的油条,曹爱玲拿起一根,咬了一截子,嚼了几下就咽了下去,又把剩下的一截放在一张报纸上。看了一眼手背上插着吊针,鼻青脸肿的张爱平,转身对吃得满嘴冒油的儿媳妇说,你在这看着爱平,俺去派出所看看啥时候能给咱处理。
乡卫生院在乡政府对面,一栋二层小楼房。楼上是病房,楼下是门诊和药房,还有临时输液的地方。乡政府公社时期修建后,就再没重修过,一栋二层石头楼,里面一个大院子。曹爱玲到门口,一个老头说你干啥,曹爱玲说俺找派出所的人。老头说,派出所早搬走了,不在这儿。曹爱玲又说,那搬到了哪儿了?老头说,在西梁屿沟口。
曹爱玲知道西梁屿,也知道那是个村子名字,沟口就是村子外面的马路边。
从乡政府所在地蝉房到那里,有七八里地。
曹爱玲在乡政府门口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天。太阳大得像碾盘,连头发丝大小的云彩也没有。长长叹了一口气后,曹爱玲向着东边迈着双脚,穿过乡政府街道上的粮油店、超市、小饭馆和大戏院,到尽头,一辆卡车拉着一车煤炭,旋风一样从她身边掠过,荡起的烟尘白加黑,扑了她一头一脸。她擦了下汗水,又手打凉棚看了看天,太阳热烈得想要从天上逃出来似的。
路上又过了几辆小轿车,其中有一个女的,从车里看她的眼睛很怪异,她觉得就像洞里的狐狸看猫和狗。再向东,还是一色柏油马路,依着曲里拐弯的山岭根,傍着一面早已水断石乱、细流如小孩尿尿的大河滩。沥青油汪汪、水津津地,还气焰嚣张,看着好像连营火。黏在布鞋脚底,有股烧糊的味道。走到一片树荫下,找了一块大石头,曹爱玲一屁股坐下,不管有没有人,解开短袖衫扣子,露出两只如空布袋的奶子,任穿林而过的风搜肠刮肚地吹。
迎面和背后跑过几辆摩托车,路过她,又箭一样飞远。曹爱玲两只脚轮番踩着柏油马路,像一架干瘪而顽强的压路机。转过一道长满洋槐树的山岭,一座高大的门楼,挂着一颗巨大的警徽,依着半截子山岭,气势威严地站在马路一边。曹爱玲穿过大门,院子里没有一个人,除了几辆摩托和一台带警灯的桑塔纳,剩下的都是阳光,给人一种满盛盈盈的焦躁感。曹爱玲左右看了看,几间房门铁嘴钢牙似地关闭着,又好像并排站立的哑巴。
有人没有?
有人没有?
有人没有啊?
喊的时候,曹爱玲眼睛和耳朵紧密关注着每一间房门和每一寸声音,几十秒钟后,还是没人答应。阳光愈加满了,而且有一种渐渐溢出的逼迫感,有一种一触即破的脆弱与不安。她这才意识到,这是正午,民警们都在午休。想到这里,她又后退了一步,瞥见拱门旁边有个断了一小截儿的红砖,下意识地坐了下来。
曹爱玲回家了,我在对面自家院子看到。那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娘儿们,走路姿势像蚂蚱,但运作得特别快。然后开门,紧接着是猪猡的哼哼声,和鸡们的咯咯声。然后是炊烟,从她家黑黑的烟囱里,盗贼一样冒起来,向着依旧烈日奔腾的青天。
曹爱玲肯定来找你。老婆在背后说。我没吭声。心想,还是躲了好,要是张二柱一家知道我给她出主意,牙都会咬成羊粪沫儿。
我说,上塘地点种完了,该去庙坪上了吧。
高崖洼的也没种,那就先去庙坪上!
俺肩膀头子疼得不行,歇一会儿再去吧。我瞪了她一眼。她脸往下一拉,嗔怪说你个死鬼瞪俺干啥?话音刚落,曹爱玲就从侧面山岭小路上转了出来,吓了我一跳。老远就大声冲我说:老三,这么早就去地啊!我下意识停下脚步,心里泛起一股怪味。想回答,舌头就是不想动,不想回答,身子却钉在那儿。
赶紧走吧!老婆催了一声,又自己背了玉茭种子,扛上头,头朝前迈出了院子。我下了门前台阶,走了几步,侧身对曹爱玲说,也不早了,好几块地还没点!再靠几天,恐连籽粒都收不回来了!
你等等,俺有个话给你说。
我又钉在原地,拒绝显然不好,不拒绝也不好。心里正颠倒时,曹爱玲已经下了河沟对面的小斜坡,两只蚂蚱腿干棍子一样朝我家门口碾过来。
天气太热了,连瓢虫都不再爬椿树了。曹爱玲到我家时,我坐在门槛上抽烟。老婆早晃着四十岁的屁股往庙坪地走了。到门边,曹爱玲说,老三,给你买了一盒烟。俺不识字也不知道啥牌子,你凑合着抽。我没接,看着她那两只皱纹深陷的眼睛说,咋了?曹爱玲一手拿着烟,抬腿就往家里迈。
见到副所长,所长不在。
咋说?
副所长说,他们三个太嚣张了,扰乱治安,还把人打成脑震荡,简直是无法无天,欺压良善。我们会坚决严肃处理。
那就行了啊!
可副所长说,叫俺回来叫张二柱家人去派出所。
哪有这规定?
俺不知道。
你叫张二柱了没?
还没,你说这话……他爷儿仨打了俺孩子,俺再去叫他去派出所。这话咋说?
有传票没?
没有!
那你叫个屁啊!
哪咋办?
你叫派出所开个传票,最好叫他们给了乡政府,乡政府民事调解员再给咱大队干部拿回来给张二柱。你去人家家,不把你打出来才怪。
也是啊!那俺再去派出所,叫他们开个传票。我说,只有这样!曹爱玲一脸焦急,问我几点了,得赶紧去。要不人家下班了找不到人。说着话,人已经出了我家院子。
从莲花谷村到蝉房乡政府,再到西梁屿沟口派出所,单程二十一华里。曹爱玲不会骑自行车,路上要是遇不到顺路的车,就能靠那两条老腿了。想到这里,我叹息一声。忍不住想,要是她是我娘,遇到这样的事儿,我该咋办?会咋办?要是我,张二柱爷儿仨早成肉泥了,不杀了他们,也让他们少胳膊瘸腿!要是也出其不意半路打我,我起码揪住他们当中一个,先把卵蛋拧下来!可张爱平,一米八几的个子,走起路来晃悠悠地,像一棵刚成活的小柳树。可那么不禁打呢?见张二柱爷儿仨空手窜过来了,自己还没一点防备,把水桶一扔,抡起扁担打残他一个算一个。
庙坪地也是上坡,我挑着一担子水,两只水桶吱扭扭响,比喜鹊叫声还响亮。这样想的时候,不由得咬紧了牙齿,脸也绷着,神情肯定也凶,但觉得挑水上坡也不气喘了。到一面平坦的小坡上,我刚小心放好水桶,一个人从地里挑着一副空担子走了过来。竟然是张二柱。我没吭声,眼睛看着对面茂密的棌树林,有些鸟在飞,但都飞得很低,好像也怕灼热的日光。张二柱走到近前,说老三你点种哪个地里的?我说二柱叔,就点种你地上面那块。张二柱啊一声,错了一下肩膀,向下走了。我看着他背影,也快六十的人了,不算胖,但腰背都不驼,挑的水桶比我的还大一圈。心想,这家伙,比我这个四十多岁的人还能干。又想起他俩小子。老大张再一米七五高吧,不算胖,但算壮实,整年在石子厂抡着铁锤敲石头挣钱;老二张军,个子不算高,初中毕业后就在面粉厂干活,经常出去拿面粉换玉茭,扛个麻袋像抱小孩一样。
我倒吸一口凉气,要是我和这爷儿仨遭遇,真说不定只有挨打的份儿。张爱平虽然个子高,可比小洋槐树还瘦,从小就那样,只长个头不长肉。
天气越发热了,晚上拎着被褥到房顶睡,十点多了水泥顶还烫。正迷糊,老婆也上来了。天黑,就穿了个大裤衩和一件背心。我知道她想啥。果不其然,挨着我躺下没一袋烟功夫,粗茧子手就到了我裤裆。三下两下,下身就火烧一样跳了起来。那一次还真是平生第一次。感觉比在床上爽快和有力度,尤其是那感觉,风连续吹,我身子起落,不像是做那事,像是在做健美操。完事后,老婆也不擦,也不找裤衩,拧着屁股转了身子就去睡。
公鸡打鸣的时候,我听到对面曹爱玲家木板门吱呀响了,然后看到灯光、人影,然后是关门锁门声音。又看到一个人打着手电沿着小路向马路走。从走路声响判断,一准是曹爱玲。心想,她一定又去乡卫生院。想起昨儿个和张二柱对面时候,心里有点反悔,觉得不应当管曹爱玲家闲事。毕竟,张二柱家人没侵犯过我的利益,几十年从来也没大声对我说过话。这一次帮曹爱玲,要是张二柱知道了,肯定有怨气,一个村儿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往后有个事儿交集,啥事儿也难说。
可曹爱玲一家又叫我心生不忍。丈夫张远见在外地,即使在家,也就顶一个人头,地里活儿干得好,家庭和村里事儿看也不看,问也不问。据我多年观察,张远见看起来木讷迂腐,实际上很有心眼。他不参与家事儿,是因为老婆曹爱玲强势,不参与村事儿,甚至以妻儿受辱做代价,是想替她们卸力。村子的暴力传统由来已久,丛林法则在这里体现得很明显。他以自我退让甚至牺牲的方式,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老好人,从而看在他那张薄面上,对妻儿手下留情。但事实上,这是行不通的,无论是谁,最在意的是今生今世怎么样,是眼前饥饱和既得利益。
曹爱玲到乡卫生院,儿子张爱平还在输液,老婆腆着大肚子躺在另一张闲床上。曹爱玲问张爱平头还疼不疼,晕不晕?张爱平说不疼不晕了。曹爱玲说那就好。又说了派出所的态度。儿媳妇慢悠悠坐起来说,俺昨晚上见张二柱两儿子,跟着派出所人去了前边的红又红饭店。
曹爱玲叹息一声。
张爱平没吭声。儿媳妇说,估计是吧!
曹爱玲低了一会头,觉得心里有些东西蝎子一样乱跑,稍微不注意,就被蛰疼蛰肿一样。她没说一句话,走出乡卫生院,举着头冲对面的乡政府看了看,叹息一声;又朝东边街道望,几辆轿车过去过来,摩托车轰轰地。还有一些人,提着东西或者甩着两手。她低着头想了一会儿啥,然后迈开步子,又朝西梁屿沟口走去了。
这已经是第六趟了,单趟二十三华里,六趟就近一百公里。她那两只腿还真能走,要是我的话,肯定厌烦了。住院费多少没啥,就是一个理儿。曹爱玲多次对我说,这一次派出所不好好教训一下张二柱一家,他们家以后就没法在村里待了。无形中,张二柱爷儿仨暴打了张爱平,又没得到相应处罚,那就间接说明,她曹爱玲一家怂到底儿了,以后在村里就是破鼓乱人捶,想过体面的生活那是痴心妄想。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她本人不可能,男人张远见压根不抱希望。
到派出所,所长、副所长都不在,一个新分来的民警看到她,笑着说老婆子你咋又来了啊!曹爱玲说,事儿没给俺处理,俺不来咋个办?民警脸色变了一下,有啥处理的,不就是一个村的打了一场架,也没致残,更没出人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说不定有个啥事相互帮忙呢,算了吧老婆子!曹爱玲眼睛暗淡了一下,眼泪刷地冲了出来。
这确实叫人绝望。要换了我,也会气晕,会对派出所领导说,你们既然不管,那俺也照葫芦画瓢,自己解决,打死谁算谁!你们派出所接到报案也别来!可这话貌似有理,实际经不起推敲。即使按土方法解决,打死打残一方,跟派出所也扯不上半毛钱关系。你打架打残了照样抓你,打死了照样赔命,和人家所长副所长小民警有啥关联?
听了这番话。我也憋了一肚子气,要是曹爱玲是我娘,我拼死也要把张二柱家人弄死一个。可事实上,我又能帮她点啥呢?想了半天,只能对她说,张爱平好得差不多就回来了,不然,医疗费还是你自己全部出;你还要想说理,只有打电话给你在部队当兵的大儿子张如平。曹爱玲面无表情,擦了一把眼泪鼻涕,对我说,前天个,也给俺如平打了个电话,他也着急,打电话给派出所,派出所副所长说这事是小事儿,没啥处理的。你知道如平那人也性格暴躁,就责问人家,人家比他还急,说愿意你他妈的去哪儿告就去吧,老子不怕!
我也叹息一声,瞅了瞅她拧成秋瓜的脸,摇了摇头,安慰她说,认了吧。曹爱玲没说话,起身出了我家门。我看着她脚步极慢地走到对面小山岭上,正要回屋,却听到一声长嚎,突然得像是一声雷,打得我耳膜生疼。